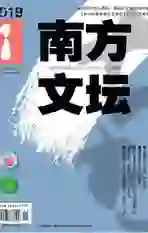“我”所创造的世界
2019-03-21谢有顺
昨天为了赶飞机,起了个大早,出门时忽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黎明了。那个万物苏醒的过程,黑夜与白天的界限从模糊到清晰,尤其是黎明前那混沌、朦胧、慢慢呈现的状态,特别像文学。路过一个湖边的时候,想到文学作品就如同湖边柳树的倒影,兼具现实与想象的双重面貌:只写岸上的柳树,未免拘泥和老实了;只写柳树的倒影,全是务虚的笔法,无一片叶子是实在的、真实的,又太过任性和缥缈了。文学的存在正是弥合事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裂痕。科学、历史、考古,志在记录、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尽管本来是怎样的,不可复原,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至少有此志向,以实证为准绳,对世界进行事实层面的重建。宗教更多是想象的产物,一种精神奇迹的提出与确认,负责现实如何超越、日常如何升华的精神层面的建构。
文学大概是居中的一种存在,它不只是对事实负责,也不完全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好的写作总是物质和精神、事实与想象的综合。
这其实不是文学的原创,而是文学对日常意识、日常生活的模仿。没有人只生活在事实之中,而无梦想、诗意、神游万里的思绪;也没有人只生活在幻想之中,而完全无视现实世界对他的限制,除非他是一个精神病。但日常意识与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混杂的,多声部的,尤其是说话方式,更是杂语喧哗的。比如会议发言,是专业的说话,用的都是理论语言。会后呢?日常的说话呢?没有人一天到晚用理论语言说话,也没有人的话语只有单一的叙事或抒情。日常说话就是叙事、抒情、议论的杂糅。讲个故事,发个议论,所谓夹叙夹议,是常态;回忆、评点、感慨也经常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如此。
写作作为对一种说话方式的模仿,本不应有森严的文体分隔,强行区分出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的文体,并要求写作者遵守或对号入座,并不适合所有人。尽管这样的文体分隔,有利于对一种说话方式的提纯,符合现代社会专业细分的要求,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文体的牢笼中待久了,也要警惕文体区隔之后的精神分裂,以为自己只能在一种文体里精益求精,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誤区。
我们来回想一下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些宏文。回想一下《论语》《圣经》《可兰经》,包括李敬泽写作中经常提及的柏拉图的《会饮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文体?没人说得清。这些经典是思想巨著,也是文学作品。如果要为它们概括一种文体,不过是说话体——对日常生活的思想与语态的模仿。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各种笔调都有。如此自由、深刻,又如此真实,并且都有一个智者的腔调,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人在说话、行动、思索,甚至在恳求、呼吁,牺牲自己。文字背后这个人强大而坚定,他不隐藏自己,而是力图展现一种生命和实践之间的完美融合。读到这样的经典,谁还会在乎这些话语到底是小说还是随笔?到底是在叙事还是议论?文体的界限不存在了,这是语言的自由,也是写作的极高境界。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是伟大的文学,那也是有“我”的文学。有“我”的面容,“我”的观察,“我”的思想,用“我”的方式说话。这就有了李敬泽的写作。它的写作难以定义,他自己也无法定义。他是故意的,也是无意的。他有话要说,又想自由无忌地说,于是下笔万言,纵横万里,写出了一批无法为固有的文体所界定的文章。近年一直有关于李敬泽的作品文体的讨论,越界,革命,独创,大家都看出了他不想落人散文俗套的写作野心。其实他也是在向经典致敬,他意识到了有必要重新恢复一种说话方式,管他什么文体,关键是要找到“我”的说话方式。
这样的写作是原创的,也是先锋的。李敬泽对现代文体区分的反动,是因为他看得更远,回到了一些源头性的话题。苏珊·桑塔格说:“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文学就是自由。”无自由就无人类历史中那些奇思妙想,也无文学史上那些创造性的篇章,所以德里达也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青鸟故事集》其实写于二十年前,但那个时候就可看出,李敬泽对现代社会以来的文体建制是不信任的,甚至认为是应该颠覆的。到《会饮记》,有一些语言实践走得更远,“他”像是一个伪装的“我”随意穿行,若隐若现的真实事件,恍兮惚兮的叙事改造,唯一可靠的线索不过是个体的想象——而恰恰想象是自由的,充满意外的转折和旁逸斜出的语言枝蔓。许多时候,叙事从一个点进入,估计连作者自己都料想不到会从哪个出口出来,而李敬泽似乎就是要证明“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自由不可失去,更不能拱手相让。这就是先锋写作。先锋不仅是前进的、未来主义的,也可以是后退的、古典主义的,核心是自由,是反对业已成型的建制。写作最大的痛苦就是限于语言的牢笼,与其在一种不合身的文体中左冲右突,不得其门而人,还不如忘记文体,就写文章吧,总有一种说话方式适合你。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轻松了,容易了。其实更难。不是写不了其他文体才跨文体,不是厌倦了单一文体之后才采用多文体。文体的自由和驳杂一旦失控,不过是一些语言的碎片,或者是一个不顾一切标新立新的姿态,跨文体、多文体的成功,显露的是对一个写作者心智的全面训练,是他对自我的重新认识。理性与感性混杂,故事与道理并置,口语与书面语同台。健康、饱满的心智本就应拥有多种能力:可以讲述,也可以思考;可以面对现实,也可以沉迷于虚构。真实的事件可以入文,道听途说也可以人文;书面知识可以入文,个人冥想也可以入门。任何固定的知识、板结的观念,我都不轻易认同。我要建立一道自己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世界。这个“我”一直在怀疑,一直在想象,一直在肯定和否定,这就是写作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故事,而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我”;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缺少语言,而是缺少“我”的语言。有“我”的写作是自我立法的,往往谦逊而专断。世界为“我”所用,知识和材料为“我”所用,甚至每一天见闻也为“我”所用。有“我”的写作是很气派的。李敬泽之所以可以在孔子、孟子、宋徽宗、曹雪芹、柏拉图、布罗代尔之间自由往返,潜意识里是觉得这些都可以为“我”所用——“我”对这些有自己的理解,哪怕是错误的理解。
这是非常现代的观念。自我立法,重估一切价值,语言狂欢,文体革命,游戏之心,文字下面的庄重与坏笑,熔于一炉,李敬泽的写作充满个性与原创。但同时他又是传统的,非常中国化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重诗文,轻虚构。詩文是崇高的,小说、戏曲是不入流的,没有地位的。这种观念的形成,根柢上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看重有“我”存在的文字。“我”在天地间行走,“我”如何独与天地共往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柳树何时发芽,雨何时停下来,都与“我”的心境有关。孔子的“我”里有天下,杜甫的“我”里有苍生。这些阔大的“我”,有思想力、感召力和行动力的“我”,正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存在。天人合一,物我俱忘等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令我想起钱穆在《人生十论》中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和一位朋友在苏州近郊登山漫游,借住在山顶一所寺庙里。我借着一缕油灯的黯淡之光,和庙里的方丈促膝长谈。我问他,这一庙宇是否是他亲手创建的。他说是。我问他,怎样能创建成这么大的一所庙。他就告诉我一段故事的经过。他说,他厌倦了家庭尘俗后,就悄然出家,跑到这山顶来。深夜独坐,紧敲木鱼。山下人半夜醒来,听到山上清晰木鱼声,大觉惊异。清晨便上山来找寻,发现了他,遂多携带饮食来慰问。他还是不言不语,照旧夜夜敲木鱼。山下大众,大家越觉得奇怪。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所有山下四近的村民和远处的,都闻风前来。不仅供给他每天的饮食,而且给他盖一草棚,避风雨。但他仍然坐山头,还是竞夜敲木鱼。村民益发敬崇,于是互相商议,筹款给他正式盖寺庙。此后又逐渐扩大,遂成今天这样子。——这一座大庙,看起来是信众造的,是他们筹款盖的,也可以说是这位方丈的一团心气在天地间涌动、生长,是方丈那个“我”建造出来的。钱穆说:“我从那次和那方丈谈话后,每逢看到深山古刹,巍峨的大寺院,我总会想象到当年在无人之境的那位开山祖师的一团心血与气魄,以及给他感动而兴建起那所大寺庙来的一群人,乃至历久人心的大会合。后来再从此推想,才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事一物,莫不经由了人的心,人的力,渗透了人的生命在里面而始达于完成的。”
写作也是“我”在创造世界。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不断地生,世界就不断丰富。中国的诗里面有“我”,小说呢,是说别人的故事。同样是小说,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地位更高,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高,也因为《红楼梦》是“我”的故事,而非只是别人的故事。钱穆还说过,中国的诗人不写传——不写自传,也不请人给自己写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传记,“诗传”。“我”的诗歌可以为“我”作证。在中国,传记风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但在古代,文人通过作诗,就能让人看到“我”的胸襟、旨趣、抱负,“我”的行迹与心事。
我们何以记住李敬泽的文?包括他平时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致辞何以能与众不同?腔调独异,文采飞扬,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他的文字中有一个“我”——那个确定、自信而又飘忽、神秘的“我”,那个宽阔、沉实而又驳杂、恣意的“我”,那个有话要说而又找到了自己的说话方式的“我”。任何时候,李敬泽都不放弃“我”的存在,即便这个“我”有时必须沉潜,也偶尔会在一个比喻、一个词里露出痕迹,而这个痕迹总会鲜明地打上李敬泽的色调。《会议室与山丘》收录了他很多访谈,记者问的许多问题都是俗套的,有些更是大而空泛,但李敬泽总能找到自己的角度,新见迭出;他一直坚定地在陈述“我”的文学观,从一些说法、用词中,你就知道是李敬泽在说话,所以他的访谈也是文章,他的思路和逻辑是自我的,不会受制于访问的人或现成的观念。《咏而归》是重读经典,而且是大家所熟知的经典,关于《论语》《孟子》,很多人都可以说上一段,但李敬泽力图把它读成“我”的经典,是“我”在此时的阅读感受,是可以给此时的“我”带来启示的思想对话。更多的时候,李敬泽说了些什么你未必记住,也未必同意,但你不知不觉为他的说话方式所吸引。印象中,中国文坛多年不讨论“怎么说”这个文学的本体问题了,但在李敬泽近年的写作中,反而让我意识到有一个“怎么说”的问题一直顽固地存在,而且极其重要。李敬泽的许多文章我都读过多时了,但我至今想起,仍旧忘不了那个有腔调的“我”——写作到这个地步,写的到底是什么文体,写得有多好,真的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我”因文而立,也会因文而传。我想,这是对写作最高的奖赏。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本文系作者根据在“中国之文与当代散文写作的变革——李敬泽散文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