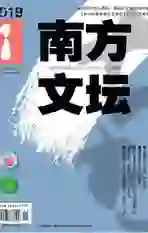孟繁华:“我的”当代文学
2019-03-21洪子诚
洪子诚
编者按:孟繁华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前沿一个优秀的存在。2018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报告厅,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范大学、北大培文联合主办。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孟繁华文集>研讨令。本刊选取部分发言以飧读者教请关注。
我认识孟繁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当时是我的领导,所以我一直尊称他为老孟,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字。当时他担任中央电大一些课程的负责人,我和张钟老师是主讲教师。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编写过教学大纲、教材,后来还录制了教学视频。1987年在黄山、1989年在洛阳,他组织了令我至今我都很难忘的两次电大的当代文学教学讨论会。后来他到北京大学访学以及在谢冕先生那里读博,我跟他一直有很多的联系。
和孟繁华一起,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为什么不呢?”,这是句无所畏惧的话。它让我学会了喝酒、抽烟,也让我在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事上增加了勇气。1993年秋天,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他和谢老师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集体科研项目,计划分给我“1956”这个年份。我说可能难以承担,因为材料等一点都没有准备。1999年重庆当代文学年会,他和张燕玲策划“当代文学关键词”的集体写作,也让我参加。我说许多学者我都不认识,和他们完全没有交往,约稿可能很难办到。这些顾虑都是他给打消的,让我这些项目得以完成。他的热情进取让我那种有点消极、虚无的情绪有所缓解、有所抑制。
他的文集有几百万字,有的以前读过,有的还来不及讀。我想讲两点感想。第一,他选择从事的工作,比起我做的要困难得多。从学术研究上,他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有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化研究和现状批评等方面。他的第一本书是《文学的新现实》,就是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的。推测老孟可能觉得这本书不是很成熟,“文集”里面没有收录。在他有关文艺学的研究中,《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值得重视;可以说是最早系统提出并讨论当代前三十年学术体制和大学文艺学教学的著作。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成就卓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国当代文学通论》,特别是他和程光炜教授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得到了学界极高的评价,多次修订再版,被很多学校作为当代文学课的教材。自然,大家都会认为孟繁华贡献、影响最大的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现状的勘查。1997年,他出版了评述90年代文化现象的著作《众神狂欢》,共时态地对那个时期的复杂文化现象做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而在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的《新世纪文学论稿》中,他对二十年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了近距离的考察。“当下中国文学状况”——这不仅是他一组文章的总题目,而且是他三十年来写作、研究的主题。
对于文学批评、研究工作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意识到,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式,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气的。有效地、持续地关注文学现场和作家作品,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需要有广泛的阅读所形成的充足的文学记忆。需要对语言、形式的敏感,同时更需要责任心以及大量阅读所需的精神和体力。好在孟繁华基本上属于山东的大汉,他能够承担这样的压力。
说起现状批评和新时期文学现象的评述的批评方式和文体形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解的人相信都不陌生。不过,说它是俄苏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特别的批评传统,恐怕也不是妄言。从文学史的角度,这也许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别林斯基的文学概评的写作。在那个时代,别林斯基以十二篇文章,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从1841年开始,他以每年一篇的长文对俄国文学的状况做年度评述,一直持续到他1948年去世。这种近距离的文学概评的写作和动机,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根源于批评家对民族文学建构的希望和焦虑;它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有没有文学”,俄国文学“是不是存在”,以及俄国文学能否也像法国文学、德国文学那样成为“世界性文学”的问题,是为了推动文学成为“民族精神和生活的表现”。这种别林斯基式的责任心,也构成了孟繁华阅读、写作的驱动力。我有时想,在当代文学研究上,我和他的区别是,我认为“当代文学”就是当代文学,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孟繁华内心真是热爱这个对象,在他的心里,“当代文学”就是“我的”文学。
第二点感想,在孟繁华那里,文学批评不可能在纯粹美学操作中远离“现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他的批评有一贯的理念支撑;他曾提倡的“新理想主义”,体现了他对80年代启蒙精神在反省基础上的承继和展开。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我见识了他那种深切的忧虑,听过他对现状峻切的言辞。他的关注、批评,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传达了90年代以来,那些仍怀抱理想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价值转换中的痛苦,以及一直试图战胜意识衰颓所作出的努力。1996年,苏珊·桑塔格为她写于60年代的《反对阐释》一书的西班牙版写了序言《三十年后……》,里面谈到,在20世纪60年代,说那个时代的特征是没有怀旧的色彩,而到了90年代,“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都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一个“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促进了——实际上是加强了——文化的混合”的“虚无主义”的时代。桑塔格说,她希望她写于60年代的这本书,“有助于堂吉诃德的任务”,就是维护这些文章所依据的那些价值。桑塔格描述的这个状况和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些相像,所以我们要向老孟学习,感染他的乐观精神,也来一堂重启乌托邦想象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