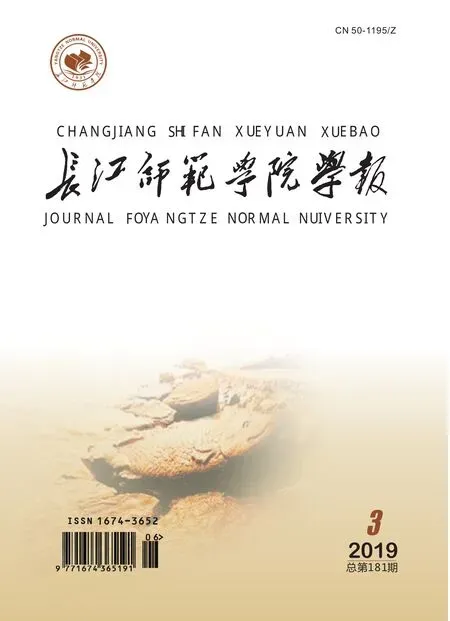汉代镜铭体式演变与七言镜铭的生成
2019-03-21时嘉艺
时嘉艺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镜铭出现于战国,发展至汉代成为铜镜的主体装饰,其体式发展历经三言、四言、六言再到七言的转变,每一次变动都有其内在生成机制。镜铭是七言体式文学诞生的早期形态之一,从内容、结构等角度将汉代七言镜铭与七言诗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颇多近似之处。通过梳理镜铭的体式演变和生成原理,可以从结构的视角构建较为完整的镜铭发展史,亦可对汉代七言诗歌的起源予以补充。
一、汉代镜铭体式的演变
从语体角度考察,诗歌的语体呈现从三言、四言、五言再到七言的发展趋势。镜铭与诗歌的发展线索基本一致,西汉时期的镜铭中有三言体、四言体,其中以四言为主。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六言体、七言体,新莽时期直至东汉中晚期,七言体得到大量运用,三言体亦有存续。
西汉早中期镜铭体式与诗歌类似,均受《诗经》的影响,多以三言、四言为主。而与诗歌相异之处在于,镜铭作为附属于铜镜上的实用性文字,其表现空间受到限制,故更加简短。四言类镜铭中多有类型化的固定书写:“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1]34;“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1]86;“服者君卿,万岁未央”[1]94。还有一些较长的镜铭,在简单铭文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其实大同小异。比如:“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千岁,幸至未央,常以行。”[1]134内容多为求长寿、求富贵简短韵语的组合。
又有三言类镜铭,如祝寿类“寿如山,西王母,谷光憙,宜子孙”[1]84;求富类“长富贵,乐无事,日有憙,常得所喜,宜酒食”[2];相思类“悲思愁,愿君忠,君不说,相思愿毋绝”[3]。镜铭中三言句子多是由四言省略而来(不说四言镜铭由三言镜铭增补,是因在目前所知出土西汉早期镜铭中,四言出现更早,所占比重更大)。例如:“美宜之,上君卿,乐富昌,寿未央。”[1]110其中“上君卿,乐富昌”明显是“上(服)君卿”“(大)乐富昌”的省略,“寿未央”也是“(长)寿未央”的省略,其他镜铭中亦有“长乐未央”“万岁未央”出现。由于镜铭书写空间多为固定的环形一周,所以对字数有严格要求。镜铭中常出现省字现象,在一篇镜铭末尾,如果书写不完,就直接省去,如末尾本该出现“寿如金石为国保”,直接简化为“为国保”三字,此类情况也较常见。
镜铭中的三言韵文亦受同时期三言诗歌的影响,如汉武帝命人创作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七首全为三言,《赤蛟》一篇有“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4]154,从中可以看出帝王对永生的渴求。大约同时期的镜铭也载有十分相似内容:“见日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延年益寿,敬毋相忘,幸至未央。”[1]200又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4]154,与镜铭“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请(情),修毋相忘”[5]记载相似。
三言、四言体式延续直至新莽时期,镜铭篇幅增长,内容更丰。求富类镜铭会加入“贾市”“程万物”等用语,显示出当时商业的繁荣,如《洛阳烧沟汉墓》考古报告中有镜铭:“日有憙,月由富,乐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贾市,程万物。”[6](“乐毋”后缺一字,应补“事”,“贾市”前缺一字)简单的求长寿类镜铭演变为求仙类镜铭,如新莽时期镜铭:“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贵富昌,乐未央。”[7]该类镜铭又有赋体类七言形式“上大(太)山兮见仙人,食玉英兮饮澧(醴)泉,驾交(蛟)龙兮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8]。三言铭文与七言赋体的转化在镜铭中屡见不鲜,又如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有铜镜,其铭为:“泿精华,精皎日,奄惠芳,承加泽,结微颜,安佼信,耀流光,似佳人。”[9]而在《汉铭斋藏镜》中,同类铭文呈现出略有不同的赋体风貌,西汉中晚期清华铭圈带镜铭文如下:“泿精华兮精皎日(白),奄惠防(芳)兮宣加(嘉)泽,结微颜兮似佳人。”[1]250这种转化不仅仅是句读的区别,更与镜铭体式演变密切相关,镜工依据汉代不同时期流行的诗歌体式,在原有镜铭上加以创造。
镜铭发展至西汉末年,六言镜铭出现,主要为昭明镜和清白镜两种,因其与骚体诗联系更加紧密,为行文省便,将在下一节探讨,这里直接讨论占据镜铭主体形式的七言镜铭。七言镜铭以新莽时期的“尚方类”铭文镜最盛,如:“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皂,非(徘)回(徊)名山采芝草,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寿如今(金)石得天道。子孙长相保兮。”[1]312其中“尚方”表示官署,承担为帝王制造用器的职能。王莽曾被赐予新都侯的称号,篡位后定国号为“新”。故“尚方作镜”“王氏作镜”“新家作竟”,均表示王莽时期的官府制镜,王莽为“安汉公”至新莽王朝建立,尚方机构已由王氏经营。至汉章帝时期,官府造镜渐趋衰落,民间造镜工坊兴起,全国出现大量造镜中心,镜铭中的造镜主体更加丰富,例如“朱氏”“杜氏”“龙氏”等等,“朱氏作竟快人意”此类铭文,亦多是七言为主。此外,又有杂以三言、四言和七言形式的镜铭,参差错落,别有韵致。例如西汉晚期镜铭:“日有憙,月有富,乐毋有事宜酒食,居必安毋忧患,竽瑟侍,心志,乐已茂兮年固常然。”[10]更有“桼(七)言之纪从镜始”[1]366之类语句明确标识镜铭为七言诗之始的记录。
通过对镜铭体式的梳理会发现一个问题:镜铭中为何从未出现过五言体?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11]说明语体的使用与诗体功用相关,五言、七言均可用于“俳谐倡乐”之属,可是五言并不见于镜铭,而挚虞也没有说出某种形式不能用于某类文体的原因。陈直曾提及汉镜铭缺失五言的原因:“或因当时五言歌谣流行,作者为了有别于这些通俗作品,所以就避免了五言。”[12]而镜铭作为一种通俗韵文,恰应与当时流行的文体相合才是,故而镜铭体中五言体的缺失应有其内在文体机制方面的原因。
笔者试图对镜铭中五言体的缺失作一推断。根据葛晓音对五言体诗歌生成的论述,汉语词汇的音节演变,是从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过渡的过程,这种过渡在五言体中的运用相对困难[13]。以《诗经》为例,五言体在《诗经》中有以下几种运用方式:一是“二+X+二”型,其中“X”多为虚词,如《郑风·女曰鸡鸣》中“杂佩以增之”。二是“X+四”或“四+X”型,例如《小雅·斯干》“唯酒食是议”,《邶风·简兮》“西方之人兮”。镜铭原有的三言、四言很难转化为这种形式。三是“二+三”型,如《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其人美且卷”“其人美且偲”,这种句式多为复沓节奏,相似或重复的内容也不适合在镜铭中使用。故在镜铭生成发展的过程中,五言体并不符合其以凝练为主的要求,镜铭中缺少五言体也是事出有因。
二、七言镜铭的生成
葛晓音曾探讨过七言诗歌的生成原因,她认为:“在七言产生之前,四言和骚体这两种诗体都是从散文句中提炼出主导的基本节奏音组。”[14]通过对楚辞、骚体诗和民间歌谣语句内部的拆分可以发现,四言和三言可以连缀成句形成七言,《成相篇》《为吏之道》就可视为连缀而成的杂言体七言。
镜铭中的一类七言体即可视为三言体的连缀,“三+(兮)+三”型镜铭是由三言句式组合而来。例如七言镜铭:“上大(太)山兮见仙人,食玉英兮饮澧(醴)泉,驾交(蛟)龙兮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1]352在另一则镜铭中,同样的内容则以三言形式呈现:“上华山,凤皇(凰)集,见神鲜(仙),保长命,寿万年,周复始,传子孙,福禄进,日以前,食玉英,饮澧(醴)泉,驾青龙,乘浮云,白虎弓(引)。”[1]350每两句三言,以虚词相连,便形成七言句式。随着制镜技术不断成熟,镜铭可以容纳更多文字,也就有一些虚词出现,呈现出骚体诗的美感。
另有一类“四+三”型七言镜铭则可视为骚体诗的简省,对于该种镜铭的溯源还需追至近期出土的海昏侯《衣镜赋》一文。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出土的方形衣镜,该镜镜掩(盖)部分残损严重,碎为数十块,文字图像辨识较为困难。镜掩正反两面都有彩绘和墨书文字。正面漆文为韵文,句式、意境与常见铜镜铸铭相同,且文字中直接写出了“衣镜”之名,故专家名之“衣镜赋”。背面为孔子弟子图像和传记。刘贺生于公元前92年,卒于公元前59年,据此可推知《衣镜赋》创作的大致年代为西汉中期。《衣镜赋》释文目前对外公布的有19行,包括缺失的一整行。内容如下:
新就衣镜兮佳以明,质直见请兮政以方。
幸得降灵兮奉景光,脩容侍侧兮辟非常。
猛兽鸷虫兮守户房,据雨蜚雾兮匢凶殃。傀伟造物兮除不详。
右白虎兮左仓龙,下有玄鹤兮上凤凰。
西王母兮东王公,福熹所归兮淳恩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
□□□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
临观其意兮不亦康,[心]气和平兮顺阴阳。
[千秋万]岁兮乐未央,[亲安众子兮]皆蒙庆,□□□□□□□□。[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公众号“器晤”上发布了关于《衣镜赋》的一些简单释读。笔者文末附有补充注释,以期捋顺行文。专家将海昏侯镜掩上的篇章命名为“衣镜赋”,显然是因其具有明显的“赋体”特征,句句又带“兮”字,故可将其视为骚体赋的简易形态。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引《毛传》“不歌而诵为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6]。汉代文人从功能、技巧等方面对赋体文学进行探索,产生了以《楚辞》为模仿对象的骚体赋,骚体赋的典型特征是以“兮”字句作为其基本句型[17]。骚体赋在汉初兴起,以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等为代表,至武宣时代显盛。武帝命人为《楚辞》作传,《楚辞章句》载:“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18]由此推动对《楚辞》的研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骚体赋在这一时期也乘势而起。刘安或其门客创作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等为该体裁的代表作。这一风潮至宣帝时渐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再难达到前人的高度。
笔者认为,虽然《衣镜赋》具有明显的骚体赋特征,但其文辞简朴、篇幅较短,亦无铺陈扬抑,更加接近骚体诗。汉代的骚体七言多为“三+(兮)+三”“四+(兮)+三”的混杂,并渐趋成为一种固定的书写形式。如刘邦《大风歌》是一句“三+(兮)+三”和“四+(兮)+三”。《秋风辞》也是以“三+(兮)+三”为主,杂两句“四+(兮)+三”。东汉民谣中也有“四+(兮)+三”的节奏句,如《后汉书·皇甫嵩传》引百姓歌:“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19]
《衣镜赋》每句八言,呈现出与同时期镜铭不同的语体特征。如果将其“兮”字去掉,每句呈现出“四+三”的句型,可将其视为早期七言镜铭的起源。在东汉时期,句式为“四+三”型的七言镜铭大量出现,例如西汉中晚期镜铭:“湅治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长年益寿去不羊,与天长久而日月之光,千万旦而未央。”[1]228新莽时期镜铭:“尚方御竟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寿敝(比)金石如侯王兮.”[1]314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后世镜铭都与该篇赋文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倘若赋文中的“兮”字脱落,便形成“新就衣镜佳以明,质直见请政以方”的七言诗体。可以推测,后世常见的七言镜铭是从八言的赋体镜铭中脱化而来,进而演变为相对独立的韵文,可见骚体文学在当时影响之大。
关于骚体赋“兮”字脱落的原因,林晓光在《从“兮”字的脱落看汉晋骚体赋的文体变异》一文认为在传抄过程中“兮”容易发生脱落:“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兮’字作为虚字,在赋已经转化为书写文本后,有无此字都不影响语意表达;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其极高的重复率,这一点可以从《九愍》这样大篇幅的文辞中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对一个抄写者而言,每隔若干字就要抄写一个相同的字,无疑是十分厌烦的工作。”[20]镜铭的书写也是如此。一者因为镜铭书写空间有限,对字数有着严格的要求,省字现象在镜铭中时有发生,“兮”字作为无意义的虚词,只起舒缓语气的作用,是很容易被省去的。而《衣镜赋》书于镜掩之上,书写空间较大,自然可以呈现出内容、句式都更为丰富完整的面貌。又及刻工甚少重视文体的表现形式,省去多余的字体倒是为书写提供了便利。而为贵族阶层制作的器物在纹饰、赋文、书法等方面会更为考究,“兮”字可以造成句中延迟,使行文富有韵律之美,舒缓而有起伏,造镜者便可选择当时盛行的骚体赋(诗)来作为衣镜文的载体。
第三类七言镜铭体式由“六言句末+(兮)”型构成。上文曾提及镜铭中有一些六言镜铭,带有明显的骚体诗风格,有其独特的韵律之美。例如“昭明镜铭”:“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21]“清白镜铭”:“洁清白以事君,怨阴欢之弇明。焕玄锡而流泽,恐志疏(或作疏远)而日忘,怀靡美之穷礼,外承欢之可说。慕窈窕于灵景,愿永思而毋绝。”[22]稍晚也见到合昭明镜和清白镜铭于一镜中,多见于铭重圈镜,此类铜镜完全以镜铭作为镜背的装饰纹样。如梁鉴藏“内清质”全铭镜,其内圈铭作:“内(纳)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外圈铭文则为:“洁清白以事君,怨阴欢之弇明。焕玄锡而流泽,恐志疏(或作疏远)而日忘,怀靡美之穷礼,外承欢之可说。慕窈窕于灵景,愿永思而毋绝。”[23]357该类镜铭文辞精美,又屡见于出土铜镜之上,可自归为一类。在出土铜镜中,多见的是残缺镜铭,例如梁鉴藏有一面残铭镜:“洁(挈)精(清)[白]而事君,志(患)[污] 驩(秽)之合(弇)明。彼(被)玄锡之[流]泽,恐疏远[而]日忘,怀[媚]美之穷(躬)礼(体),[外]承驩(欢)之可说(悦)。[慕窈窕于灵景,愿永思而毋]之纪(绝)。”[23]357因笔者未能见到实物,故摘录李零补充的镜铭,其中缺字用[ ]补出,错字用( )补出。李零认为汉有完整镜铭流行,人人皆熟读于心,由于镜铭设计不周,难以容纳完整镜铭,故有减省,造成残铭镜的现象[23]357。通过对镜背装饰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残缺镜铭的出现也并非完全由于工匠失误,例如该条疏漏颇多的镜铭出现在八角连弧纹镜上,镜铭亦多与繁复纹饰相搭配(参见《古镜今照》图44与高本汉《中国早期铜镜》图F8),说明在这些铜镜中,镜铭只是作为图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修饰意味高于文字本身内容。而在以铭文为主体内容的全铭镜和《衣镜赋》中,铭文是铜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未有随意减省的现象,文辞的体式之美及教化意义才得以凸显,使今人得以窥见镜铭的完整面貌。在梳理镜铭体式演变历程时,应以其最完整的一则为主,才能反映文体的真实面貌。
全铭镜的内外圈铭文亦可自由组合,例如山西朔县汉墓出铭重圈镜,其内圈铭与“昭明镜铭”一致,外圈铭文替换为“姚皎光”镜铭:“如(妙)皎光而耀美,挟佳都而无(承)间。怀驩(观)察而性宁(纾),志(爱)存神而不迁。得并观(见)而不弃(衰),精昭折而伴君。”[24](括号内文字为李零对释文的修正)该类镜铭在句末加“兮”字,便又构成了七言镜铭,例如梁鉴有两件“姚皎光”镜,取镜铭完整者如下:“姚(眺)皎光而曜美兮,挟佳都而承闲。怀驩(观)察而恚予兮,爱存神而不迁。得竝埶(执)而不衰兮精(请)昭折(皙)而侍君。(外圈)”[23]357
故而,楚辞体对七言镜铭的影响是灵活的,既可以通过删去八言赋中的虚词形成七言句式,又可通过在句中或句末增添“兮”字把韵文塑造成七言的形态。而增添“兮”字与刻工力求文字简省也并不矛盾,在新莽时期,七言镜铭已颇为普及,为适应当时的惯用句式,增添“兮”字凑为七言句亦在情理之中。不过,七言镜铭也并非完全脱胎于楚辞体,廖群曾指出有些七言镜铭更近似于民谣、顺口溜:“扬州出土的规矩镜有‘浮游天下及四海,坚如大石之国宝’句,就很难在四字后面加入‘兮’字,这种句式显然并非是由楚骚‘兮’字句演化而来的。”[25]该镜应为新莽时期规矩镜,在镜铭七言体的演变中已属于后期成熟形态,完全脱离楚辞体形态,更接近于当时流行的民谣。
三、镜铭的内在结构
镜铭的主体内容为祝颂类文辞,与祝颂类诗歌不同,诗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一种定式。例如《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期的一组朝廷乐歌,其使用场合应为庄重的祭祀礼,文本结构安排必定具有严格的秩序性。例如《赤蛟》一篇,记录了享用祭祀的全过程:“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昼暗濭。百君礼,六龙位,勺(酌)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辑(集)万国。灵禗禗,象舆,票(飘)然逝,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讬玄德,长无衰。”[4]154神灵从享用祭品到降下福祉,这个顺序是固定而不可随意更改的。同理,《练时日》中的“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4]145记录了神灵从远方到来的过程。
早期镜铭的结构安排并没有显明的秩序性。西汉早期三言、四言镜铭中,只注重相邻两句是否贴切,句组之间关系任意性较大。例如“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1]86前两句中“天”“地”相对,“富贵”之后,祈求“长乐”,而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没有太多的逻辑联系。西汉早期镜铭句序安排灵活,结构松散,可以调换。“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乐未央”的各分句顺序,在另一组镜铭中会略有不同,在“清练铜华,杂锡银黄,以成明镜,令名文章,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寿敝金石,与天为常,善哉毋伤”[1]226一则中,本位于句末的“长乐未央”被放置句中,而“与天为常”(近似“与天相寿”)被替换到句末。镜铭的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祝颂语,制镜者和用镜者都熟记于心,个别句序的调整,并不影响对整篇镜铭的理解。
而在海昏侯《衣镜赋》中,赋文已具备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句子之间联系紧密。赋文前四句首先陈说了衣镜的品质及功能。中间部分描述镜框上所绘的图案,有白虎、苍龙、玄鹤、凤凰,以及西王母和东王公,它们保佑人们享有福泽。而后又描绘了圣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卜商等人,提示人在照镜时,可以圣人和其弟子的言行检视自己,如此便可保持康乐、调顺阴阳。最后的“乐未央”“皆蒙庆”则为常见的祝颂套语。可以想见,镜赋的作者应为级别较低的文人或较有文化的镜师,他们根据上层的授意,结合当时流行的祝颂用语来创制镜文。
铜镜铭文中的七言体亦是如此。例如“尚方御竟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寿敝(比)金石如侯王兮”[1]314一诗,先说明铜镜的来源为“尚方制镜”,品质是“大毋伤”,再叙述图案,位于镜周四方的是“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处在中间的是受福对象子孙;继而描写高高在上的仙人,他们是长寿的象征;最后表达祝颂“寿比金石”。这种“镜作者+镜品质+镜纹饰+祝颂语”的叙述方式与《衣镜赋》如出一辙,多数镜铭的结构均可以此为例。此时的三言镜铭也渐趋成熟,例如:“上华山,凤皇(凰)集,见神鲜(仙),保长命,寿万年,周复始,传子孙,福禄进,日以前,食玉英,饮澧(醴)泉,驾青龙,乘浮云,白虎弓(引)。”[1]350句序间逻辑性更强,完整呈现了上华山遇仙人,求得长生之法的过程。由于具有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句间顺序也不会任意变动。镜铭形成了固定模版,比诗歌模式性更强,模板数量有限且不会轻易变更,各地域铜镜亦会互相流动,融汇彼此风格,故出土铜镜众多,雷同却也不少。但镜铭毕竟是一种实用器具,镜师在铸造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文化水平限制,或镜体空间促狭等,随意增删更改文字,这类现象在制造较为粗糙的铜镜中时有发生。
镜铭的书写内容、顺序与镜背图案息息相关,换言之,镜铭是对图案的释读,可视为图案的脚注,铭文结构的安排依图像而定,以四灵镜和画像镜最为典型。新莽时期四灵镜兴盛,常有镜铭:“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旁),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理、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千秋万岁乐未央。”[1]328铜镜主纹分布了四灵纹饰:北(下)玄武,南(上)朱雀,东(左)青龙,西(右)白虎。中心十二地支的“子”在下(北方玄武位),“午”在上(南方朱雀位),子午线穿钮而过。纹饰与铭文相配,镜背布局协调,浑然一体。北京瑞平2014年春季拍卖会拍卖一件龙虎铜镜,镜纽外龙虎对峙,铭文为“佳镜兮乐未央,辟邪天禄居中央。杜氏所作成文章,服之吉利富贵昌。子孙备具金甫(铺)堂,传之后世以为常男封列侯皆九[卿]。”[26]诸多学者据此认为该类铜镜命名为龙虎镜实不确切,依镜铭所言,镜上图案应为辟邪与天禄。画像镜多见于东汉,铜镜内区的画像旁往往标识榜题,如东汉永元三年,有铭神人白虎画像镜,镜内按顺时针方向分布有“永元三年作”“仙人”“西王母”“白虎”“仙人”“王公”“玉女”“云中玉昌(倡)”的榜题,镜铭为:“石氏作竟世少有,东王公,西王母,人有三仙侍左右,后常侍,名玉女,云中玉昌□□鼓,白虎喜怒毋央咎,男为公侯女□□,千秋万岁生长久。”[1]372铭文中出现的神仙恰与图像对应。镜铭与榜题相辅助,为四灵与画像的辨识提供帮助。由此可知,镜铭的书写并非是独立的系统,文辞之始与图案息息相关,可以推测,上文所举镜铭是特为该类画像镜所作,据图稿而成文。正如一面瑞兽博局镜铭刻写“上有禽守(兽)相因连,湅治铜锡自生文”[1]354,可以看出制镜者在刻绘图案和编辑铭文时的用心精巧。随着造镜的规模化生产,镜铭与图案的联系才渐渐松散,有些绘有四灵图案的铜镜并没有与之相配的“四灵类”镜铭,推测此类铜镜的制作不如“特供镜”极费心思或可能较为晚出。
四、小结
汉代的七言诗并不多见,主要存于民间谣谚和乐府诗中。学者普遍认为七言诗主要是在《楚辞》和民间歌谣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同时铜镜铭文、荀子《成相》的“三三七言”和《太平经》等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7]。事实上,七言的铜镜铭文的构成以四言和三言的组合为前提,生成方式与骚体诗(赋)息息相关,又和民间歌谣多有共通之处。某种新文体样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种文体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承袭革新、孕育与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