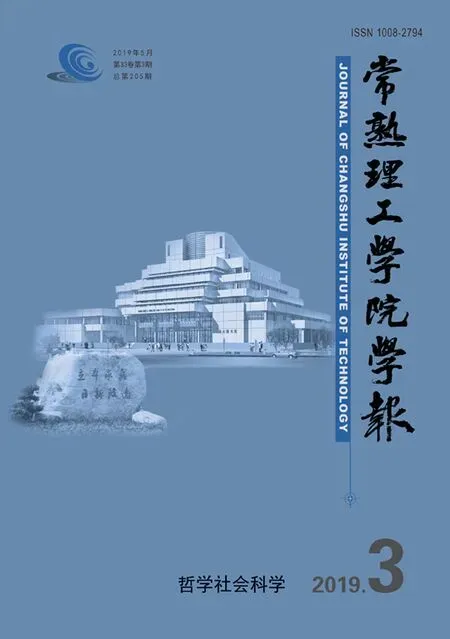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对夫妻关系的重构
2019-03-21魏淑赟
魏淑赟
(天津社会科学院 a.历史研究所;b.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天津 300191)
明清时期,在弹词小说这一体裁中,女性作家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都超过同时期的男性作家。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是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官宦闺阁群体对社会的看法和感受,特别是集中表达了对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不满以及追求。夫妻关系的重构是这些不满和追求在婚后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表达。
一、 我国古代礼教中的夫妻关系
(一)夫尊妻卑
在封建礼教中,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男尊女卑,反映在家庭中,其核心之一就是夫尊妻卑。《周易·序卦》对这一社会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妻关系被认为是从天地规则、万物延续演化而来,上升到天道的伦理规范。在这套规范中,上下和夫妇的关系脱离自然范畴和逻辑推理,被人为规定出尊卑上下。此后,历代文人依此对夫妻关系进行阐释,并用来指导现实生活。
董仲舒以阴阳规定夫妻之“道”,即“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797在《训子孙文》中,司马光对这种夫妻阴阳之道详细加以阐释:“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这一夫妻间的伦常也超越社会的等级尊卑,有“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1]797之说,这一礼教主要作用于封建社会等级较高的女性,突出的例子是公主等皇室女性。虽然与丈夫君臣有别,皇室女性依然被要求尊崇丈夫、敬奉公婆。如果遵守,则受到赞誉;反之,则会受到责难,甚至会被从祸乱国家的角度批判。《汉书·王吉传》将汉朝的祸乱归因于夫妻尊卑易位,认为“夫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可见,夫尊妻卑被提升到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
(二)妻子从属丈夫,且不可再嫁
妻子从属丈夫是封建礼教规定的夫妻关系的主旨。女子在各个人生阶段都被设定为家庭中男子的附属:“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2]67丈夫是妻子的“天”,妻子要遵从相应的行为规范来侍奉丈夫。如《女诫》教育女子作为人妻,境界上要追求“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行为上要“以顺从为务,贞悫为首,故事夫有五:一是平日 笄而相,则有君臣之严;二是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三是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四是规过成德,则有朋友之义;五是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3]2453妻子要做到像儿子孝顺父亲、臣子侍奉君王那样敬奉丈夫,凡事遵从丈夫,要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中汲取优点来完善自己的“妇道”,要成为驯顺的传宗接代工具。
女子嫁人之后往往终生属于丈夫。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亡故时,女子常被社会和家庭赋予“守节”的义务,男子却可以续娶和纳妾。这种对女子的单方面要求被身为女子的班昭合理化表述为“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虽然这一封建礼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不同,但总体而言男子再娶的限制要远远比女子再嫁宽松。
(三)男女双方配偶数目不同
封建礼教对男女双方配偶数目有不同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妻妾制度。妻妾制度从根本上破坏了男女双方的对等关系。妻妾并有的现象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期,西周时形成制度。这种不平等的制度规定,女子只能拥有丈夫一名男子,而丈夫可以在拥有妻子的同时,拥有地位低于妻子的女子作为妾室。妾的数量,视男子的地位而定。按照周朝礼法,男子地位越高,除一位妻子以外,可拥有的妾室也越多。具体来说,庶人不准纳妾,士人可以拥有一妾,卿大夫可以拥有二妾,“诸侯一聘九女”,周天子在后宫可以纳一百二十个妾。纳妾的规定在各个朝代也有所不同,如明代对庶民纳妾限制条件有所放宽,《明律·户律》规定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方听娶妾”。鉴于实际情况,在明代,富商大户纳妾的比比皆是,尽管他们的身份是庶民,也并非无子。清代律例进一步放宽,对纳妾男子的庶民身份和年龄不再设限。
在夫妻关系中,女子被封建礼教禁锢在附属品的位置,即她们在家庭中要以卑下的姿态顺从和侍奉丈夫,不能追求地位和情感的平等。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对这种夫妻关系进行了反思,并进行了挑战和重构。
二、 女作家弹词小说勾勒的理想夫妻关系
(一)平等相待
女作家弹词小说中能体现男女互相尊重的人物形象有王文彩、惠希光、李凤倩、张飞香等,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夫妻模式的互相尊重。如《玉连环》和《梦影缘》中的王文彩和梁琪、惠希光和庄渊两对夫妇之间的遇事相商、相和、相敬;《梦影缘》中何湘月与林武之间亦夫妻亦良友;《精忠传》中岳飞和李凤倩相互尊重、扶持和体谅,且在岳飞亡故后,凤倩能够继承夫志,事事以大义为重。另一种类型是友人的相处模式。《凤双飞》中郭永忠与张飞香二人虽是夫妻,却各以潇洒平淡自认。妻子“不沾脂粉丝毫气”,“好一副,潇洒风流才子派,绝不似,妖娆稚弱女儿腔。”[4]319丈夫则恼恨女子浓妆艳抹,认为如此行径使得秽气腥风扑鼻飘。这夫妻二人赋予对方最大的尊重,并以此获得了较为自由的生活空间。同书中的还有一对理想夫妻是沐梦熊和他的公主贤妻。沐梦熊与妻子才智相当,相敬相爱,他的眼中只有妻子。夫妻间的理想模式有时还通过假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如《玉钏缘》中女扮男装的假丈夫被妻子评价为“稳重端庄无比赛,不负前妻心意坚。少年诚实真君子,无将正眼视丫环。与奴相敬如宾客,举案齐眉效古贤。”[5]119
这两种类型的夫妻相敬都得到了弹词小说女作家的赞扬,是理想夫妻关系的基础模式。
(二)妇唱夫随
女作家弹词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将“夫唱妇随”逆转为“妇唱夫随”,代表性人物有姜德华、左仪贞和桓琦徽等。《笔生花》中,姜德华并未出嫁,而是招赘入门。她的儿子随姜姓,丈夫文炳在姜家承子职。文炳曾形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为“向来闺闼随唱义,卿可知,此语而今已倒颠。”[6]1322《天雨花》中,桓楚卿对妻子左仪贞爱慕甚深,敬重有加,每每遇事恨不能以身相代。作为旁观者的妹夫向妻子(左仪贞的妹妹)描述左桓二人说:“令姐要上天,他就掇梯。令姐要入地,他就把锄头。”[7]953《榴花梦》中的罗传璧最初到处留情,对妻子桓琦徽十分疏冷苛刻;醒悟之后,他追随桓琦徽至沙场,在误以为妻子亡故后意图自尽。
另有十分有趣的事例,妻子还未入门,丈夫已经做好惧内的准备,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和未婚夫皇甫少华。成婚之前,皇甫少华已经见识到了“岳母大人手段凶”,想到自己的未婚妻“丽君若是同其母”,自己也“只好低头做岳翁”。他甚至满怀热忱地憧憬自己“惧内名儿逃不去,能得个,重偕伉俪靠天公。”[8]822
“妇唱夫随”是相对“夫唱妇随”而产生的生活理想,比互相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独立意识。
(三)质疑“贞女”,赞扬“义夫”
对女子的贞操要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呈现越来越严苛的总体趋势。明代,守节的女子可以获得朝廷表彰;此外,朝廷还会给予经济补助。在这种大环境下,宗族制定相应规定对无法守节的寡妇进行惩罚,如子女不能为被出之母服丧,不能与改嫁的妇女来往,否则会受到家族的处罚;改嫁妇女的牌位不能进入祠堂等。贞女是指未婚守节的女子,是寡妇守节的变态化发展,曾受到肯定。封建统治者也曾对此进行旌表,但其合理性旋即受到质疑,进而促使封建统治者不再对此类现象进行大规模表彰。
大部分女作家弹词小说对“贞女”持反对态度。这种态度大多表现得比较平淡或隐晦,如在《榴花梦》中,有婚约在身的桂恒魁和梅媚仙听闻未婚夫身亡,当即表示要守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两人极有可能是为守节而守节。她二人女扮男装,在朝为官,各有功名在身。桂恒魁本来已计划男装一生,梅媚仙虽有恢复女装之念,所期盼的也不过是继续追随桂恒魁,同嫁一人。对于她们二人,特别是对桂恒魁而言,守节不仅不是礼教的束缚,反而是一种成全。在《天雨化》中,未婚夫去世的女子袁氏被再次说亲时,并没有受到批判。《玉钏缘》以“贞女”为非,安排一度成为“贞女”的女子嫁给皇帝为妃。
封建礼教一度推崇“贞女”,女作家弹词小说则追求夫妻关系的平等,推崇“义夫”。“明代史籍所谓的‘义夫’,主要是指那些丧偶不娶的守节男子。”[9]46但弹词小说女作家笔下,“义夫”的准则上升至为死去的未婚妻守节不娶。在《再生缘》中,皇甫少华认为未婚妻孟丽君自尽而亡,愿为其守节。其父认为如果另有儿子,不妨让皇甫少华和未过门的儿媳“做对义夫和节妇,也不枉,多才烈女跳清波。如今唯有双儿女,再联姻,辜负冰霜女丈夫。”[8]363可见,其对儿子的行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皇甫少华在受到独子不可无后的责难后,表示“儿也知,不孝有三无后大,愿则愿,苦守贞性四五年。”[8]294在《天雨花》中,杜顺卿钟情于表姐黄静英。黄静英被父亲黄持正之妾污蔑,被迫投水。杜顺卿认为表姐已亡,从此以“男子中之未亡人”[7]677自居,坚拒提亲,后得知黄静英被救,不惜长跪求亲。《笔生花》中,文佩兰被骗婚,为避免受辱而投水。她的未婚夫谢春溶得知后,“立心原欲书窗老,以报佳人尽节哀”[6]867。《凤双飞》中的郭永忠在未婚妻张飞香失踪后,曾表示如果找不到张飞香,则终身不娶。这些“义夫”的形象表现了弹词小说女作家们对夫妻双方付出同等忠贞的期待。
(四)将夫妻关系异化为合作关系
这一类型夫妻关系的特点是排除男女情感,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女子对丈夫怀有的不是爱恋,而是礼教赋予的责任。夫妻关系不以感情为基础,而是遵守礼教秩序的合作。这一类女子往往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或赞誉、摆脱丈夫的纠缠而为丈夫纳妾。
《 龙镜》中,崔龙珠和未婚夫康王之间君臣有别。从被迫离家到帮助康王复国,她时刻牢记自己“昭阳”的身份,并努力进行符合这一政治身份的行动。在女扮男装的生涯里,她娶妻,而后将这位妻子转移给了康王。崔龙珠不关心康王的爱情归属,只关心他的安危和自己的行为能否符合礼教对自己的要求。
《笔生花》中,姜德华的丈夫文炳曾两次草草娶妻后又将她们厌弃。第三次结婚时,文炳娶得原聘姜德华。因爱慕姜德华的美貌,文炳向妻子立誓不纳妾。姜德华了解丈夫秉性,只求“克尽乃职,使闺门内各得其所而已。”[6]1208她还非常愿意为丈夫纳妾,甚至准备“画屏十二列金钗。教成一部霓裳曲,看舞听歌与子携。”[6]1207文炳戏妻子“只晓得,自图贤惠把名沽”。这看似戏言,实则点破了姜德华与文炳的相处模式。姜德华对文炳不抱有爱情期待,只是依“礼”行事而已。
对丈夫不抱爱情期待的还有冯仙珠、谢玉娟、李艳贞和山夫人等众多角色。在这种“另类”的夫妻关系中,妻子不肯将感情错付给无法回应同等感情的丈夫,展现了别样的夫妻平等追求。
(五)同情妾并赞同不纳妾
女作家弹词小说中,赞同一夫一妻、反对纳妾的思想是主流。这种思想主要通过两种情节描写来表达:一是设置正面人物反对纳妾,并使其获得福报;二是通过描写女性的痛苦,来鞭挞这种摧残人性的家庭模式。
第一,提倡不纳妾。在《凤双飞》中,郭宏殷虽无子,但坚决不肯纳妾。四十八岁时,他的夫人终于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并且这个儿子聪慧无比,忠正无双。在《天雨花》中,品性良善、治家有法的忠臣家庭少有纳妾的现象。在最受作者推崇的左家,左彝即便过四十且无子,仍不肯纳妾,其后连得二子。左、杜、王、桓四家都没有纳妾,夫妻间较为和睦;而纳妾的黄家,因家主听信妾室谣言挑拨,致使嫡女被迫投水。文中还对愿做妾的女子进行了辛辣嘲讽,并安排了她数次被打的情节。可见,这一部分女作家弹词小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期望,反映出弹词小说女作家对夫妻关系对等的追求。
第二,描述女子在妻妾并存家庭中的痛苦。在《玉钏缘》中,谢玉辉广置妻妾,他的后院分化为两个小集团,矛盾不断。虽然谢玉辉极力安抚妻妾,但是效果甚微,有时还被妻妾借力伤害她人。妾室曹燕娘因无法适应这种生活而早逝;妾室郑如昭则“只祈来世先周折,全偕百载永欢娱。还思作正休为妾,一心一意不分离。自由自主无拘束,恩情美满至齐眉。”[5]1715《再生缘》中,身为妾室的刘燕玉担心皇甫少华迎娶正妻和新的妾室后对自己不好,当她听到少华夸赞未婚妻时,马上发怒;少华又赶紧夸赞燕玉。这样,皇甫少华夹在自己的妻妾间,感觉“出言吐语这般难。方才赞得孤元聘,金雀夫人就忿然。若有三妻和四妾,倒须得,留神着意偏周全。”[8]847身处不对等的情感关系,无人可以避免随之而来的痛苦。《笔生花》中,文炳前后三次赘婚,先娶慕容纯,再娶沃良规,最后娶原聘姜德华。但文炳秉性凉薄,只爱惜最漂亮的原聘姜德华。慕容纯只能依靠姜德华护持,痛苦终生。对沃良规,文炳唯求其早亡。后来,沃良规难产而亡,文炳竟然私下庆幸。《玉连环》中,梁琪纳有两妾,但对妾室动辄厌弃。感受到姬妾的痛苦,正妻王文彩劝诫丈夫:“相公,我若做了东君,必定三妻四妾同看待,绝不使闺门有怨姬。”[10]200
女作家弹词小说对妻妾,主要是妾的痛苦进行了细微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妻妾制度中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半数的保护者是同为女子的妻子,丈夫却常常以迫害者的面貌出现。这反映了弹词小说女作家对夫妻关系中丈夫的深切失望。
三、 重构夫妻关系愿望产生的思想基础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社会转型,市民阶层兴起。新思想随之涌现,与旧观念产生激烈碰撞。这一时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主要有民本思想、“重商”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夫妻关系进行的反思。
(一)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
明清时期,部分进步文人对封建专制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如顾炎武主张分散君主的权力;王夫之和唐甄主张对君权进行约束;黄宗羲反对现有的专制统治方法等。与政治思想对专制的反抗相辉映的是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在《焚书》中,李贽认为应该为学术获得自由而发声,“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11]黄宗羲也提出不能“孤行一己之情”[12]103。部分进步文人还更进一步地对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进行质疑,如《焚书》中质疑“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思想的松动为反思夫妻关系提供了发芽的土壤。
(二)明清时期的“重商”思想
鉴于商人对社会的有益影响,有识之士主张士农工商同等重要。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14]941。李贽在《又与焦弱侯》中提出“商贾亦何鄙有?携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携着重,所得者末。然必交于市大夫然后可收其利而远其害。”赵南星认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15]296。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6]41。何心隐甚至认为商胜农工一筹,即“商贾大于农工”。除了直接表述“重商”思想,当时的文学作品也间接传达了这些观念,如故事中描述的将经商作为与其他行业一样的家传正途、官宦之子经商和重商轻儒等情节。这些作品的描述反映了“重商”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女性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谋取经济收益。缙绅和富庶家庭女子的经商、平民女子和知识女性的体力和脑力劳作都是这一社会环境推动的结果。
(三)对夫妻关系的反思
在文化领域,传统理学因陷入教条和形式主义的困境,而遭到批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对夫妻关系的反思从造物、智识、顺从和操守等各方面出发,提出了女子能够与男子平等、在特定情况下甚至高于男子的观念。
第一,论证男女在造物和智识方面并无优劣之分。这种观点认为性别不决定见识的高低,“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7]131对此,那些“皓首大儒不敢望焉”[18]152的知识女性,如班氏、文姬、窦璇玑等受到高度赞扬。这一思想从根本上斩断了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妻子不一定要顺从丈夫。李贽在《初潭集卷三·俗夫》中提出,如果“夫而不贤,则虽不溺志于声色,有国必亡国,有家必败家,有身必丧身,无惑矣。彼卑卑者乃专咎于好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议于治理欤!”[19]家庭的事务权,不应取决于性别,而应该赋予相对贤能的人。在才能优于丈夫的前提下,妻子应该被赋予做决定的权利。
第三,提出男女应该遵循同等标准的操守。相对“妇道”,提出“夫道”。丈夫应该与妻子遵守一样的操守,要求女子只有丈夫一人,丈夫也应只有妻子一人,如无“再嫁”,相对地就不应该出现“再娶”。“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20]276“假如男人死了,女子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21]61“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义……苛求妇人,遂为偏义。”[22]793-794对女性单方面提出的贞操要求,是无耻的表现。“义夫”应该得到提倡,“世无义夫,则夫道不笃;夫道不笃,则妇人之心不劝于节;妇人不劝于节,则男女之廉耻不立。”[23]713可见,时人有践行“夫道”,“义不再娶”者。
此外,进步思想家明确地表达了对“贞女”的反对。如“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24]58-59“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妇也。待母而行,行不逾阃,以顺父母,故曰贞。贞者顺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礼不备,则贞女不行,行则非贞也矣。”[25]95
四、 结语
绝大部分明清弹词小说女作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机会接触社会思潮,部分幸运者还能进行社会实践。弹词小说女作家们父辈大都是官宦,她们或是受到家庭影响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或曾经因随外出任职的父亲而游走多地,见多识广。同时,作为知识女性,部分弹词小说女作家曾经担任教职。
虽然家庭内部的交流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弹词小说女作家的视线透过一扇扇亲友打开的小窗,将对生活的思考融入社会的洪流中。相对于困于闺阁的弹词小说女作家,能够外出工作的部分弹词小说女作家则能更直观地感受社会的变化,对生活进行反思。在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意识独立、甚至经济独立的她们显然不可能继续满足于卑下的从属地位,于是从互相尊重、妇唱夫随、转变对“贞女”和“义夫”的态度、将夫妻关系异化为上下级关系、同情妾并赞同不纳妾等五个方面对夫妻关系进行了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