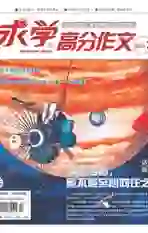红杏枝头春意闹
2019-03-20卢冀璇
卢冀璇
风散墨花香
昼永暖翻红杏雨,风晴扶起垂杨力。
——题记
我们罗城有“三尖”——“山尖,筷子尖,笔头尖”,俗话说“罗城自古出文章”,一点也不虚。这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曾走出周钢鸣、曾敏之、包玉堂、刘名涛、潘琦、鬼子等文化名人;同时,这片充满文学气息的土地也长养了罗城高中的红杏文学社。
“红杏”一词源于宋代诗人叶绍翁的诗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罗城高中取红杏活力与朝气、青春向上之内涵而得“红杏文学社”。罗城高中红杏文学社始建于1986年,至今已有33年。从这里启程,你将走进文学的殿堂;从这里扬帆,你将畅游经典的海洋。在这里,你可以尽洒激情;在这里,你可以飞扬文思。
本社以“繁荣校园文化,丰富课余生活”为宗旨,以“拓展知识视野,提高读写能力,培育文学新苗”为目的,积极探讨文学的内蕴。文学社既能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又能展现文学的魅力。都说文学不是人类造出来的,而是人类心灵长出来的。我们坚信,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带给人力量,也能滋润人的心田。
春光轮回,红杏常开;人类不死,文学永在。
难忘浸润心灵的那段时光
罗衍浩
已在北大度过了一个多学期,算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了。回想起高中,许多事情已经模糊不清,唯有在红杏文学社做事的那段时光,仍记忆如新。
大约是高二下学期吧,《红杏》复刊,于是招社员,选社干,而我有幸成为主编。当时的我们,毫无经验,也毫无头绪,所幸,凭借着对文学的热爱,我们有满腔的热忱和无尽的激情。
社长很是辛苦,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在课间难得的休息时间,总是穿梭于教学楼之间,将下一期社刊需要用的稿子拿给我,就那么点时间,还要将稿子上的问题与我说清楚,再又穿过教室回去学习。而我呢,负责审稿,每天都翻阅社长拿来的稿件,或独自思考,或与人讨论,像在忙一项事业。
但这种忙,并不耽误学习,它像学习之余的拓展,是在与数学题做了斗争之后,难得的心灵休憩时间,只让人感到无尽的充实。
能因为一个题目与社干们讨论好久,能因为一首诗与社员们争论不休,那些为了一个字的修改而忙碌的时间,那些为了放哪张图更合适而思考的岁月,现在都成了最值得珍藏的回忆。
现在的我,回想着那段在红杏文学社的时光,又发现了它给我带来的一些别样的东西。
“很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多读书、多写文章,总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东西。诗歌也好,散文也罢,有灵感有时间写写小说也无妨,不一定要写得多好,也不一定需字斟句酌,这是一种爱好或是一种追求——用文章记录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也用文字展现平淡的生活的另一种形态。这些文字会成为你的识养,会成为你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许有一天,当你翻开你曾经的日记,想起你写过的某篇文章,有过的某次沉思,你的记忆里,那段沉寂地带,会在一瞬间醒来。那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它们在时光里永存。
我大概永远不会忘了红杏文学社,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为了某一件事而付出心血的时光。我真心希望红杏能一直存在下去,并在有才华有追求的后辈们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
书香瀚海
小城旧迹
龙周娜
这是一座坐落在群山丛中的小城。芳草遍植,郁郁葱葱。漫天白蓝的纯净,明亮到晃眼的阳光,梦一般浮动的麦浪,此起彼伏的鸟鸣,全部藏在心底,错落成珠。这是我所熟知的小城,我的故乡——罗城。
已近深秋,街旁道上的桂花盛放在枝头,嫩黄点点暗香袭袭,循着这一条条烂熟于心的路,我慢慢拾起散落在小城各个角落的过往……
老屋
老屋,是经历了一番风雨的。当时,它还算得上是豪宅吧。
六十多平方米的两间瓦房,两扇朱红色的笨重木门前垫着几十厘米厚的被切割得参差不齐的大石板;房前一袭竹林投下一片阴影,风来或雨过时,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屋后是一块斜斜的菜地,连着小山,菜地里的小菜如山间长出的苗芽。
我曾与外公外婆住过老屋,那时我们养着一头老牛、一群小鸡和一只肥大的老猫。那老猫,一身柔软的金黄色皮毛,整日静卧享受静谧的阳光,它不怕人,我每每试探着走过去,它就动动胡须,头都懒得抬一下。
外婆会在每天清晨早早起床,吃了早饭便去河边洗衣服,而我则在旁边玩水嬉戏,间或听外婆与其他人说着杂事,倒也不觉时光难过。眨眼便到午时,吃完了稀饭,我便跟着外婆到田埂上去摘猪菜,就是那种在田里能自生自长一大片的有着细小叶瓣的草,外婆说这猪草是给家里的老牛吃的,为此,我还曾疑惑过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给牛吃猪的菜。
傍晚时分,外婆会在夕阳的余晖中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与其他老人闲聊,我则是在她身后帮她“绑辫子”的小小造型师。外婆是短发,黑白夹杂的头发被我插上几片绿叶或红花,现在想来,那造型大概是有几分刘姥姥的形态,也怪不得我每回都能被自己绑的发型逗得笑个不停。
而到了晚上,我们通常只点两盏昏暗的煤油灯,伴着微动的烛光晃出几丝铁锈潮湿的气息,我们早早睡了觉。
老屋的日子一天天重复,时间如阳光下瞌睡的老猫,慵懒得紧,又如老牛嚼着猪草,慢得看得见,我在这里度过了我最童真的年岁。但当外婆的鬓角被岁月染上了大片的花白时,我便也知道,时间虽看得见,但依然往前走着,而老屋在不知不觉间也被时间刻上了斑驳的苔痕。
小巷
约是六七岁的年纪,我被爸妈从乡下接到镇上。所处的小巷横贯了一条小河,潺潺的流水声响彻四季。
调皮是孩童的天性:我们曾调皮地敲响每户人家的门后迅速逃离,也曾一起捉弄过一个聋哑妇女。她是小巷中卖冰棍的,夏天时我们这群小捣蛋几乎天天光顾她家。她长得瘦小,总是穿着灰扑扑的衣服,有时嘴里会发出“咿咿呀呀”的怪調,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那声音便格外刺耳,且还总是“手舞足蹈”的。于是我们每次去买冰棍时都会捉弄她一番,如故意将她递给我们的冰棍扔回冰箱,挑三拣四好一通后又要回原来那根冰棍,或是故意问她价钱,她说不清楚时,我们就笑嘻嘻地看着她急得手忙脚乱。为此,不少挨家里大人的骂。但奇怪的是,她似乎没有脾气,被我们捉弄了那么多次也不恼火。
我们蹿过小巷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每家每户都认得我们这群捣蛋鬼。大人们却很热情,见又是我们,也不责怪,反而笑吟吟地招呼我们到家里吃饭。
就这样,我在小巷中度过了最无忧的童年,伴着叮叮咚咚的河水声,小巷深处萦绕的是我们银铃般的笑声。
倏地,思绪被一阵桂花香拉回现实。原来,我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小巷,小巷人家依然是当初的人家,小河也依然欢腾着往前,想必,老屋的老猫此刻又在眯着眼睛打盹了吧,不过,在那片翠绿的菜田旁,小洋楼怕也已经拔地而起了。
大黑
李祖月
今天天气很好,我在院子里慵懒地晒着太阳,任阳光洒在我早已失去光泽的毛发上。我叫大黑,我是一条狗,已不年轻。
我和福生住在一间平房里,还有几只鸡和一头母牛。母牛在几星期前生了一头小牛,是福生和我一起接生的。福生是一个倔老头,爱抽烟,爱喝酒。我知道,福生不快乐,即便福生已是儿孙满堂。
平时家里只有福生和我们几个,他的老伴经常被儿子叫去带孩子。三个月前,他的老伴又去浙江带孙子了。前两天福生的大女儿回来砍甘蔗。福生很开心,整天忙上忙下,停不下手,女兒叫他不用干那么多活,他也不听。我想,在女儿眼里,福生可能是个说什么都不听的老顽固。但我理解福生,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待在女儿身边而已,毕竟,他们都难得回来一次。
不久后,福生的女儿砍完甘蔗就回她自己的家了,家里又只剩了福生一个。他依旧爱喝酒,不过他的酒伴又变成了我,家里偶有人来,他才能拉着人家陪他喝上一杯。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到春节了,福生如往年一般开始忙活起来。他起了个大早,自个儿去置办了年货。今年他买的东西格外多,有两大麻袋的柚子,半个麻袋的荸荠,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
村里人都说,福生得享福咯,儿孙那么多。
那天晚上,福生如往常一样,倒一大碗酒,就着一些微冷的菜,自饮自酌。他刚才打电话给老伴,问老伴什么时候回家,老伴说要再过几天。福生和老伴说,他自己用水泥把屋后的那块小地方给铺好了,过几天儿女开车回来就有地方停车了,又说了许多有的没的话。
他一个人慢悠悠地呡着酒,自言自语。他说,儿女们都在忙,过年的时候能够一起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就不错咯。我趴在他脚边,轻哼了两下表示理解。夜深人已静,不知哪来的车在大声鸣笛,惊扰了在梦中啃骨头的狗狗们,于是个个跑出去一通乱叫。只有我在福生身边趴着——我已不年轻,我不会因为外面的一点小动静就叫个不停。人老了,喜欢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狗老了,却懒得说了。
福生那晚说了很多,嘟嘟嚷囔的,大抵又是在想家人了,而我懒懒地躺在他脚边, 静静地听他回忆。之后,他直接就着衣服,睡在客厅里那又冷又硬的沙发上,完全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了。我溜达到房子,舒了一下筋骨,我不愿意去打扰他,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厚了,我一直都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我听到客厅里传来“砰”的一声响。当我急忙跑过去的时候,福生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拍了拍福生,他轻哼了两声后,再也没动静了。我成了他生命最后的唯一见证。
后来来了很多人,哭泣,悲哀,难得的热闹,福生却没有看到。对于他们的悲哀,我熟视无睹,我在院子里继续晒我的太阳。
他们把福生送走了,又商量着要不要把我也送走,毕竟福生走了,家里就没人了。后来在福生老伴的极力阻止下,我还是留下来了。这次和我住一起的不是福生,而是他的老伴。
我并不在乎。我是一条狗,我的名字叫大黑,我已不年轻。这个时候,我正慵懒地躺在阳光里,专心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我每天倾听福生的心事,到底是狗的幸运,还是人的不幸?
我蜷缩在福生的菜园子里,阳光很明媚,没有了福生的絮叨,周围也很安静,我看着阳光,却没有力气接受它了。我说过,我已不年轻,我觉得是时候去陪福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