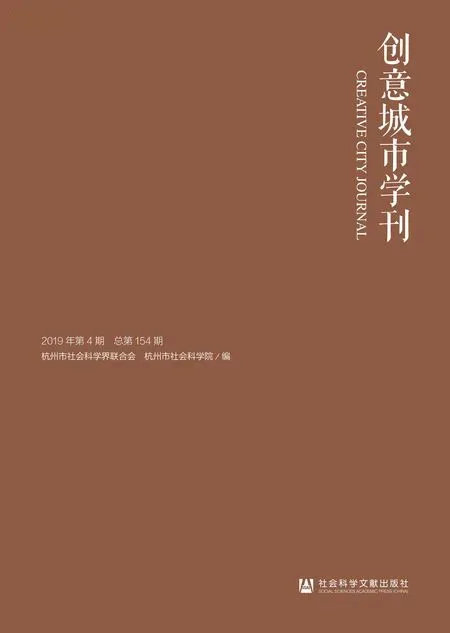王文韶遭劾后的杭州赋闲日记探析
2019-03-20仇家京
仇家京
提 要: 在云谲波诡的晚清政坛, 王文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参与过当时诸多内政外交事务, 深得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宠信。 因受云南军费报销案牵连被劾回籍, 家居五年后奉诏再度出任湖南巡抚等职并连连擢升, 终授武英殿大学士得以身名俱泰, 被时人冠以“油浸枇杷核子” 的绰号。 在《王文韶日记》 中, 游离于官场之外的“杭州记事” 鲜为学界关注, 却真实地袒露了他隐秘的内心世界。本文以此为叙述主体并加以解读, 力图揭示其复杂的人生真相。
杭州图书馆所藏手稿本《王文韶日记》 (以下简称《日记》), 自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以来, 研究者分别对日记中的不同史料加以采择利用, 专题或概述性的文章渐趋繁多, 时有创见。 而笔者着意之处, 则在于鲜为学界论及的王文韶因“云南军费报销案” 被劾回杭州后约五年间(1883 ~1888) 赋闲生活的记事。 揆诸原委大致有二, 其一, 在王文韶近五十年的职官生涯中, “云南军费报销案” 被劾回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而杭州作为事主的故乡, 既是此案落幕后的归宿, 又是其再次出任湖南巡抚直至位极人臣的起点。 尤其是在“台下” 闲居期间所遇、 所想和所记, 自然显示出与在位时谨饬不苟的心境以及行事的差别, 在官书或时人的记载中均难以获见。 其二, 因赋闲期间的日记游离于官场之外, 不能预知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个人升迁经历, 即便受到时势变化的影响, 也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叙述, 故信笔所至, 记载事实较详, 坦露心迹较显, 可信度颇高。 笔者曾撰文列举王文韶被劾经过、 回杭闲居时的“退隐” 愿望等内容[1], 尚不足以揭示他在“皇恩” 或时代浪潮驱动下进退难以自主的复杂性以及自身性格的多元性。 这些赋闲琐记, 因缺少看点易为论者所忽视。 其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 反映了王氏的内心世界并延伸至复出后的心理轨迹, 这对于揭示或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是不可或缺的。
一 因“云南军费报销案” 的牵连被劾回杭的缘起
清朝祖制, 历来赴部报销军需等项, 均要给予“部费”, 意在补充办公费用,至晚清演变成报销者和户部司官、 书吏的贪污门路。 而“云南军费报销案” 不仅涉及晚清的财政制度, 还牵涉到当时官僚集团的党争或派系倾轧。
光绪八年(1882) 七月, 云南省为报销军需一事, 派人前往北京商谈贿赂数目一事外泄, 御史陈启泰奏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 继而御史洪良品上奏, 据“外间哄传”, 直接指明时任军机大臣的户部尚书景廉、 左侍郎王文韶“均受贿巨万”[2]。 清廷指派刑部尚书麟书、 潘祖荫确切查明, 务期水落石出, 以成信谳。 其间,清流党邓承修、 张佩纶先后上疏, 为景廉开脱, 以激烈言辞斥责王文韶并做道德与人格上的攻讦。 邓说: “胥吏必赃证俱确, 始可按治, 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评……景廉素称谨饬, 不应晚节而顿更……若王文韶赋性贪邪……才不足以济奸, 而贪可以误国”[3]。 而朝廷上谕, 以王文韶“数年以来, 办事并无贻误……仍著照常入值”[4]。因该案迁延日久, 张佩纶在同年十月间连上四道奏折, 声援邓承修: “舍赂遗而论素行, 原景廉而劾文韶, 较得事理之平而为纠慝弹违之正论。” 并进一步为景廉辩护: “户部事体皆文韶主持, 景廉虽列衔在先, 仅于随同画诺……景廉崎岖西域十有余年, 如果素行贪婪, 拥军截旷, 久可致富, 何待今日而始货殖以自封哉!” 贬斥王文韶“坐拥巨赀, 乾没不已”。 甚至在《三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 的奏疏中声称: “今文韶甫被慰留, 地气即不安靖。 臣不必谓文韶足致地震, 然也适然而相值矣”[5]。 推定其贪污并假以天人感应的说辞, 请求将其速行罢斥。
早在光绪七年七月, 给事中邓承修就以“彗星见于北方, 初指紫薇, 近犯钩陈”为名, 上《为星象示变宜任贤去邪以固邦本而应天遣》 一折, 指斥王文韶为“楶棁之材、 斗筲之器。 为曹郎日, 即以奔竞著名, 已为清论所不予……老猾贪庸, 岂足以当重任”[6]。 王文韶在召对养心殿闻此奏劾后记曰: “位高速谤, 夫复何言!”[7](此后凡出自《王文韶日记》 的引文, 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不再出注) 云南军费报销案事发后, 邓、 张专攻王文韶贪污, 并连带诋毁已死大学士沈桂芬“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 实为知人之累”[8]。 以致被上谕驳为“臆度之词”。 可见, 此案并无坐实王文韶收受贿赂的证据, 学者已有论述, 毋庸赘述。
王文韶遭劾后不安于位, 几次奏乞开缺归养。 虽经慈禧一再慰留, 但是在张佩纶再三弹劾之下, 去意已决。 结案前, 他在《日记》 中相继载道: “余此次乞养,义不可留” (第603 页), “余以请开缺养亲折内曾声明, 俟云南报销案结再行回籍,不得不留此少候” (第609 页)。 这与他五年前入都并迎接母亲进京时“从此供职事亲, 庶几心安理得矣” 的心境迥异, 流露出“滇案尚无具奏日期, 焦闷之至” (第613 页) 的心绪。
光绪九年七月五日, 云南军需案以王文韶“失察书吏” “夺两级” 了结, 上谕亦“准其开缺, 回籍养亲, 裨遂孝思”[9]。 王接阅邸抄后归心似箭, 随后与诸僚属辞行, 偕八十四岁的老母以及家眷赴津乘船南下, 七月十八日抵达杭州。 当天记道,“余自蒙恩准归养, 至此初愿始遂……冒险航海, 平安抵里, 天之待余为不薄矣。余自通籍后以官为家者三十年, 至此乃为有家之始” (第618 页)。 亲友迎接、 备筵洗尘, 相聚甚欢, 开始了故乡的闲居生活。
二 王文韶在杭州的赋闲生活场景探析
(一) 杭州清吟巷祖居的由来
王文韶早年曾奉母乡居, 曾与云栖寺住持僧宏熹订为方外之交。 咸丰二年考中进士后, 长年为官奔波在外, 对暌隔已久的故乡依然一往情深。 据其父《王又沂墓志铭》 载, “先世出太原宋平章事爚从, 南渡始居越之上虞, 明正德迁钱唐后, 改籍仁和……少孤, 依姑夫符业鹾吴之嘉定”[10]。 他祖上早在康雍年间, 就已居住在杭州清吟巷, 至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时, 已是家道中落, 子孙涣散。 光绪元年,王文韶之子庆均赴杭应省试, 无意中以九千元价格购定清吟巷瞿宅房屋。 继从清吟巷族祖王乃斌《红蝠山房诗钞》 残本中读到《谢人赠红蝠笺》 诗注, 了解到曾有五只红蝙蝠绕梁飞行于清吟巷祖宅的吉祥之兆。 光绪六年五月, 王文韶再度从清吟巷宅旁包姓地基购得四亩多地, 以兴建规模宏大的宅第。 并在日记中载道, “包姓交出老契, 系嘉庆十七年我家曾祖行林照公售出者, 香雪叔祖代书。 相隔七十年, 仍归于我, 此亦数有前定也” (第512 页), 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光绪七年十一月, 王文韶倩左宗棠为之书写“红蝠山房” 匾额, 悬挂于京城寓所, 并撰有《红蝠山房记》, 记其出处甚详。 光绪九年, 王又获八千卷楼藏书楼主丁丙所赠《红蝠山房诗钞》 初刻本时, 称“获此家珍, 致足喜也” (第631 页)。
在杭州清吟巷居住的五年间, 《日记》 记录了王文韶“无官一身轻” 背景下的闲居生活, 并营造“退圃” “归舟” 船厅等建筑, 与此相关的一些楹联、 诗文等文化符号, 无不隐含着撰者对官场生涯的总结以及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二) 见客会友、 品茗听戏或游山泛湖的惬意长日
王文韶人缘颇好, 回乡后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同时, 故友知交纷至沓来, 拜客见客不绝。 从日记的片段中, 尚可感受其轻松闲适的心情:
早起偕桐侯、 筱饮、 嵩云、 乔梓、 恒岩, 挈森儿、 熔孙至丰乐桥吃点心,出涌金门至三雅茶园小坐, 乘小舟泛湖, 至钱塘门登岸而归……午刻祀先, 经伯、 子惠、 梦九同来, 约明日听戏。 (第621 页)
早起偕同人登吴山一游, 瞻仰赵恭毅、 阮文达两祠, 在四景园小坐, 下山吃王饭(作者注: “王饭” 当是“王饭儿” 的省略), 家常风味颇为适口。 (第622 页)
下午偕桐侯、 筱饮并挈桢儿出涌金门登湖舫, 约陈右铭同年一游。 至三潭印月, 设行厨晚膳, 乘新月放舟毛家埠, 宿灵隐。 (第623 页)
卯刻登韬光, 下山寻飞来峰诸洞, 午膳后放舟游凤林寺、 巢居阁, 绕孤山之麓, 至平湖秋月, 小坐乃归。 (第623 页)
偕吴筠丈、 少伯、 茗笙公请仲良中丞、 子和学使, 席设吴山阮公祠, 酒半登文昌阁清秀山房一眺, 全湖在目, 风景绝佳, 酉初始散, 到家已上灯矣。(第634 ~635 页)
偕芸史、 桐侯、 克斋诸君孤山探梅, 携樽赵公祠后楼小饮, 甚为畅适。 散后渡湖至弥勒院少坐, 登楼一览, 胸次豁然。 (第635 页)
起早偕桐、 孟诸君至三潭印月看荷, 清气袭人, 尘襟为之一涤。 回至三雅园吃茶。 (第648 页)
王文韶居杭期间发生了几次家庭变故, 以致《日记》 缺失一年零两月有余。 光绪九年八月十八日, 其长子庆钧病卒后心绪恶劣, 断记约两月有余, 至十一月初一又续记。 次年十月二十日其母吴氏辞世, 这对事亲极孝的王文韶来说情何以堪, 《日记》亦从此日起辍笔。 接踵而来的是夫人钱氏去世, 直至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始恢复日记。 总之, 除了抒发对亲人的追思之情以外, 在家乡会客酌饮、 听戏品茗, 或登山泛湖, 日子过得颇为惬意。
(三) 深谙官场险恶而萌生退意
见十三日邸抄, 恭亲王撤双俸, 开一切差使家居养疾, 宝原品休致, 李、景降二级调, 翁革留, 均退出军机。 朝局一变至此, 真非意想所及, 鄙人若非早日乞养, 到此地位, 便欲归不得矣。 吁, 可畏也! (第641 页)
慈禧太后这次大规模改组军机处, 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交织的产物。 王文韶庆幸自己因归养而脱身于政治旋涡的同时, 亦萌生退意, 并在所建府第的相关建筑以及楹联中无所顾忌地坦露了心迹。
宅后辟地三亩余, 为种竹栽花之所, 拟名之曰“退圃”。 地多积土, 叠成小山, 本日种梅二十株, 杂以桃李, 两三年后当蔚然可观也。 (第663 页)
至退圃闲步。 接翰卿信, 为拟晚香小筑楹联曰: 清风明月何时无? 记前尘梦幻, 尽偷闲脱巾读画、 拄笏看山, 总觉得利锁名缰, 不如老圃; 布袜青鞋从此始, 趁暮飞腾(作者注: 日记原文“趁暮飞腾” 疑脱一字), 聊就近叠石栽花、 疏泉种竹, 却早与莺盟燕约, 还我西湖。 (第684 页)
接翰卿复书, 为酌定归舟跋语曰: “舟可以远行, 破浪扬帆瞬息千里, 然风涛之恶往往有之, 知进而不知退, 信不可欤。” 余自乞养归, 就屋后隙地构数椽以容与而偃息焉, 是固余之舟也。 (第690 页)
光绪十二年五月, 王文韶赴嘉定探望亲友, 返杭后大病一场, “几濒于危”。 痊愈后补记云: “余此番病起不啻再生之庆, 痛定思痛, 万念俱灰。” (第683 页) 是年十月为五十七岁生辰, 继有“年未六旬而病魔缠扰, 竟颓然如老人矣” (第685页) 之叹。 数日后又获悉时任四川永宁道沈守廉(字洁斋) 有“开缺送部” 之旨后, 《日记》 载道: “宦海风波, 其不可测也如是” (第701 页), “为之怃然” (第710 页)。 同时, 与王文韶交谊匪浅而被罢官的奕, 寄赠《萃锦吟》 (集唐人句)诗稿三册, 酬酢唱和、 感时伤怀或托物言志, 巧妙地表达了他淡泊权力或与世无争的态度。 而在王文韶看来, 咸同光三朝重臣且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诗作, “阅之知其近年家运屯邅, 心境抑塞, 有非人情所能堪者, 回首前尘, 感喟曷已” (第702页), 则是另一番感受。 这时的王文韶, 已不再把游宦生涯的道路视为当然, 再次透露出对官场变数的忧虑。 可见, 所命名的“晚香小筑” “归舟” 等建筑并非为了休闲逸乐, 而是铭文中所揭示的“匪闲之耽, 而险是避” (第690 页) 的旨意。 身体渐趋衰老的外在原因的背后, 流露出规避宦海“风涛之恶” 以终老“退圃” 的情绪。
光绪十三年三月, 正当王文韶忙于经营修葺近二年的杭州毛家埠祖茔工程之际,朝廷传来了皇上“王文韶著自病痊后即行来京听候简用” 的朱批。 王上奏以“天恩高厚, 非梦想所敢期, 惟以病体未复, 未能及时报效为憾耳” (第697 页) 为辞,继续滞留杭州。 是年底, 经媒人作筏, 娶得“姬貌中人, 性格似颇和平, 心地亦尚明白” 的苏州籍赵氏为妻, 以为“朝夕奉侍之需” (第725 页), 似有终老故乡、 颐养天年的愿望。
DU Bing-ying, FAN Cun-xiu, LU Xiao-yan, CHEN Chao, BI Xiao-ying
次年四月, 清廷再次任命年届花甲的王文韶为湖南巡抚, 所谓“天恩高厚, 感悚实深” (第736 页)。 朝命难违, 于是请假一月, 并拜请精通命理的高宰平“看五星”, 记道: “言生平癸运最坏, 是为枭神得食(五十二至五十七), 现行已运, 平顺无疵, 此后甲、 午、 乙三运一路平安, 午运尤吉。 惟未运欠佳, 志之以备征验。”(第739 页) 继而饯别亲友、 拜谒祖墓, “松楸葱郁, 依恋实深, 回顾徘徊, 情难自已” (第743 页), 怀着忐忑不安以及不舍故乡的留恋之情, 家居五年后再次赴任。
三 王文韶简评
王文韶再任湖南巡抚一年余, 即奉上谕补授云贵总督;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 甲午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应诏入都, 直至接任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并授以武英殿大学士得以善终, 可谓破浪扬帆于宦海风涛。 时人质疑其“既不如李鸿章之左迁, 又不至有瞿鸿禨之窜谪, 周旋于新旧党、 帝后党之间, 得以令终。 使非圆滑, 曷克臻此”[11], 或以“油浸枇杷核子”[12]“琉璃球”[13]绰号相讥。 《清史稿》则称其“历官中外, 详练吏职, 究识大体。 然更事久, 明于趋避, 亦往往被口语”[14], 以致王文韶多以无所作为或圆滑平庸的形象示人。 上述推定或评语, 试图诠释其获咎源自所持的不同立场。 要解析这些行迹背后的主客观因素, 还要回归到王文韶本人。
首先, 王文韶的退隐构想在杭闲居期间已见端倪, 但未能如愿。 光绪十九年,复出后的第四年, 在云贵总督任上因身体不适与水土不服等因, 上呈《沥陈病状恳请开缺折》, 并记曰: “蒿目时限, 无能补救; 久居高位, 实切疚心。 惟有奉身以退自保末路而已, 非敢自外生成也。” (第841 ~842 页) 朝廷命以“批赏假两月, 毋庸开缺”, 于是叹道: “天恩高厚未许归田, 孱体支离深虞旷职, 不禁感悚交萦也。”(第846 页) 后俟赏假期满, 以“病体未痊” 再次恳求恩准免职, 仍赏假二月。 无奈自云: “忝窃至此, 出处自有前定, 特孱躯不堪久膺重寄, 不能不为朝廷据实自陈耳” (第856 页), “欲归未得, 心向往之” (第862 页)。 甲午战败后, 王文韶奉旨赴京帮办北洋事务, 进入朝廷中枢, 协助李鸿章等人, 苦苦支撑和维持着国家的局面, 诚有“误蒙朝宠, 时事仍亟, 不敢萌退养之志”[15]的苦衷。 而“时艰适值,巨任骤膺, 不胜惶悚” (第871 页), “一官羁绊, 仍不能不衣冠见客, 殊黯然也”(第876 页) 等记录, 则道出了他擢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时无奈而落寞的心境。 当李鸿章赴日签约遭日人枪击经调养痊愈后, 他在《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为臣力小任重请令李鸿章即回本任奏》 中坦陈: “生平于地方吏治民情粗有阅历, 独军旅之事素所未谙。 ……两月以来, 无日不战兢惕厉, 幸蒙随时指授机宜, 并有李鸿章成辙可循, 得免陨越。 此时大局将定, 惩前毖后, 首在北洋。 且一切善后事宜, 亦非资轻望浅之生手所在地能就理。” 恳请朝廷“饬令李鸿章即回本任”, 以“维持时局,图济艰难”[16]。 数日后, 天津塘沽海啸, 正所谓“时事正棘而灾变如此”, 又具折由驿六百里驰奏: “自请立予罢斥, 以应天变” (第885 页)。
光绪二十七年(1901) 七月, 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约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 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并控制从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关的交通路线等, 将清政府置于直接控制之下。 遭此世变, 时以大学士授为会办大臣的王文韶心力不济, 补苴乏术, 继以“精力衰颓、 两耳重听恳辞” (第1031 页), 终未获允。 上述事例表明其确有隐衷, 并非恋栈权位而出于矫情。
其次, 漫长的职官经历与见闻, 为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他看来, 越是居于高位, 所承受的风险越大。 王文韶进入清廷中枢后, 更是身陷复杂的党争, 并无可靠的奥援, 唯有明哲保身而已。 在“每思持盈保泰之义, 则兢惕不能自已”(第930 页) 这些寄语的背后, 更是基于临深履薄、 忧谗畏讥的谨慎与思虑。 《日记》 中对慈禧剪除“帝党” 羽翼时的心迹以及所见官吏贬黜的感受或议论, 多有所表露。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 光绪皇帝数召朝臣问询对策, 时任吏部侍郎的汪鸣銮支持亲政后的光绪帝筹谋新政, 反对后党掣肘, 奏对尤为切直, 于是招来后党的忌恨, 以致与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被特旨革职, 永不叙用。 王文韶因此载道: “上谕有不学无术, 迹近离间等语, 知其于召对时语涉两宫也。 噫, 处人家庭骨肉间尚非易事, 况上及宫庭乎! 志之以资警惕。” (第919 页) 次年三月, 曾为瑾妃、 珍妃之师的侍读学士文廷式被西太后剪除, 《日记》 为此记曰: “阅邸抄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 杨崇伊原参, 谕旨与内监往来, 虽无实据, 事出有因, 且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可以知其所由来矣……闻其才华绝世, 惜无福以载之耳。” (第937 页)
晚清官场, 钩心斗角, 尤其是帝党与后党之争, 且其中夹杂着微妙的“家庭骨肉” 关系, 更使得为官者如履薄冰。 所持立场或情绪, 一旦不慎, 左右支绌, 动辄见咎, 《日记》 中屡见“志之以资警惕”, “宦海风波, 真不可测哉” (第955 页)之类的记录与感叹, 正是寄寓了他避免重蹈覆辙的自警之意。
王文韶以寒素起家, 仕途顺遂, 离不开当时朝廷重臣的援引举荐, 加之自身的勤劳干练, 为官所到之处皆有治绩可称, 在士林中具有一定声誉。 从当时满汉大臣的评价来看, 诸如“奕素赏其能……其由湘抚入值军机、 云贵移督直隶, 皆所荐”[17]; 左宗棠、 李鸿章先后上奏举荐, 称其“才长心细, 器识闳伟, 素为中外所信服” (第3 页), “该司才明识练, 廉干有为, 正赖匡襄咨度之时” (第133 页),恐非过誉之词。 而屡为时人称道的是, “王公性通识明, 老于政事。 其遇物无同异,一接以和, 盖器量有过绝人”[18]。 或称“公之相貌极清, 望之如春, 和蔼可亲, 尤善气迎人。 御下极宽, 据侍其左右者言, 从未见公以急声厉色对人。 待遇庶司百僚,更谦和异常, 有过失者, 但婉言以戒之, 令其自省耳”[19]。 这些话, 道出了他个人性格的特质。 据《日记》 所载, 与王交往者如大臣或僚属友朋等不下数百人, 其品评人物或钦服时贤情见乎词, 遇贫弱者赠以钱财以纾其困, 对涉世未深的晚辈或僚友则赠人以言。 诸如:
生甫年来养气之功甚浅, 以身入世, 深虑非宜, 临行谆谆劝勉, 冀其能随时省惕为幸。 (第64 页)
手致生甫书, 以“择交游, 惜声名, 少议论, 慎行止” 十二字嘱之。 (第272 页)
惟有忠君敬上, 虚己下人, 为人所不可及处。 若以勋业自多, 兀傲自喜,便使人一览无余矣。 (第254 页)
处事不可不脚踏实地, 愈阅历愈不敢不详慎耳。 (第303 页)
恽莘耘辞行赴江西, 候补回避, 奏留部驳改掣, 现始请咨, 临别以“学吃亏” 三字赠之。 (第755 页)
宁乡监生周柱坤年二十一, 肯读书, 天分极高, 自陈求见, 人颇隽爽, 却嫌其亟于自见, 以深藏勿露勖之。 (第773 页)
这些谆谆劝导之语, 颇具长者之风, 爱才之笃、 待友之诚以及谨饬不苟的性情约略可见。 在待人温厚忠恕的背后, 也隐含着他虚己下人的性格以及“忠信可以涉波涛” 的处世信念, 无疑是多年游宦生涯中的经验之谈。
尤为难得的是, 王文韶能秉持“勤慎从公、 无负国恩祖德为训” 这一理念并践之于从政。 光绪二十六年, 义和团兴起后, 在刚毅等官员以“拳民可恃” 的默许下进入京城。 针对义和团“剿” 与“抚” 以及对列强的“战” 与“和” 的内患外侮问题, 慈禧、 光绪帝连续召开五次御前会议。 史载“拳匪肇衅, 首祸诸臣, 惑于邪说, 文韶力持正论, 再三上陈, 深中其忌”[20]。 王曾站在主和派立场参与廷辩云:“中国自甲午以后, 财绌兵单, 众寡强弱之势, 既已不侔, 一旦开衅, 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 孰料这番话激怒了慈禧, 竟然击案大骂: “若所言, 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 若能前去, 令夷兵毋入城, 否则且斩若”[21]! 六月二十一日, 清廷颁布《宣战诏书》。 八月, 英、 美、 日、 俄、 德、 法、 奥、 意八国联军侵陷北京, 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促“西狩”, 王文韶因未及随扈同行, 仍以七十一岁的高龄, 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携带军机处印信, 三日内狂奔一百九十余里, 追至怀来拜谒两宫,以“白发老臣一人, 相从西幸, 备极贤劳”[22]。 慈禧召见时, 相持而泣, 感慨系之曰: “此后国家惟汝是赖”[23]。 时人为此誉其“赴难之勇如此”[24]! 国家危乱之际未见其畏葸退缩, 而是敢于担当任事, 这与“柔媚无风节” 等时论讥评则显得大相径庭。
综观《王文韶日记》, 在其历次仕途升迁时, 不乏“天恩高厚, 感激荣幸之至”, “宠擢兼圻, 恩深责重, 感悚何似”, 甚或“恭设香案望阙谢恩” (第765 页)等记录。 尤其是两次奉诏入都后充任军机大臣等职, 随时宣召, 得以与皇帝、 西太后等近距离接触, 所记上朝时辰、 穿戴服饰、 磕头请安、 赏赐谢恩等琐事, 不厌其烦, 颇为读者诟病。 在罗列衣冠、 赏赐的背后, 不仅意味着朝廷的优渥和恩宠, 也是光耀祖宗门楣、 福荫后世子孙的事情, 故详加记录, 以显尊荣。 光绪十五年, 王文韶复出后由湖南巡抚擢升云贵总督, 他给时任云南临安开广道道员汤聘珍(字幼庵, 湖南善化人) 的书信中, 以白香山《送敏中新授户部员外郎西归》 “上到青云稳著鞭” 句赠之, 直接拈出“窃自附于互相警勉之义焉” (第816 页), 可谓夫子自道。 而当时内忧外患交迫的晚清, 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朝廷和职官的个人命运相融合、 摩荡, 宦途中“持盈保泰” 的冀求和时事风云的变幻、 不测的天威之间, 有着不可预知的冲突或变数, 荣辱利害, 依违两难, 加剧了宦海沉浮的不确定性。 王文韶自被劾回杭起, 数次退隐不就。 在受命于时局艰危的情势下, 徐图补救, 即便坦陈“力小任重” 的苦衷, 也只能被历史的潮流或皇权所裹挟, 顺势勉力而为。
注释
[1] 仇家京: 《杭州图书馆藏稿本日记鉴赏述例》, 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 第14 辑,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第96 ~98 页。
[2]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 第2 册, 中华书局, 1958, 第1401 页。
[3] 邓承修: 《语冰阁奏疏》 第2 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12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4] 邓承修: 《语冰阁奏疏》 第2 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12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5] 张佩纶: 《涧于集》 第3 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10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6] 邓承修: 《语冰阁奏疏》 第2 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12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7] 《王文韶日记》, 中华书局, 1989, 第568 页。
[8] 邓承修: 《语冰阁奏疏》 第2 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12 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9]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 第2 册, 中华书局, 1958, 第1439 页。
[10] 周保珪: 《王又沂墓志铭》, 《附杭州图书馆地方碑帖目录提要》, 《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录》,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第160 ~161 页。
[11] 小横香室主人: 《清朝野史大观》,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第559 页。
[12] 小横香室主人: 《清朝野史大观》,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第817 页。
[13] 何刚德: 《春明梦录》,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第33 页。
[14] 赵尔巽等: 《清史稿》,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第9490 页。
[15] 项士元: 《云栖志》, 新光印书馆, 1934, 第100 页。
[16] 戚其章: 《中日战争》 第3 册, 中华书局, 1991, 第148 页。
[17] 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第148 页。
[18]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 “安徽古籍丛书”, 黄山书社, 2002, 第171 页。
[19] 罗养儒: 《云南掌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丛书”,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第559 页。
[20]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第387 页。
[21] 李希圣: 《庚子国变记》, 《续修四库全书》 第446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第443 页。
[22] 罗养儒: 《云南掌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丛书”,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第33 页。
[23] 罗养儒: 《云南掌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丛书”,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第387 页。
[24] 龙顾山人: 《庚子诗鉴》 第3 卷, 中国书店, 2008, 第22 ~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