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就像塑料花,永不凋谢
2019-03-20
1988年的元旦,我买了两张票,请哈文看演出,她还真来了。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我说:“哈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你别老羁押着我。我就看你挺好的,就愿意你当我女朋友。凭我这条件,你吃亏吗?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我就再没这念想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要么你就……”
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最后一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闷了好一阵儿,她都没说话。最后,她一伸手,把花拿走了。
一朵野花,就这么改变了李咏的一生。
1989年春节,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她爸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爸,首先要搞定奶奶,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喜欢得不行,拉着我的手不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本来是一件大喜事。谁承想,我在顺义刚接受完十天保密培训,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里面什么样,就直接被发派到西藏电视台播《西藏新闻》去了,一去就是一年。
对于一个在热恋中同时又满怀抱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
那年我23岁,一个人在西藏,开始读尼采。又开始每天一封信,倾诉思念,倾诉孤独。
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而此时,近乡情怯。积蓄已久的思念、爱恋、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一年没见,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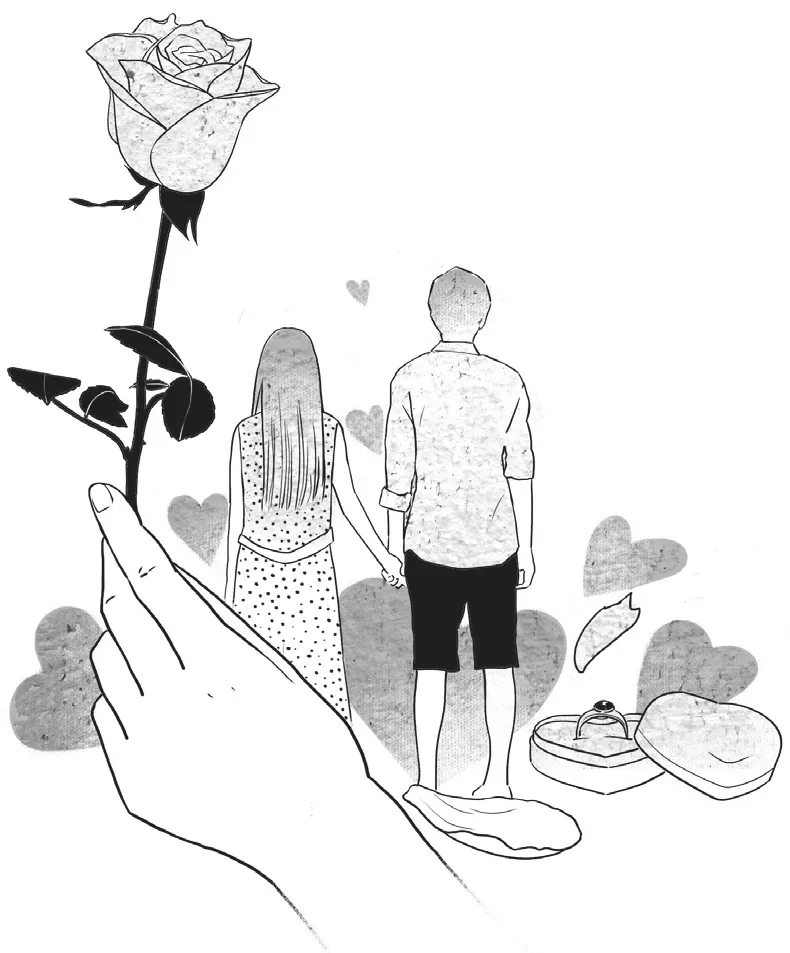
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却特意地没有告诉她时间。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先回台里报到,报完到,我赶紧去“四联”理发,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然后回去洗澡、刮胡子,换上新衣服、新袜子,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
穿戴一新,坐地铁到西单,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花了我九个月的工资。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仔仔细细包好,庄严地捧在怀里。
接着,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倒是便宜,太慢,我等不及啊。
车到天津,已是暮色四合。我捧着99朵玫瑰站在路边发傻。上次来是白天,有人接送,现在这黑灯瞎火的,哪儿是哪儿啊?没办法,只好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天津电视台。
逡巡片刻,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沉住气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我举起手,“当当当”,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没人理我。“当当当”,又敲三下。“谁呀?”哈文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那一刻,我心中忐忑。我怕啊,生怕她对着门外,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不,别说名字,就算她兀自在屋里嗔怪地说上一句“真讨厌”,老子就能一脚把门踹开!我还是不吭声,屏着一口气。“当当当。”紧接着就听见“咚咚咚咚”一溜儿小跑。“吱扭”一声,门开了。
她还是短发,比过去胖了点儿,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我皮肤黝黑,两腮凹陷,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一年里瘦了4斤,倒是不多,但全瘦脸上了。
“我回来了。”相视半晌,我说。流泪的不是我,而是她。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化了。这99朵玫瑰,此时可真多余啊。想拥抱她,都腾不出手。
很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了。
西藏一年,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了,心被揪得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如胶似漆地腻了十年。
到了第十个年头上,哈文主动提醒我,两个人过日子有些无聊,家里有些太清净,我是老李家的独子,总该有个后代云云。
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
结婚17年,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凡事她不允许而我做了,比如喝酒,就得央求所有目击证人替我保密、替我保密、替我保密。我怕她,只要她一瞪眼,一生气,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者干脆消失。我怕她,一百次争吵,一百次是我认错。我怕她,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我还给自己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成熟的稻子总弯腰,我弯腰,因为我成熟;我怕她,是因为我爱她。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怎么说的都有。“玫瑰。”“红玫瑰。”“百合。”“麝香百合。”
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料花。”闻者皆惊。
“塑料花很普通,但永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我解释道。
科学家深入分析人类荷尔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定律:所谓“爱情”,保鲜期不超过36个月。或许不少人都亲自验证了这一说法。
但是对我来讲,爱情是无限期的,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
摘自《咏远有李》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豆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