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旅
2019-03-19饶宗颐
新加坡五虎祠
—谈到关学在四裔
今日的新加坡,经济蓬勃,为现代化十分成功的国家,居四小龙之首。回溯开埠以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八一九年莱佛士(Raffles)最初登陆,据说由台山人曹亚志(一作珠)冒险带路,英人酬以加冷河(Kalang River)畔丛林之地,曹氏在该处建祠,号曰曹家馆。另该河峨螬地区的Lavender街,有一座小庙,俗称社公庙,亦名五虎祠,里面奉祀约百多位神主,神龛祭坛分为五列,柱上刻写“志明义士”、“待明义士”、“候明义士”等字样。在庙宇之前,站着绿叶成荫的大树,复有石马,香炉两旁杂祀诸神像,有关公、伯公及大圣、包公、观音,很像古代所谓丛祠,故被称为社公庙。这庙的历史向来无人注意,扶桑友人田仲一成研究,认为是奉祀诸义士的秘密会社,为义兴公司的前身。星洲档案馆庄钦永仔细考察,利用档案及碑铭材料,考出其中神主义士,像许戊芝,代理过绿野亭首事,张族昌、余增涌是茶阳会馆副理,林亚泰是潮郡义兴首领,想不到这座社公庙对移民史关系这么重大。古藤蛛网还悬挂着先代拓殖者辛酸的泪痕与血迹;可惜经过频年城市绿化的洗礼,这古庙在坡面的历史上的重要性,久已给人忘记了。
这庙中所有神主都标识义士的徽号,庙祀以关公为首。关公在海外的秘密会社成为忠义的表征,似乎和满族人有点渊源。
满人入关,继承明代的祀典,对关公崇祀益隆。在未入关以前,《三国演义》一书已由达海译成满文。(《清史列传》卷四:“达海……奉(太祖)命译《明会典》及《三略》(在天聪以前)……六年三月,详定国书字体,六月卒。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其时小说和兵书都是满人翻译的对象,《三国演义》的英雄事略,亦是满人学习作战的参考凭藉。顺治入关以后,对关公更加重视:
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甲午遣官祭关帝君。(《实录》卷一六)
三年复祭。(《实录》卷二六)
九年,于解州关圣庙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山西通志》卷一六七《祠庙》)
清人似乎利用关圣忠义勇敢牺牲的精神来鼓励军队加强“巴图鲁”的战斗力量。历代对关帝都加上封号,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书“义炳乾坤”匾,悬于解州庙殿内。乾隆三十三年加封灵佑;嘉庆十八年加封仁勇;道光八年加封威显;咸丰二年加封护国。可见有清一代对关圣的隆典。
满族人家供奉神板(在正室西墙高处),所供之神是关圣、马神、观音大士三神,但空其位(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坤宁宫中每日朝夕分祭之神,朝祭有三:(一)释迦牟尼,(二)观世音菩萨,(三)关圣帝君(孟森《明清史论丛》页五一四)。其《邺河(叶赫)伊拉里氏跳神典礼》跳大神所祭者即为关帝(见《启功丛稿》页一七七)。满人把关公与佛祖、观音并列。北京雍和宫(喇嘛庙)其中亦有关帝殿。由于自万历以来关公已被公认为伏魔圣君,故特别被重视,道教、佛教都和关公拉上关系,道教经典里,居然有《关圣帝君本传年谱》收入《道藏辑要》之中。
时代愈后,捏造的传说越多,越来越复杂,关汉卿决没有想到他所突出的关羽,足迹竟能遍及海内外,连我国新疆、蒙古亦有关帝圣迹出现。西方学人近时引出关公热来,有人筹措一笔基金欲专为关公庙宇作调查工作,华人足迹所及之地,几乎无不有关帝庙。我看过李福清(B. Riftin.)写的《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一文所述,其传播之广,令人吃惊,关学在四裔,逐渐为人所注意,已有点像“红学”了,真是一门无中生有的学问。
新加坡五虎祠的“义士”观念,自然亦是受到关公的影响,所以,我在此再作一点补充。
附注:
可参看《亚洲文化》第十八期,庄钦永《新加坡社公廟神主考》,一九九四年六月。
关圣与盐
我于一九八一年参加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接着于山西各地作一个月的漫长旅行,跑了许多地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解县瞻仰关帝庙。该庙规模宏伟,一座古庙几乎等于一个城池,周围古柏苍翠,主殿名崇宁殿,高三十米,树立蟠龙柱子共廿六根,真是“海涵地负”,气象万千。他出生地的常平村去运城南二十五公里,那里又有关帝祖祠,亦有崇宁殿和娘娘殿,祀关夫人胡氏及其祖先。
我在运城住过一夜,记得年轻时暗诵洪亮吉《出关与毕侍郎(沅)笺》写他展视好友黄仲则(殡于此地)句云:“朝发蒲阪,夕宿盐池,阴云蔽亏,时雨凌厉。”我于盐池参观碑刻的时候,天气阴霾,无精打采,寒风习习飘客衣,不免与稚存有异代萧条的同样惆怅与郁结。一九九三年十月号《明报月刊》忼烈兄大谈关羽。我的另一外国朋友俄罗斯的李福清,他专门研究关公传说,写了不少文章,我问他有无到过解县?他说没有。其实关公起家全靠显威灵于其家乡的盐池,现在让我试作一点补充。
运城在宋代是一个重要产盐区,其时和安邑同属解州管辖,著名的“解盐”即产于此。《宋史·食货志》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引池而成者曰颗盐……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宋真宗乾兴初,计岁入二十三万缗。一九八七年,在安徽宿县出土一方宋苗正伦墓志,其中有一句话说:“仁宗朝,三司荐公监解州安邑县之盐池,盐利富饶,号为天下最。”(影本见安徽《文物研究》第五辑)可见解盐出产量的丰富。
关公自汉季至隋,被人冷落了许多年。到文帝开皇十二年十二月,忽然与天台智者大师拉上关系。时智者在荆州当阳的玉泉山准备建寺,他在大树下入定,乃有具王者威仪的美髯公和一位秀发青年出现于面前,愿意驱役鬼神,助他立庙来护持佛法。七日以后,师出定,居然巍峨焕丽的栋宇亦落成了。南宋僧人志磐在《佛祖统记》卷六有绘声绘影、离奇怪诞的描写(《大正藏》四十九册页一八三)。这即是《三国演义》中“玉泉山显圣”故事的由来。

这次旅行,可写的题目甚多,未遑下笔。日前忽接俄罗斯李福清教授自台湾来信,告知他正在编写关帝文献目录,令我联想起玉泉山和关陵,因草此文,写出我观察所得的一些看法,他旅华时足迹遍及南北,惟未知曾到过当阳否?
谢客与驴唇书
雁荡、武夷、丹霞是同一类型的名山。武夷以清邃胜,雁荡以奇伟胜,丹霞与之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和雁荡山结过两度游屐因缘,首次是从天台来乐清,第二次则从温州再探大龙湫。今之温州本汉会稽东部,晋太宁中于此置永嘉郡(《元和郡县志》)。由于谢灵运而著名,故东坡句云:“能使山川似永嘉。”谢灵运的名字和永嘉是分不开的。谢灵运于刘宋永初三年出任永嘉太守(他有《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到郡初发都》一诗记其事)。肆情于山水,他期望“资此永幽栖”,果然留下了许多好诗和胜迹。温州城内的谢公宅、江心亭即因为他的警句“池塘生春草”、“孤屿媚中川”而来的。他的祖居始宁墅在会稽(绍兴),他复喜欢和高僧辈历游嶀、嵊名山,在浙东都有他的足迹(昙隆就是其中一位。见他写的《昙隆法师诔》)。他究心佛乘,《辨宗论》便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名作。
谢客的学问是朝多方面发展的,长期以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题目。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温州市举办“谢灵运与山水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在发言中指出谢客的学识最特出的是他对梵典梵文的认识与学习精神。他的著作有一篇叫做《十四音训叙》,讨论梵语字母的文章,本已失传,幸得日僧安然在《悉昙藏》一书中几处引用宋国谢灵运的零碎说话,可窥见一斑,有趣的是他谈及佉楼书。他说:
……胡书者,梵书道俗共用之也。……胡字谓之佉楼凿,佉楼凿者,是佉楼仙人抄梵文以备要用。譬如此仓、雅、说字,随用广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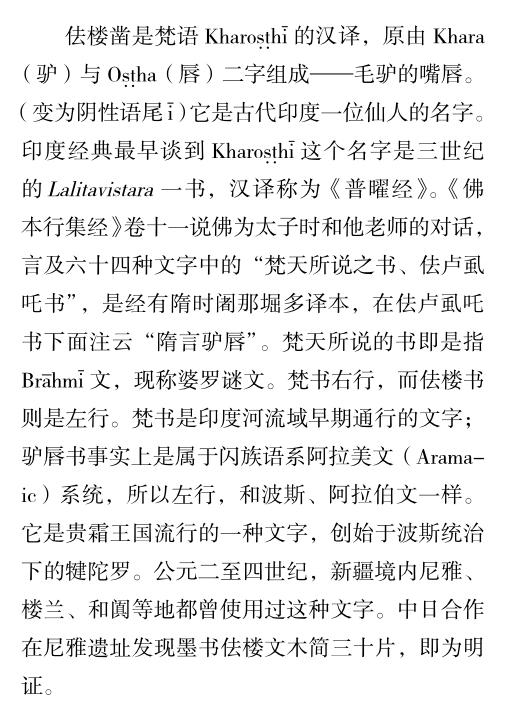
把Kharo译作佉楼,现在看来,应以谢灵运为最先,以后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唐吉藏《百论疏》、玄应《一切经音义》)等都沿用着。谢灵运何以懂得梵文?据说是得自慧睿。《高僧传》说:“睿师曾行蜀之西界”,后“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音译诂训,殊方异文,无不……晓……俄又入关,往什公(鸠摩罗什)咨禀。后适京师,止乌衣巷。”安然引谢灵运云:“诸经胡字,前后讲说……故就睿公是正二国音义。”这证明慧睿南来居住于乌衣巷,谢即从他问业。可见谢公的梵文知识是有渊源的!《普曜经》在三国蜀时有译本,现已失传,只有“隋译”,慧睿到过蜀地,很可能亦见到蜀译本。西方学者研究驴唇书的人很多,大都采用唐时僧人的著作像《法苑珠林》之类,《珠林》资料的来源,以前我在印度曾著文讨论(参看拙著《梵学集》页三八〇)。国人专门研究佉卢文的有林梅村氏,翻读他的新书《沙海古卷),他在导论中说道:“我国旅行家、僧人、翻译家的著述译述中,留下不少有关佉卢文的记载,最早提到这种文字的是梁僧佑(按应作祐)《出三藏记集》的《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他没有注意到谢灵运之说,故认梁僧佑为最早,那是不对的。
记得熊十力书中非常反对人学习梵语,我则认为多懂一点他国语文,自然比不懂的好。以谢公的地位,尚有余暇向僧人请教,研究一点西域语文,进而加以论述,这种求知精神很值得后人的尊敬。从世界关于驴唇书的记录来看,印度的《普曜经》之外,就现存资料而论,谢灵运是中国人中谈及驴唇书的第一人,又是第一个懂梵文的中国诗人,光这一件事就很了不起,是值得加以表扬的。
《诗品》记谢公幼时名曰客儿。以前我在香港古玩铺见过青瓷杅底部隶书“客儿”二字,该物尝在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出,或即谢客遗物。原物现不知下落。
温州因谢客而著闻的事情很多,温州杂剧、书会的历史尤为举世所瞩目。温州城北瓯江中一个小岛,上有禅寺,因谢诗而名为中川寺,元时称江心寺。早在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已曾演出有名的《祖杰戏文》,情节震动一时。祖杰即是江心寺的僧人,他的故事详见周密的《癸辛杂识》和刘埙写的《义犬传》,这可能即是宋元间所谓“九山书会”在当日上演的名剧,后来演变成为昆剧的《对金牌》。由于江心寺一名取自谢诗故附带提及,以供谈助。

武夷山忆柳永
武夷山是横亘赣闽两省的“屋脊”山脉,纵横五百里。萧子开的《建安记》说:“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他引用陈时顾野王的话:“谓之地仙之宅”。末云:“半岩有悬棺数千。”(见宋本《太平御览》地部卷四十七)不免有点夸大。据实地调查,九曲溪的三曲四曲为现存悬棺集中之处。武夷地区近年曾有一批船棺出土,成为该地吸引游人瞩目的新事物,说明武夷是古代东南绵延到长江一带悬棺葬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陈书·顾野王传》云:“年十二,随父(烜)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他年轻时候,亲到武夷游览,言之凿凿。
先代地志已注意到悬棺的重要性,为今日人类学家导夫先路。
武夷山因武夷君而命名,武夷山君,始见于《史记》:《封禅书》中说当日“用干鱼祭祀”,故有人给它别名为“汉祀山”。流行南朝的地券,广东出土很多亦称作武夷王(像宋元嘉十九年【四四二】地券,上面记着:“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参看《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图五八)。后代的地券,或称为“地主武夷王”,可见顾野王谓武夷君为“地仙”一说之有来历,地仙与地主,正可互证。
以上把“武夷”名称的历史说了一番。我游武夷到崇安,知道朱熹父亲朱松的墓在中峰寺之后,中峰山是武夷山群之一,“一峰奇秀,特出众山之表”。亦名寂历山,因松诗句“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而得名(见何乔远《闽书》)。中峰寺即在山麓。唐景福元年(八九二)建。寺在今崇安县东三十里的上梅里,这是柳永的故乡。柳永一生留下来的诗只剩三首,有七律咏中峰寺,句云:“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这诗可能是他少年时在崇安所作的。他的词集里面,《巫山一段云》五首,中有“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几回山脚弄云涛”几句,有人怀疑是咏武夷山,但很难确定,因为五首是联章为颂寿之作,言及“萧氏贤夫婦”不知是谁人?又句云:“一曲云谣为寿”,使我联想到敦煌石室所出的唐季五代初年写本的《云谣集》一书。
这里真的是屈大夫的故里吗?记得有人曾向题匾的郭老提出三项质询加以否定。我们不妨考查这一说的来历。《水经注·江水》说道:
(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谓此也。
所记十分确凿,袁山松是晋时宜都的地方官,所著《宜都山川记》经郦道元引述保存下这一段可贵的记载,他是柳宗元以前最有成就的山水游记作家,以擅写“挽歌”著名,他与桓玄来往讨论“啸”的美学意义的书札,在当时播为美谈(文见《艺文类聚》卷十九)。他又说道:“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照他所说,秭归一名取义于阿姐回归,却招来了郦道元的反驳,认为“恐非名县的本旨”。
现在考之殷代卜辞,屡见“伐歸”的记录,归是地名,即古代的归子国。这些可以证明汉末经学家宋忠(衷)“归即夔”之说的可信性。归子国殷代已存在,则山松“来归”之说,自然属于无稽。但秭归之为屈子故里,晋时尚存有许多遗迹,这一说事实应该溯源于晋代,绝不是后来的杜撰。
此地向来有不少楚国先王的陵墓。唐初魏王李泰的《括地志》说:熊绎墓在秭归县(贺次君辑本),宋陆游《剑南诗稿》:“归州光孝寺后有楚冢,近岁或发之,得宝玉剑佩之类。”早已有人盗掘。近年于秭归东七点五华里的鲢鱼山遗址掘出大量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陶器,商代遗物以及西周至战国的遗址,在西陵峡附近发现且近百处,因此,考古家认为商人兵力自应及于三峡口夔子国地方,归为殷代方国是可能的事。虽然熊绎的丹阳正确所在尚有许多不同说法,但春秋时候,夔子熊挚由于不祀祝融和鬻熊而为楚所灭(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从秭归地区出土兵器之多,可为佐证。“生长明妃”的香溪镇,亦出了一把越王州勾剑。归子国西境远及于巫山县,近时在三峡探测,楚文化最西可至云阳的李家坝,这是考古最新的结论。
谈到大溪文化,除了花样丰富的彩陶纹样和形形色色的陶器之外,以距今约六千年的杨家湾新石器时代大量出土共一百七十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最令人瞩目,揭开了原始文字的序幕。
杨家湾遗址位于西陵峡的南面宜昌县三斗坪村,北临长江,南依黄牛岩峰。袁山松描写此处风景:“南岸重岭叠起,如人负刀牵牛。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迳信宿,犹望见此物”,故有“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之叹。杨家湾遗址达六千平方米,文化层厚达三米以上,乃有这样重要的刻划符号出现,为文字起源提供新的篇章。我很幸运,翌日能够在宜昌博物馆接触这批实物,亲手摩挲,眼福不浅。有的与纺轮花纹很接近,有的记号似崧浦、吴城,可说是远古夔越先人遗下的手迹。这些记号比殷墟文字早二千年,而且出于长江中游,足见文字起源的多元化,堪与山东丁公村各地相媲美,弯曲、迅疾的笔势,似乎在表演出古文明的节拍,有些很熟悉,有些很陌生,还有待于深入的探索。
我在秭归城游览,时间甚暂。可惜天色已晚,大家再没有勇气到屈原庙去走一趟。回到舟中,我写了一首七律:
月黑能来问水滨,当年战伐迹犹新。
尝从骚赋开天地,尚有丰碑动鬼神。
江汉寂寥云漠漠,女媭婞直话申申。
大溪文字仓沮业,点缀河山在比邻。
目前三峡工程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已引起许多抢救与保护文物的呼吁。据说工程完成以后,水位将上升一百七十五米。作为屈原故里的秭归,地面及附近一切古迹,将全部淹没。万一屈子魂兮归来,临睨故乡,不知作何感想!人为的沧海桑田,恐怕无法制止女媭婵媛的眼泪和解去她绵绵无尽的惆怅。
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
从汕头市乘小艇向东行约三小时即抵达南澳,这是一个蕞尔小岛,面积只有一百零六平方公里,在历史上却对东南沿海地区起了重大的桥梁作用。眼见逝川白浪滔滔,不知淘尽几多英雄人物。被浓雾锁闭着的危峰果老山,俯瞰汪洋无际的碧海,猎屿、青屿环抱有如襟带,镇慑云、深两澳的交界,横跨南北的雄镇关,气势雄伟,不问而知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形胜地。远在郑和下西洋时候,南澳的名字已登上航海针路的记录(见黄省曾《西洋朝贡录》)。屹立雄镇上的石城为明时海寇许朝光所造,嗣后吴平、林道乾出没外洋,都窃据其地,故福建巡抚刘尧诲奏请“为闽、粤两省久安之计,必先治南澳,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兼领漳、潮二府兵事”。于是遂有南澳镇副总兵之设,肇始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当日即物色曾供职于卫所而富有海防经验的人物来充任。首任副总兵是北直昌黎人白翰纪,由雷州卫指挥升任;第二位是晏继芳,来自漳州卫,饶平风吹岭上有他的摩崖“闽广达观”四个大字;第四任是倡修《南澳志》有名的于嵩,他由杭州卫指挥来此。深澳的碑廊,尚保存有他在万历十一年立的《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碑文,这时关公尚是侯爵,还没有升上帝座。深澳又有规模宏大的郑芝龙坊,芝龙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十二月莅澳任总兵,十七年升为福建都督,以后即由他的部将陈豹接任,陈于康熙元年降清。陈豹前后镇守南澳,与金门、厦门首尾为犄角之势,奉晚明正朔历二十余年之久。在明、清易代之际,沿海军事部署全在他控制之下。郑成功出师北上,是以南澳为基地,作为跳板。请看下面几桩重要的大事: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忠孝伯行驸马都尉事郑成功莅南澳,收集士卒数千人。
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监国鲁王自金门移跸南澳,越年幸金门。
顺治十五年延平王郑成功会师浙海,鲁王在南澳。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全师北指,张煌言抵瓜州,成功攻镇江,克之。迁鲁王于澎湖。
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一)三月,陈豹降清。杨金木起为镇将,数月去之。郑成功部吴升,挂观武将军印,旋由杜煇继任南澳总兵。
康熙二年十一月,清总兵吴六奇招降杜煇,授以清广东水师提督。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入台湾,郑氏亡。
陈豹被迫降清,据说起于郑成功的猜忌,南澳长官相继叛去,郑氏自戕其臂助,终告失败。吴六奇《忠孝堂文集》载有招抚南澳杜(煇)吴(升)两镇文书多篇,他委实花了不少“统战”工夫。当日潮州方面六奇任饶平镇总兵,康熙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启丰嗣职,另一儿子启镇两度出任黄冈协镇,在柘林的雷震关上有康熙十九年巨石刻碑:“启镇招抚各岛伪镇官兵人民数万在此登岸”的记录,字大如斗,令人触目惊心。可见吴六奇一家在当地举足轻重,影响之大,近年大埔湖寮出土《六奇墓志》更可说明这一事实。
清人入关,统治能力本来非常薄弱,对沿海施行“迁界”政策,更是怯懦无能的表現,受害区域北起山东,南迤江、浙、闽、广,“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生民涂炭,庐舍为墟。由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先后五次颁布海禁苛令,历时二十九年之久。整个海岸线变成“荒原废垅”,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荷兰人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已占领澎湖,立足于台湾共四十年,开辟了闽南和海上商业路线。由于迁界的自我封锁,对外完全隔绝,造成中国对西方认识的阻碍与误解,拖缓了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的抬头。

我游南澳,参观“海防史博物馆”陈列的展品,馆方介绍我看一幅有关南澳总镇府署金漆贝雕画屏风的放成十六英寸彩色照片,整个屏风宽六米,高三米,上面绘制三面环海的南澳镇城内当日的主要建筑和郑芝龙坊贵丁街的仪仗队,亭阁中官兵饮宴,乐坊演唱景象,镂金着色,光彩夺目。屏风背面书写康熙三十八年孟夏曾华盖撰写的《麟翁周镇台寿序》,文长一千二百字。是时海宇敉定,南澳镇总兵是直隶龙门人周鸿昇。为庆祝他的六十寿辰,故制造这幅屏风,表扬他的军功劳绩。撰文者曾华盖是海阳人,康熙九年庚戌进士(不是武进士),著有《鸿迹猿声集》等,广东图书馆藏有其书。
这类的屏风制作,在十八世纪非常盛行,欧洲人称之为印度科罗曼多(Coromandel)式。荷兰东印度公司惯于经营这些漆屏运往欧洲,印尼的万丹(Buntan)即其贸易站。当时徽州、福州都出有名的雕刻家(荷兰国家博物馆藏中国款彩的《汉宫春晓》六曲屏风,即其著名之一件,详周功鑫所著论文,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下册),这是十七世纪以来中外交流习见的工艺品。赠送屏风颂寿的风气,清代非常流行,我们看《红楼梦》贾母八十大寿,亲朋即馈以十六架围屏祝寿。这一南澳周鸿昇总兵祝寿屏风照片,原由法国工程师雅克·马兰德君所赠,南澳当局要我托人向其商量转让,他没有同意。其实,法京博物馆尚有同类的屏风多件,不是十分稀奇的东西。南澳孤悬海外,由于陈豹扼守其地,没有受到清人“迁界”的破坏,这屏风镂刻当日该镇关隘、街道、庙宇、各种风物形形色色的现状,清初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记得抗战胜利之翌年,我回汕头主持修志工作,在揭阳黄岐山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物。我后来携带陶片到台北“帝国大学”,和日本考古家金关丈夫、国分直一两教授交流探讨,那时陈奇禄兄还是学生。日人未完全撤退,值魏道明当政,草山仍是一片荒凉,百废待举。我又在南方资料馆搜集有关资料,顺便到屏东南部的潮州郡调查,方才知道该地住民全部都说客家话,不懂潮语。后来于新竹县图书馆见到一本日文书名曰《呜呼忠义亭》,是记述为清室殉职的客属人物,然后了解施琅入台,继而助清兵平定朱一贵的多是客属人,而说潮语、从郑成功,来自海阳、潮阳、饶平的人们,在清代后期几乎全被视为反动而归于淘汰。
我在南澳听说近时有数万台湾人士来此寻根,明末镇总兵于嵩所建的关公庙,粉饰一新,香火顿时复旺盛起来。郑成功在台时,藉南澳为跳板,进兵江南,潮人随他迁台的甚多,想不到几百年后彼此间历史关系的葛藤仍未切断,宗族伦理观念之深入人心,正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回想我为研究历史初次去台旅行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时序的推移,许多年轻后辈逐渐据上高位,衰病的故交相继凋殂,不是“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而是旧日的山上大起了华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瞬即逝的历史事实,还值得回头一顾。
本年八月,“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将在南澳举行,来函邀请参加,不能分身前往,因草此文,聊当芹献。
(选自饶宗颐著《文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