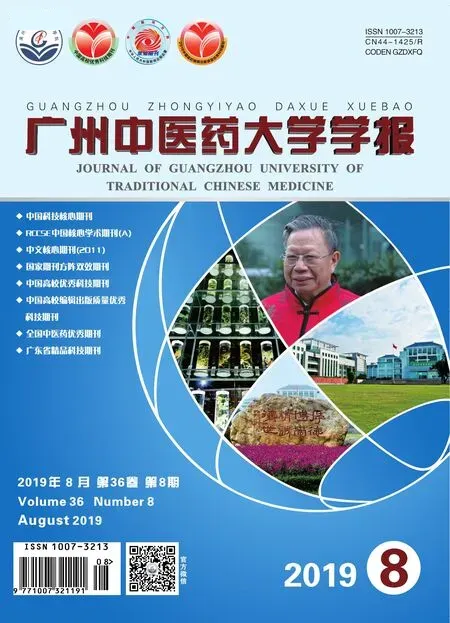岭南中医对肾病的辨治特色
2019-03-18张礼财汤水福
张礼财, 汤水福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第一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405)
岭南中医为我国中医最具特色的地方流派之一。明清时期,随着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中医有了较快的发展;至民国时期,岭南中医发展达到了高峰。据统计,历代广东中医药文献约有408部,其中明代以前65部,清代230部,民初113部;历代岭南医家大约有953人,其中明代以前74人,清代429人,民初有450人[1]。
传统中医虽无明确的肾病学分科,但对于肾系疾病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较丰富的治疗经验。根据肾脏疾病的临床症状,多将肾系疾病归于“水肿”、“关格”、“腰痛”、“虚劳”等范畴。岭南中医作为我国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肾系疾病的治疗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具备鲜明的地方特色。以下通过总结以广东省为代表的历代岭南代表性医家对肾系疾病的认识与治疗特点,特别是通过对广东省近现代主要中医肾病名家的治疗经验进行整理,以总结岭南中医治疗肾病的基本特点。
1 岭南中医继承中原医学对肾病的辨治思路
岭南中医是发源于中原文化的医学体系。历史上,中原士民经过数次南迁,在此过程中把中原文化带入岭南地区,中医学也随着此过程而传入岭南。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其出身于江南士族,晚年隐居于岭南罗浮山,在岭南医学史上居重要地位。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的《治大腹水肿方》,多选用峻下逐水之药治疗水肿。清代医家何梦瑶,其代表作《医碥》将水肿称为肿胀,对于水肿的治疗,强调“治水当分阴阳”,书中还引用了《金匮要略》对于水肿的分类及方药。
从岭南医家的相关论著中不难看出其受中原医学影响的痕迹。如近现代岭南著名温病学家刘赤选,认为水肿与肺、脾、肾有关,特别是与脾肾的关系最为密切[2]。著名老中医张阶平提出治疗肾炎水肿的“治水七法”[3],其中利尿、消导、发汗三法,实乃“开鬼门,洁净腑,去菀陈莝”的具体体现。著名老中医何汝湛,精于《金匮要略》,擅长于肾系疾病的治疗,基于《灵枢·五癃津液别论》中“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论述,临床善用行气利水法治疗尿毒症[4]。何炎燊基于叶天士“邪干阳位,气壅不通”的理论,于《黄帝内经》治水三法之外,善用清肃上焦法治疗肾炎水肿[5]。上述医家虽非肾病专科医生,但对于肾系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上述医家均精通于中医经典著作,其辨治肾病的思路明显受中医经典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各中医院校成立之后,各地中医院先后成立了肾病专科,中医开始有了肾病专科医生。著名的岭南中医肾病专家如叶任高、洪钦国、杨霓芝等,其对肾病的辨治思路虽各有特色,但一致认为慢性肾病的病机为本虚标实,这与中原医学对于本病的基本认识相一致,亦体现出岭南医学继承性的一面。
2 岭南中医开创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肾病
明清以后,岭南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也主要经海路进入我国。岭南濒临南海,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医学的地区之一。中西方医学的碰撞,使不少岭南医家尝试把西方医学知识运用到中医肾病的辨证治疗上来。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先驱黄省三,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等知识解释肾系疾病,治病强调专病专方,著有《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法》一书,并创制“黄氏肾脏炎肾变性有效汤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
著名肾病学家叶任高,师从黄省三学习中医治疗肾病,成为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叶任高通过临床观察,认为慢性肾炎的血尿、蛋白尿、高血压、肾功能减退与中医的证型有一定的关系,可将其作为中医辨证依据之一。对于肾病综合征采用激素治疗的患者,叶任高分阶段运用不同的中医治法与激素配合,减少了激素的副作用[7]。黄春林对于肾病治疗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临床用药多结合现代中药药理知识,主张根据慢性肾病的分期及并发症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中医治法[8]。杨霓芝主张中医辨证与实验室检查相结合,认为患者尿液检查结果以蛋白尿为主者宜以益气健脾补肾为主,而以血尿为主者当以养阴清热活血为主;肾脏病理检查结果以增生为主者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以硬化为主者当以活血化瘀为主[9]。由此可知,在中、西方医学的接触过程中,岭南肾病医家积极吸纳西方医学知识,拓展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在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肾病中作出了新的尝试。
3 岭南中医对肾病的辨治特色
3.1 重补益脾肾 中医认为肾炎水肿与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慢性肾病虚实夹杂之病机已成为医家之共识,其中尤以脾肾虚损为常见。而岭南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气候炎热潮湿,湿重则碍脾。独特的气候特点,致使岭南人多见脾气虚弱兼痰湿的体质特点[10]。脾为后天之本,脾气虚损,久则必然及肾。所以岭南医家治疗肾病尤重补益脾肾。如刘赤选论水肿之治疗,认为本病初起多伤脾,迁延日久必伤肾;张阶平“肾炎水肿七法”中包括健脾、补虚、温补三法[3],并自拟“虚肿方”、“肾损方”,分别用于治疗肾炎水肿及尿毒症[3];梁端侪善用人参培本固元以治疗慢性肾炎[11];国医大师邓铁涛认为肾炎早期表现为脾虚湿困,中后期表现为脾肾阳虚,后期表现为肝肾阴虚,而脾虚是本病的共性,主张治疗过程中应注重调理脾气,其所拟“消尿白方”及“尿毒症方”亦重在补益脾肾[12];林品生对于慢性肾炎水肿的治疗,十分推崇张景岳“温补即所以化气,气化而愈者,愈之自然,攻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愈者,愈之勉强”,主张用温补法治疗慢性肾炎,并把“扶正”的观点贯穿于治疗的始终[13];梁剑波精通东垣学说,临证治疗慢性肾病尤其重视脾胃功能的调治[14];叶任高认为慢性肾衰存在着虚、浊、瘀、毒四大病理机制,以脾肾虚衰,浊毒潴留为病机关键[15];黄春林治疗慢性肾病强调“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用药重视调补脾肾,并提出调脾七法[16];沈英森治疗肾炎水肿亦强调健脾补肾以固本[17];刘恩祺认为蛋白尿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肺、脾、肾虚为病之本,尤其是气虚[18];杨霓芝认为慢性肾炎为本虚标实之证,而本虚以脾肾亏虚最为常见,故治疗尤重补益脾肾之气[19]。此外,李俊彪、罗仁等岭南中医肾病名家对慢性肾病的治疗均无不重视补益脾肾。
3.2 重清利湿热 岭南气候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春夏多雨,天热地湿,故《岭南卫生方》提出“岭以外号称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而患不降;地湿故阴常盛,而患不升”。肾系疾病又多因脾肾功能失调。脾主运化,肾主水。脾肾功能失调,则外湿易感而内湿易生。湿郁化热或湿热相熏蒸,故成湿热之候。岭南医家基于当地气候特点,认为湿邪或湿热之邪是慢性肾病最重要的实邪之一,故临证治病无不强调祛湿药的运用,其中尤以清利湿热之药为多。张阶平治疗肾炎蛋白尿提出“湿热不除,蛋白难消”的理论[3],足见其对清利湿热之重视。刘仕昌治疗慢性肾炎尤其重视湿邪对于疾病的影响,强调湿与热合,胶结难解,使病情缠绵[20]。黄春林治疗慢性肾病的“调脾七法”中有清热利湿和温阳化浊二法以治疗湿热及寒湿之邪[16];杨霓芝治疗慢性肾炎也十分重视湿热之邪的致病作用,认为湿热是慢性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临证强调清热利湿之法的运用[19]。刘恩祺、梁宏正、李俊彪等医家均强调湿邪是慢性肾病邪实之一,认为临证当在扶正的同时兼顾祛湿,方能获得较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因岭南独特的气候特点以及慢性肾病的病机特点,岭南中医对于运用清利湿热法治疗慢性肾病已基本达成共识。
3.3 重通腑泄浊 慢性肾病发展至后期,脾肾由虚及损,由损及败,痰湿浊毒之邪充斥三焦,变证蜂起。叶任高治疗慢性肾衰曾于方中加用大黄,认为大黄可清热解毒、行瘀通便,具有推陈出新、安和五脏、延缓肾功能进展之功,尤其对于年轻体壮者效果尤佳[7]。洪钦国治疗本病本着“祛邪以扶正,泄实为先”的观点,根据《素问》“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认为糟粕化成粪便而排出是脾胃降浊功能的延伸,故临床多喜用大黄、虎杖以通腑泄浊,使邪有出路[21]。黄春林治疗本病亦善用通腑法,并根据慢性肾病分期的不同,配合不同的治法,如氮质血症期以健脾补肾法配合通腑化浊,尿毒症期以温阳化气法配合通腑降浊[8]。骆继杰认为人体脏与腑之间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治疗上可通过治脏病以治腑病,治腑病以治脏病,故治疗慢性肾衰强调“通腑健脏”的思想,临床上灵活运用生大黄、熟大黄或加用润肠通便药以达到通腑之功[22]。杨霓芝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多配用大黄胶囊通腑以泄浊,或配合灌肠法以增加通腑泄浊之功[23]。尽管不少岭南医家都重视通腑法的作用,然而他们均强调慢性肾病以正虚为本,所以通腑不可使排便次数太过,以每日排便2~3次为宜,太过反而于患者不利。
3.4 重活血化瘀 慢性肾病多脾肾亏虚,气不行血,因虚成瘀,加之病情缠绵,久病则入络。而岭南之地炎热多雨,患者多湿多痰,痰湿阻滞气血,可因滞成瘀;痰湿郁而化热,热蒸血脉,亦成瘀血。故岭南肾病医家尤重视活血化瘀法的运用。刘仕昌认为慢性肾炎的治疗切忌一味扶正或只顾攻邪,需在补脾肾的基础上,加用益母草、郁金、丹参等药以起活血化瘀之功。林品生用药力主精专,尤善用益母草,对于慢性肾炎多重用益母草配以黄芪,再结合其自拟固守丸或其他益精补虚、益气养血之品进行治疗[24]。叶任高从西医病理出发,结合临床经验,认为慢性肾病自始至终都有血瘀的存在,并认为血瘀是本病持续发展及肾功能进行性衰竭的重要原因[25],其自拟“肾衰方”采用大黄、丹参、当归、赤芍配伍以获活血化瘀、改善高凝状态、延缓肾功能衰竭之功[26]。杨霓芝治疗慢性肾炎以擅长运用益气活血法著称,认为慢性肾炎的邪实虽然有瘀血、湿热、湿浊之分,然而以瘀血最为关键,并认为气虚血瘀是慢性肾炎的基本证型,故主张将活血化瘀法贯穿在慢性肾炎治疗的始终[19]。洪钦国重视祛邪以扶正,其中活血化瘀是最常用的祛邪法之一。沈英森、刘恩祺、李俊彪、罗仁等在治疗慢性肾病的过程中也均强调活血化瘀法。
由上可知,治疗肾脏疾病时对于活血化瘀法的重视程度,年轻一辈岭南医家要强于老一辈医家,而肾病专科医生的重视程度又强于非肾病专科医生。
3.5 善用岭南地方草药 岭南草木蕃盛,可用药材资源丰富。历史上有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赵寅谷《本草求原》、肖步丹《岭南采药录》、胡真《山草指南》等一批岭南草药医家及本草论著。岭南医家在治疗肾病时,亦多配用地方草药。如邓铁涛运用三叶人字草治疗血尿,运用珍珠草、小叶凤尾草治疗慢性肾盂肾炎;洪钦国治疗肾病善用积雪草、肾茶等;梁宏正家学渊源,其治疗肾病尤喜用岭南特色草药,如用三白草、珍珠草、肾茶、葫芦茶、塘葛菜等利水通淋,以磨盘草、金樱根治疗腰痛、耳鸣、遗精,用山地稔、大血藤、花生衣治疗肾性贫血,用马缨丹、小飞杨治疗皮肤瘙痒[27]等。除此之外,岭南草药如五指毛桃、牛大力、火炭母、布渣叶、救必应等均为岭南中医治疗肾病的常用药。
总之,岭南中医渊源于中原医学,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本着中医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治疗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中医治疗肾系疾病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岭南中医对于肾脏疾病的认识及治疗有继承于中原医学的一面,如对于慢性肾病基本病机的认识、对于脾肾的重视等均与中原中医对于本病的认识相一致。同时,因岭南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岭南中医治疗肾病积极吸纳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并将其运用于中医肾病的辨证治疗的实践中。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特点以及岭南人独特的体质特点,促使岭南中医治疗肾病尤重视补益脾肾及活血化瘀。岭南草木蕃盛,药用资源丰富,岭南医家对于地方草药的运用有悠久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岭南医家将岭南草药运用到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成为其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