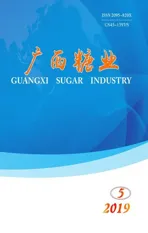中国糖史之三
——建国前蔗农与糖厂、土糖与机制糖的关系及抗战前糖业恢复
2019-03-18陈世治蓝艳华
陈世治,蓝艳华
(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316)
0 前言
不同的糖业加工企业类型,与农户有着不同的关系。第一种类型是蔗糖业中的大型机器糖厂和农户的直接关系。这一类型所显示的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变化。第二种类型,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小糖寮,其产品仍然是农民自产自销,农民将土糖卖给糖户,或卖给糖栈。至于机器糖厂收购土糖来精制白糖,是土糖经营商和糖厂的关系,与农民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种是在抗战中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小型糖厂。其生产水平比糖寮稍好,但出糖率和产品质量仍然很低。这类糖厂与大型糖厂的区别是:只向农民收购甘蔗,不一定负责供应良种和化肥;而且与大型糖厂争夺原料,向蔗农拼命压价以盘剥农民。
1 蔗农与糖厂的关系
1.1 随着新式糖厂的建立,旧的糖业流通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的蔗农,要自己生产蔗糖,再挑去圩市出卖;或者将产品卖给糖户、糖栈,流通环节多,除了受到多渠道的盘剥,还加重了交易成本。上世纪30年代所建的新式机器糖厂直接向蔗农收购甘蔗,使向糖厂供应甘蔗的蔗农脱离了手工业,减少了流通环节与蔗农的交易成本。如在顺德新蔗区,豪绅收购农民的甘蔗再交给糖厂而盘剥农民,后来广东省合作事业委员会组织中小农民建立合作社,直接接受糖厂的贷款,堵截了豪绅的中间剥削[1]。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的糖业统制政策,虽然是广东地方政府与商争利的措施,但它打击了洋糖的倾销和走私,有利于国内制造的糖品在境内的销售。
陈济棠实行糖业统制,营造一个庞大的,以商业资本和军事权利相结合的营销渠道,即以十大营销商来实行蔗糖专营,以销售的垄断将流通领域的大部分利润落入军事集团的口袋,另一部分落入营销商的口袋,也有利于实现糖厂建立以后的销售。以军事权力打击蔗糖走私,有利于广东本地的食糖销售市场[2]。
1.2 糖厂以农业贷款方式向农民供应良种和化肥,使农业生产资金流通方式发生变化
民国期间的调查表明,糖寮由蔗农按所出的牛或其他生产资料或劳动力进行组合。一间糖寮组合大约80~100亩的蔗地作为原料基地才能开榨,规模很小。这表明,从明清到近代的糖寮是与农民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去广东的蔗农“虽知种蔗有利,但是资财不裕也很难经营”。在甘蔗生长期间,“蔗栏”或糖栈向农民出借高出市场价格1倍的蔗种、肥料,及支撑甘蔗生长的竹木、缴纳地租用的现金,加上“蔗栏”或糖栈在收购糖蔗时压低价格,农民还要承受佣金、杂费和低估品等之类的损失,合计起来,“蔗农实际付给蔗栏的利息比月利6分还要多”[3]。
1934年李锡周记载东江流域蔗区的蔗农向糖商借款100元,最后计算借款仅得61、62元。在高利贷的盘剥之下,农民被迫向糖商低价出卖产品,所得连维持日用也难,遑论扩大再生产。大型糖厂在局部地区实行农业贷款制度,不但降低了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门槛,在一定时期内还打破了旧的金融流通方式——普遍存在于民间的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农民向糖厂出卖甘蔗,而不用自己榨糖向糖商出卖产品。陈济棠军阀系统的惠阳糖厂向农民种蔗贷款,糖厂附近的蔗区“平潭马安一带,及平山梁化等地一带,均受糖厂贷款之益。农民所种之蔗,全部照约定价格卖与糖厂”,当地的高利贷和旧的产品购销体制“在平潭、马安一带,已不复存在矣”[4]。
根据记载,1934年的贷款总额为398000元:贷款订约的蔗田,有36000亩分布于番禺、顺德、东莞、中山等县。贷款种植甘蔗,从1934年1月开始,第一期贷出款99200余元,第二期86100余元,截至1934年的第三期贷款还没有结束,广州附近的蔗区贷款种植的甘蔗栽培面积增加了2万余亩。1935年1月到9月间,第一蔗糖营造场贷出款额达659000元,订约的蔗田有33000亩。同期,顺德、中山蔗区的第二蔗糖营造场贷出款额为349000元,而订约的蔗田有16000亩。东莞与惠阳两县的蔗农贷款,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粤分行办理,根据黎献仁的统计,1934年陈济棠集团军阀系统的惠阳糖厂贷出款38万元,计7000余农户,蔗田有3万亩以上。在潮汕平原,1935年政府的糖厂也向蔗农“贷肥豆饼与人造肥”。政府贷款利息只有8厘,比民间借贷低得多,不仅农民踊跃贷款,有不良分子更用不法手段骗取贷款再高息转贷。为了保证真正的蔗农获得贷款,甘蔗营造场后来提高了甘蔗贷款的门槛。如加强贷款过程中的调查程序,营造场安排调查员,由“各农业学校毕业生充任,从事调查及测量蔗农填报之蔗田”,其目的是为了“杜绝虚报滥借款”。
2 土糖与机制糖的关系及其历史启示
上世纪30年代的广东机器糖业,具有近代早期工业化二元模式的特征[5]:糖业机器工业突进式发展,同时并没有摧毁自明清以来就存在的手工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土糖业有了生存空间。这不仅是因为糖厂蔗源不足,要收购土糖作为原料制作精炼白糖,而且政府的糖业统制政策对洋糖倾销、洋糖走私的打击使土糖业有了生机;限制民营资本建立大型糖厂而不限制土糖业的生存,同时机器糖业的发展间接推动了土糖业榨蔗制糖环节的技术变革。
在抗战中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小型糖厂,为了提高榨蔗的效率和能够加工粗茎的爪哇蔗而改用铁制压榨机。动力由牲畜牵引改为机器牵引,制糖方法亦由漏糖而改用分蜜机,遂使产品质量均稍提高,成本亦比小糖寮要低。到1950年,广东省私营糖厂有150家。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在生丝出口不景气的时候,就转而利用缫丝厂的动力生产蔗糖。此外,顺德还有不少专门榨蔗的小糖厂,在1950年小型糖厂74家,大部分使用小型加工机械。这些小糖厂是作为大糖厂的补充而存在的,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雷州半岛甘蔗除了制糖生产的主用途外,也开始了其他用途,如民国26年(1937年)《农声》刊物第209期《徐闻县之糖业》一文中记载:“徐闻人用糖漏收糖,漏内糖液徐徐流下,土人称此糖为‘糖仔’,每漏可得‘糖仔’约1.5公斤,用为蒸酒之用”,这说明糖业制酒从民国初期已开始流行。
在扶持蔗农生产方面,30年代所建的机制糖厂比抗战中或之后发展起来的小型糖厂所起的作用要大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兴产业的制度安排——政府的作用往往是重要的。民国时期如山东溥益糖厂、上海国民蔗糖公司等同类型的企业,在洋糖倾销的打击下失败了——这是因为单个企业在洋糖的倾销和猖獗的蔗糖走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而且也没有广东机器糖业的政府背景。
3 抗战光复时期糖业发展历程
华南甘蔗栽培是经过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广大蔗农在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本地传统技术进行改造和升华的结果。如在运用肥料方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珠三角本地甘蔗栽培,化肥的运用在整个栽培过程中总用肥量仍然未占很大优势,有机肥料和利用珠江冲积土的“上泥之法”仍然唱主角,而有目的轮种绿肥与豆科作物成为重要的改良土壤、恢复种植甘蔗以后地力的一种轮作方式。又如糖业复兴时期甘蔗有性繁殖技术开始出现,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只是当时有性繁殖技术还没有大规模使用。此后,中大农学院的梁光商等专家从未停止过这一研究,对甘蔗有性繁殖技术研究为解放前后的良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3.1 甘蔗栽培业的恢复过程
糖业复兴时期创造的甘蔗表证方式,为20世纪下半叶的甘蔗栽培业所继承和仿效。糖业复兴时期的机器糖厂所采用的工业企业加农户或农场的形式,是推广农业技术的一种先进模式。虽然其并非独创,早在欧美日的近代农业中出现,但这一方式无论在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农业推广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这是近代先进的栽培技术向传统技术渗透的最佳方式。甘蔗表证方式直接给蔗农树立榜样,用最简单的田间试验和最有说服力的经济核算方案展示给蔗农,致使研究室中的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蔗农手中、散播到蔗田之中,在短期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常规农业的转型。
糖业复兴时期的机器糖厂虽然在抗战的烽火中变成废墟或残破不堪。但其与生俱来的一套甘蔗表证方式和农业推广模式却没有在战争的烟火中消失。抗战结束后,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曾经计划引进美国的机器设备,并将在台湾一些糖厂的设备运到广东,恢复昔日广东糖业大省的地位,还计划从台湾等地大规模引进良种和将甘蔗表证方式运用于甘蔗栽培业[6]。客观上这为解放后广东甘蔗糖业的迅速恢复创造了条件。1951年广东糖业公司撰写的《广东糖业调查》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甘蔗栽培业和糖工业,定为近代广东糖业的“新生阶段”,广东蔗糖业伴随全国人民的胜利而走向新生。人民政府大力扶助蔗糖业,公营糖厂恢复发展,1950年广东蔗糖业由衰退转变为欣欣向荣,糖价上腾而趋稳定,蔗糖生产情绪高涨,顺德、东莞两大糖厂复工,生产任务超额完成,1951年又修市头、揭阳两大糖厂,处处表现人民糖业之前途光辉万丈。
抗战前,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品种结构仍以竹蔗为主。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引进的甘蔗良种,至1951年已繁育5000~6000亩,这些蔗种在解放初期的甘蔗良种繁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20世纪上下半叶新旧时代更替过程中,一度释放了生产力,糖加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糖业是广东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机器糖业带动了甘蔗栽培的发展,广东糖业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7]
3.2 机制糖厂的复建过程
抗战时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顺德等一批重要的制糖企业落入日伪之手,部分制糖企业纷纷内迁。数年努力经营的广东糖业瞬间遭到毁灭。四川、广西等地成为中国新的蔗糖生产中心,大后方的制糖企业支撑着中国糖业生产,支援着前方的抗战和大后方人民的生活用糖及工业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恢复生产,成立了资源委员会。1948年5月资源委员会决定邀请翁文灏及接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的孙越崎到广州,商讨在广州和广东省发展工业的问题。由资源委员会台湾糖业公司从台湾拆迁多余的糖厂设备运回广东建设糖厂。鉴于台湾省内糖粮争地,制糖设备有余,甘蔗供应不足,榨季短,成本高。利用台湾糖业公司的人力物力在广东和四川2个产糖地区建设新糖厂。委派从北平清华大学毕业的甘蔗糖业技术专家冼子恩为广东糖厂筹备处主任。1948年春台湾糖业公司派出总公司协理兼第二分公司经理张季熙到广东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报告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运用台湾糖业公司现有剩余的机械设备与人才,先恢复广东的揭阳糖厂及番禺县的新造糖厂。报告中“查揭阳厂损失较轻,恢复较易。惟新造糖厂厂基荡然,从新规划约需一二年功夫”。这句话对以后的糖厂厂址选择发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中山顺德两县甘蔗面积估计约有三十余万市亩。除顺德糖厂和东莞糖厂共消纳约七、八万亩外,均供给旧式土榨糖厂。非设新式糖厂,不足以消纳剩余之甘蔗。第三,关于厂址选择方面:“建议在中山县古镇或新会北街附近设一个一千吨厂;在顺德县三洪奇或陈村附近设一个一千吨厂;在顺德县小杭镇附近设一个一千吨厂”。第四,利用珠江三角洲糖厂盈余为基础,继续向雷州半岛之徐闻、遂溪、海康发展。待雷州半岛糖业具有规模后,再向海南岛发展。
张季熙回到台湾后,又提出分期分批将台湾苗栗糖厂(日榨能力1000吨)、埔里社糖厂(750吨)、乌日糖厂(800吨)、恒春糖厂(650吨)、湾里一厂(700吨)及台中二厂(550吨)等迁到广东。前面3个糖厂的机器设备完整,当时仍在生产。但由于甘蔗少,经常开工不足。以苗栗糖厂为例,每个榨季仅能开工30天左右。其余2厂,每年仅开工榨蔗60天左右。产量太低,成本高,没有继续经营的价值。后面3间糖厂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部分被美国飞机炸毁。恒春糖厂仅存压榨机器设备,湾里糖厂仅存制炼设备。台中二厂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改为酒精厂的发酵室,将制糖设备拆卸分散到各地,接管前已转拨一部机器设备给其他糖厂。张季熙主张将这批糖厂的机器设备全部都迁到广东,既不会影响台湾糖业的大发展,反之,还可延长另一些糖厂的压榨天数,降低食糖生产成本,对台湾糖业更有利。
1948年7月资源委员会成立四川糖业公司与广东糖业公司,由冼子恩任广东糖业公司经理。1948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了广东糖厂筹备处。其任务是分期分批将台湾10个糖厂拆迁到广东,逐步成为广东甘蔗糖业的垄断组织。首先是从花莲港将日榨蔗能力1000吨的寿丰糖厂拆运,建在番禺县的市头,即市头糖厂。
1949年5月,东莞糖厂还未停榨。除了总务科和会计科人员自动辞职外,其余全部留用。技术留用180人,占总数240人的75%。这是历来停榨后留用人员最多的一次,对保存技术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6月积极做好年底开工制糖的准备工作。广州解放后,军管会派白烽军事代表,负责接管东莞糖厂,冼子恩仍留任厂长。1949年11月中甸糖厂开榨,这是广东省解放后第一家开工的大型糖厂。
4 结语
1943年,广州湾沦入日军之手,土糖生产进入衰落期。抗战胜利后,中国制糖业得到一定恢复,土糖生产一度起色。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扶持农民种蔗,稳定糖价,粮糖比价趋于合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糖业不断得到发展,广东当时所办的糖厂成为全国各地发展现代制糖业的蓝本,所培养训练的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成为了新中国甘蔗糖业界的中坚,为我国制糖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