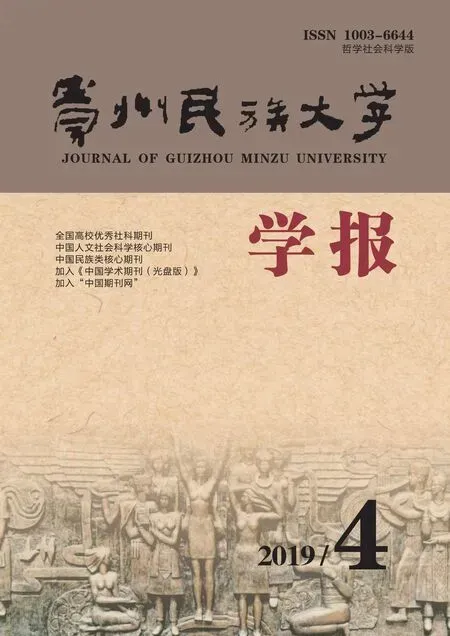荆河戏的文化渊源与传承发展
——《荆河戏研究》序
2019-03-18黄永林
黄永林
荆楚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勤劳智慧、勇于开拓的楚先民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荆州出土的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和整套石磬编钟,无不折射出楚文化的熠熠光辉。[1]荆江文化作为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沉淀丰富,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影响很大,流传于荆江流域的戏曲——荆河戏,就是荆江特色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荆河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河戏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保护和传承荆河戏,由长江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荆州市群众艺术馆组织、桑俊教授和李斌馆长共同主编的《荆河戏研究》即付梓,她们约我为这部书写序,尽管我对荆河戏研究不深,但我仍欣然答应,因为我觉得这是自己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当我认真学习这部书后,感慨万千,受益匪浅!回望荆河戏发展的历程,数百年历史,沐雨栉风,春华秋实,艺人辈出,光彩夺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源于一条河流——荆河,盛于一座城市——沙市、兴于一批艺人——名师,传于一所高校——长大。我被荆河戏强大的艺术魅力所感染、被无数辛勤守望者的精神所感动,我要向那些曾为荆河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川胜地、名流学子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要将他们的伟绩融入到字里行间,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一、荆河:孕育了荆河戏文化
河流是地球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河流与人类文明相互影响,不仅孕育了生命,也孕育、产生了人类文化。人类的社会文明起源于河流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积淀河流文化,河流文化生命又推动了社会发展。人类对河流文化的文化、文明类型的认知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将其称为“大河文明”,如尼罗河之孕育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孕育两河流域文明,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黄河、长江之孕育华夏文明。这些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大河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
文化是流淌的文明,文明是活着的文化。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开始,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是世界上传承时间最久且从未间断过的人类文明,中国是极典型的大河文明型国家。中国历史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即长江和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巨大作用。长江流域是炎帝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是黄帝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是传承炎黄文明而来,我们是炎黄子孙。
长江,从雪山走来是一首歌,向东海奔去是一幅画。长江浩浩西来,汇细流,纳巨川,逶迤万里,亘古不息。长江出三峡,在宜昌枝城进入中游后,穿过夹江对峙的虎牙山、荆门山河谷,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两岸不再是“猿声啼不住”了,而是进入“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的大平原。由于长江进入平原后流经古荆州地区,因此这段河道通称荆江。荆江原长404千米,后来缩短为331千米,有上荆江和下荆江之分。湖北省枝城至藕池为上荆江,河道比较稳定;藕池口至湖南省岳阳城陵矶为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2]荆江以北是古云梦大泽范围,有富饶的江汉平原;以南是洞庭湖,是洞庭湖平原。其北岸有沮漳河、玛瑙河入汇;南岸有松滋、虎渡、藕池、调弦(已封堵)四口分泄荆江洪水南注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于城陵矶复注长江。荆江流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荆江文化,在这里人类创造了大溪文化等原始文化,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文化的核心区,更有着地域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化。荆河戏就是荆河流域的民间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承、积累、吸纳、流变而形成的传统剧种之一,是荆河文化的一朵奇葩,是长江文明激流中的一朵美丽的浪花。
据传荆河戏原是汉剧荆河、襄河、府河、汉河四大支流中的荆河派,因流传于长江荆河而得名。过去荆河又称上河,包括荆州、襄阳、郧阳、宜昌、施南在内,一般说是上五府,故流行于荆河上游的荆河戏也有“上河戏”之称。府河又称下河,包括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在内,一般说是下五府,称府河戏为下河戏。常德戏和荆河戏,本是同根发脉,荆河戏对常德戏而言则叫北河戏,常德戏为南河戏。沙市人过去把襄河和府河来的戏都叫府河戏。荆河戏发源于荆州与府河戏是亲兄弟,因为它们的唱腔和剧目基本上相同的。荆河戏是一个汉族戏曲声腔剧种,因不同的地方风俗习惯有所不同,因此荆河又叫上河路子、大班子、大台戏、高台班或汉班子等。抗战期间又曾被叫作楚剧、汉剧、湘剧。
荆河戏发源于湖北荆州、沙市一带,从沙市老郎庙石碑记载的永乐二年间荆河戏班活动的踪迹,可以推断出荆河戏大致发端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现流传于此地的荆河戏为尚保留着诸多原生形态的“单钹路子”的荆河戏(湖南的荆河戏为“双钹路子”)。到清代初年基本完成了楚调与秦腔的“南北结合”,形成荆河戏弹腔的“南北路”,荆河戏基本成型。荆河戏形成初期,主要在沿长江的宜昌、沙市一带活动,以后逐渐向湖南的澧水流域转移,后来流行区域遍及湖北的石首、松滋、公安、监利、恩施和湖南的澧县、津市、临澧、石门、大庸、岳阳等地。[3]清嘉道以后,荆河戏日趋昌盛,当时在湖北沙市演出的四大名班,就有荆河戏的三元班和太寿班。湖南的澧州(包括慈利、临澧、津市)也有老同福、老同乐、老文华、长寿、双胜、松香等十多个荆河戏班,常年从事演出活动。清光绪至辛亥革命的三十余年,湖北荆州和湖南澧州所属诸县,又相继成立了清和、文华、彩庆、仁寿、云乐、宝衡、春台、新舞台、公和园、翠和、瑞云、福林、同乐、同福、华胜等六十多个荆河戏班,直到20世纪30年代,其间虽时起时落,但仍还有三十多个荆河戏班常年从事专业演出。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荆河戏受到极大的摧残,其戏班被破坏殆尽。[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河戏获得新生。因其长期流行于荆河两岸,于1954年始定名为“荆河戏”,并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幸存的永乐、翊武、松秀、同福、新华五个戏班进行了定点安排,分别于湖南的澧县、石门、津市、临澧,湖北的石首等五县,成立了专业荆河戏剧团。1955年,经过调整,建立了“沙市业余荆河戏剧团”,活动至今。近年来湖南省艺术学校设有荆河戏科,湖北省石首县也办起了荆河戏剧学校,先后共培养了新生力量五百多名,从业人员由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二百来人增加到六百多人。
荆河戏发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风雨数百年,其间虽历经王朝兴衰、政权更迭,但荆河戏艺人们通过不断融合创新与艺术坚持,使得荆河戏得以一脉相承。荆河作为长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永远奔流不息的河,它在惊涛骇浪中前行,也在舒缓细流中流淌。荆河戏将与荆河同在,在艺术家的传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人民的喜爱中走向更大的繁荣。
二、沙市:铸造了荆河戏辉煌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市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缔造了自己的城市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中最积极、最辉煌、最具有创造力的成分以及智慧的结晶。[4]每一座城市都以自己独特的城市形态风貌、历史和文化等鲜明的个性,造就着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和展示着自己的文化光辉。荆河戏在湖北沙市曾创造过昔日的辉煌。
沙市,这个楚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古郢名镇,这个曾镌刻着长袖细腰、婆娑舞姿、翩翩倩影,流传了高山流水,知音佳话的文化古城;明代以来,又呈现出一派丝竹喧哗,百戏杂陈的繁兴景象,她哺育了戏曲这朵艺苑鲜花,更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名优巧伶。荆河戏、汉剧早期的“四大名班”曾名噪荆沙,誉满湘鄂。昔日两剧戏班若标明“从荆沙归来”观众当刮目相看,演员若冠以“荆沙驰名”便身价倍增。沙市因而赢得了“戏剧城”的桂冠。这里曾经商贸发达、文化繁荣、戏曲盛行,这为荆河戏的辉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
商贸经贸中心。沙市地处湖北省中部,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早在五六千年前,这里就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有“大溪文化”“龙山文化”遗存,沙市的先民据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沙市曾是楚国都城郢的外港,初称“津”,意即长江渡口。至唐代,始称沙头市,简称沙市,意为古长江与沮漳河、夏水之间三角洲顶端的市镇,是著名的鱼米市场。明中后期,沙市商业、手工业渐趋发达。清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写道:“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荣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号称 “三楚名镇”,是当时长江沿岸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全国十二大商业都会之一。《沙市地志》中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开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后,此处更见兴盛耳。乡人谚云:‘天下口,算汉口;天下市,算沙市’”。咸丰年间,沙市为湖北中西部货物和粮、盐总汇,全国十余省、市的商人在沙市组织的行会有十五六个之多。“商路即戏路”,凭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繁荣的商贸往来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沙市已成为当时戏曲流布交汇的中心。[6]3
荆楚文化根基。荆沙一带,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地自古“信巫鬼,重淫祀”,古楚歌、舞、乐高度综合,戏曲演出盛行。早在战国时期,楚大夫屈原曾写下了作为南楚巫鬼文化结晶的《九歌》,直至唐代,仍为“荆、楚鼓舞之”(唐·刘禹锡《竹枝词》序)。明隆庆《岳州府志》引《隋志》说:“荆州风俗……大抵敬鬼重祠祀,竞渡之戏,诸郡率然,又有牵钩戏。”唐宪宗时,澧州幕僚李宣古诗中,有“觱栗调清银象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舞来挼去使人劳。”之句(清同治十三年《直隶澧州志·丛谈》)。明时期,袁宏道更是在《午日沙市观竞渡歌》中写道:“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摩”。明万历年间(1573-1620),荆沙乐户、伶人遍布,时有外地优伶来荆沙演出“高腔”“昆腔”及本地的“楚调”,诸腔杂陈于戏曲舞台。[7]明代,荆州都是藩王封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徙蜀献王子悦耀由武冈迁澧州,仍旧号华阳王,历十一王至祟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攻破澧州为止,共二百一十八年。按明代诸王封藩通例:“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李开先《张小令小传》)王府的娱乐活动、民间歌舞对荆河戏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民俗文化浸润。明清时期的沙市,经济繁荣,商旅云集,各种行帮组织甚多、寺、庙、宫、馆林立。据清同治五年(1866)《沙市志略》载:明末以来,沙市有寺、庙、观、宫、堂、庵四十一座。其中可供戏班演出的有“九宫”“十八庙”。“九宫”是赤地宫、帝主宫、老天后宫、禹王宫、老文昌宫、万寿宫、川主宫、江渎宫、玉清宫(三清观);“十八庙”有址可查者有老杨泗庙、老郎庙、东岳庙、南岳庙、城隍庙、灵官庙、泰山庙、三义庙等八庙。清代末叶至民国初期,沙市行会兴起,成立了许多行帮组织,有汉阳、武昌、黄州、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南京)、浙江、福建、徽州、山陕(山西、陕西)、太平(安徽泾州、太平府)等十三帮。多数行帮组织都修建了会馆,以便进行生意经营的联络或举行庆典活动。上述寺、庙、会馆,一般都建有戏台(有的有内、外两个戏台),可供戏班演出。每逢寺庙酬神、礼佛,做会、祭祖、开张、贺岁,寺庙行帮均会请戏班演“庙戏”“会戏”。[8]荆河戏在这里演出“会戏”“庙戏”曾盛极一时。明清时期,沙市老郎庙是戏曲优伶祭祀戏剧祖师和业内聚会议事之所,由戏曲艺人集资明初修建,曾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和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两次重修。据《中国文学珍本·袁小修日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公安人袁小修在沙市时,“晚赴……诸王孙之饯……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文中的“吴歈”是江浙一带的昆山腔,“楚调”不知为何腔,但系本地声腔无疑。由此可见,最迟在明代后期,沙市已有演唱本地声腔的戏班和老郎庙建筑。清末沙市文人刘竹荪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写成的《沙津竹枝词》曰:“酬神名庙常多戏,唯有忌辰锣不开,今日有无台演戏,老君庙首看牌来。”由此可见老君庙在当时的地位。光绪以后,荆河戏班蓬勃兴起,更向乡村发展,临时搭台演出“草台戏”。根据农事季节和旧俗,旧历正月尾和二月间唱“土地戏”,三月唱“财神戏”,四月唱“单刀会”,五月唱“青苗戏”,六月唱“雷祖”“观音”会,七月唱“盂兰会”,八月至年底唱“丰收戏”,形成了“沙市天天有戏,荆州月月有戏”的局面。[9]
民间戏曲土壤。劳动群众不仅爱戏成癖,且自唱自乐,于是就形成了古沙市繁花似锦、星罗棋布的业余荆河戏队伍,从开始的“挑鼓架”到“围鼓堂”十分活跃。挑鼓架是类似围鼓堂的演唱班子,有一副专门陈设乐器的架子,演唱时可置挂各种乐器,演员坐在架子周围边唱边奏乐器,转移时,架子可由一人挑走,十分方便。荆河戏围鼓班(或称为“堂”,或称为“包”),这些荆河戏的爱好者往往以街巷、村镇为片组班(称之为“扎包”),班名多以街巷名名之。围鼓班由一位有一定艺术造诣、颇具声望、具备一定组织能力的荆河戏艺人掌班,其成员为相对固定的荆河戏玩友(票友),也有一些专业戏班出身的荆河戏艺人参与其中。沙市有名的围鼓班有“过街楼”“大赛巷”“张家台”“宝塔河”“便河西”“龙门巷”等。清末民初,沙市的围鼓堂有二、三十个之多。清末沙市文人刘竹荪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写成的《沙津竹枝词》亦有描述此盛况的篇章:“一年两度各为乐,赴会归来作醉翁。挤满大街听坐唱,家家门口点灯笼。”“惹得游人逐队来,品项题足聚成堆。布棚下面听围鼓,贪看佳人不走开。”[10]216时至今日,每逢喜庆之日,即有邀约荆河戏围鼓演唱,荆河之调赏心悦耳,乡音俗调绵延不绝。老人们每每谈及仍眉飞色舞,双眸生辉。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一座名城成就一门艺术,沙市过去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成就了荆河戏曾经的辉煌!但愿沙市曾有的荆河戏辉煌不是落日的余晖,而是喷薄而出的朝霞,给人以希望,给荆河戏以生机与活力!
三、艺人:传承了荆河戏血脉
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传递者和守护神,他们用自己记忆和聪明才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统和技艺进行继承发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延续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荆河戏作为一个古老剧种,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剧目、曲牌、锣鼓经等资源丰富,声腔融高腔、昆腔、弹腔、杂腔小调于一体,变化多样,运用灵活,表演大气直率,贴近生活。无论是剧目、音乐、表演和舞美,无不凝聚着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荆河戏历经400余年的沧桑冷暖,这颗沧海遗珠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们的执着坚守和护养。
仅就荆河戏旦行的艺术流派讲,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童(童乐秀)派、瞿(瞿翠菊)派、谢(谢福香)派之分,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将这三派的代表性人物及艺术特点简介如下:
童派艺术的代表性人物童乐秀出生于1900年,桃源县人。民国元年(公元1912)入澧县牛奶湖乐字科班习艺,师宗谢安凤。童乐秀自幼聪颖好学,刻苦钻研,甚得老师器重。出科后到沙市泰寿班唱戏初露头角,令沙市观众刮目相看。他功底扎实,嗓音圆润,以武旦戏见长,演《飞熊山》中翠环,踩晓子,跳“掩脚方”“双蹦子”动作利落,姿态优美,塑造了女中豪杰的形象。摇旦、花旦戏也很拿手,在《牧羊山》《赶春桃》等戏中扮演大娘泼妇,动作夸张,神情狠毒,恰到好处,为观众所称道。20世纪30年代初,童乐秀离开沙市舞台到津市松秀班演出、授徒,后起之秀松庹霞等均受其教益。
瞿派艺术的代表性人物瞿翠菊,出生于1898年,1912年入安乡翠和科班向胡恒翠学艺,出科后,在湖南津市松秀班拜邓金秀为师,后在湖北沙市三元班、湖南澧县新华班、临澧县同福班做戏。凡唱、做、念、打、跷功、发功、水袖、翎子等功俱各尽其妙。特别是他的跷功,能使身材变矮。青年时期即名噪荆、澧。他的戏路宽,尤擅长闺门戏。《樵子口》的王金爱,《祭江》的孙夫人,《祭塔》的白素贞,《二度梅》的陈杏元,都演得很好。花旦戏《百花亭》《梅龙镇》,武旦戏《盗旗马》《寒江关》,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唱腔多花腔,唱得声媚音柔,又会偷腔换气,行腔时袅袅余音,连绵不断,能收到回肠荡气的效果。晚年致力于培养青年一代,鲁小翠、张淑容、李惠云等皆出其门下。
谢派艺术的代表性人物谢福香,出生于1899年,1913年在本地福兴科班学观,出科后随班演出。1918年到沙市三元班,从岳父王金凤参师。因而场底厚实,文武兼备。前期多演“弓马”戏,以《盗旗马》《斩三妖》《两狼关》等跷功戏见长。后演青衣,又以《祭江》《樵子口》《武家坡》《三击掌》等唱功戏拿手。他的花旦戏也有特色,在《耍凤冠》中,把荷珠丫头淳朴天真而又矫揉造作的双重性格,刻画得准确细致,丝丝入扣。在《活捉三郎》中饰阎惜姣的鬼魂,碎云步飘若浮云,甚是优美动人。先后在同福、新华、宝垣、水乐等班唱戏。1933年在临澧县新安新舞台料班当教师。王新凤、谢新娥、董新菊(女)等,皆出其门,成为后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传承人中,湖北省的刘厚云和谭复秀、湖南省的萧耀庭和王与佑为国家级传承人,他们为当代荆河戏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厚云(1928-2009)系沙市荆河戏刘氏第五代传人,从小受家庭熏陶,12岁开始,先后拜沙市荆河戏名师杨文宣、李友本为师学习荆河戏,以司鼓为主。由于师父传授得法,自己刻苦努力,硬记曲牌、锣鼓经、唱词,因此入门很快。在打鼓的同时,还特别留意丑行、净行、生行一些角色的唱腔、道白和表演,学会了不少戏,因此,他不单能司鼓,还能上台演出。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沙市专业戏班演出,为汉剧名伶徐万春、王子林、刘玉楼、江金钟、荆河戏名伶筱精培、杨华福等司过鼓。1952年加入荆河戏新华剧团,1953年,该团落藉石首,成为石首县荆河戏剧团。刘厚云在该团曾任业务团长、艺委会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同时担任司鼓、导演兼演员。除了担任传统的司鼓,参与一些演出外,他曾导演过《血债血还》《王贵与李香香》《望娘滩》《宝莲灯》等戏,在《血债血还》中饰蒯金镖,《枪毙张友三》中饰张友三,《王三保回头》中饰三保,《王贵与李香香》中饰连长等。1974年,从石首回沙市棉织二厂工作,担任荆州市业余荆河戏剧团业务团长,长年坚持为演员说戏,排戏,参加演出,排练演出了大量荆河戏剧目。多年来带徒授艺,培养了不少乐手和演员。
谭复秀(1932-)自幼热爱荆河戏,1952年她先后拜荆河戏名师李有本、徐元富、李方元为师学戏,主攻生行兼习老旦、小生,有时也串演丑角。那时,学戏演戏都是业余的,每天上完班,不管有多累,她照样回来学戏。在台上,她甘当小角色,跑龙套。有时她演丑角,刚刚挨板子,又要当替身,被拖出去斩首……不管演多么小的角色,她都精益求精,深受大家赞誉。她很快就成了剧团的“柱子”,登台演出了《莲台山》《禅台报》等。1964年,她担任沙市业余荆河戏剧团团长。除上演传统剧目外,她还组织排演了《查账》《小虎参军》等新剧目,受到文化部门表扬。“文革”结束后剧团重新恢复,谭复秀继任团长。1999年在荆州市业余戏曲大赛上,谭复秀以《三元会》荣获一等奖。其《郭子仪封王》唱段被录音记谱载入《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北卷》。为使荆河戏后继有人,她热心培养年轻人,使她们成长为荆河戏的骨干力量。谭复秀和老艺人将20多箱荆河戏服饰、道具、剧本手抄本500余件,无偿的捐赠给长大荆河戏基地。今年她已经85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一线的舞台上,唱功不减当年。
萧耀庭(1935-),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分配在内蒙古教书,后因病退职返乡。1962年进临澧县荆河剧团,师从著名乐师黄绩三学习荆河戏音乐。1963年起任临澧剧团的专职音乐设计,先后有100多首戏曲音乐作品问世(包括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文革”时期的移植样板戏),在澧水流域颇负盛名。除此之外,他还曾改编、新创《孟良一家》《双合印》《程咬金娶亲》《和氏璧》等剧本,其中《程咬金娶亲》剧本1982年获省文联颁发的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后主要从事荆河戏音乐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有相关的创作与研究成果,代表作有主编《荆河戏音乐研究》,编撰《荆河戏音乐集粹》,创作剧本《程咬金招亲》等。
王与佑(1952-),他的祖父是荆河戏戏班文场师傅,父亲是原永乐剧团(现荆河剧团前身)的鼓师,姐夫、姐姐曾是荆河剧团的台柱子。1971年,王与佑进澧县荆河剧团,拜荆河戏音乐泰斗黄绩三的得意门生许安和为师,学习荆河戏的传统曲牌与演奏技法,挖掘整理出传统唱腔、曲牌近百首。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担任剧团音乐设计的主笔,前后为近百出日常演出与调(汇)演剧目设计唱腔,多次获省、市音乐设计奖。其中《郑宫恩怨》《桓公拜相》《夫人令》等戏在中央电视台、湖南省电视台播放,部分作品收录于《湖南新时期10年优秀文艺作品选·音乐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常德卷》《荆河戏音乐集萃》中。
在历史上著名的荆河戏老艺人有许天喜、王赛喜、田育远、张春喜、张多宝、朱三元、李楚祥、伍云春、罗炳寿、徐宝楚、王金凤、杨彩洪、傅庆寿、郑金秀、谢升和、欧清喜、刘金玉、许宏海、潘化林、王席香、彭化万、黄乐元、邵春霞,滕和英、杨化富、翦同荣、孙瑞全、周精培、马福金、张觉华、王天柱、孙春云、张申华、杨宏枝、孙香华、任和猛、孙升福、蒋玉和、胡醉趣、黄绩三、徐国才、李友本、陈登亮、吴生荣、徐泽秀、李正栋等等。现代著名的荆河戏传承人还有,湖北的陈顺珍、胡兴春、徐方贵、刘怀春等。湖南省还有方觉东、张又军、张兴、周乃国、胡红、张蓉蓉、胡小元、陈大华、杨翠均、攀明全、黄生峰等等。[11]
荆河戏技艺传承的路径有家族传承,也有师徒相传,但以师徒传承为主,因此谱系错综复杂。荆河戏形成之后,代代有创新,流派纷呈,呈现出“多师”的格局。荆河戏苑因名家荟萃、大师如云、百花齐发、异彩纷呈而精美绝伦!
四、学校:延续了荆河戏薪火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高校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高校的重要功能。坐落于荆江之滨、荆州城内的长江大学勇立时代潮头,以身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的传承与保护为重点,积极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为荆河戏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长江大学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为湖北省重点建设的骨干高校。早在它的前身江汉石油学院时期,学校就同荆河戏的社会剧团进行了多次交流。2006年,长江大学协同地方政府推进荆河戏申遗,荆河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与荆州市群众艺术馆配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在《荆州篇》中,重点介绍了荆沙的古老剧种荆河戏,推动荆河戏的抢救保护。2009年,成立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学社,并同荆州市群众艺术馆下属荆州市荆河戏剧团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加强对荆河戏的传承保护,并于2010年6月合作拍摄完成荆河戏专题纪录片《十年的守望》。同年,还与荆州市群众艺术馆共同承担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珍稀剧种的抢救保护工程中荆河戏《望儿楼》《斩于吉》的录制工作。2012年,秉承“荆河戏进校园,传承荆楚文化”的理念,初步建立荆河戏校园演出机制、校内荆河戏学员培训机制。2013年,长江大学非遗研究中心成立,这对推动长江大学荆河戏传承的专业化、科研化、组织化建设,打造“荆河楚韵”文化品牌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在长江大学非遗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荆河戏专题纪录片《荆河魂》完成拍摄,该片播放后吸引了国内外数十家媒体的关注。2017年3月9日,在荆州市群众艺术馆、长江大学非遗研究中心的共同支持下,群众业余戏曲保护与传承组织——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成立,在全省乃至全国戏曲校园保护方面起到了示范效应。多年来,长江大学先后举办“荆河戏走进长江大学专场晚会”“荆楚戏曲长大行晚会”“荆河戏小品剧之夜专场晚会”“橘颂荆河情戏曲专场晚会”等活动,培育了一大批校园荆河戏传承人,吸引了荆河戏非遗传承人的进驻,输送了一批有一定戏曲表演能力的学生,奠定了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老中青、传帮带”的传承组织基础。2017年,在荆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戏曲进校园”荆州城区团队竞演活动中,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与荆州市荆河戏剧团联袂出演,拉开了在荆州城区十所学校巡演的序幕,受到广泛好评。2017年6月10日,为响应国家“文化遗产日”号召,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邀请美国纪录片大师大卫·布鲁曼克鲁兹开展“荆河戏”跨文化之旅活动,一展剧团的国际化能力和专业化素养。在积极进行荆河戏传承保护的同时,长江大学的学者们致力于荆河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年来长江大学在荆河戏的保护和研究中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9]
学术研究与表演传承相结合。在荆河戏保护方面,长江大学一直坚持研究与传承相结合,先后成立了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学社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长江大学)开展荆河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发表了《荆河戏调查报告》《地方戏校园传承反思》《荆河戏的历史源流与表演艺术》等论文数十篇,收录了传承人生活照、演出剧照、教学照等珍贵影像资料数万张,提升了荆河戏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2017年还成立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该剧团拥有一支集高校教师、博硕本等不同层次学生、非遗传承人的专业化团队,包括组织策划团队、拍摄团队、宣传团队和演员团队等,积极开展校内外巡回演出,为荆河戏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2]
专业艺人与青年学子相结合。长江大学在荆河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模式探索中,创造性地利用荆河戏原有组织框架和互联网平台,积极建立了学校平台与荆河戏艺人的互动共享机制,加强老一辈荆河戏艺人同师生间的情感联系和艺术共鸣,调动了师生参加荆河戏保护传承的积极性,形成一种学荆河戏的良好氛围。通过学校平台也逐步聚集了大量荆河戏爱好者,展现了本土戏剧文化生命力,扩大了荆河戏的影响力。
政府机构与高校社会相结合。多年来,长江大学荆河戏的校园保护与传承得到了荆州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荆州市文化局、市群艺馆多次提供扶植资金,用于荆河戏的演出、研究和人才培养。长江大学积极发挥高校人才和平台优势,确立以高校教职工为传承中坚力量、国家、省级、市级荆河戏传承人为教导教师、以高校学子为主要培训对象的荆河戏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荆河戏成果理论化、科学化、影像化、数据化。长江大学业余荆河戏剧团也积极引进社会资源,致力于构建以高校、中学、社会为中心的荆河戏巡演体系。目前,长江大学已形成政府、高校、社会相结合的荆河戏保护传承体系。
原味传承与不断创新相结合。长江大学积极推进“戏曲进校园”活动,学校业余荆河戏剧团在演出实践中,在保持戏曲原味的基础上,在内容上,着力推动荆河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市场;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升艺术创新能力和审美趣味。在近年来的演出中秉持“生旦净丑同台演绎,用荆河戏讲民族历史”的理念,推出了《挑担围观唱荆河》《八百八年》《双驸马》《寒江关——樊梨花》《大回荆州》《莲台收妃》等一批精品,不仅向观众普及了荆楚历史文化知识,而且集中展现了荆楚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显示出了荆河戏强劲的生命力。
传统传承与现代传播相结合。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长江大学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技术,记录荆河戏演出过程,建立荆河戏影像资料库,加强对宝贵的荆河戏资料的保护;积极探索荆河戏传统口头传承与现代化媒体传承相结合的方法,创建了荆河戏规模化、市场化、层次化的现代传媒传播平台,建立了大型荆河戏同好论坛和群组等。这不仅让热爱荆河戏的青年学子能随时随地学习、传承和研究荆河戏,而且也能让广大荆河戏爱好者能及时欣赏和传承荆河,增强了荆河戏的传承传播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创造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文化的兴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文化的传承靠一代又一代人来担当,让我们接过薪火相传的火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荆河戏这一中华文化奇葩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