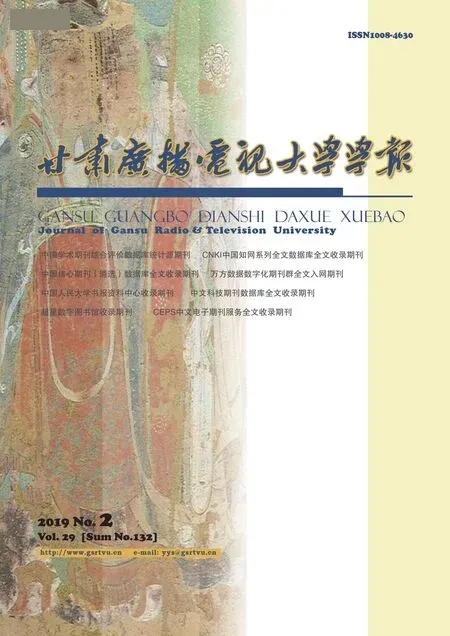“家”中的孤独
——《颓败线的颤动》和《变形记》的比较分析
2019-03-17张思远
张思远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一、无路可走的“母亲”
钱理群曾指出:“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成为不自觉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观察、感受和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的个人印记。”[1]通过考察鲁迅的小说,发现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存在着对于“家”的思考和审视。在他的书写中,“家”大多是不幸的、无奈的、痛苦的、凄凉的、破碎的,体现出鲁迅作品中隐含的孤独绝望的无家之感。鲁迅的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言说有关“家”的内容,“而是在其作品的开放式的复调性内容和结构中,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潜伏着”[2]42。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通过子女对母亲的谩骂,写出了彻底的“家”的无可依处。
在中国,母亲总是和“港湾”“家园”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国人对母亲普遍的依恋情结。鲁迅的作品中有着许多慈爱的,温柔的、无奈的、悲哀的母亲形象。如《铸剑》之中的母亲,《药》中的华大妈,《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补天》中的女娲。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塑造的的母亲形象虽然是瘦弱贫困的,但她却坚韧有力量,这样的“母亲”形象更加的贴合传统中华文化中的母亲形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顺并敬爱母亲是基本的道德规范。但在《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女儿一家,自以为站在道德的立场来指责自己的母亲。他们不思考历史限定的残酷性,而是得意的以为自己有着不同于母亲的高尚情操,抓住母亲屈辱的历史加以鞭挞。同时她们又忽略了“血浓于水”的起码的人性,她们没有反思自己的劣根性,没有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反而呈现出了一种阴损和刻薄的嘴脸。鲁迅深刻且严厉的揭示出了“儿女们”对母亲谩骂和侮辱背后所隐含的道德的沦丧。他写道:“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3]简单精炼的一句话便深刻的展示出了“家”的荒凉、残忍、凄楚和绝望。“幼者”是一个“家”的未来和希望,而在这句话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自己进化论理想的怀疑与否定,也体现出了他对“家”产生的焦虑感和危机感。更令人深思的是“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4]205,斥责老人的并非是一两个孩子,而是“一群”孩子,显示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特征。鲁迅在这里所写的“家”中的悲剧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小家”的范畴,而是表现出了他对于“大家”(国家)的绝望与担忧。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所塑造的“孩子们”是忘恩负义的、绝情的。他笔下的孩子之所以不再天真,除了有着他自己深刻的人生感悟之外,还有他对于国民的生存现状的深刻思考。
二、无家可归的“孩子”
在《颓败线的颤动》中的家庭凝聚着鲁迅自身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通过破碎的家庭不仅表达了自己潜意识里对于家的温暖的渴望,而且表达了对于国家和人民不能给予他宽慰的忧虑。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所体现的对于家庭的思考,显然和鲁迅是不同的。《变形记》是个体对于家庭生活的一种想象性的审视和冥想,没有更多的涉及国家和民族,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卡夫卡写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的精神困境,许多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碾压下挣扎的人们,都可以在格里高尔的身上找到共鸣。他曾就《变形记》的封面设计专门致函出版社,要求“封面上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啊”,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凄苦的哭着离家出走的青年,很直观的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是被家伤害后想要逃离的思想感受。
卡夫卡生于犹太家庭,他的性格脆弱、敏感、多疑。但是他严厉的父亲却想将他培养成一个果断、勇敢的男子汉。在父亲的重压下卡夫卡没有成长为父亲想要的样子,反而变得更加的懦弱,对家庭对社会也开始失去了信心。他将自己这样的心理寄寓在格里高尔身上,揭示出在家庭亲人之间,表面恭恭敬敬,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疏离和陌生的实质。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亲人有父母萨姆沙夫妇和妹妹葛雷特。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之前,他是家庭中的经济支柱,为了一家人的幸福“他开始以异乎寻常的干劲拼命的工作,很快就不再是个小办事员,而成为一个旅行推销员”[5]17,他为家庭的幸福拼尽了一切,然而在他变成甲壳虫之后,他的家人却放弃了他。
他的父亲会毫不犹豫的将中苹果砸向格里高尔,也是这个苹果导致了格里高尔的死亡。这不是第一次在卡夫卡的小说之中出现父亲导致儿子死亡的情节。《判决》中的格奥尔也是在父亲的威压之下走向了死亡。在一个家庭中,严父慈母是我们普遍认知的家庭架构,但是大多数的“严父”对自己的孩子是关爱的,只是将严格作为了一种父爱的表达方式,然而在卡夫卡这里父亲让他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温暖。《变形记》中的母亲也没有给格里高尔一丝宽慰,母亲在看见儿子变成甲壳虫之后的第一眼竟然晕了过去。曾经被哥哥宠爱的妹妹,在格里高尔没有劳动能力之后,也不顾亲情抛弃了哥哥。一家人把曾经带给他们幸福生活的格里高尔当成了累赘,将格里高尔的死亡当成了解脱。《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悲剧人生实际上是卡夫卡本人对现实生活的夸张性预测与想象,是卡夫卡人生悲剧的缩影,也是卡夫卡对家庭温暖的绝望的哀歌。
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查尔斯·库利曾经提出一个人所在的“首属群体”如家庭、邻里、玩伴等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其中家庭在“首属群体”中的影响是最大的。很多作家“借助‘家’来隐喻的表达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状况”[2]8。一个作家对“家”的关注之处往往能够折射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和他想要解决的社会人生问题。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和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提到了关于家人的背叛、家庭的抛弃。二者都在家庭的框架中表现出一种人性的缺失,即面对个人利益的时候,人们习惯性的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这样的人性的缺失表现在一个家庭之中便更显得讽刺和深刻。
三、 “生”的反抗与“死”的解脱
格非曾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是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6]面对家庭和社会给予的绝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斥责时她站在荒野之中发出非人间所有的“词语”,她站在天空下无言的颤动,她绝望失望,但是却不想就此灭亡。而在《变形记》中,面对家人伤害的格里高尔默默的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同样是面对家庭的伤害,两位作家反抗绝望的方式截然不同。在《颓败线的颤动》中,老母亲的绝叫是充满着虚无和幻灭的痛苦的叫喊。鲁迅把这种包含着悲观和痛苦的心绪变成了自己韧性的铠甲。正如他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7]老母亲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传统的道德原则对立,在这里显示出她的第一次反抗。她被自己的子女辱骂,在她的外孙说出“杀”之后,“她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的,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4]205,这时的老妇人已经心死。她感受到了绝望,然而她确于荒野上“颤动。”“颤动”蕴含着老母亲的寒心、衰怨与不甘绝望,但又得不到希望 ,追问但又没有回答的苦闷、孤独 、焦燥、激愤等复杂的情感。鲁迅和文中的老母亲一样,在沙漠般荒凉的人生中发出痛苦的绝叫,那叫喊的声音饱浸着悲观和虚无。他将这种饱含着悲观和痛苦的心绪变成了自己的战斗武器。人生之路就是死亡之旅,鲁迅和卡夫卡都从不拒绝死亡,他们知道拒绝死亡就是拒绝生存。不同的是卡夫卡陶醉于死亡,而鲁迅却是追求向死而生。他曾在《野草》题辞中说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4]159鲁迅超越了死亡的极限,把希望投向了未来。文中的老母亲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的精神也热烈地痛着,但是她仍然选择站在荒凉的原野上抬起眼睛看着天空,“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原野”[4]206,鲁迅坚持用屹立不倒的老母亲的形象审视着自己的灵魂,考察着民族的灵魂、考察着民族病态的根源,以起到疗救的可能。
卡夫卡曾经说过目标有一个但是道路却无一条,他能时常感受到外部世界对他的压迫,正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让他觉得温暖的地方,他常常感到恐惧和慌张,感到孤独和绝望。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能拿起武器和现实斗争,勇敢的呐喊。他反对毫无价值的消极的死亡,虽然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死亡的主题,但他却主张爱惜生命。而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懦弱的,现实似乎还没有发挥出全力打他,他便没有反抗地走进绝望和死亡。《颓败线的颤动》和《变形记》中同样写了家庭中亲人的背叛,但是老母亲和格里高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体现了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态度。卡夫卡曾经说:“我们的拯救是死亡,但不是这个死亡。”[5]238可见卡夫卡将死亡看成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格里高尔在面临家庭的冷漠和无情的打击之后默默的选择了死亡。这个为家庭幸福全力拼搏的青年人,没有如鲁迅一般在经历失望之后于荒原上发出无声的呐喊,而是当他觉得失望时便走向了自我的毁灭,将死亡当成是一种逃脱的方式。这和卡夫卡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世界上最瘦的人”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定位,他对自己处理周围一切事情都没有信心。在父亲的威压之下,他过于依赖父亲,他似乎已经没有逃离现有生活的其他方式,唯有死亡。因此在卡夫卡的许多小说之中都表现出了从容死亡的意愿。死亡也成为了卡夫卡小说之中的基本主题,法国批评家布朗肖曾说卡夫卡的写作就是为了平静的死去。格里高尔面对家人的伤害只是一味的逃离,他以一种几近无言的卑微的姿态走向绝望和死亡。
卡夫卡作为一个敏感的有才情的文学家,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在他所追求的世界里他看不见前进的路也看不见未来的光。他每天看着自己瘦弱的身躯,看着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样凝视死亡的勇气仍然让人佩服。他在对死亡的书写和对死亡的渴望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四、结语
“家”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并已成为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的母题。《颓败线的颤动》和《变形记》在家庭伦理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二者都表现出了一种“家”的焦虑和个体在“家”中的孤独。两位作家的“家”实际上都是一个多层次的象征体,都表现出他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面临的生存困境。
鲁迅和卡夫卡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具有民族魂的战士,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卡夫卡就像一个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的压迫和折磨,他的叙写中充满着恐惧和脆弱,然而透过那些颤栗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清醒者,因为只有清醒者才会清晰的感觉到世界给予他的恶意,才会觉得苦闷和孤独。就如我们可以在格里高尔的形象之中,找到“那些迷失自我又追寻自我、迷失方向又寻找出路、身处迷宫而又探求真理的人物的共同命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