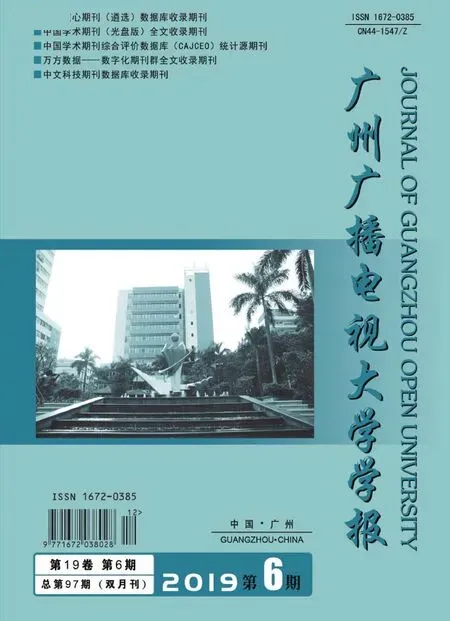《屈原贾生列传》的屈原部分与历史剧《屈原》的叙事比较
2019-03-17朱晨
朱 晨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屈原贾生列传》是现存关于屈原最早的细致刻画的作品,对于这两位人物合传的原因,有多种观点,褚斌杰认为:“屈原始得怀王信任,后遭馋被疏,以至自沉,贾谊则始得汉文帝信任,后亦遭馋言被贬:二人都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1]相似的命运将两者紧密结合,合传的方式将屈原刻画得栩栩如生,对于屈原的刻画,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进行大幅度、多方位人物塑造,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形象。屈原的形象在此之后流传千古,他的忠君爱国的精神经久不息地在华夏大地上熠熠闪光。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屈原比较近,撰写时多实地考察,塑造接近历史真实的屈原。千年后,郭沫若再次将屈原作为艺术形象展示在作品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艺术成就极高的历史剧《屈原》诞生,它恰当地处理虚实关系,历史现实与艺术创造、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相较于司马迁“深入”到恰当的历史资料与实地中去进行创作。郭沫若深入现实生活中去挖掘创作题材,时代赋予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能够运用考古学、史学、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手段,对屈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地分析研究。所以创作虽然晚,呈现的某些方面却十分接近屈原所生活的时代,但作为艺术品的历史剧不会再现所有历史事实,艺术性更强,这与求真求实的《屈原列传》不同。
一、人物形象比较
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具体到人物刻画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主要是他忠于国家与人民的高尚品质以及悲剧命运,“叙述者对屈原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他“存君兴国”,但终至于“无可奈何”的光辉品质与悲剧命运,这无疑构成了整个《屈原列传》的主题所在。”[2]。对人物的刻画详细,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作时正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刻,抗战时期,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问题萦绕身边。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到国家层面,表现国家的内忧外患,更多丰满的次要人物形象出场,艺术想象更夸张,艺术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以此表达对侵略势力及黑暗统治的强烈批判,对光明国家的呼喊。
(一)《屈原贾生列传》中爱国高尚的屈原
屈原形象具有多面性,他忧国忧民、敢于反抗权贵、才华横溢、忠心耿耿人格高尚,宁肯投江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首先,屈原才华横溢,是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在文学方面,他的造诣颇深。《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离骚》有高度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3]。司马迁笔下的屈原才华超群,他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这一正面形象在传记高度评价的不朽杰作《离骚》中可以展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形象超凡脱俗,是屈原这位诗人的映射。《离骚》自始至终贯穿着诗人的顽强斗争精神,这与现实中屈原孜孜不倦地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不谋而合,对内在的黑暗势力他不惧怕,一直与他们做斗争,对外他绝不屈服,坚持自我。作品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想象新奇,用香草美人来象征自己高尚的品格,文采绚烂。他擅长创造由神话传说虚幻与自然现实结合的境界,表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作品夸张的描写,映射出诗人的品格异常的崇高,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质。“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4]他高超而独创的艺术技巧影响了后世无数作家。这种浪漫主义的特点正是屈原的才华之所在。司马迁在肯定其人格之余,对其创作的《离骚》也大为肯定,认为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诞生,与屈原这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受到不该有的打击和迫害是有关的。在那个艺术经验积累少的时期,意象与手法的创造与作者超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有绝对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公引入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长诗《离骚》。“我们在阅读《屈原列传》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离骚》中与此相对应的成分,从而使得《传》《骚》之间形成为坚强的互证关系,同时也造成了《屈原列传》浓重的抒情氛围。[5]所以说屈原确实是一位前无古人、才华横溢的浪漫诗人。
其次,屈原是一位忠君爱国之人,在传记中,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即使自己的遭遇很悲惨,他也不忍心抛弃自己的故国。他虽然出身贵族,但自幼勤奋好学。《屈原列传》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文首点明早年的屈原受楚怀王信任,任三闾大夫期间怀着一片忠心与怀王商议国事,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在国家方面主张清明的法度,提倡任用贤臣。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日益增强。但无奈奸臣当道。在修订法规时他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当时令尹子兰、上官大夫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运用奸计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6]。在公元前305年,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这并没有改变楚国灭亡的命运。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楚怀王囚死秦国。史公突出屈原忠君爱国的品质。他长于辞令,敢于直谏,把国家的安危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劳任怨地燃烧着自己。他一生跌宕起伏、怀才不遇、遭奸佞陷害,在文中,他的一生如一副画卷,缓缓展开。端午节延续至今纪念屈原,司马迁对他的客观评价是最好的证明。
司马迁刻画的史公具有独特的高尚品格,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屈原行至江滨时,出现渔父这一形象:“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7]渔父的话代表世人的普遍观念,屈原有自己的坚守,他期望与自然界的纯洁、美丽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坚决不混入世间。司马迁将屈原的作品《渔父》引入传记,塑造渔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形象,在对比中展现屈原艰难的处境,侧面展现出他的孤独、苦闷的心情,将他的高尚品质衬托得愈加突出,文章节奏张弛有序。
(二)《屈原》中勇于斗争的屈原以及其他人物形象
在《屈原》中,屈原同样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更突出的是他勇于和恶势力作斗争。在剧作中,他性格两面性的冲突减少,侧重于爱国与热血一面的大力渲染,不同于传记中的孤高自傲,他“在这战乱的时代”[8],心中时时牵挂的是国家。他“沉着而沉痛地”[9]劝诫楚王,“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10]。他斥责南后“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11]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少了几分无可奈何,面对昏庸专横的楚王,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满腔愤怒,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载他到“那没有阴暗,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岛上去”“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12]“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13]叙事节奏快,塑造的屈原具有更强烈突出的爱国特征,他的爱国是显性的,敢于直谏,遇到黑暗势力的阻挡及陷害,他敢于呼喊,戏剧采用“颂”的形式展现他如火的性格。
历史剧作中,郭沫若还塑造了许多典型的次要人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婢女婵娟,她的身份让子兰、宋玉等自认为高贵的人所不屑,但是到最后,她展现出来的不屈的意志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误认为屈原死了后,任凭别人如何劝说,不为所动,她怒喊“我的态度怎样,我的态度就跟先生一样,先生说过:‘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先生绝不愿苟且偷生,我也是绝不愿苟且偷生的!这就是我的态度!”[14]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来,婵娟是当时有伟大精神的年轻人的代表,尽管他们没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有着当时的黑暗统治者身上所缺乏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婵娟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代替了屈原的牺牲,她觉得光荣和幸运,当时的百姓已经遭受了百年的屈辱,是选择继续接受压榨,还是团结起来奋力反抗,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婵娟这个人物形象就是典型的反抗者,郭沫若在塑造该形象的时候,人物语言通俗易懂,动作表现爱憎分明,这些叙事特点使得该剧在演出时让婵娟这一人物很快被观众接受和理解,并且联系到当时的生活环境,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达到批判黑暗统治、振兴中华、团结人民的创作目的。
屈原仍然是那个才华横溢、忠君爱国的屈原,但在后面的作品中,他的心中多了燃烧的熊熊怒火,他不再宁肯“举世独浊我独清”,而是勇于投入到污浊的世间,竭尽自己的力量,呐喊、拯救污浊的世间,痛斥黑暗的政治,这是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屈原形象的最大不同。
二、叙事内容与叙事手段比较
司马迁对屈原的形象塑造主要是他忠于国家与人民的积极一面和无可奈何的孤高的消极一面。所以传记的主题歌颂主人公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明道德之广崇”,[15]将屈原这个正面形象与很多恶势力比较,运用对比的方式,用概述调节叙事节奏。运用侧面烘托的手段展现其精神。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是愤怒的,一腔热血的他能高喊出《雷电颂》,直抒胸臆,自白充斥着愤怒,剧作旨在抨击当时黑暗的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故采用借古讽今的方法,故事时间远超文本时间,戏剧冲突震撼,在一天中将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演绎展现。
(一)《屈原列传》的叙事内容与手段
作品在尖锐的对抗与冲突中,鲜明地呈现出传记的主题,塑造了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于屈原的经历描写,十分详细,以直接性的描写突出他命运的悲惨。文中“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16]一篇之中三致其志,他一心想要为国尽忠,为国家贡献自己的生命,这份一腔热血遭遇的是流放。
《屈原列传》对屈原的刻画在与其他形象的对比刻画中体现出来,与屈原悲剧命运相关的密切人物是楚怀王,对他的细节刻画到位,“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17]怀王这一庸君,与屈原此类忠臣一个是消极躲避,一个是积极应对;楚怀王听信奸臣,不听忠言相劝。运用了屈原与楚怀王的对比的手段,还有屈原与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都能形成对比。被比较的有屈原的君主,他的国家敌人还有政事上的意见不同的大臣,而另一方只有屈原一人,屈原这一孤独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对比早年屈原的这种孤独感与失落感深入人心。
在叙事内容上对楚怀王的刻画有侧重,在屈原的传记中用大量的篇幅将楚怀王这一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原因是他和屈原形成的对比特殊。像屈原和张仪的对立,两个人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一个是楚国,一个是秦国,两个人本就是敌对状态。但是楚怀王不同,他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和屈原是相同的。两人都希望楚国可以日益强盛。目的上一致却为什么导致了意见的完全相左?“王怒而疏屈平”“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怀王怒,大兴师伐秦”“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18]怀王贪婪,脾气比较暴躁,“竟”字可以读出作者对于这位君王的态度,他固执己见,最终导致自我的灭亡和国家的衰亡。楚王的结局令人感叹,更令人感叹的是屈原的命运。连自己效忠的君王都不理解自己,屈原孤独英雄的形象在比较中跃然纸上,这种叙述表明作者将悲剧责任更多地归于君王,在内容上强调君王的过错与固执。
叙事特点有概述,言简意赅,开篇“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19]这一段是整个生平叙事的出发点。几句话将其生平展现在读者面前,背景性的介绍概略地写,这样避免了因刻画人物一生导致地繁杂。简明引起后面的叙事。其实当时的关于屈原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对于司马迁来说,搜集关于屈原的资料并不全面,因为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收集资料的方式常常是亲自考察,用这种方式弥补资料的不足,再通过侧面刻画的方式塑造屈原的艺术形象。最终使得传记很流畅,屈原的形象丰满。屈原的春风得意的为官生活过后,他的人生转折到来,上官大夫进谗言导致“王怒而疏屈平”,后来有一系列矛盾产生:张仪访楚、楚齐绝交、伐秦失败,最后以屈原沉江的悲剧结束,楚王被杀的个人悲剧和楚国破灭的国家悲剧,这种悲剧性灭亡形成了传记开头君臣和睦和结尾悲惨的强烈对比,使得作品跌宕起伏,文学性强。楚怀王是次要人物却是主要被聚焦者,占很大篇幅。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显然也是与屈原事迹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联,采取侧面烘托的方式恰好弥补这一不足,司马迁在叙事手段的巧妙配合,造就了流传千古的名篇。
(二)历史剧《屈原》的叙事内容与手段
史公在刻画形象时采用对比的手段,在叙事节奏上张弛有度,尤其是概述与侧面烘托,总体看来节奏相对缓慢。在历史剧作《屈原》中,叙事节奏明显较快,如作者所说的写成只费了十天,但其经历了二十一年之久。历史上的屈原出身富贵,地位崇高,历史剧的体裁不允许作者对他的地位以及发生的事件长篇大论。他的创作具有爆发力,“郭沫若对戏剧性追求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使人物在各自意志的指引下迅速行动起来并发生意志冲突,人物的意志冲突作为情节的基础进一步突显了情绪的感染力。”[20]为了使戏剧冲突紧张集中又能真实地体现屈原的“历史精神”。他采用了把屈原艺术生活的“一天”与历史上屈原的“一生”有机结合起来的手段。戏剧展现的是屈原从清晨到半夜一天的时间,表现了屈原悲剧的一生,管窥全豹。
在艺术方式上,郭沫若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恰当结合。屈原作为伟大政治家和诗人的悲剧一生是历史记载客观存在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也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他的联齐抗秦主张被昏庸的楚王否定,驱逐出朝廷。作者在创作中将这种历史真实,通过艺术形式加工之后呈现出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为了使戏剧冲突高度集中的表现屈原悲剧的“一生”,他继承与发扬传统美学精髓,在传情达意上采取了诗化抒情方式,在戏剧结构上又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形式,强化了戏剧的表现力,“他还认为剧是诗的分化,是诗的一个分支。听以他总是以诗写戏,戏也便成了诗。他把早期几个剧本称为‘诗剧’并收入诗集。”[21]以表现屈原的不屈精神为主,选取各种有用的材料构成屈原生活中最紧张激烈的一天,最终塑造了爱祖国人民、光明磊落,忠贞不屈,敢于同恶势力顽强斗争的伟大政治家和杰出诗人的形象。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具体来说,第一幕,清晨,屈原漫步橘园读诗,虚构了小人物——侍女婵娟,这个人物在《史记》中并未出现,在婵娟身上,有当时底层群众正直的影子,誓死守护家园,不屈服恶势力。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戏剧这种演出形式还不能被底层群众广泛接受,创造这个人物,对话采用白话,观众容易理解其涵义,起到很好的呐喊作用,具有强大的时代性。第二幕,宫廷中屈原被陷害、被罢官,其他人物陆续登场,贴合历史,语言进行大胆的创造。第三幕,《招魂》是屈原代表作,剧中出自老百姓之口,这反映屈原的创作来自群众,来自现实生活。第四幕,屈原向危害祖国的罪恶势力展开了勇猛的进击。不同于传记中的无奈和落魄,在这部分叙事内容上,屈原表达自我的感情酣畅淋漓。第五幕,“烧庙出走”,屈原终于高喊出感人肺腑的人生之歌——《雷电颂》,一曲高歌在演出时以极强的感染力给迷茫的观众们极大的震撼。作者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积极反共、迫害抗日志士的政治阴谋和卖国行径,以历史事实反映现实斗争,在感情奔放的剧本中,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了与史公笔下不同的热血屈原。
两部作品,一部采用对比的方法,在多方冲突中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忠君爱国又孤高自傲、无可奈何的忠臣形象,概述使得文章多了几分真实,形象贴近历史,言简意赅,是优秀的史传文学。另一部进行大胆创新,将屈原一生的经历浓缩在一天当中,对于历史真实中空白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与创新,他少了几分无可奈何,多了几分勇敢无畏,这时的他能够高歌《雷电颂》,警醒世人,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束强有力的光,一点点驱散愚昧的黑暗,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手法中表达强烈的爱国主题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痛诉,节奏感强烈,全文更具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