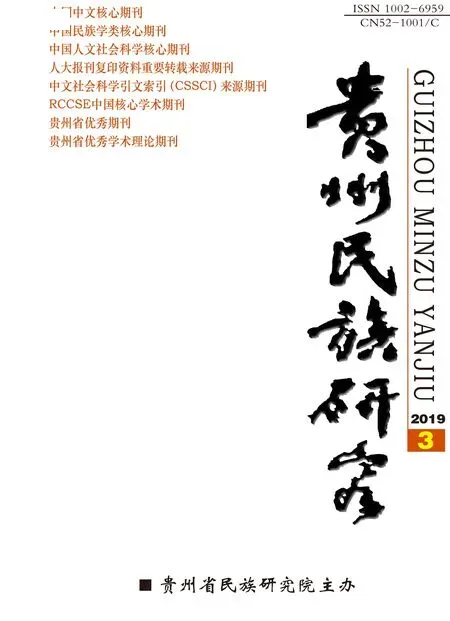民族经济法中非制度性渊源剖析
2019-03-17胡金华
胡金华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01)
“诸法合体”是现代法学门类审视下民族部门法的基本特点,“习俗镶嵌,文化延伸”是民族经济法法律原始形态和法律渊源的基本浓缩。一方面民族经济法所调整的民族经济关系与民族经济活动是传统民族文化习俗形态最为雄厚的环节。比如:维吾尔族群众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始终恪守童叟无欺的诚信法则,并在长期的经济习惯法锻造中成为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法理学前提,并在维吾尔族习惯法中被视为“黄金法则”。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活动所附带的群体性喜闻乐见的经济活动法则,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演变为朴素民族经济法。比如,早期东北赫哲族群众以狩猎为基本经济形态,在狩猎过程中按照先来后到确定“暂时性狩猎权”,随着赫哲族群众经济形态由狩猎向农耕转变过程中“暂时性狩猎权”也一直延续,成为赫哲族群众妇孺皆知的经济法则。当然,基于法的社会性认知,民族经济法渊源中制度性法律渊源始终是显性的主导因素,这是法的阶级性的基本体现[1]。而非制度性渊源虽是隐性却不可忽视。所谓非制度性渊源,是指与社会机制相对应的环境和潜在制度性的总和,既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聚焦而成的、众人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规范性文化与经济环境,又是社会制度性机制在经济领域的潜在影响力。“诸法合体”本身是民族经济法在习惯法发展中的必然趋势且难以在现代法学视域中剥离,因此,探究民族经济法中非制度性渊源,是民族经济法的历史性审视和现代性对接。毫无疑问,民族经济法的非制度性渊源是民族经济思维指导下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非制度性解读。
一、基于法社会性审视民族经济法的发展
民族经济法是在诸法合体的民族习惯法中不断分离的部门法形态[2]。相对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民族习惯法可成为民族地区经济法的重要渊源,基于文化视域和跨政治机制下的民族经济法,主要有以社会运行机制为主体的经济法和民俗文化中潜在的经济习惯法,以社会运行机制为主体的经济法中,封建政权的制定法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民族地区地方政权运行过程中的经济法,比如, 《吐蕃六法》《十五法》《十六法》中对税收等经济法有着明确的记载,牛退税对畜牧肉类征收税赋、按照耕地量征收税赋等税收法律都有规定。第二类是中央政权在民族地区设定的制定法,比如,明清时期土司制度附属下的自然资源配置、经济纠纷化解等经济法。第三类是民族地区村寨、村寨同盟制定的经济法规,比如,哈尼族“牛宗碑”、彝族“天规”等都有自然保护等朴素经济法[3]内容。民俗文化中的潜在经济习惯法通常以乡约寨规、宗教文化为载体,比如,佤族关于雇佣关系、土地管理均有详细的规范约束。当然,民族经济法在历史的推移中经济法权益性不断扩张,本身的法律渊源也就不断扩散,涉及民族群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民族经济法中典型非制度性渊源剖析
(一)背靠经济形态中的经济法则
民族经济法是特定经济形态在群体活动中的规范性剥离,从民族经济法所依托的经济机制而言:民族经济法中非制度性渊源是民族经济转型中法的历史渊源与本质渊源的文化截取。一方面在特定经济形态中民族群众将自然敬畏和感恩自然的行为准绳习惯性移植到经济活动,并在历史的推移和法律载体的演变中成为群体必然遵循的经济法则[4]。比如,鄂伦春族狩猎生活中尤为注重可持续发展,禁止捕捞幼苗、砍伐树木要采取砍伐与种植相对应的原则,在集市买卖中忌讳且禁止买卖幼苗。而在鄂伦春族由狩猎向农耕转型过程中,狩猎时期的经济法则被无形地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成为农耕时期重要的经济习惯法渊源。另一方面,民族经济法在不同经济形态的转型中,因规范意识的单薄和社会阶级基础的延伸,前一阶段经济形态中的经济关系被上升至后一阶段的“法律理论”并在参照中不断渗透,逐渐成为民族习惯法重要的法律渊源。比如,五指山一带黎族不管是采集时期还是农耕时期,注重买卖自觉的“拜贡”,从野果到农产品,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始终秉持[5],并未因经济形态的变迁而搁置。同样哈尼族向封建社会转型时部落之间的纳贡,成为领主征收赋税的最早雏形,在此后的社会转型中传统的纳贡形式逐渐成为习惯法的法律渊源而不断被制度性习惯法所采纳。换言之,背靠经济形态中的经济法则之所以无形地被沿袭,关键在于本身作为经济法渊源的适用。
(二)习俗文化中的经济活动规则
习俗文化中的经济活动规则是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摇篮,是民族经济活动规范和经济关系确立的潜在规则和基本原则。习俗文化中的经济活动规则作为民族经济法典型渊源,将非制度性渊源的法律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6]。
一是乡土习俗文化中经济活动规范在传承中的法意识上升与规则的法律效力凝聚。民族乡土习俗是法社会性涉猎最为广泛的文化载体,乡土习俗文化以其妇孺皆知的大众性,确定了资源配置的形式和经济活动的框架性规范。比如,彝族、门巴族等民族群众通过乡约寨规中的习俗文化,沿袭区域性基本经济规则,在资源配置中注重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结合,特别是门巴族既允许“差巴”私有的存在又明确特定区域土地、树木的公有制[7]。“寄赖”本是京族典型乡土文化,随后作为经济规范中的重要渊源,至今是买卖退换中矛盾化解的有效依据之一。
二是家族宗祠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在不断辐射过程中的扩散。家族宗祠是民族群体基本社会组织形态,在家族宗祠经济活动中,家族内部社会运行所依赖的财政、税收等规则和彼此等级关系附庸下的劳动关系的确立都需要家规、宗祠文化的约束,并不断成为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重要组成。比如,苗族群众在采集经济时代,尤为注重商业欺诈和不正当竞争的抑制,对不正当买卖、欺诈性商业活动除家族内部经济惩戒外,还取消经济活动的主体性身份。在长期经济习惯演变中,此类惩戒和约束成为苗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重要依据。
三是民族经济习俗文化中经济活动规则法律文化的载体性接纳。以乡约习俗文化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规则作为民族经济法法律文化的基本蕴含和有机统一体,是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社会性的集中反映。一方面在乡约寨规文化中,民族群体通过习以为常的约定性经济活动法则调整经济关系。而后在法制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为经济法的理论性渊源之一。比如,纳西族群众在民族文化《普称乌路》中明确规定“禁止采摘和买卖尚未成熟的果实”,否则将会受到村寨惩戒和神灵诅咒的双重处罚。同时民族习俗文化对法律价值位阶也有所反映,比如:哈尼族在自然资源配置、环境保护领域,同一规定的法律渊源位阶也逐渐凸显,除家族规定的破坏林木、山林所属外,按照家族内部约束、村寨乡约、部落协定的效力对应协定。另一方面,乡约习俗作为民族经济法沿袭的文化载体和法制环境,就法律渊源而言:乡约习俗的权威性在经济习惯法形成中逐渐被继承。比如,哈尼族在典当、雇佣中受乡约文化的影响,禁止有偿开展,而后在习惯法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天规”所吸纳。
(三)宗教文化中的“精神性信赖”
宗教文化是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基本源泉,是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最终归宿。特别是宗教文化中的“精神性信赖”是民族经济法不可规避的法律渊源,宗教文化对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神秘性的浇筑,超脱了法的社会性,为经济法的理论渊源植入了难以调整的神秘权威。比如,哈尼族“天规”、彝族“毕摩”,自然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宗教文化强化法律效力。因此,任凭政权的更替、经济基础的变更,宗教文化中的“精神性信赖”始终成为活动中最令群体遵从、信服的经济规范性渊源[8]。比如,维吾尔族群众在伊斯兰教教义的熏陶下,除在经济活动中推崇童叟无欺的诚实信用原则外,在潜移默化的宗教文化影响下维吾尔族群众对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极为排斥。
此外,同宗教文化相伴而生的是忌讳文化。忌讳文化对经济活动规则神秘色彩的塑造是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最为显著的组成,是民族经济法历史渊源的重要依据。忌讳文化是规范性、约束性最强烈的非制度性文化载体。忌讳文化在民族经济法的渊源中,具有以时间的维度塑造法不可逆的社会效力。比如,纳西族受东巴文化的影响,在自然保护当中毫无保留地映射到经济法思维当中,成为典型的非制度性渊源。老虎等作为纳西族图腾和东巴教所信仰的神灵,在资源配置中也禁止买卖交易,此外,受东巴教等级关系的影响,雇佣关系、劳动报酬的差异性,也逐渐被吸纳到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当中[9]。比如,门巴族在宗教忌讳的影响下忌讳破坏草场、私自开拓草场的行为,主张草场公有制。在此后的门巴族习惯法类似规定均有体现。仡佬族通常以山林中最大最粗的树作为神树来祭祀和崇拜,并通过忌讳文化的形式逐渐渗透到生态保护当中,成为仡佬族重要的法律渊源。
神话传说文化对法阶级性权威点缀的传递也是宗教文化在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经济习惯法表现形式。比如,仡佬族推崇祖先崇拜,在神话传说中通常以祖先遗德为主题,在自然资源配置和土地管理的经济活动和习惯法中,推崇祖先崇拜的法律文化不断被经济习惯法所遵循。一方面在以坟墓为主的土地资源管理中,仡佬族老人、长辈具有任意选择权和使用权,但是并不能支配所有权;另一方面,在宅地基使用权中,仡佬人享有平等权,且禁止“煞星门”(门对门)。此外,民族神话通过警世骇言赋予法不可逾越的权威。比如,佤族神话传说“司岗里”对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当中以图腾、祖先崇拜的形式为民族经济法规范赋予神秘效力[10]。
(四)制度性习惯法中的基本嫁接
制度性习惯法中的基本嫁接是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的主要内容,是民族经济法赖以延续的基本法律价值体系。一方面制度性习惯法在经济基础变更、政治机制运行中始终以文化形态的姿势影响着下一阶段的习惯法机制。比如,“天规”“牛宗碑”作为哈尼族习惯法的重要渊源,本身同社会政治机制相吻合,但是,在时代不断革新中,“天规”“牛宗碑”作为民族经济法的重要文化载体,不断充实着民族经济法的情感认同、法制理念的互通[11]。另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经济法在转型中始终要以制度性的思维凝聚经济法规范的合理性。比如,红河地区哈尼族雇佣法,在长期的发展中成为当前佐证劳动法合理性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关于“定工”的规定一直沿袭先前习惯法的思维。整体而言,首先,制度性习惯法在历史的变迁中通过嫁接成为民族经济法的渊源,并在实践中不断凸显出法律渊源的延续性价值。诸法合体的民族法律机制中经济法本是现代法学视域下的民族传统法律规范和法制观念习俗的集合。民族传统习惯法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对经济领域的涉猎,使得在法思维发展过程中不断成为民族经济法的影子。比如,傣族习惯法中经济互助行为的规范性调整和有效惩戒,逐渐成为傣族经济法领域通用的法则,特别是村寨公约当中至今还保留着传统习惯法的影子[12]。其次,依附于政治机制的习惯法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在民族经济法整合中不断成为本身法律渊源的引线。民族习惯法中关于群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调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张,并在相互串联之中为成为民族经济法的历史渊源。当然,在制度性褪却政治色彩时也不断浓缩为民族经济法重要的非制度性渊源。比如,早期社会分工不明显,商业发展缓慢,但在农林经济活动的调整中以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共有为自然资源共享提供了便利。随后,随着村社、村寨联盟关于经济法则制度性的出现,为怒族经济法的补充提供了渊源同时凝聚了较为完整的参照[13]。再者,制度性习惯法在当代民族经济法中充当着调和与补充的法律渊源角色。比如:藏族经济法中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经济法规范基本上均源自不同历史时期习惯法的基本要义,《吐蕃六法》等习惯法对猎杀鹿等行为给予了明确处罚规定,除特定的以财代罚外,经济领域的越轨行为不断纳入刑法当中。这些朴素的经济法思维逐渐成为一种法律文化被延续至今,成为当前藏区经济法的法律渊源和重要补充。
毋庸置疑,在诸法合体、行政主导下的民族经济法基本以生产质量、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为基本形态[14]。在自然敬畏的法思维中,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则以朴素生态理念为向导,以生产环节、物物交换质量中的乡约习俗为枢纽,以宗教文化中潜移默化的精神性信赖、世代性传承为经济活动准绳,并在制度性习惯法的基本嫁接中转变为无形的约束性潜在规则。因此,审视民族经济法非制度性渊源要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文化载体,注重潜在约束性经济机制隐性价值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