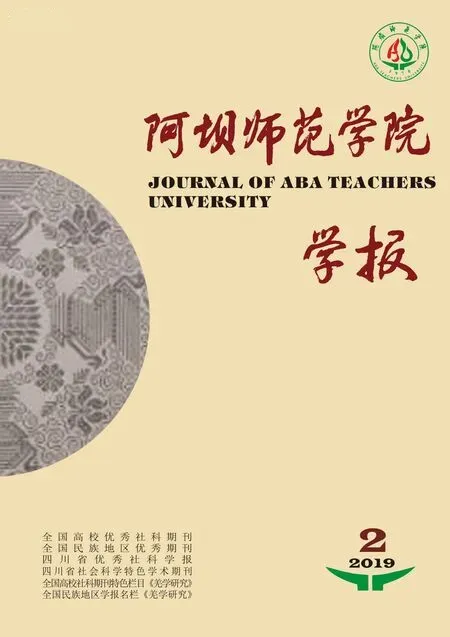日常生活视角下侗寨的秩序构建与侗人的自我实现
2019-03-16孙旭
孙 旭
在对社会秩序的探讨中,日常生活中面对面互动及言语交流日益受到重视,作为行动者的人不再被看作受社会结构框定的提线木偶,具有了在行动中形塑自我进而织造社会的能动性[1]。这一视角强调日常生活的“拟剧性”特征和仪式化行为对自我的建构[2],言语交流隐含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功能[3],互动过程的文化表征[4]和政治性[5],情感与感觉的私人性与集体性[6],更在后现代的潮流中,反思人类学调查者于田野的介入和当地人互相缠绕的关系[7]。
贵州黔东南侗族社会,群体的归属和认同范畴,如“款组织”、寨集体、房族、年龄群体等,为侗人有秩序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支撑,基于此,人群被分类并建立起了内部运作和外部交往的规范,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分享的集体观念和共同体意识,成为了他们建立认同和划分界限的标准。
相对于这些明确的范畴,侗人的日常实践无时无刻不在与另一套“细碎的文化”——爱面子、重礼性、讲闲话、好议论等发生关联。与结构性范畴不同,“细碎的文化”应对的不是群体类属的问题,虽然二者对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集体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前者赋予个体在集体中的“身份”,后者体现着个体在集体中寻求“地位/位置”的努力以及个体对集体道德价值的内化。
“细碎的文化”展现出的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为人们所定性的“就应该是那样”的实践原则,它们并非外显的、结构性的规范,而是蕴含在人们持续的互动中。个人的努力和他者的看法在这里有同等意义的重要性。它们和结构性范畴并非泾渭分明,恰恰是这些“细碎的文化”为侗人的实践提供了贯通个体与集体的可能:个体的实践既将集体赋予的身份涵括进来,为个体在集体这一既定框架中游走的话语,又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着集体的秩序。
一、 爱面子、讲礼性:侗人生活中的“自我修养”①
侗人十分重视“面子”和“礼性”。讲礼性是一种一般性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礼性”来行事,懂礼是一个侗人在当地生活中应有的“修养”,也是众人认可的评判标准。一旦行为在礼性要求之外,就会“没面子”、“丢脸”、“不好看”。
中国语境中的面子研究,通常将面子和人情联系起来,将之看做一种与个人的身份地位、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性概念[8][9]。将“面子”问题置入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深究,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适用性和动力的认识。“面子”和“面子功夫”所揭示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的“拟剧”性,可溯源到戈夫曼[10]甚或莫斯②,尽管它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有不同言语表达,却代表着个体面对集体生活时可能会发生的对集体意识和道德价值“归化”与“内化”的普遍过程。
(一)我的“失礼”经历:情景化的饮酒礼俗与社会规范的自我呈现
我在老人丧事中醉酒的经历令侗人对礼和面子的重视展露了出来。我初到南寨③两个月余,住在南寨吴昌德的家中,寨中一位和吴昌德同房族的百岁老人突然过世。当地人根据我的生活所在,把我当作了吴昌德房族中的一份子,和房族成员共同承担起出殡和接待客人的工作。上坡安葬回来后晚餐时,我和几个同房族人同桌吃饭,我一碗米酒尚未喝完,就晕头转向,举着碗提议一同干杯,却被同桌的人赶忙劝住,讲这是丧事,不能干杯。可我终于还是在一碗酒之后就彻底醉倒,被人搀扶回去。
第二日,尽管吴昌德的儿子吴永学告诉我醉酒后没有做什么失礼的事,但他也讲,一般白事是不能醉酒的,否则老人会说(意思是老人会批评),别人会认为醉酒的这个人不懂道理。对此,永学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当地人的话,老人肯定会说的,但我是外来的,老人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待我和吴永学一同来到了寨中坪子上,寨里人见我来了,话题也转到醉酒的事上,一个早晨的闲聊和讨论,人们对我的醉酒问题,偏向了寻找解脱的一面。其一是归结为我喝酒没吃饭,所以才醉了;其二是说那些和我同桌的人的不是,他们明知道不能喝多还在劝我喝酒;其三是说百岁过世算是喜事,醉酒不会受到责难;其四是关于我的身份,在他们看来是“既是主又是客”,在归属和活动参与方面,我已经算是南寨的一员了(主),但在对我的礼俗情理判定上,还是要用“外来的大学生”(客)来定位。
寨众对于我这次的“失礼”行为,一直做着消解的努力,也反映着他们的认知中实践关系场的界限所在。在他们看来,虽然我可以通过学习和掌握地方文化知识而获得对他们的理解,但我依然未在,也不必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占据一个位置。这个关系场,常常只能用“当地”指代,但模糊之处在于,其并非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应的礼俗构造出的意义空间。
然而,当地人替我消解“失礼”行为的努力,并没有掩盖他们因为这一“失礼”行为本身而感到不适。“既是主又是客”的定位并非万能,对事不对人和转移责难,成为他们调和这种不适的策略。此后,一旦遇到办酒的场合,吴昌德一家人总会提前提醒我,再不可醉酒了。寨上的人也不时提起我醉酒的故事,在每次喝酒的场合特别地照顾我。“失礼”行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那种他们彼此知晓、如履薄冰地对待却难以用概念把握的“关系”的形象化展示,人们会将这一”印象“转变为富含教育意义的故事,提点着每一个听说眼见的当地人如何在这样的“关系”中生活。不适感来自他们对于“失礼”背后所强调的情境化的言行规范的普遍接受,遂我的故事于他们,成为了一段深刻的记忆。
当我因为“客”之身份享受着众人对我的“赦免”之时,作为寨里的人却背负起了本应属于我的责难。一日,我醉酒时与我同桌的吴启辰和吴启明两兄弟就突然邀我吃饭。晚饭话题也和醉酒有关。二人先是说我们都喝的一样多,怎么也料想不到我就醉了,讲到我当时想要干杯,还是他们将我阻拦了下来。又提起醉酒的事,寨上的人肯定会说闲话。
饭后回到家中,吴昌德一见我就问:“你去吴启明家里吃饭啦?”我点头称是,他继而说:“哦,哦,应该的,他们是应该请你吃顿饭。”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应该”从何而来?后来吴永学同我讲:“他们在那桌子上是长辈,那天你醉酒,他们也有不对。这两天在寨子上,大家都在说他俩,不分场合要你喝酒,把你搞的醉酒了,所以他们今天才叫你去吃饭的。”原来这是一餐“赔礼饭”。人们将本应指向我的矛头转向了他们,他们成了“不好看”(丢脸)的人。此次请我吃饭,是他们在众人的压力下弥补他们“不好看”的方式。在言谈间,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和“不好看”划清界限,以表明他们在当日的作为,都是合适的,事情本身若不是与我无关,也至少是一个“意外”。
至此,对他们来说,“请客赔礼”有着对外和对内的双重意义:对外来说,涉及“礼性”,侗人对之如此看重,即便他们善意地消解了我的过错,却还是无法容忍过错本身,从而从自己人中找到了“替罪羊”,他们请客赔礼也就成了“应该的”行为;对内来说,二人迫于外界众人压力的赔礼行为,其目的,不仅是作为一次展演让自己能够在寨众那里重获认可,更是通过与“不好看”划清界限来纾解这一无缘无故被贴上的“污点”,在自我实现的层面上,贯彻自己在这一关系场中从未偏离过(绝不会偏离)的人生立场。
(二)“脸脏了”与“送炮洗面”:失礼的地方性表述与禳解仪式
吴广威结婚让南寨人忙碌了起来。结婚当天,寨上的老人都被邀请到古楼中吃午餐,由房族的人挑吃的过来。老人们聚在古楼里正吃着,吃过饭的亲戚陆续进到古楼里休息,吴广威的堂姐夫吴泰安就是其中之一。吴泰安看到有些离席的老人桌上还留着吴广威家送来的礼肉,就问怎么回事。老人说:“都是肥肉,吃不下,不要了。”吴广威一下子火就上来了,对着老人训斥他们不懂礼,这是吴广威办喜事专门送来的礼,是对他们的尊重,他们还挑剔。他边说边把桌子上的饭菜礼肉收到筐里,说道:“我是吴广威的姐夫,你们既然挑剔,不尊重他,我就替他把东西都挑回去,你们也不用吃了。”这些老人中有几个就同吴泰安吵起来,讲你这样做也不合适,还有老人没吃完呢,就把肉挑回去,对老人不尊重。两边相争不下,一直到吴广智(吴广威的哥哥,此次婚礼的主事人)从新娘家的寨子赶回来调解才散场。
晚上吴泰安和另一寨子的石老师在一桌吃饭,石老师在寨中威望很高,全寨干什么事都听他讲。吴泰安一见石老师就说:“石老师,我今天出丑了,顶撞了老人,要送炮洗面了。”接着将中午的事情经过都说了一遍。石老师开始给吴泰安出主意:“你这么做的确是对老人不敬,但这么做事是对的,还是那些老人不懂道理讲话不合。这时候,你再挑礼回去,送炮洗面,那么就是树了榜样。以后再没有人敢这么做了。”听了这话,第二日中午,吴泰安逐一通知了全寨的老人,中午放着炮,挑着礼肉和饭菜到古楼给老人们吃了一餐。此次的不快才算化解,之后,寨上再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
送炮洗面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侗人有俗语“犯天,打天醮;犯地,拜地公;犯人,送炮洗面”。意思是对人做了不敬的事情,出丑丢脸了,就像脸上有了污点、脏了,而送(放)炮赔礼道歉,就如同在河里洗净了脸面,将因失礼出的“丑”洗刷掉了。
侗人很少直接表述关于“爱面子”的问题,他们对之的看法,并不是获得正向的强化,而是避免“不好看”、“丢脸”这一负向的行为判定。为了弥补丢脸带来的难堪,当地人发展出了各种方式来对丢脸的行为予以禳解。送炮洗面就是其中最富仪式性的,它以一种富有“礼性”的方式来达至对于失礼造成的丢脸以纠正,为的就是显示丢脸的人并非不懂礼,只是一时激动犯了糊涂,对冒犯的人以赔礼,也就将自己复归到了讲礼性的“正轨”之中。这些禳解方式的显著特点就是面向公众。正如丢脸会引发集体的责难一样,“找回脸面”也必须从集体的评价和认可中才能得以实现。这进一步说明了“爱面子”和“讲礼性”对于我们理解侗人日常实践的重要意义,它们揭示了在集体之中个体实践的界限。
二、 讲闲话、好议论:个体行为集体化
“闲话”在南寨蔚然风行。讲闲话和侗人“爱面子、讲礼性”总是相伴相生,失礼的行为必然会引发他人讲闲话,在考虑一件事情做得对错的时候,人们也总是忌惮“别人讲闲话”,“丢脸”往往就和“被人讲闲话”相当,所以才有“不好看”之说。
有关闲话的研究,将闲话视作了一种人类普遍的行为,闲话通常和集体或群体有关,通过将之比喻为一门技艺或艺术,学者们凸显了这一边缘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例如传递信息,强化群体的道德价值观与社会结构的互动[11][12][13]。
在侗寨之中,闲话内容多是负面的、具有破坏性,说闲话也会和当地伦理观念相关联,“有的人就是爱讲闲话”这样的话语常常会作为对一个人的负面评价。“议论”则不涉及当地人的道德判断,而是作为一种常态被接纳,有事众议是当地人处理集体事务采取的基本方式。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或关涉集体的利益,个人不做决断,而是会说 “我个人说了不算,要大家都讨论了,听过了同意了才行”,因而议论也体现着建设性的一面。无论是讲闲话,还是议论,都是一个将问题引向集体的过程。
(一)桥是桥,路是路:吴林开的处世之道
和寨上许多人一样,吴林开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但比寨上大部分人的打工经验都要丰富得多。1984年,他刚15岁就一个人去黎平闯,干过碎石头的苦工,学习了电焊,又自己在黎平开过店。2004年,看到别人都在广东找到不错的活路,便放弃生意不好的店铺,去了揭阳。在揭阳,凭着自己电焊的手艺,找到了一家装锅炉的厂子,一干就是八年,工作不重,工资却不断升高,到了2012年,吴林开因想要照顾80岁的老母亲,辞工回了寨子。
吴林开讲他的打工经历的时候,不时地掺杂着他这些年的人生感悟和他对于寨中情况的个人看法:“比起村子里面的那些人,我的经历要多得多了。我没什么文化,就靠这些年的社会经验。并不是看不起村里面的人,而是觉得他们的经历太浅,许多事不明白。”他也习惯不断地摘取着各种“典故”来表达他积累的为人处世之道:“你知道赵本山吧……他这么红,关键是有人捧他,没人捧他他能那么红?你说是不是。做人是一样的,别人都讨厌你,你肯定不行。”接着,他又提到:“‘穿鞋的人’你懂什么意思么?就是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合适自己的,别人讲的都是没有的,有时候还会害了你。”对于村寨生活,他认为:“我在村里,虽然觉得村里的人不如我,但是人情我还是讲的。我这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只要是违法违纪的,哪怕再亲(的人),也不会帮。但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只要能做到,不管是谁都一定会帮。在村里,我也不爱乱讲话,讲,就都是要有理有据的。”
尽管如此,在寨上人看来,吴林开的行为却没那么“合理合法”。平时闲聊的人总会问我:“你见过他老婆啦?”我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就在纳闷为什么大家会感兴趣这个问题。后来听寨上人说,吴林开还有一个尚未离婚的妻子在广东,和吴林开育有一女一男。现在这个老婆是隔壁寨的人,他从广东回来的时候,前任老婆没跟着回来,他回来没多久,那边的离婚还没办,这边就从高寨接来了现任的老婆,喜酒也没办。寨上的人就觉得他这么做于礼不合,说他是南寨的“陈世美”。有一回人们在坪子上讲起这个事,恰好吴林开走过,坪子上有人就直接冲他说:“你这样不好吧,万一晓奇(吴林开儿子的小名)的妈回来,看你怎么办。”吴林开毫不畏惧,回道:“你们这些在田埂上的,莫要担心我这在河中船上的,我能在河上行,便是有不翻船的把握,不要为我闪折了腰。”说罢扬长而去。
后来他把说那句话的意思解释给我听,一口气列了几条理由:“第一晓奇他妈在那边从事的是不正当的行业。第二她已经签下离婚协议书了,只是还没办手续。第三我家里面母亲生着病,要人照顾,我之前叫过她回来,她却坚持不回来,是不孝。就这么三点,所以不必担心她有什么道理。”至于对寨上人讲闲话的事,他的态度是:“那些人都是不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在那里讲闲话。我这是自己家的事情,我当然是有把握的,我这个人不会乱做事情。这些事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毕竟是晓奇她妈,说了这些对晓奇也不好。”
面对侗寨中集体意识强烈的社会生活,侗人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就像当地人的另一个俗话“桥是桥,路是路”④一样,只要是没有触犯礼俗,也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吴林开的故事,就可以看作这种个人应对闲话时积极的一面。但是,在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中理解闲话与议论,更要注重人们“怎么说”和“实际怎么做”之间的区别和张力。吴林开在言谈间维持着自己不理亏的信念,但在侗寨的日常生活和大小活动中,却一直是疏离的,少有和寨中人一起同坐闲聊娱乐,总是一个人做着自己的事情,身处集体的边缘。到了2014年,他留下母亲在寨中,选择了再次长期去外地工作,离开了寨子。
(二)集体的抵抗:吴勇贵春节跑车遭遇的闲话与议论
吴勇贵在2013年春节前夕买了一辆面包车,每个赶场天,他便开着车在水口和南寨两地拉人赚钱。春节临近,村里上镇上采购年货的人多起来,吴勇贵首先提出面包车收费要从平日里一个人5元涨到7元。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所以他在路上只要碰到跑这条路线上的车,就会拉下车窗同迎面来的车主讲:“哎,涨价了啊,现在春运,都是7块钱了啊。”
刚开始的几天,其他的车主也一同将价格涨了起来,闲话也跟着来了。有的人就说:“人家班车春运涨价,是有春运证的,这些面包车又没有证,凭什么涨价,有本事他们也去搞个春运证啊。”“就是贪钱,尤其是吴勇贵,以前过春节从来没有涨过价,他没车的时候也说过要春运,现在他有车了,就说什么春运涨价。”其他的车主迫于压力,纷纷改回了5元,唯独吴勇贵还坚持7元钱。春节往返街市采购的人多,车辆有限,所以大家没办法还得坐他的车。
过完春节,大家也没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去街上了,就又在坪子上古楼里讲起吴勇贵来,讲他“贪钱”、“做事情不合适”、“不讲人情”。有人说:“像其他的车,那些小孩都不收钱,坐他的车,再小的小孩都要算一个人来收钱。”有的说:“周五学生放学从水口回来,像很多人看着天晚了,学生在路上走,不收钱就拉回来了,都是本村的孩子嘛。他也是从来都要收钱,没钱的还不给上车。”有的说:“别人的车都是拉满了就走了,最多超载两三个。他的车是一路不停地停,不停地装,挤得不行,看着都不安全,还耽误时间。”一来二去,大家竟然商量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以后谁也不坐吴勇贵的车。
对于吴勇贵涨价一事,不光是南寨有意见,南寨旁的另两个寨子也有不满,南寨一做出这个决定,传来传去,一下子成了几个寨子“共同的决定”。过了正月十五,每个赶场天,其他的车来来回回都坐满了人,可吴勇贵的车跑来跑去都没人坐。吴勇贵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得像摆设一样把车停在家门口,闲置了三个月,便又将车转手卖了出去。
闲话的意义在于,通过由闲话引向的议论,人们凝聚起了共识,本来只是几个人在言说的事情,经由公开场合的传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当共识形成之后,本来只是如风的言语,也具有了对于人们心理和日常生活实质的影响力。吴勇贵就在这样的情境下,被集体排斥而导致发横财的愿望破灭。
在两个故事里,闲话和议论总是由个人走向集体而又再次指向个人。要理解闲话和议论如何能够超越个人意图和辩解,产生具体的影响力,仍要将之与群体的集体意识相关联⑤,无论是吴林开还是吴勇贵的经历,都要在一个时刻凸显集体、监管个体行为和消解其能动性的侗族文化语境中理解。闲话展现出寨子中人际关系的实际状态,每个人都通过讲别人闲话和被人讲闲话确立了自己在关系场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包含的地位与价值。村寨中日常生活的实景,就是这种个人化关系网多重交织的状态。同时,正是由闲话转为议论的过程,制造出了一个高悬于个体之上的有强制力的“集体”,这一进程也呈现出侗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并非先验存在,恰在于通过闲话和议论不断被生产与再生产。
结合我自己醉酒的故事,还能看到,一个侗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俗切片式的封闭环境,他们面对着外来人,也面对着外来的知识和经验。Besnier对“闲话”(这里就把gossip译作闲话)研究特别指出,闲话惟有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关系情境和象征符号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同时,经由闲话,也能够从中发现人们在一个市场的、流动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如何表达“地方感”(localness)和“情感的政治性/政治的情感性”(political nature of emotion/emotional nature of politic)[14]。
过去三十余年的时间,南寨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的内部认同、共同体意识并崇尚集体生活的侗寨,卷入在一个日益开放、流动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身处于变化之中,我的故事和吴林开、吴勇贵的故事从”内/外”两个角度构成了互文。如果说“既是主又是客”是当地人在用超越地缘和族群身份的文化属性来表达他们的“地方感”和于变中求不变的群体存在感的话,那么“桥是桥,路是路”则表现出侗族世界和更大的世界并接时加诸于个体的矛盾感。至少是在这几个故事中,闲话与议论的问题也在于,它在构建集体秩序的同时,也将个体逼入了两个世界的夹缝之中。
结语 集体秩序与社会自我的生成性分析
结构性研究所揭示的侗人乃至西南山地民族社会崇尚集体生活的社会形态,其集体观念总被当做一种客观的实在,进而成为研究者理解山地民族社会的立足点。然而,当我日益频繁地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尝试着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时,却发现他们鲜有关于“集体是什么”的清晰的描述。集体,于南寨人,与其说是实然的,不如说是应然的,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文化理念,与村寨中每个个体的主观经验紧密相关。
这里所说的主观经验,指的是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崇尚集体理念的社会中呈现与理念相符的“社会自我”[15],其方式通常不是申明某种身份归属与规范——尽管它与社会结构和规范相关,而是紧密的日常互动与言语实践。不论“爱面子、重礼性、讲闲话、好议论”凝聚性地出现在特定的具体的事件时还是弥散在生活中,总会经由人们的活动产生某种清晰或不清晰的“集体时刻”,在这些时刻中,南寨人促生着集体的力量,消解或约束着集体中个体的自由,从实际的行为和情感、道德层面明确着应有的做人操守。这些时刻是即时的,也会因记忆和言说延续,甚至刻板化为某种具有教育意义的“范例”。这个过程揭示了,经由集体所映射出的社会秩序,在日常中既是习得的,也是生成性的。
注释:
① 根据人类学调查和写作的伦理规范,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论文中的地名和人名,均采取化名。
② 莫斯(Marcel Mauss,又译毛斯)通过跨文化比较和历史溯源,探讨了人的概念和自我的概念形成的理念演进历程。其中,莫斯通过民族志材料说明了普埃布洛和夸扣特尔印第安人中,个体缺乏自治,面具、姓名在个体承担起部落集体特定角色中发挥作用,并提及拉丁语“Persona”的原意为“面具”,意味着个人本性如何以特定方式与集体的道德理想虚构的人物贴合,从而使个体获得被认可的“人”的身份。参见:[法]马塞尔·毛斯. 社会学与人类学[C],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71-298。
③ 南寨是贵州黔东南一个全侗族的寨子,有80余户人,分为六个房族。本论文的田野经历和论述内容围绕南寨的生活展开。
④ 这句话发生在做事情的人都清晰地认识寨中人喜欢讲闲话的情境中。他们用这句话表达的既是一种生活智慧,即“反正做什么都要被说,那就他们说他们的(桥是桥),我们做我们的(路是路),问心无愧就好”,也是在作为个体表达面对集体时的自我意识和态度。
⑤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不在于它多么符合客观事实,而是谣言身后潜在的群体意图和他们的信仰立场一致,他们既在立场上免于‘少数人’的心理危机,又在组织上有群体归属感。所以,一旦深入研究谣言控制问题,我们立刻就闯入了谣言叙述的核心规律:即进入了个体和集体的精神信仰领域,而这完全是一个主观世界。”参见:李永平. 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谣言、流言及叙述大传统[J]. 思想战线. 201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