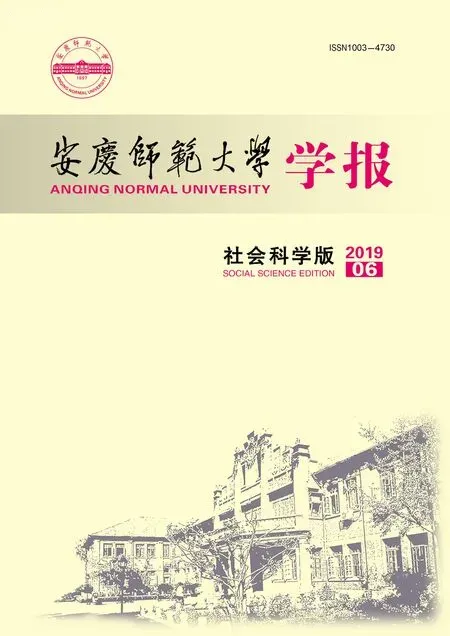多丽丝·莱辛小说文本的叙事形式
2019-03-15章燕
章 燕
(1.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2.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滁州239000)
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的作品叙事形式多变。在写下《野草在歌唱》《玛莎·奎斯特》等描写非洲的现实主义小说后,她写出了《金色笔记》《四门城》《简述地狱之行》《幸存者回忆录》等形式独特的作品,“莱辛的变化并不是一种突变,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1]32。这些小说很难用固定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等叙事范式来归类,而往往杂糅多种风格。有学者指出,“对于莱辛来说,永远不是了解真理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好地讲述,把它传达给别人的问题”[2]499。叙事形式在莱辛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她认为“形式是一种思维方式”,她的思想要“通过本身的形式说话”[3]8。
但对于莱辛的叙事形式变革,历来争议不断。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论莱辛后期作品,为莱辛放弃现实主义,使读者无所适从而惋惜[4]5。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莱辛后期的作品不如前期作品那样光彩夺目,因为她丢弃了文学创作中两样宝贵的东西:为人间正义、公正呐喊的激情和写亲身体验的熟悉题材”[5]79-82。实际上,理解了莱辛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思考,才能真正读懂莱辛的作品,她作品中多变的形式是和她对小说叙事功能的思考密切相关的。
1949年,当莱辛从生活了25年的南罗得西亚回到英国时,她面对的是迥异于非洲的社会环境,她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感知内容和感知方式都不同于本土作家,如何用小说来传达她感受到的独特现实境遇,如何用语言最大限度表达真实等,都是莱辛经常思考的问题。莱辛发现现实主义注重内容,而通过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表达的真实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她敏锐察觉到语言学转向以来,赖以承载作品的语言已无法明确表达内容,因此她转向发掘文本形式,通过文本独具一格的形式来表达思想。研究莱辛从内容到形式的思考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莱辛的小说创作,也能更深刻地理解莱辛思想。
一、真实/虚构的对话
英国学者简妮特·金(Jeannette King)认为,莱辛作品内在一致性在于它们一直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莱辛早期写过大量现实主义作品,《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前三部(《玛莎·奎斯特》《合适的婚姻》《风暴的余波》)等都对早年生活的南罗得西亚进行了详细描述,矛头直指南部非洲尖锐的种族对立。但莱辛很快对这种谙熟的叙事范式产生了困惑,产生困惑的原因是她自小接受的叙事理念遭受20 世纪以来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观遭到解构。莱辛对小说创作该以忠实摹仿世界为主旨还是侧重文本虚构性和语言建构性感到困惑。她自小大量阅读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承袭了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镜像式再现的理念,强调“时刻意识到有一个文本外的世界”[6]15,认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之本。这种现实主义再现论的叙事范式把文本看作再现现实的载体,认为小说是“赖以体现详尽生活观的叙事方法”的“真实生活的一个摹本”[7]79。随着西方理论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学者们开始质疑现实主义着力再现的真实与外部世界是否一致,他们认为小说是语言建构物,文本的虚构性已然消解了真实——看似指涉外部世界,实际是通过语言修辞进行自我指涉,因此建构性叙事范式理论取代传统再现说。这种叙事范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性,弱化文本对外界的模仿功能,但易于使文本陷入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消解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固有的真实/虚构悖论到20 世纪中期愈发尖锐,因为“随着作家理论修养的提高,当代现实主义作品比以往更明显地体现了小说创作的自我意识和内在矛盾”[8]152-160。莱辛意识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与修辞学的复兴之下现实主义面临的危机,但现实主义强调作家社会责任感的理念是莱辛无比看重和珍视的,所以她不断思考这一悖论的突破之法。《金色笔记》《个人微小的声音》《我们选择居住的监牢》和一系列访谈反复述说真实/虚构悖论对她创作的影响,这些作品也清晰记下莱辛思索的轨迹。
莱辛在《个人微小的声音》这篇评论性随笔中评判了当时流行的两类现实主义作品——介入文学和报道体文学,两种文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注重内容的真实,希冀“用最大的忠实来描述世界”[9]182,但这类作品艺术造诣却并不高,莱辛认为它们对文本内容和现实的关系囿于机械反映论,没有找到两者间的动态平衡。
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具有鲜明宣传色彩,但莱辛强调的并非此层含义,在英语中介入(committed)还包含“对什么负责任”的意思,介入就是责任感,因此莱辛关注的是作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如保罗·施吕特(Paul Schlueter)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一文中就认为莱辛是一个关注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介入”型作家,通过提倡个人责任把自己和其他人,乃至世界都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10]65。莱辛认为机械反映式的现实主义会在集体性宏大话语遮蔽下擦抹个人诉求从而消解个体的声音。而个体的境遇和对个人情感的书写能使读者产生代入感,“介入”需以小见大,通过书写个人情感体现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人文主义关怀,传达时代精神特质,她认为“没有信念就不可能介入”[11]6。
莱辛评论的另一类作品是报道式文学。莱辛早年的作品如《野草在歌唱》和《玛莎·奎斯特》等虽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帮助只身带着孩子回到英国不久的莱辛摆脱了经济窘境,却并不能让她满意,相反她认为作品遭到了很大的误解。莱辛认为,人们对她作品的兴趣主要来自对遥远非洲大陆的猎奇心理,把她的小说作为了解殖民地的报道体文学。实际上这种小说功能的变化具有时代特色:20 世纪中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剧,因此人们渴望了解生活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而小说是种便捷的途径,这使得小说“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12]64。《泰晤士报》说莱辛的作品“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和新闻报道极为类似”[13]8,《时代周刊》认为《野草在歌唱》是对社会各种罪恶的接近于新闻式的有效报道。这显然和莱辛对自身作品的期许是不一致的,莱辛希望通过作品传达的是修辞审美的价值观,而不是区域性的新闻报道。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弗斯特(Lilian R. Furst)所说,现实主义是通过遮掩修辞的痕迹来维持现实的幻象[14]101-126。可是小说毕竟是修辞的虚构,修辞是小说美感的载体,如果小说变成报道,就减弱了自身的美学价值。实际上,小说的真实在于其可信性而不是其描绘内容的逼真,小说的价值在于通过描写和现实世界具有相似逻辑的虚构世界来获得读者的共鸣。
二、语言/表达的悖论
意识到注重内容的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问题,莱辛开始她的实验写作,她所追求的是对个人在时代潮流中的思想变迁和命运沉浮的个性书写,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但她对这种偏内心的叙事写法是否能表达外界的真实持怀疑态度。这种困惑在《金色笔记》中表现得很突出,所以莱辛一改过去线性叙事的现实主义写法,而采用实验性的元小说书写,这种保留擦抹痕迹的书写方式也成为作品的一大叙事特色。主人公安娜先按现实主义手法写了一篇小说《战争边缘》,但她发现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对原材料的事实进行了篡改,与自己所回忆的真实情况有巨大差异。但因为迎合了人们的审美期待,小说大受欢迎,不过安娜自己很失望,觉得没有表现出她希冀表达的真实,“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12]63。出于对这一传统写法的失望,安娜在“黑色笔记”部分重写了马雪比旅馆的那段经历,这次她不是以编造故事而是以笔记体的方式回避虚构,力图呈现真实,可是“虽在描述方式上和格调上与前者有很大不同,但思想内容与第一个文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15]95,莱辛觉得无论故事还是笔记表现的都不是现实中具有个人情感和思想的人物,因此通过现实主义书写方式进行的创作失败了。最终她领悟到,无论对原材料进行怎样的加工,如果单纯强调模仿外部真实、过于注重内容的真实性,作品就不会把重心放在表现个体的境遇和对个人情感的书写上,而莱辛认为这才是小说需着力刻画的。
语言学转向以来,理论界开始意识到小说的虚构属性不需要遮掩。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认为“虚幻就是现实本身”[16]287,觉得真实不指涉外部世界,而仅指涉文本内在结构,就是对通过语言虚构建立起来的文本现实的阐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小说内容的逼真性是通过文本中充斥的细节来维持“指涉的幻觉”[17]84(the referential illusion),认为小说的真实不依赖于对外部现实的镜像式模仿,而是通过细节来营造“虚构”以捕捉时代内在精神特质。
莱辛感受到时代氛围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叙事范式变化,并用文字做了传神记录。她认为时代变化导致语言歧义性,而这一语言的变化给表达内容带来困难,使得叙事范式发生改变,导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继产生。西方20 世纪严重冲突的小说叙事观念分歧导致作家对世界有了不同的认知,对真实的看法有了很大不同,体现在语言上就表现为原先经常使用的阐释价值观的文本语言变得语义模糊。此外,对语言含混性的认知符合西方20 世纪语言学转向下文学创作的新趋势,那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叙事范式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与修辞学的复兴之下解体”[16]287。所以莱辛敏感捕捉到新的时代氛围,力图使作品摆脱外在世界的束缚成为建构性主体,她所使用的叙述语言不再是贴切表达真实事物的所指,而成了滑动在能指链上、歧义丛生的符号。
《金色笔记》中莱辛描述了当安娜想找到一个词来形容笔下的人物维利时,她发现截然对立的两组词“无情的,冷淡的,感情用事的”和“仁慈的,热情的,讲究实际的”都可以用来形容维利[12]73,两者虽然看起来彼此矛盾但都是他的特点。可见传统叙事范式是建立在作家和作品主人公主体稳定性之上,它可以明晰地通过语言传达道德判断。新语境下启蒙以来稳定统一的主体被消解得分裂破碎,使得语言具有了歧义性、含混性、不连续性的特点。
三、内容/形式的契合
既然内容和表达内容的语言都无法传达真实,莱辛渐渐转向叙事形式,希冀通过形式适配内容。莱辛认为,以往的叙事范式都有不足,比如现实主义强调最大程度忠实描述世界,但对小说虚构本性的遮掩容易贬低小说叙事的审美内涵,导致作家创作不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而现代主义等当代的叙事形式坦承小说的虚构本性,认为虚幻就是现实本身,小说并不指涉世界,而是有待解读的符号系统,这种观念虽有其合理性,但具有虚构泛化倾向,容易变成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在长期创作过程中,莱辛把她以形式传达内容的实验写作定位为一种“突破”(Breaking Through)[17]84-49。有学者把它称为边缘写作,认为莱辛既有西方欧洲文学传统观点又与它保持距离,注重叙事过程[1]2。也有学者把她的小说形式称为跨界小说[15]91,认为作品中糅合了传统和当代的书写方式,把叙事的再现性和建构性结合,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实际上再现和建构表面看似大相径庭,但思维方式和思想导向都是一致的,即通过抬高现实和文本的某一元而贬抑了另一元,成为不可避免极端化的片面表达。这种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产物,真实/虚构悖论就根源于此。而莱辛关注叙事过程的书写方式,注重现实和文本的动态平衡,因此她对叙事范式的突破也蕴含着她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期望。
在《个人微小的声音》中莱辛提出:“我相信两点之间的某个地方才是支点所在”,“对立的两极间虽然很难完全平衡,但我们要不断实验”[11]12。在她的理念里,理想的小说形态既关注外在世界,关注集体和人的社会存在,又关注个人内心情感变化;小说指涉现实,但对世界的认知是话语建构完成的;作家创作时既需要开拓内容涵盖的领域,可以描写梦境、心理、疯狂甚至虚构的外太空,也要根据内容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
正是出于为小说内容选择最妥帖适配形式的考虑,莱辛小说不断进行形式创新,以求突破。如《简述地域之行》呈倒金字塔结构,小说的人物构成一个五层的金字塔,叙述者位于顶端,警察作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位于金字塔第二层,医生是社会机构的权威,位于第三层,主人公沃特金斯的妻子、情人等是权威的拥护者或帮凶,位于第四层,沃特金斯和众精神病人则作为受压制者位于金字塔的底层,倒金字塔头重脚轻,非常压抑,而故事中前四层作为理性统治的“正常”秩序,深深压迫着沃特金斯等底层所谓的“病人”。《黑暗前的夏天》把主人公凯特汹涌澎湃的内心生活和严肃的政治、社会和生理压力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外在的实际旅行和内在的心理旅行同时进行,彼此相互映照的双层多辐射结构图,这双层结构对应于小说提出的“勇敢做自己”和“勇敢做社会一部分”的矛盾。《金色笔记》中,小说首先是在形式上首尾衔接,采用环环相扣的中国盒子结构,把记录在黑、红、黄、蓝、金五本笔记中的故事彼此穿插,以“自由女性”的叙事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内容上也是首尾呼应,如主人公安娜和情人索尔交换了笔记本,分别给对方写下小说的第一句话,索尔写的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而这句话正是《金色笔记》的第一行文字,从而把形式和内容融为一体。此外,作品还以小说形式传达文学评论的内容,莱辛不时跳出故事,对小说理论和故事创作过程进行一番评论,故意把传统现实主义叙事费心营造的真实幻象打碎给读者看,通过形式创新来反映时代,达到突破形式僵化以拓展新的叙事视野的目的。
莱辛的写作实验的突破性还在于它先于小说理论指明了小说叙事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加西雷克(Andrzej Gasiorek)以衣服和身体来比喻文本与现实间的适配关系:“衣服不与身体同构,但衣服又必须与它们要包裹的身子适配”[9]189。衣服和身体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外部世界和文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是多元共生而不应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因此作家的任务是为作品适配最恰当的表现形式以正确解释世界。既然小说的叙事不是镜像般模仿现实,而是正确解释世界,那么对世界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正如贴合身体的衣服可以有很多套一样,关键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套。
四、结 语
莱辛认为小说叙事形式需要不断在世界和文本间寻找平衡,因此单一偏重任何一元都有失偏颇,陷入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模式。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意识到内容与形式适配的重要性,不断给作品寻找最贴合的表现外部世界的方式,通过个人在时代潮流中的思想变迁和命运沉浮来表现整个社会的思想状态,从而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赞扬地那样——真实地审视自我和拷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