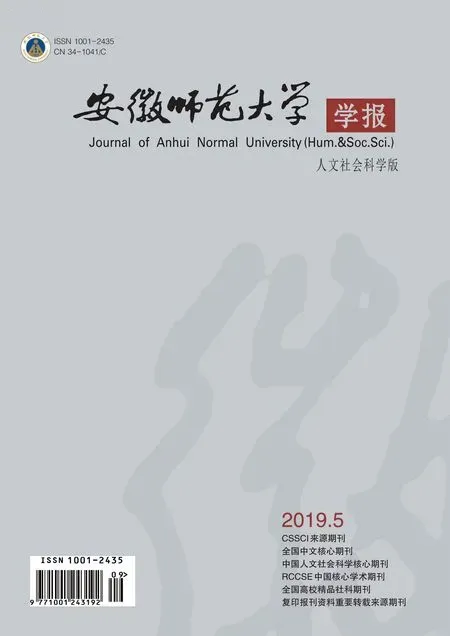晚清时期日本对华茶国际市场的侵夺 *
2019-03-15郝祥满
郝祥满
(湖北大学 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43006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近代世界贸易竞争中茶叶生产和贸易及中国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等颇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斐然。(1)相关研究成果,除本文引用外,尚有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闻云峰的《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衰减的国际市场分析》(《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由于中国茶叶最先被英国茶商控制的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红茶挤出欧洲市场,故国内相关研究侧重于印度、锡兰及其背后的操纵者英国茶商,与近代中国茶业在茶叶生产加工、国际市场方面的竞争。(2)相关研究成果,除本文引用外,主要还有: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陈一石《清末印茶与边茶在西藏市场的竞争》(《思想战线》1985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和《近代中英茶叶贸易衰败的原因和启示》(《江汉论坛》1998年第10期)、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董春美《印茶侵藏:中印关系的历史检讨》(《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俄罗斯因在中国开放口岸以后介入中国茶叶加工、出口环节,俄商在其殖民强权的保护下打败晋商,控制了中俄茶叶贸易,国内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也不少。(3)吕一燃:《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易文:《清中后期蒙古地区的对俄茶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等。但国内学界较为忽视1880年代以来中国茶叶国际竞争的最大对手日本,虽偶有研究涉及日本茶业参与国际茶叶生产和贸易竞争并影响华茶的问题,往往语焉不详。(4)赵和涛的《我国茶叶生产技术向外传播及与世界茶业发展》(《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一文有初步阐述。日本“开国”“维新”后,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极为重视茶叶、丝绸、陶瓷等传统手工业“近代转化”,尤其是针对“中国外贸商品的第一大宗——茶叶”展开争夺。[1]正如田中忠夫所言:“日本茶在海外市场与中国茶竞争,日本茶的发展就是中国茶的衰微,中国茶的发展就是日本茶的衰微,处于茶业上利害相反的立场,在蚕丝业方面也一样。”[2]120晚清茶业中的红茶和砖茶及其在俄罗斯的消费市场是其坚守的最后阵地,日本如何从茶叶生产、营销、运输等环节攻略这一阵地,非常有研究的价值。笔者拟对此加以探讨,希望能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对湖北红砖茶生产、加工工艺的调研和窃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重视红茶的生产和出口。因为欧美人喜爱饮用红茶,红茶有着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尤其是在最早与日本通商的美国茶业市场,英国茶商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被排挤出去以后,日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美国人自1773年“波斯顿倾茶事件”以后拒绝喝英国红茶,进口中国绿茶,1784年派“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广州,以毛皮、西洋参等购买中国绿茶。绿茶也是日本的传统产品。日本自1862年在横滨设置茶叶加工场,从上海聘请商人教授日本人绿茶着色技术及装箱、保质技术等,促进对美出口,故进入明治时代后,日本绿茶很快占领了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市场。由于在美国等国际市场,“超克”清朝绿茶的销售已经指日可待,故明治初期,日本茶叶生产和加工技术的引进改良,及国际贸易竞争的重点,很快转向“中国风红茶”和砖茶的研制和试卖。
日本聘用中国工匠指导制茶的档案资料显
示,日本对中国制茶工艺的调查工作从1871年中日建交后就开始策划了,对中国红茶的调查研究要早于砖茶。1874年,日本政府在劝业寮农务课中设置了“茶叶挂”,奖励实验制作红茶,编辑“中国风红茶”的制法书籍《红茶制法书》,颁布产茶各县。1875年,内务省大久保内务卿命令进行国内茶业调查,从盛产茶树地区选拔召集官费生,聘请中国茶叶匠人来日本传授中国风红茶的制茶技术。[3]1870年代以来,中国茶叶虽然在英国茶商的操控下,在印度茶、锡兰茶的冲击下失去英国等欧洲市场,依然保有俄罗斯市场。湖北汉口一时成为红茶生产和出口重镇,针对汉口红茶、砖茶这一迅猛发展势头,故日本把引进中国茶叶生产制作技术的目标定在湖北省及其中心城市汉口,注重湖北地区中国茶种的搜寻和调查研究。明治政府劝业寮于1874年向产茶地区颁发的《红茶制法书》,其第一为“总论”,第二即为“适合制红茶的茶品”,[3]1283足见其对茶种的重视。1875年11月,劝业寮的下级官员多田元吉被专门派往中国,调查中国茶业,到咸宁、东山、崇阳等产茶县调查、研究茶树的栽培技术及红茶制作技术,购求良种,于次年2月回日本。[3]1274-1325据载此人1876年再次来中国南方进行茶叶调查,1877年2月回日本。[4]538-539
从日本驻汉口领事馆1890-1891年间与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往来的文件可知,多年来,日本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等不断购买湖北武昌县等地茶种七十斤,寄回日本进行种植实验,[5]以培育良种,改良日本茶叶品种。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有关制茶贸易的调查及清国湖北省产茶叶种子购入之文件”可了解,日本购买中国茶种并寄送回国的详细过程。静冈县知事李家隆介于1907年2月6日通过信函请求日本外务省,“应本县农业实验场之用,购买清朝湖北省产茶种一斗”。外务省再命令日本驻汉口领事。3月8日,驻汉口领事馆购得湖北上等茶种一担、中等茶种一担寄回日本。[6]65-734月1日,李家隆介再次致函日本外务省通商局,请求购买湖北茶种。同一档案文件显示,1910年7月23日,静冈县知事始源健三致函日本外务省通商局,请求领事在福州、上海、汉口、重庆等处购买中国茶种。[6]94-100诸多档案记录表明,日本方面购买湖北茶种,通过实验改良日本茶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日本在这方面坚持了几十年。日本利用湖北茶种改良日本茶叶的具体表现,也见于在以下分析报告之中,如“本邦(日本)制茶缺点及其改良中应注意事项”“本邦人输出茶贩卖方法缺点及其改良应加注意之要点”等。这些报告探讨如何借鉴湖北茶种改进茶叶品质。[6]2-90
日本要进一步抢夺中国红茶的国际市场,必须保证茶叶制茶技术不能输给中国。为此日本政府通过实业教育,培养熟练工匠。为了引进中国技术,日本或直接聘请中国工匠赴日教授,或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或购买中国茶叶样本寄回日本研究。早在1871年,日本便聘请作为欧美人随从在大阪府旅行的中国制茶工匠德万、保记二人,在日本京都“制茶传习”(传授制茶技术),且“满一年”。[7]除此方法外,1874年明治政府在九州、四国等产茶地区选拔20名官费生,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聘请两名中国人(凌长富、姚秋桂)赴日教授他们红茶制作技术。[3]12981875年,白川县和大分县聘请有两名中国人教授红茶制作技术。当年在日本传授红茶技术留下姓名的中国人有凌长富、姚秋桂、吴新林,其中凌长富被聘时间长达一年半。[8]1877年,劝农局长松方正义通过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聘请清人胡秉枢赴日,在静冈县教授日本人制茶法,[9]次年在静冈县创设红茶传习所。据《静冈县茶业史》所载,是因为有了传习所才请胡赴日教授的。[10]1974
红茶传习中值得一提的是多田元吉。1875年11月,日本劝业寮的下级官员多田元吉被专门派往中国,将日本新制的各种茶品提交中国茶市的洋商和中国商人鉴定并试卖,特别在汉口、咸宁、嵩阳等地研究了红茶精制技术,[3]1298并调查红茶的销路情况。购买茶叶寄回日本研究的做法更为常见。如1898年5月,福冈县知事函请外务省通商局,请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购买汉口新品红茶样品上中下三等各一斤左右,寄送日本研究。[11]
1868年至1876年,日本茶叶制作采取的是手工揉搓的方法。1877年至1883年,日本茶叶制作虽有改变,在堺、岐阜、大分、熊本等处设置红茶制作技术培训机构“传习所”,但因出口贪多掺假,被称为是“粗制滥造的时代”。[10]144日本政府从1884年开始通过立法制订行业规则,如发布“茶叶组合准则”,禁止造假,取缔伪劣,奖励改良和技术竞争。负责茶叶改良和制造的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还提供资助派留学生(即“制茶传习生”)到中国汉口红茶、台湾乌龙茶等茶叶生产、制造地去见习。1887年到汉口的是来自熊本县的可德乾三、大分县的长盐右一郎。[12]学习内容包括混合物的减少、茶砖压榨的坚硬程度、打包的方法等,日本的这种学习到大正时代也未停止。
相比之下,日本最为重视的是对汉口砖茶制造工艺的调查和窃取。中国最早发明适应大量茶叶远程运输的砖茶工艺。湘鄂边境的羊楼洞(或作“洋楼峒”)是砖茶的原产地。砖茶工艺产生于茶叶出口的需要,由山西商人开其端。[13]50由于茶农交给晋商的干茶是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不便运输。若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于是晋商不断改进打包、储运方法,使茶叶缩小体积、保持干燥。根据戴啸州的《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记载,晋商使用的是手工机械。
日本的《中国茶业经济的考察》报告认为,“砖茶的制造,开始于前清光绪三年”[14]57,即公元1877年,由俄罗斯商人经营的阜昌洋行在汉口开设工场制造。俄商进入湖北茶市,突出的影响是吸收、改进了晋商的砖茶工艺,在俄商开设的砖茶生产工场中采用机械制茶(即“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至1891年,中国的砖茶工场多控制在俄国人手中,约有十七处工场,仅汉口有六处,附近九江一处;只有福州三门一处、羊楼峒一处及云南的砖茶由中国人自己经营。[15]761-765俄罗斯商人获得中国内地经商权后,即在汉口茶市中异常活跃,通过俄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压,减轻关税从而降低成本,在中国茶叶贸易市场中鸠占鹊巢,[16]154-159排挤了晋商。日本若想挑战中国强势的茶业和销售旺盛的红茶,必须抢占中国红茶、砖茶的俄国市场。日本对于中国茶叶和日本茶叶在俄国市场的竞争情况的调查非常重视,获得大量市场信息。日本的“中国茶业经济的考察”,依据“重要性和产量”,将中国茶分“红茶区、绿茶区、砖茶区”三区,“砖茶区”仅有“湖北省羊楼洞”一处,[14]2在汉口加工、集散的红砖茶,主要出口俄罗斯。日本对作为竞争对手的汉口红砖茶产销状况能准确地把握。
日本对红砖茶技术的钻研比较早,1880年就曾将中国砖茶和日本制茶(红茶)样本一并交俄国茶商比较,[17]企望打开俄国市场,侵占中国在俄国茶叶市场的份额。据载,日本试制砖茶开始于1881年,次年将其试制的砖茶样品送中国,委托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试卖。档案记录显示,1880年3月,日本通过领事馆向俄罗斯人展示中国茶叶和日本茶叶标本,俄国人鉴定后认为,经俄国砖茶场加工的汉口、福州产绿砖茶与黑砖茶,优于日本制茶。[17]9、13日本并未因此放弃砖茶的研制,和对俄国的砖茶推销。1895年以后,日本开始进入茶叶机械制作时代。政府提供补助金,鼓励茶商探索机械制茶技术,对于外国的相应技术千方百计搜求。对汉口茶业调查细致研究的同时,积极引进俄罗斯制茶机械。1901年,九州制茶会社为了购买俄国制茶制作、打包机械,请求驻汉口领事调查俄国制造砖茶工艺和购买机器的费用,及搜寻俄国砖茶原料标本等。[18]
1906年10月,日本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浦盐斯德(5)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语音译,或简称“浦潮”。地区贩卖的红茶砖茶,经俄国内务省卫生局的检查,发现其中有掺杂柳叶、木屑等,质量远远不及汉口生产的砖茶。俄国报纸将日本出口砖茶质量问题曝光之后,日本更加重视机械制造技术的引进和改进。湖北汉口以制作砖茶著名,而砖茶加工制作和销售主要被俄罗斯商人控制。俄国商人在砖茶机械制造方面积累了技术。[19]故日本的调查重点是汉口三家俄罗斯人经营的茶行和一家中国商人的茶行。日本对于中国传统制茶工艺的掌握不是轻而易举的,故只能不遗余力地进行对砖茶制作工艺的窃取。1908年,日本对汉口俄商阜昌洋行经营的砖茶厂的调查,很有代表性。尽管日俄战争以来该工场戒备森严,但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还是设法派人进入了严密保护的该制作工场,并拍摄了17张照片,委托当时来汉口考察中国茶业的日本静冈县农业技师山田繁平带回日本。[20]日本出口茶的工艺,能在国际上取得良好声誉,要比同时出口的其他产品工艺好很多,得益于制茶技术的钻研乃至盗窃。
为了提高日本茶业的质量,提高日本制茶企业的竞争能力,1907年以后,日本政府和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改变补助金支持方法,只对具有一定资本和规模的制茶公司,即“资本金百万日元以上”者给予补助。[6]79-83即淘汰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的小型企业,以兼并来提高竞争力,促进改良。1915年以后,日本进入机械制茶的全盛期。
二、针对华茶确定国际贸易营销对策
日本茶叶的外销,最早是通过中国商人之手从长崎出口欧美各国的。1859年横滨“开港”后,日茶在华商的帮助下开始从横滨出口海外,主要是美国,数年之间价格成倍上涨。茶叶就这样成为日本“开国”后进入国际市场“打头阵”的日本商品。1868年明治维新之际,横滨、长崎、神户成为日本茶叶出口外国的三大港,出口国增加了英国。
1869年国际市场茶叶价格高升,引来更多的日本武士和农民种植茶叶,促成日本茶园的扩张与贸易目标的膨胀。日本茶商自然希望摆脱中国茶业中间商的控制,拓展日本的国际市场,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积累资金,故非常重视对国际茶叶市场的调查,尤其是针对中国贸易及其市场的调查。茶叶逐渐成为日本重要的出口物资,为日本积累了巨大的资本,也奠定了日本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的经济基础。出使欧洲的薛福成较早注意到日本对中国茶叶国际市场的争夺,并在其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丝、茶两宗为中国利源,近以日本、印度、意大利各种茶桑夺我厚利,而中国之丝茶日形减色。”[21]426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的日记中还列举了具体的对比数据:
至中国绿茶之售于北美洲者,因日本轻税,绿茶每担仅税一元,以与华茶抗衡。去岁中国绿茶销数,有一千五百七十五万磅,较之光绪六年之销一千九百五十万磅,约减四百余万磅;日茶则光绪六年曾销三千九百五十万磅,去年涨至四千七百万磅,十二年间骤添七百万磅矣。[21]749
据日本人的调查,早在1867年,中国茶叶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47%。[22]47在1860年代,中国出口茶叶占国际市场份额的90%。进入1870年代之后,中国茶叶在印度红茶和日本绿茶冲击之下,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开始下降。日本对美茶叶出口贸易,1880年几乎与清朝平分秋色,即清50%、日本46%,[23]29因此日本把与中国竞争的目标扩大到砖茶、红茶和俄罗斯市场。日本在国际茶叶贸易战中取得成功,在于通过调查能知己知彼,及时应对。
日本能成功抢夺中国茶叶国际贸易份额,首先是去“茶业组合”等机构调查分析了华茶在国际贸易中衰落原因,取长补短,规避中国茶业的问题,从而改善日本的营销对策。日本出版的《中国的产业与金融》一书,将中国茶业“1887年以后,特别是1896年中日战争后的衰落更加显著”的“衰因”,从“生产、消费、交易、茶政、其他”五个方面归纳分析出了19种原因。[2]41“对征收输出税外加收厘金”“政府对茶业采取不干涉主义,对其栽培制造和销售未采取任何奖励措施”,被日本调查者注意。[24]5-6井上陈政的调查认为,清政府对茶业的干预,主要是国内发茶引、收茶税。[25]797-8001887年日本的调查报告认为,印度、日本等外国茶业产量的提升、外国茶业输出关税低、中国茶叶运输成本高是清朝茶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减轻关税,进一步提升日本与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竞争力。[26]因为茶叶的收购、加工、储运,均需要大量资金,流通费用往往比茶叶本身还高,资本少的茶商难以维持,往往铤而走险,盲目行动。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茶商得不到国家的支持,承受高额税收而缺乏资本,受制于人。故日本政府和日本制茶公司为提升其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经常为有一定资本的大公司提高运输补助金等。[6]81-82
清朝对本国茶叶参与国际贸易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很少注意在国际市场上推行广告宣传等营销手段,让日本有机可乘。日本调查发现,在美国市场,“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促进销路的措施,任其自然”,从收购到贩运,主要由外国人操控,[6]18、53中国商人只是帮办而已。而日本政府颇为注意广告推销,外事官员积极参与新茶的推销、宣传、广告,利用国际博览会推销宣传日本茶叶和日本茶道。茶道文化的宣传是明治日本茶叶贸易战略的一部分,可以促进国际茶叶消费;反过来,茶叶贸易也挽救了遭遇危机的日本茶道传统文化。薛福成称日本,“即如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中国”,中国“丝茶两宗,本恃为出洋巨款,今则日见其衰……日本、印度、义大利、法兰西乃起而攘其利”,[21]351-352夺取了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
到1892年,中国茶业贸易整体上呈现衰落趋势,只有从汉口运输到俄国的茶叶还未受到影响。“土货以茶叶为大宗,径往英俄二国者二十六万余担;俄商生理年盛一年,遇有好货不惜重资争购,如宁州茶、安化茶、高桥茶、聂家茶、羊楼峒茶,皆胜往年。”[21]649-650因为西伯利亚地区人民喜爱各种砖茶(如红砖、绿砖、小京砖、茶饼等),故俄商为了保证供应,渗透到砖茶加工环节,在汉口设厂制砖茶,直接从日本进口煤炭。日本既然把华茶作为竞争对象,争夺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成为日本茶业的主要任务。中国茶叶虽然1875年之后在逐渐失去英国、美国等市场,但砖茶、红茶还有俄国市场,维持了中国茶业的暂时繁荣,这成为日本调查关注的重点和最后抢夺的目标。
日本政府各机构(农商务省、外务省)参与俄罗斯的市场调查和新品推销,成为日本茶商抢占中国茶叶俄罗斯市场的后盾。俄罗斯是茶叶消费大国。鉴于日本茶在美国市场难以拓展销路,而俄罗斯存在巨大的需求市场,[27]11日本茶商认真研究俄罗斯人的口味和嗜好,反复将中国茶叶和日本茶叶的标本,送俄国人品尝,比较优劣,看哪一种茶更适合俄国人,调查俄罗斯饮茶人的喜好,根据消费者反馈的意见改良生产技术,以便扬长避短,在俄罗斯市场上打败中国茶叶。1888年7月,日本茶业组合派遣平尾喜寿赴俄罗斯调查。此人历经海参崴、黑龙江、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于1889年5月返回日本。其提交的“意见书”,研讨了开辟俄国茶叶市场的策略。[28]1894年,日本外务省次官林董将九州茶叶会社的五十箱茶寄送给日本驻敖德萨领事馆的名誉领事俄国人,请其试卖、品尝、宣传,并请其指出日本茶的不足之处,1895年1月竟得到了俄国人详细的书面建议。从俄人的意见看,此时的日本茶还比不上中国茶,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中国茶的口味和香味。[29]52、57、72甲午战争后,天津成为中国茶叶输出俄罗斯的重要港口。1899年,长崎商业会议所通过外务省通商局让驻天津总领事调查中国制茶和陶瓷事宜。[30]
明治政府的参与还体现于,利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参与国际间茶叶价格调整的调查与协调,必要的时候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提供保护日茶的入关检验等。日本政府非常注意通过日本驻外使领馆调查各国茶叶进口的质检标准,并报告外务省,再由政府告诫日本茶商,对本国茶叶的出口进行品质管理。日本与中国在美国市场的茶叶贸易竞争始于1860年代。日本在美国茶叶市场取得竞争优势,挤占中国的份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领事的调查发现日本茶存在的质量问题,并及时建议日本国内改良茶叶品质和营销方法。而中国茶商此时却忽视了茶叶品质的提升。由于中日两国输出美国的绿茶均有着色情况,“着色原料多存在有害物质”,经过两院议论,美国于1883年3月颁布《粗制赝造茶类输入禁止条例》,限制着色茶和伪劣茶的输入。[31]日本方面因此积极讨论对策,为改良茶叶品质而成立了“中央茶业组合本部”,派官员到各产茶地监督茶叶制造,奖励优质茶,取缔劣质茶。日本领事1886年的报告显示,这一年日本茶在美国得到好评。日本1890年的《官报》称中国茶“在国际上评价不好”,[32]即华茶质量问题成为国际贸易竞争中不利的根本原因。薛福成注意到,中国“丝茶两宗,本恃为出洋巨款,今则日见其衰:售之西人,西人谓其货愈劣,若有戒心。日本、印度、义大利、法兰西乃起而攘其利”。[21]351-352“日本各货,价廉物美,销售亦广。土货以丝斤为最旺,茶叶次之”。[21]651可见,日本政府重视美俄茶叶质量标准,注重茶叶质量,确保了与华茶竞争的优势。
1890年,日本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注意到,汉口地区的六帮茶商(指山陕、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与外国茶商因质量而引发的纠纷及清政府调解的照会公文。[33]町田立即将此报告日本外务省,以供日本参考应对。日本茶叶能够抢占中国的美国市场,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制止了日本茶商着色掺假,而清政府不作为,一任不良商人败坏名誉。[34]74日本驻美旧金山、塔科马、纽约各领事馆一直关注中日茶叶在美国海关检查的情况,调查美国的检查标准等,并及时报告日本外务省。[35-36]1897年日本得知美国提出新的茶叶检查标准,禁止粗茶输入后,立即在横滨、神户、长崎三个茶叶出口港设置检查所,茶业组合中央会议也发出了《关于海外输出制茶检查的建议》,[37]45-47最终使日本商人注意茶叶品质,在美国顺利通关,并在此后获得免检资格;而中国被检查出质量问题,每每被严格查检。
1897年美国颁布《粗恶制茶输入禁止条例》[38]5-13以来,中国茶因严格的质量检查被排挤出美国市场,而日本因少了中国这一竞争对手,茶叶的品质也日益下降。到1910年,在农工商部的重视下,中国出口美国的茶叶质量改善,品质优于日本而价格低于日本,这样一来日本茶叶的品质被注意,在美国海关检查时受阻,引起日本茶商的不满,认为美国的标准不当,其茶业组合请求日本政府出面干涉。[37]1911年针对美国新颁布《关于禁止输入粗恶制茶飞补充条例》,并对进口茶业的化学检测方式,有关“领事报告”告诫日本茶商为了长远的利益,“取缔日本茶叶的着色行为”,[39]此后日本全面禁止生产着色茶。
中国出口俄国的砖茶因质量较好,所以日本砖茶一时难以打进俄罗斯市场。日俄战争后,日本好不容易进入俄国市场。1906年10月,日本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销售砖茶存在质量问题,即“混有柳叶、木屑、油烟等”被俄国报纸曝光后,迫于舆论的压力,日本外务省责令调查,日本方面九州制茶输出会社与符拉迪沃斯托克领馆官员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和茶叶样品。九州制茶输出会社代表松尾九藏在《陈情书》中狡辩,于是日本政府一面承认日本砖茶不及中国,并决定今后“用心精选原料,且参考清朝制茶来改良制茶法”,一面又诡称日本是被陷害者,是中国商人制造的假新闻,并给中国砖茶泼脏水。[40]毕竟中国茶叶此前也出现过掺假作伪问题,这种诡辩可以混淆视听,为日本茶叶的掺假作伪制造烟幕弹。无独有偶,1906年6月,日本在美国、加拿大茶叶贸易中也存在问题,比如在美国市场上贩卖的茶叶中出现“将新茶和旧茶混合、将日本茶和外国茶混合贩卖”的现象。外务省通商局不得不下令纽约、渥太华等处的日本总领事,调查并检讨“本邦(日本)茶叶的缺点及其必须加以改良的要点”,调查“美加两国主要市场上日本制茶经营者中主要人物的住所、姓名和信用度”[6]2、28-30等等,并提交报告。关于缺点,调查报告称:日本在美国贩卖的茶分一、二、三、四等级,一、二是上等茶,出现质量问题的是三、四级茶在美加的出售。这多少有些搪塞的成分。
尽管在俄、美市场都查出质量问题和信誉问题,日本人表面搪塞,内心里是承认自己的砖茶存在问题和不足的。日本政商各方面积极应对。从1907年开始,日本从政府到商家都将扩展日本红茶砖的俄国市场视为“一大急务”,重点调查研究中国汉口、福州、上海等地砖茶技术和贸易情况,为此制订了详细的《在清国调查事项》(共15大项)和《在俄国调查事项》(也是15大项),[41]2并将此任务布置给中俄(敖德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各处的领事馆。调查列举了在俄罗斯受到批评的各种日本品牌的茶名及其产地。改良之后日本茶再次在俄罗斯试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汉口工商业停顿,影响了汉口的茶叶输出。中国输出俄罗斯茶叶减少,茶价格飙升。日本通过调查得知这一情况后,乘机扩大出口俄罗斯的茶叶。[42]这成为日本挤兑中国茶叶俄国市场的一大契机。总之,日本茶叶能够越来越多地占据国际市场份额,和日本政府、茶业组合(商会、行会)的监管、督导是分不开的。
三、以航运优势影响汉口砖茶输出方式与路线
1890年代以后,日本企图侵占清朝在俄国的茶叶市场,并参与中国茶叶国内、国际运输环节的竞争,特别是国际运输环节。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劣势日益突出。日本对中国茶业调查都特别关注中国茶叶出口、运输、销售的路线。
中国茶叶作为中国特产,在没有贸易竞争对手的年代,中国商人掌控了茶叶生产、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可以待价而沽。清政府的茶叶专卖贸易使广州、恰克图成为南北两大口岸,茶叶出口运输、销售路线因此形成。政府因掌控“茶叶之路”的陆路运输获得巨额税收。中国商人参与境外茶叶运输则可获得巨大利润。中国云南之西南方向也有一茶路,“茶叶一项,为缅甸贸易之大宗”,“近中国边界者,皆种茶之地”。[21]156进入19世纪,随着印度、斯里兰卡茶叶在欧洲的畅销,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汉口等新口岸的开设,此“茶叶之路”便日益没落了。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清朝唯一的外贸港口,水路出口欧美的货品,皆从此上船。英国专此利,日本难与争锋。汉口开港通商,“茶马古道”外运茶的流向因此变化,沿古道的产茶区如羊楼峒、大溪洞的茶叶主体北上,汉口成为茶叶集散地,并发展成为“东方茶港”。日本主要想分享这里的茶叶外运之利。自1886年调查了“从汉口到产茶地方的水旱路程”[43]后,日本详细记载了自汉口起运陆路北上和水路东下的两大输出路线,[44]其目的是研究日本有无可能参与其部分运输环节。湖北湖南茶叶陆路北上到蒙古、俄罗斯,起点为汉口,终点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从汉口出发,先溯汉水而上,至襄阳、樊城再转陆运,途径泽州(今晋城)、平遥、大同、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45]202、205再从恰克图进入俄境(主要销售区域为西伯利亚)。日本外务省藏档案详细记载了这一商路历史发展和近代变迁,[44]以及汉口红茶的集散、俄国商人在汉口的活动情况、搬运方法等。俄国茶商因此“茶叶之路”的开通而富裕起来,成为新贵族。商路上的城市,如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因茶叶而兴盛,成为西伯利亚最大的工业城市、交通和商贸枢纽。日本很早便派间谍沿这条茶叶商路探险。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1908年7月到内蒙古旅行,8月在张家口停留,对茶叶中转站张家口交通枢纽地位、商业、运输方式等有如下介绍:
张家口地当库伦、乌里雅苏台、归化城、丰镇等地来往的要冲,并作为对蒙古及俄国的贸易地,处于交通枢纽之地位。商业大体掌握在山西人之手。除俄国人以外,外国人的商业不甚兴旺。我邦人经营的商业有二,一为义成洋行,在上堡,一为三井洋行,在下堡。俄国人自一千八百六十年起,来往于张家口,专营茶叶。中国茶由南方海运至天津,再由天津溯白河至通州,由通州利用骆驼或骡马运送至张家口。据说从张家口至库伦的大约六百里路程,通常是利用骆驼,有时也靠牛车来运送……夏季虽说是冷清的淡季,但街道上仍是行人车马往来如织,即使在中国北方的都市里也是难得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如今人口称七八万,但近期京张铁路开通后,定会更加繁荣。[46]250-251
由此可见,日本参与中俄“茶叶之路”的陆上运销环节,难度很大,故日本积极调查中国砖茶水运路线,目的是向参与中国茶叶出口的运输环节。
国际茶叶贸易竞争主要体现在价格上。运输成本增加推高茶叶销售价格,从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中国茶业在国际贸易竞争失利的原因之一在于,国内运输成本高,且无法控制茶叶的国际运输和销售环节。在国际间,茶叶运销一体则有利可图。一些种类的茶叶有保质期的限制,茶商若在运输上受制于人,则在销售上将会变得被动,产、运、销完全脱节则更加不利。运输畅通是茶商获利的重要保证。轮船取代帆船的远洋航运,铁路运输的兴起,对近代茶叶贸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和产业的落后,对近代中国茶叶海外输出产生了负面影响。
汉口就因临江,“轮船转运捷而脚费省”,并接近茶叶产地而成为中国主要的茶市。从道光三年(1823)开始,[44]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陆上运输的一段或全部逐渐被水路运输替代。水运落后的中国茶业,其国际竞争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外商拥有远洋长途运输的优势,中国茶叶商人逐渐从运输环节被排挤,乃至影响到华商在茶叶销售环节中的话语地位。由于中俄“万里茶道”的分流,汉口地区茶叶的输出,除了利用汉水、湘江、赣江等水路外,越来越多的是从汉口沿长江东下,经过九江、安庆、芜湖,从上海口岸远运欧美俄诸国。鸦片战争之后开通的这些口岸和路线,在国际贸易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故日本调查了“中国茶海陆输入俄罗斯的景况”,调查重点为海上运输路线。[45]13-14日本一直企图参与长江航路的茶叶运输,[48]232明治政府为远洋航运提供补助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访问汉口,参加俄商新泰洋行的25周年庆典,并力图扩大中俄茶叶贸易。此后汉口运往俄罗斯的茶叶大多改为水路。俄国开辟了从汉口经过上海的以下水运路线,即:从汉口经九江、上海,南下南海,过苏伊士运河,到敖德萨、巴统。或从汉口水运经九江、上海,从上海北上到天津,再从天津改为陆路,经恰通州、张家口、克图至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圣彼得堡、华沙。或直接从上海水运到海参崴,从海参崴改为铁路运输。由于“轮船转运捷而脚费省”,于是“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49]9外国轮船成为茶叶输出的主要运输工具,使中国茶商只能保住生产环节和部分加工环节的利润。
中国与日本在美国茶叶市场竞争失利,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有方便的海运。日本有“日本邮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两家船运公司开通北美航路,不担心其他国家的海运公司加价,甚至可以迫使外国海运公司在竞争中降价。故日本静冈县茶业组合联合会于1904年4月1日向日本外务大臣请愿,要求在日本已经掌握日俄战争制海权的情况下,在茶叶运输繁忙的“5月初旬至7月末”,开通与美国、加拿大茶叶海运航路,以免受制于外国船运公司。[50]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便努力恢复日俄贸易。1906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向外务省大臣林董报告了汉口红茶集散情况及俄国商人茶叶运输方式、路径的变化,日俄战争对汉口茶叶输出俄国的影响。[44]1907年,日本与俄国缔结铁路轮船联运条约,利用运输优势抢占俄国市场。[27]21轮船和铁路的联运,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将每天制作的新茶及时送到市场,以获得高价。1912年4月,日本农商务省函请外务省,命驻上海事务官员加紧调查“上海制茶运美国、加拿大的船舶及其所属轮船公司名称,及各轮船装载茶叶吨数及其运价”,且强调应“必须是在明治三十九年以后的累年数据”,以及“规定的运价之外,实际上运价打折”的相关情况。[51]随着清朝茶叶输出中水路运输数量的日益扩大,在对俄国在汉口制茶及运输状况的调查中,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和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渡边注意到俄国商人将茶叶通过水运经上海到天津(从天津改用陆路),或直接从汉口到浦盐斯德的保护措施。[52]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利用大连和南满铁路参与红茶的运输,于1910至1912年间,与俄国探讨铁路船舶联运茶叶和生丝等货物的问题(亦即货物直通运输)。[53-54]京汉铁路的开通,使部分茶叶通过铁路北上,再从京张铁路运至张家口,运往俄罗斯,或再利用中东铁路运往俄罗斯,中国可以掌控部分流通环节。即便如此,日本也控制华茶对俄输出的相当大部分。
日本茶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于日本政府“富国”的追求,能以政策引导民众,激发民众的“殖产”热情。政府参与茶叶产生、贸易、质检、运销等制度的安排。其“茶政”包括,通过茶业教育机构培养了制茶工匠,通过日本驻外领事的调查为茶商提供情报,通过政府的补助金(相对于当今的农业补贴)提升日本茶业的国际竞争力等。相比之下,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清朝茶业在生产、运输(包括仓储)、销售等环节都处于无组织、无政府支持的无序状态。华茶的国际市场自然被日本侵夺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