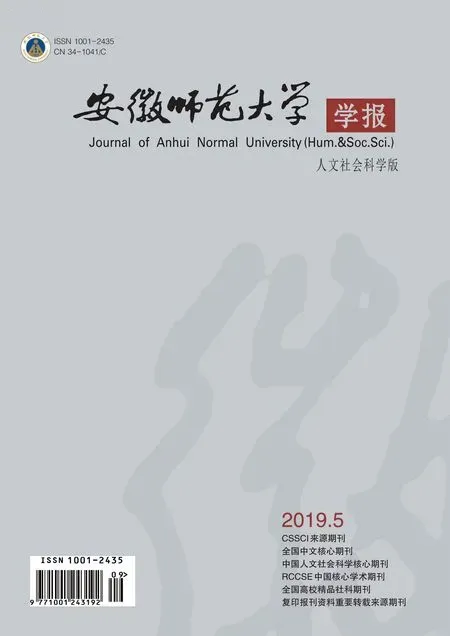“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2019-03-15郭书愚王亚飞
郭书愚,王亚飞
(1.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2.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一、中体西用与实践中的主义
近代中国受“西潮”的严重冲击,中学在与西学的“学战”中惨败,如何迎纳西学并安顿中西学之间的关系,成为越来越多时人着力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难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晚清中国主流的文化观,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1)笔者管见所及专门以此为题的代表性论著有: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限)、谢放《中体西用:转型社会的文化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9页)。此外美国学者(Joseph R.Levenson)对“中体西用”也有较深入的析论,详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卷第二部分)。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论自兴起之初(大致在洋务运动时期)即重在引进“西用”。大约自甲午战败后,“西用”的地位明显攀升。至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176由此中、西学由最初的主辅(本末)关系转变为并行不悖的取向。
这样一种“中体”与“西用”并行不悖的文化观成为清季盛行一时的主流思想言说(discourse),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系统阐释和鼎力提倡相关。张氏也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普遍视作“中体西用”论的重要代表和典型。梁启超即观察到:“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2]97在“举国以为至言”的氛围中,“中体西用”的论调对当时官方的维新和改革进程有深远的影响。陈旭麓教授注意到,戊戌维新运动的“不少具体兴革”即“以‘中体西用’的词旨为号召”,而自光绪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后陆续展开的“新政”改革“仍未远离此旨”,正是“中体西用”论的“实际作用”所在。[3]李细珠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一推动清末新政开展的重要文献正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4]
进而言之,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着力强调“中体西用”是兴办西式学堂的首要法则。多少与此有关,“中体西用”通常被视作张氏办学的指导思想,成为后之研究者考察张之洞兴学乃至整个晚清“新教育”的重要视角。据王先明教授的观察,张之洞对于“晚清新学的构建作用主要侧重于学制方面”,而“中体西用”正是他自两湖地区开始的办学努力一贯坚持的原则。[5]桑兵教授注意到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的主旨是以“中体西用”为主,力图借以解决“学堂的中西学之争”。[6]关晓红教授指出,庚子后朝野上下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实际上接受了全面学习东西列强的主张”,最终走上“合并科举于学堂的快道”。[7]章清教授认为“中体西用”不仅“主导着对西方知识的接引,还制约着对学科建制的规划”。晚清以降“对学科次第的论辩”既与“中体西用”论相关,“还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方向”,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8]209-253
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论固然以几至“化民成俗”的极大“风势”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打下了相当深的烙印。唯就本质上讲,它毕竟是一种学理层面的思想言说,这一“词旨”究竟多大程度上在实际的“政务”(尤其是“学务”这一当时最重要的“政务”)运作中“见之于行事”?“中体西用”是否能完全涵盖整个晚清“新教育”的办学思路和履迹?二者间是否存在着疏离或者说不那么契合的面相?相关问题尚有较宽广的研究空间。
苏云峰教授已注意到“中体西用”理论在湖北“新教育”的“实际应用”上有明显“偏差”。故提醒我们“研究张之洞的思想时,不要单看他的理论,还应该看他的实际。这中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9]138刘龙心教授的研究则揭示出,“中体西用思想”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科体制和课程配置方案中“仍然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只是体用之间的坚持渐有消弭之势,中学范围固有的科目坚守本体位置的态势依旧十分明显,而西学类目则已在学科类分的观念下,突破‘西学为用’的限制,全面采行现代学科体制”。[10]44-45
唯值得注意的是,当西人以坚船利炮轰开晚清中国大门后,在“技器之术”层面,西学的优良固然让中学相形见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学这一渊源流长的文化体系中与所谓“西用”对应的所有层面皆一无是处而统统被时人摒弃。即便是“中体西用”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意识形态”而“‘西学类目’突破‘西学为用’的限制”之时,中国传统的办学方式和教法,仍部分地隐伏在“中体”与“西用”的巨大光环背后,被赋予护翼和保存“中体”之责。它们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更与外国学堂办法碰撞交融,但大体上仍是“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状态。(2)这里的“传统中变”是鉴取柯睿格(E.A.Kracke)教授对宋代社会的观察和表述。参见E.A.Kracke,Jr.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14(4):479-488.
就张之洞的办学履迹而言,在着力倡言“中体西用”的同时,其“见之于行事”的办学运作似乎并未囿于“中体西用”的学理框架,而是奉行“参酌中、东(日本)、西,期于可行而无弊”的务实方针。他在《劝学篇》、“江楚会奏”、修订全国学堂章程、制订《学务纲要》等一系列办学努力中,实际“参酌”的“中”不仅仅是“中体”,还包括部分“中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授受理念和方式由此得以在相当程度上与“新教育”建制(institution)接榫。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在“新教育”中实际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相关面相值得做稍更深入地考察。
本文拟以“实践中的主义”为视角,关注清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风靡一时之际,张之洞在“中体”、“西用”两个巨大的“主义”光环下,低调而务实地“参酌中用”的办学努力,侧重其“新教育”的办学设想中,明显在“中体西用”的学理框架之外,甚至多少有些突破“体、用”二分思路,力图追寻中西之“通性”的面相。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体西用”这一“主义”回归其社会思潮和学理言说的本质,展现其与“实践中的主义”之间紧密缠结而又明显不同的历史图景,从而增进我们对“中体西用”以及晚清“新教育”的理解;而将张之洞戊戌变法以降的办学努力回置到他整个一生的兴学脉络中,从“细节”入手,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稍更深入地认知这位晚清重臣办学理念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二、“品行”课的源流与嬗替
光绪二十九年下半年,张之洞主持完成对《钦定学堂章程》的修订工作。同年十一月底,新的《奏定学堂章程》及《学务纲要》颁行全国。这一近代中国首次付诸实施的学制体系与此前张百熙等人所拟《钦定学堂章程》相比,在课程设置上有一大改变:增加了“品行”课。《学务纲要》列有专条要求“各学堂尤重在考核学生品行”:
造士必以品行为先。各学堂考核学生,均宜于各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同记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说、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在讲堂由教员定之,在斋舍由监学及检察官定之。[11]491-492
《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更是明确提出所有学堂学生“以端饬品行为第一要义”。至少在建制层面,“品行”已俨然成为“新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具体的教学运作上,“品行”课不占用学时,也无须教员升堂讲书,而是由教员、监学、检查官“随时稽察”学生的言行举止和日常活动,核定分数后汇总到专门的“品行总分数册”。[12]477-488除临时考试外,所有考试在计算各科平均分以确定成绩排名时,“品行”课与其它课程有同等的效力。不仅如此,“若平均分数有同等者,则视品行分数之多少以定先后”。[13]511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品行分数实际占有超出其它课程之上的权重。
若以“前后左右”之法观之,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通令各省改书院兴学堂的谕旨明确提出,“新教育”的目标是“务使[学生]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14]176两年多后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有关“品行”课的定位和设置,大体可说是对“文行交修”这一办学宗旨的强调和具体化(实际上应该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源流和脉络,详后文)。唯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奏定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同时奏准颁行的《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张之洞是将“重行检”列为新式学堂与科举相比的一大长处: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15]171
奏定章程中的“品行”课重在考察学生日常言行,并无教学活动,名为课程,实质上是出以课程形式的学生“管理”办法。而近代西式教育的一大特点即是“注重管理”。[16]29“新式学堂办法”在管理方面的优势和长处,实为张之洞等人在清季兴办“新教育”时竭力利用并刻意彰显的面相。[17]由上引张之洞的表述看,“兼重行检”显然是其中应有之义。
概而言之,《奏定学堂章程》及《学务纲要》力图走智育与德育并重之路,在办学的大方向上适与当时国人对日本学制的观察一致,应该不是巧合。日本于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约1890)颁布《教育敕语》,“把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宗旨的智育与以灌输‘忠君爱国’思想为宗旨的德育相结合”。[18]最晚至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即从访日考察学务的心腹僚属姚锡光处获知:日本学校“首重伦理一门,博采其国及中国并各国名人忠孝大节,绘之以图,演之以说,日讨而训之,故童焉而知爱国”。[19]6日本明治十三年(光绪六年,约1880)颁布的“改正教育令”,将“修身”课置于小学各学科首位,正是《奏定学堂章程》的榜样。[20]
尽管有明确的外国榜样,《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修身”或“伦理”课仍明显可见西式教育建制“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履迹。(3)黄兴涛教授的研究已揭示出,清季《奏定学堂章程》的“修身”或“品行”课是将“重视伦理教育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教育体制并不困难地结合了起来”。参见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这里所言“重视伦理教育的儒家传统”大体可说是“中用”的教育层面中相对较虚的部分(教育思想和观念)。换句话说,“修身”或“品行”课是“中用”之“虚”与“西用”之“实”绾合的结果。而同属“德育”范畴的“经学”和“品行”课则皆无外国经验可资鉴取。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皆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实际上,若将《奏定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回置到张之洞自同光以降的整个办学履迹中,不难发现其“经学”、“品行”课的设计方案皆是渊源有自。以下专门考察品行课的源流与嬗变,有关“经学”课程的演进,拟另文探讨。
同光之交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在他眼中,当时的书院已是普遍“溺于积习”的景象:士子“嬉谈废日”,甚至“嬉游博簺,结党造言,干与讼事,讪谤主讲”。[21]370-371扭转世风、整顿士习遂成为其学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对蜀中诸生的“发落语”——《輶轩语》共分三篇。首篇即是“语行”,其中“德行谨厚”、“人品高峻”两条更被置于篇首。张氏并告诫尊经书院诸生,在求学业“进功”之前,应“先求寡过”。而书院、山长等人责任重大:
凡为山长,不可懦也。牖导必宽,约束必严。山长主之,监院佐之,斋长承之,各衙门督之……院设斋长四人,以助钤束、稽程课,增其月费。以学优年长者充之,由学院选用,无过不更易,阙则请命而更补之。监院不得私派,不得以钱物璅俗事委斋长。有犯教条者,监院、斋长不以闻,轻则记过,甚则更易。
与后来的“新教育”普遍以外国为榜样不同,张之洞办尊经书院,以北宋胡瑗(安定)的“湖学弟子”为典范,整个办学设想基本未见“西力”的影响。唯中国传统书院历来讲求“重在自修”、“自求多福”,原不怎么特别注重“管理”(仅整体上概而言之)。[22]张氏为尊经书院谋划出“山长主之,监院佐之,斋长承之,各衙门督之”的一整套综合管理体制,更创设“斋长”一职,力图在书院内部建制上寻求突破,以便将“约束必严”的办学思路落到实处。这样的办学尝试至少在“注重管理”的办学大方向上,与后来的清季“新教育”殊途同归。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尊经书院的例子多少提示着近代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在尚未怎么受到“西法”影响之际,其自身演进的内在理路即已孕育了与“西式学堂办法”相向而行的倾向。
至光绪十二年(1886),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创办广雅书院,在其学规中专列“敦行”一条,要求:
入院诸生先行后文,务须检点身心,激发志气,砥砺品节,率循礼法,理求心得,学求致用,力戒浮薄,归于笃厚,谦抑谨饬,尽心受教。由院长暨监院随时考核,察其行检是否修饬,分别劝惩。[23]198
这里对入院诸生的要求,尤其是“先行后文”、“检点身心”、“学求致用”等条,与前引光绪二十七年通令书院改办学堂的谕旨中所言“心术端正”、“文行交修”、“讲求实用”的兴学目标基本一致。[14]176进而言之,若将广雅书院的这一学规与前引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将“重行检”列为新式学堂一大长处的表述对照而观,不难看出,《奏定学堂章程》中新增的“品行”课大体可说是力图用“新式学堂办法”完成“随时考核”学生“行检”这一张氏此前在兴办书院时即已着力强调的工作。
至光绪二十五年初,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遵照此前慈禧太后的懿旨札饬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懿旨原是要求各书院讲求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而张之洞的札文则在饬令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分门讲授上述“经世”课程后,特别强调“欲成有用之人才,必以砥厉品行为本。欲望学业之进益,必以率循规矩为先”。为此:
三书院均应另立行检一门,由各监督、院长每日酌定时刻,分班接见,训以四书大义、宋明先儒法语,考其在院是否恪遵礼法,平日是否束身自爱。每月终分别优绌,亦定为分数,开列清单,并经、史、天、地、兵、算诸门合较分数之多寡,为每月之等第。[24]201-202
这里的“行检”已是湖北三大书院统一设置的独立课程,不仅考核院生的日常言行举止,还有“四书大义、宋明先儒法语”等教学内容。而前者是重中之重。两湖书院监督梁鼎芬曾为三年学程的品行课拟出共计二百道题目,张之洞“诚觉其多”,在张氏看来,若真做完所有题目,则“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何况还要“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如果“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更为重要的是:
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曰,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25]81
“考文”既非“行检”课的旨归,则所谓“训以四书大义、宋明先儒法语”自然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讲道理”:以宋明理学作为人格和修养锻炼的传统资源。王汎森教授已注意到,回归宋明理学传统的“主体性的锻炼”是清季民初改造个人的风潮中“极为重要的一环”。[26]117-148这里的“行检”课多少提示着王先生观察到的重要“风势”也浸润到当时官办书院的教学运作中。
唯张氏强调并看重的,是在“见之于行事”的层面考核读书人的人格和品行。这一“贵躬行而忌空谈”的倾向实是渊源有自,(4)张之洞在同光之交的《创建尊经书院记》(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中回答诸生“何以不课性理”时明确表示:“宋学贵躬行,不贵虚谈。在山长表率之下范围之,非所能课也。”这一对宋明理学学科特点的认知和实践在晚清民国的知识界并非特例。民初就读于四川国学学校的蒙文通即认为“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而“道理”又“常体会不得;盖以其非仅闻见之知,而更为德性之知,须于事上磨炼、心上磨炼”。蒙先生的同学彭云生说得更直白:“理学是不须讲的,要实践”。彭氏并与同学曾宝和约定每月“具所得相质且以规过”。详郭书愚《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更一直延续到《奏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务纲要》中。(5)《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专条指出“理学宜讲明”,而“宗旨仍归于躬行实践”。新式学堂的“品行”课不设任何教学内容,而“言说、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则明显较“行检”的“考行”更具体而详备(相当能体现“学堂办法”在“管理”建制上的优势和长处)。具体运作仍是用“积分法”与其它功课一体同记分数,作为核定学生优劣等第的依据。就大的办学思路而言,湖北三大书院的“行检”门大体可说是《奏定学堂章程》的“品行”课的雏形,而后者在注重“考行”方面显然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品行”课固然完全以“考行”为宗旨,但湖北三大书院“行检”课“讲道理”的学程并未被“新教育”建制摒弃。王汎森教授已指出《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的修身课摘讲朱子《小学》、刘宗周《人谱》,正是“使用”传统思想资源进行人格和修养锻炼的努力。[26]117-148且《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专门强调“修身本贵实践”,适与“行检”课注重“考行”的倾向趋同。[27]308若说“新教育”的“修身”课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承继着湖北书院“行检”课“讲道理”的功能,似不为过。(6)值得注意的是,《奏定中、小学堂章程》的经学教程明确规定,讲解“止能讲其大义”(详后文)。这里的“大义”或与修身课教学不尽相同,但说其多少也有些“讲道理”的成分,似不为过。清季不少时人批评修身与经学两课重复混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张之洞原将理学式的“讲道理”与“考行”纳于一门“行检”课中,正有避免“空疏虚谈”之意。至“新教育”中,“讲道理”的教程尽管仍强调贵在实践,但毕竟与“考行”分离出来,分散至“修身”“读经讲经”等课中。这一变化实不可谓小,详另文。
可知湖北三大书院的“行检”门与后来“新教育”中的“品行”和“修身”(“伦理”)课皆渊源甚深。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强调“行检”门的宗旨是“学行交修”。这与大约两年后清廷通令改书院兴学堂的谕旨中所言“文行交修”的“新教育”目标,几乎可说是同义词。在清季不少时人眼里和趋新舆论中,学堂与书院已是势如水火般对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俨然成为“学务”中“新”与“旧”的代名词,但其实际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式学堂延承传统书院的一面,似乎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
如果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品行”课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的,是书院与学堂间隐而不显的内在关联,那么张之洞等人在中小学堂的读经课教程方案中,则无可回避地要正面处置当时广为时人关注的“记诵”与“讲解”等中国传统教法,在鉴取“中用”的同时尚有主动迎应西学冲击的一面,相当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
三、记诵与讲解:传统经学教法的嗣响
“记诵”与“讲解”两种教法的权衡取舍是清季官绅兴办“新教育”时关注的焦点。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即《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中举列“泰西各国学校教法”的四大长处,第一项即是“求讲解,不责记诵”。唯这样的“外国榜样”当然是针对西学而言。而州县官绅所办小学校在“兼习五经”时,则应“先讲解,后记诵”。[28]8-9这里的“讲解”与“记诵”固然有先后之别,但“记诵”毕竟没有被摒除在教法之外,实与“求讲解,不责记诵”的西式教法异趣。
至翌年七月清廷颁布张百熙等人拟订的《钦定蒙学堂章程》,其中明确提出:
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力,所当切戒。[29]284
这里的“教授之法”是就蒙学堂教学统而言之,当然包括经学课程在内。虽非完全“不责记诵”,但背诵只是“择紧要处试验”而已,已被淡化到相当程度。而有关“遍责背诵,必伤脑力”的告诫,正是清季时人对于“背诵”之弊较普遍的负面认知,相当能体现当时的时势和风貌。(7)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中即有专论指出“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中国之教人,尽于记性者也”,又“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前者“导脑”,后者“窒脑”。“导脑者脑日强,窒脑者脑日伤”。至清季“新政”之初,吴汝纶东游日本时认为:“西学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吾学则必应倍诵温习,此不可并在一堂”(吴汝纶:《答贺松坡》,施培毅,徐寿凯:《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07页)。这里对西式教法的认知已由梁氏的“偏于悟性”推进到“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吴氏作为桐城派名士,尚是颇重诗文吟诵传统者。至于中国传统记诵法有伤学生脑力的言说,更是清季报刊舆论屡见不鲜的“常言”,详另文。
唯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十月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将“幼学不可废经书”列为学堂“防流弊”的三大要义之首,具体办法是:
令仿古人专经之法,少读数部可也。或明其大义,不背全文亦可也……核计诸经字数,自十岁起至十八岁止,即日读一百字,可读毕四书一部,大经一部,中小经一部,可期记诵纯熟。其愿读何经,听父兄及本人自择。[30]94
在习经的数量、要求以及具体内容上,张氏此时的主张仍然相当宽松而有弹性,甚至明确提出“不背全文亦可”。但与一年多前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有关小学堂“习普通学,兼习五经”的规定相比,读经在这里成为了10至18岁学程阶段每日的必修科目,且明示以“记诵纯熟”为目标,对经学课程的注重和强调显然已大不同,实也事出有因。
在张氏眼中,当时“略知西法办学堂者,动谓读经书为无益废时,必欲去之”的“大谬”言论已到“百喙一谈,牢不可破”的地步,多少提示着此时的办学舆论和氛围与一年前变化颇大,趋新论者的“学堂废经”言说已颇具“化民成俗”的巨大风势,让张之洞这样的办学重臣感到压力和忧虑。张之洞可能是当时对舆论和社会思潮较敏感的办学大员。当张百熙等人在《钦定学堂章程》中仍竭力尊西趋新之时,张之洞已在着力防止学堂荒经之流弊。清季尊西趋新的办学思潮加速激进发展的进程以及张之洞力图挽回文化危机的努力似乎皆早于我们既存的认知。
一年多后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明确规定,初、高两等小学堂的“读经讲经”课,总的教学方针是“少读浅解”,所谓“少读”是指经学授受内容宜少不宜多。但每日所授之经,“必使之成诵”。记诵成为经学课必须完成的学程。[31]294、301、309、314另一方面,初、高两等小学堂章程皆有专条指出:
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谓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实不能背诵者,宜于试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
在这里,前引《钦定蒙学堂章程》所谓“以讲解为最要”的教学思路固然仍在延续。但与钦定章程强调“遍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同,奏定章程只是提醒授经者可对少数“记性过钝,实不能背诵”的学生网开一面。这显然不是一个微小的改变。实际上,在此时的张之洞看来,除少数“记性过钝”者外,绝大多数学生必须将本已“损之又损”的学堂经书熟读成诵。只要课程安排适度且循序渐进,“讽诵”经书并不会损伤脑力。《奏定学务纲要》中有专条说明:
外国高等小学不过五点钟,初等小学不过四点钟,所以养息幼童精力,用意本善。兹因中国学堂须读经书,不得不酌增数刻,初等小学五点钟,高等小学六点钟。然初等小学每日功课共止两个半时辰,在中国书塾,时刻并不为久,且所讲各科学时常更易,并非专执一卷,令其埋头讽诵,自已足活泼精神。至初等小学每日止读经书数十字,递增至一百字而止。高等小学递增至一百六十字而止。在学童断不以此为苦,而学生可无荒经之弊。此实培养本源之要义,不得以课多借口。
日本小学堂亦有高声诵读、期于纯熟者,亦常有资质较钝、迟至日暮始散者。陆军学生每二点钟讲授一二千字,必以全能记忆者始给足分,谓外国读书必不责其记忆,无是理也。[11]499
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西式初等教育学时少且形式和内容较“活泼”,正是清季时人较普遍的认知,也是趋新士人及其掌控的舆论着力抨击中国传统教育的面相。张之洞显然认同并力图在“新教育”中体现西式初等教育的上述优点,但因坚守学生必须读经的原则,而无法完全照搬西式学堂办法,故选择以西式办法为模板而略作调整的课时设置方案。在张之洞看来,这样的微调无碍清季“新教育”充分发挥西式学堂办法“养息幼童精力”以及教学活动颇具“活泼精神”的长处。《学务纲要》进而以日本为例驳斥“外国读书必不责其记忆”的言论,与前引《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将“求讲解,不责记诵”视为“泰西各国学校教法”四大长处之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张之洞对西式教法的认知转变实不可谓小。
记忆既非西式教育必然排斥的教法,当然也无碍多数幼童的脑力发展。张之洞特意以日本小学堂为榜样要求学生记忆,意在塞激进趋新者的“悠悠之口”以推行奏定章程的经学教程。唯经学毕竟不在“外国读书”的范围内,西式小学教育即便有“高声诵读、期于纯熟”的教法,也绝非针对经书而言。《奏定学堂章程》较此前的《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以及《钦定学堂章程》明显更强调小学堂经学课的“记诵”环节,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于张之洞对于西式教法认知的变化,而是另有渊源。
上引《学务纲要》中的“讽诵”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极为看重且渊远流长的读书法。朱熹即明确提出,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只要能“心到、眼到、口到”三者合一,“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古训即是指“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32]374元代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规程中,要求学子自八岁入学后,读书须将“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33]28
“熟读”不仅是最佳的记忆方式,更是精思文义的基础。朱熹认为“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正在于熟读可“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34]321这样的读诵传统一直延续至晚清,曾国藩即告诫其子曾纪泽,对于《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35]362张之洞庚子后兴办“新教育”的履迹,始终没有完全摒弃“记诵”这一传统的授经方式,即便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力倡西式教法“不责记诵”的长处时,也不例外。《奏定学堂章程》正是依循“先读后讲”的原则设计初、高两等小学堂以及中学堂的经学课程,且学时安排上明显向“诵读”倾斜,(8)《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高两等小学堂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六点钟”,另有“温经[自习]钟点每日半点钟”;中学堂的“读经”和“温经”课时不变,“挑背及讲解”的周课时减半,“讲解”学时的比重进一步降低(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309、319页)。说其是力图在“新式学堂办法”中延承传统经学教法的基本思路,似不为过。
唯这样的延承也不乏“在传统中变”的痕迹。前文所述张氏庚子后的一系列学堂授经方案对“记诵”环节的具体安排和配置确有不小的变化。“讲解”一度被置于“记诵”之前,至《学务纲要》中尤有“以讲解为最要”的表述。如此着力提升“讲解”环节的重要性,与中国传统整体上并不那么强调“解说”而相对更注重“诵读”的经典授受取向明显异趣,实有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时代的风貌。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刊行的《劝学篇》中,张之洞即感慨学务面临着“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的两难局面。[1]169-170西学为用既是办学的重心所在,整体的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自然向这一重心倾斜,而中学教程则被“损之又损”。《劝学篇》中即有专篇强调“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其中首列“经学通大义”条,提出就清代解经著述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张氏进而倡导以“明例、要指、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项“节录纂集”成“学堂说经义之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在新式学堂一年或一年半讲授完毕。这样的“学堂说经义之书”从编纂到讲授皆以“浅而不谬,简而不陋”为宗旨,实与“求博求精”、“殚见洽闻”的传统“经生著述”明显异趣。在这里,讲授显然已是新式学堂学生以“守约”学程通晓经学大义的重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劝学篇》的设计,学子十五岁以前要读完诸经全文,此后进入全力通晓中学大略的“守约”学程。讲授上述“学堂说经义之书”即是这一“守约”学程的经学部分。几年后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则完全改变了《劝学篇》“先中后西”的教学模式,力图“中西学并行不悖”。经学由于课时的压缩,整体学程明显加长。读书人自7岁入学,要到中学堂毕业时才基本读完五经,时已21岁,[31]291-317至高等学堂的“经学大义”课程始大体对应着《劝学篇》中的“守约”学程。(9)即便是作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预备学程的“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其中学课时平均每周也不到10个钟点,约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张之洞:《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9页。
但能够由初等小学一直递升至高等学堂者实为少数。在此情形下,更多倚重“讲解”的教学环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小学堂学生(尤其是毕业而不升学者)相当精简的经学教育不会因“半途而废”,以致“全无一得”。故《奏定学堂章程》多次强调:因为“晷刻有限”,中、小学堂的“讲经通例”是“止能讲其大义”。[36]294、309、319这大体可说是将《劝学篇》旨在“通大义”的经学“守约”学程中最为浅显的部分,分摊至中小学堂的基础诵读阶段。这样的“讲经”,意在“开其性识,养其本根”,更有“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的考虑,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至宣统元年三月,学部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折中说,据学部官员的调察,各地兴办小学数量低于预期,办学官绅有数种“借为口实者”,其中之一即是“读经卷帙太多,不能成诵”。这从一个侧面提示《奏定小学堂章程》对经书“损之又损”的程度仍不能让各地办学官绅满意。“成诵”则是办学实务中经学课相当有难度的环节。对此学部的应对是与其“多读而不成诵,不如少读而成诵”,一方面进一步减少授读内容(实际上是将经义高深的《大学》、《中庸》以及“篇幅太长”的《孟子》延缓至高等小学阶段);另一方面仍以日本为榜样,将读经课的学程定为“讲解、背诵、回讲、默写”四环节,缺一不可。[37332-333原来的“温经”被“回讲”所取代,显然是力图以“回讲”的方式完成“温经”环节。原来的“挑背”则扩为“背诵”和“默写”两个学程,意在强调“熟读成诵”。整体看,学部的初等小学经学课程方案在“少读浅解”之路上走得更远,同时又进一步向“熟读成诵”这一传统经典授受重心回归。
四、结语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张之洞在致时任吏部尚书张百熙的电文中说:
考察学堂、商订学制及编译教科书必须参酌中、东、西,期于可行而无弊,关系极巨,条理极繁。[38]370
这里所谓“参酌中、东(日本)、西”,正是张之洞办理各项学务的基本思路,“期于可行而无弊”则提示着张氏的学务运作有相当务实的一面。唯当时中国社会尊西趋新的世风愈演愈烈,几至形成某种程度的霸权。在此氛围中,“新教育”建制鉴取“东(日本)、西”的部分被置于显要的位置并着力宣扬,而“参酌”中国传统做法的部分则大多隐而不显,低调为之,更有不少出以“外国榜样”为依据者,其中明显可见“防守”的态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清季最后十年主流的思想言说可能已至“举国以为至言”的程度,而张之洞本人更是大力提倡“中体西用”的代表人物。但若将张氏戊戌以降办理“新教育”的努力回置到他自同、光之交开始的整个办学履迹中,认真重建并梳理其办学实务中前后延承和演变的动态历史图景,可以看到他在倡言并践行“中体西用”的同时,实际并未完全摒弃“中用”,其“参酌中、东、西”中的“中”不仅仅指“中体”,还包括“中用”中他认为尚“有用”者,就维护和延承“中体”而言甚至还是“必须用”的部分。
本文所述清季“新教育”建制中的品行课设置以及记诵与讲解相结合的经学教授方式,其渊源和主体皆是在当时的不少时人看来与西(新)学对立从而明显边缘化(甚至已多少有些被“妖魔化”)的“中用”。《奏定学堂章程》的品行课即与张之洞自光绪初年以降兴办书院的努力,尤其是着力整顿书院“积习”的举措一脉相承。但在清季“新政”的学务改革中,西式学堂办法与“书院”的区别正是朝野普遍看重的办学要点,甚至一度成为“新教育”的评定标准和依据。(10)当时不少省份皆试图为科举停废后的读书人宽筹出路并保存国粹而兴办学堂。学部以“外标学堂之名,仍沿书院之实”,皆批驳在案。详见郭书愚《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书院”几乎完全是作为被取代和批判的对立面存在。而有关讲求“背诵”的中国传统经学入门教法有伤儿童脑力,远不如西式初等教育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认知在清季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已颇具“化民成俗”之势。
多少与上述“风势”有关,张之洞的相关学务运作的确呈现出明显的“防守”态势。《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品行”课设置更多以“参酌”西式学堂办法的面目出现,若非以“前后左右之法”比列考察,甚至不易发现其与此前张氏兴办书院的承继关联。而《奏定学务纲要》更是特意说明中小学堂经学课虽要求讽诵,但课时少且每天各门功课“时常更易”,整体上无碍西式学堂体制施展“养息幼童精力”、颇具“活泼精神”的长处,进而寻求外国读书也要责令学生记忆的例子作为依据。张之洞办学实务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实良有以也。
唯“防守”的态势并不意味着保守,更不等于“抱残守缺”。隐伏在“防守”表象背后的,是张之洞“参酌东、西”学,对“中用”进行的颇有创造性的变通。《奏定学堂章程》的“品行”课即延承着传统书院在近代中国演进的内在理路上自身孕育的加强管理、整顿积习趋向,试图发挥西式学堂办法“注重管理”的长处,进一步改进书院的“行检”考核举措。而戊戌以降中小学堂的经学教授方案一方面始终没有摒弃诵读与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坚持以“中用”保存并延承经学这一“中体”,并最终向“熟读成诵”的传统教法回归,另一方面则通过“少读浅解”的方针、提升讲解的地位、以“守约”之法编纂学堂经学用书等方式积极迎应西学冲击、适应时代需求。
虽然《劝学篇》中对于“旧(中)学”、“新(西)学”及其体用关系有明确的界定,更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列为“新教育”的首要法则。但张之洞的办学实务似乎并未过于拘守“中”与“西”、“体”与“用”的界域。“中学”可与“西学”相通,学堂可与书院相承,“中用”甚至可与“西用”整合并调适出颇具在地化特征的教育建制,经学课程的设计可以既贴近传统教法又积极迎应西学冲击和时代需求,所有“参酌中、东、西”的努力皆以“有用而无弊”为目标。(11)这一“实践中的主义”并不仅见于学务。李欣荣博士新近的研究即认为:学界有关张之洞晚年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是囿于“中体西用”观的认知“有失片面”。张氏在实践中“尽量扩充‘西用’范围以致用”,同时“以守约的方式来维持‘中体’”,试图“在礼教、法律和收回法权之间取得平衡”。而清廷核订新刑律最终走上“中学不能为体”的“完全以世界为主”之路。李欣荣:《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这样一幅“中、东、西学”紧密缠结,“体”与“用”多歧互渗的复杂办学图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所谓“中西体用”的畛域,其开放而前瞻的意味、灵活而具弹性的程度,似乎超出了我们此前的认知。相关面相尚有相当宽广的研究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整体上概而言之,在张之洞的办学实务中,“中用”只是少数具体而微的零星片羽,与“中体”与“西用”两个居于显要主体位置的巨大光环形成鲜明对照。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对中国传统办学模式的长处和特点重视不够、利用不足正是晚清以降的“新教育”可能存在的弊端。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观察。(12)民国菁英学人对此已批评有加,更有兴复书院的努力。参见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炳照教授也注意到,毛泽东1920年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认为,“从‘研究的形式’一点来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故力主“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详王炳照:《书院教学的革新精神》,《寻根》2006年第2期。这一认知显然是成立的,或也多少凸显出张之洞“参酌”书院“行检”考核、向传统经学教法回归等办学努力,的确是相当值得关注的面相。它们未必是当时众皆认同的办学思路,实际的办学效果也颇不如人意,但毕竟是在面对文化危机,力图改进传统办学形式、接续并传承中国传统学问时曾经有过的思考和选择,更浸透着张之洞乃至《奏定学堂章程》这一近代中国首次付诸实施的学制体系对于中西教育共通之处的探索。对于西式学堂办法“在地化”(glocalization)进程的尝试,应能帮助我们跳脱对传统的过度解构(deconstruct),深入认知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积淀,进而以开阔而通达的眼光,思考怎样才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