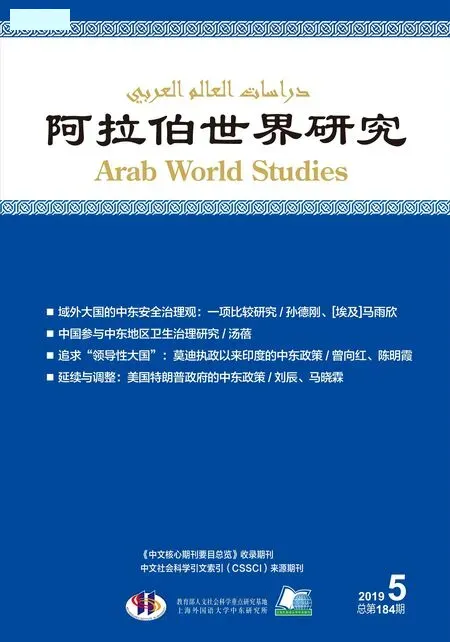“食利契约”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社会在
2019-03-15田宗会
田宗会
社会是国家治理的承载基础,治理的发展与变革不能长久背离于社会发展水平,否则便会出现治理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反之,社会也会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及国家治理水平与方式的影响,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关于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社会的研究,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大多为专题类研究,且国外研究成果比国内更为丰富。其中,关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教育问题,法蒂玛·巴德里(Fatima Badry)与约翰·威洛比(John Willoughby)在《海湾地区的高等教育革命:全球化与制度活力》一书中探讨了海合会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困境,认为实践和应用能力不强限制了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工作机会。(1)参见Fatima Badry and John Willoughby, Higher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the Gulf: Glob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 Via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其他相关文献参见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民兴:《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福利制度》,载《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2期,第67-68页;[美]G.高达特·巴赫贾特:《海湾六国教育回顾和展望》,周峰、石学斌译,载《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15页。阿米拉·艾资哈里·索博尔(Amira El-Azhary Sonbol)的《海湾妇女》则对海湾地区妇女权利与社会地位的嬗变进行了系统性探究。(2)参见Amira El-Azhary Sonbol, ed., Gulf Wome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其他相关文献参见Ruth Margolies Beitler and Angelica R. Martinez, Women’s Rol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lifornia: Greenwood, 2010; Eleanor Abdella Doumato and Marsha Pripstein Posusney, eds., Wome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Gender,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陈静:《海湾妇女发展问题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第45-48页;陈小迁:《多维视域下的中东人口治理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第57-72页;陈小迁:《中东阿拉伯国家人口治理失范的政治经济表现》,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第88-97页。安德鲁·加德纳(Andrew M. Gardner)的《陌生之城:海湾移民与巴林的印度社群》以宏观研究与案例结合的形式,对巴林的外籍移民的社会形态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3)Andrew M. Gardner, City of Strangers: Gulf Migration and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Bahrai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
除教育、妇女和外籍移民等问题外,国内外学界也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各组成单元,如马兹哈尔·祖拜(Mazhar Al-Zoby)和比罗尔·巴斯坎(Birol Baskan)主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4)Mazhar Al-Zoby and Birol Baskan, ed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Berlin: Gerlach Press, 2014, pp. 1-6.和赫勒敦·哈萨·纳吉布(Khaldoun Hasa al-Naqeeb)的《海湾和阿拉伯半岛的社会与国家》(5)参见Khaldoun Hasa al-Naqeeb,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Gulf and Arab Peninsula: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L.M. Kenny, tra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其他相关文献参见安维华:《论海湾部落社会的演化与部落传统》,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3期,第41-47页;王铁铮:《试探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特点》,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第60-68页;韩志斌、李铁:《文明交往与巴林伊斯兰社会变迁》,载《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6-80页;吴茴萱:《当代卡塔尔国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96页。,从不同角度对与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了梳理。事实上,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海湾君主制国家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但有关“食利经济”对社会形态的塑造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影响的深入研究仍相对匮乏。学界围绕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研究虽使用过“食利契约”的概念,但这类研究往往让位于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探求,缺乏对社会领域尤其是“食利契约”所建立的现代福利国家方面的研究。
事实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似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快速演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石油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呈现出“食利契约”的特征,政府履行“食利国家”的分配职能为民众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从而建立福利国家。在历史发展路径、政治经济模式、社会群体构成(6)本文中的社会群体构成是指本国民众与外籍移民的构成,并不特指族群问题。在海湾君主制国家中,除巴林的族群分布较为复杂外,其余五国的本国民众的社会构成相对单一。等方面,尽管海湾君主制国家国情各异,但它们的社会具有高度的相似性。(7)Richard I. Lawless, ed., “The Gulf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reign Institutions and Local Response,”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Durham, 1986, p. 1.因此,从整体上分析海湾君主制国家“食利契约”的形成及其现代福利社会的构建,有助于理解石油经济模式下君主国福利社会的相关特征。在过去数十年间,“食利契约”如何主导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福利社会的机制与功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缺陷,将是本文重点探究的问题。
一、 “食利国家”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食利契约”
在《食利国家》(TheRentierState)一书中,哈齐姆·贝布拉维(Hazim Beblawi)与吉亚科莫·卢西亚尼(Giacomo Luciani)指出,“食利国家”的运转实质上受到国家财政支出的支持,但国家财政本身则源于外国租用该国土地而产生的租金;换句话说,更普遍的现象是,租金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主导作用。(8)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Introduction,”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p. 11.作者归纳了“食利国家”的四大基本特征:其一,租金占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较高,但是由于国家类型不同,没有统一且精确的比值标准。其二,租金来源的外部性对于“食利国家”的概念判断至关重要,即使存在大量的内部租金,甚至其衍生出强大的“食利阶层”,也不足以称之为“食利国家”。(9)Ibid., p. 51.此外,数额庞大的外部租金可以在没有国内生产部门的情况下加以维持。其三,只有一小部分社会群体参与创造财富的进程,其余民众则只负责分配和使用财富。其四,政府作为承接外部租金的委托人,控制租金收入,国家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行为体,且在社会体系中扮演利益和惠赠分配者的角色。易斯兰·亚辛·卡西姆(Islam Yasin. Qassem)认为,“食利国家”的特征可大致概括为,收入主要源自于石油等外部资源(超过40%),且国内生产总值大多用于支出。(10)Islam Yasin Qasem, Neo-Rentier Theory: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1950-2000), Doctoral dissertation, 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Leiden University, 2010, p. 24.
当前海湾君主制国家具有典型的“食利国家”特征。一方面,海湾君主制国家采取国家主导型的治理手段。资源型导向的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引导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对创造真正的经济资产的作用较小。(11)Martin Hvidt,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Arab Gulf Countries: Lip Service or Actual Implementation?,” in Matteo Legrenzi and Bessma Momani, eds., Shifting Geo-Economic Power of the Gulf: Oil, Finance and Institution, Surrey and London: Ashgate, 2011, p. 4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逐渐将作为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石油业收归到政府手中,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力量,将石油收入分配给社会,公共消费成为首要分配渠道。因此,国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从某种层面上看,海湾君主制国家具有经济非生产性,产品市场指向呈现出非本土性的特点。资源型经济所造成的分配型治理模式,使得海湾国家对从事生产人口的需求较低,大部分经济部门均不承担生产职能。(12)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ckensack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4, p. 12.
在“食利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向国家主导治理的方向转变。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石油收入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近代,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双向“自治”的状态,国家只担负最基本的治理职能,社会也只对国家和中央政府予以最基本的税收回报。部落、显赫家族或其他宗派势力都对国家的职能权限与治理范围形成制约。(13)Nazih N. Ayubi, 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1995, p. 133.那一时期的沙特阿拉伯、特鲁西尔海岸国家还只是酋长国,更确切地说是部落聚集体,国家大体仍处于“社会的想象”之中。(14)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2.从20世纪初至石油开采前,对海湾君主制国家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缓慢进入到相互依赖的状态,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了诸如保护地方安全、维护总体社会秩序等治理责任,但其财政来源依赖于税收和关税。(15)Mazhar Al-Zo’by and Birol Baska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rab Gulf Region: Dilemmas and Prospects,” in Mazhar Al-Zo’by and Birol Baskan, ed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p. 4.
石油的开采以及由此带来的滚滚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对社会的依赖,此前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平衡迅速发生改变。至20世纪70年代,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时,各国政府已经基本卸下了从社会汲取财政及其他资源的重担,转变成为连接外部收入与本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中间人,同时也担任财富分配的执行者。(16)Hootan Shambayati, “The Rentier State,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aradox of Autonomy: State and Business in Turkey and Ir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1994, p. 309.与此同时,社会基本丧失了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沦为政治与经济决断的附属品。(17)Mazhar Al-Zo’by and Birol Baska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rab Gulf Region: Dilemmas and Prospects,” p. 5.事实上,伴随巨额石油财富的涌入,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与民众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如何分配财富并不像“食利国家”理论所总结的那样条理分明。但从实际情况出发,统治者并不想将数量庞大的财富让与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也确实无力自发组织从事开采、精炼、运输和销售石油等活动。于是,基于石油财富的“食利契约”初具规模。
简而言之,“食利契约”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一是国家向民众提供福利,二是民众出让政治权利。(18)F. Gregory Gause, Oil Monarchies: Domest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4, p. 42.与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打出的“无代表、不纳税”口号相反,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呈现出“没有征税、无需代表”的特征。(19)Dirk Vandewalle, “Political Aspects of State Building in Rentier Economies: Algeria and Libya Compared,”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p. 160.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其中沙特最为典型。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石油繁荣时代的到来,沙特政府完全扮演了财富收取者与分配者的角色,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彻底转变。一方面,沙特社会开始全面依赖国家给予的公共服务,民众获得免费的卫生和教育服务,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大幅增加。虽然经济利益没有实现平均分配,但几乎每个民众的收入境况都大幅好转。另一方面,沙特既不需要向社会征税,也不需要征召大量兵源。沙特军事部门被民众认为是高工资的上等工作岗位。国家只需要民众在政治上处于服从状态,(20)Islam Yasin Qasem, Neo-Rentier Theory: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1950-2000), p. 133.在社会中去政治化并减弱政治异议的不和谐声音。(21)Kiren Aziz Chaudhr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Lineages of the Rentier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7, No. 1, 1994, pp. 18-19.
在经济方面,“食利契约”改变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机制基础。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福利服务的机构,还是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有利可图的“摇钱树”。各类私营企业或个人通过竞争政府合同,申请补贴或银行贷款来提升自己的收益。正如卢西亚尼所言:“对于个人而言,他们认为福利制度所给予的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当前的机构中想办法获益,这总比寻找其他同类的人结成联盟而采用政治手段更有效。”(22)Giacomo Luciani,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p.74.因此在民众们看来,为了追求自身价值与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应该减少对国家的反对。换句话说,海湾君主国王室建立了一种基于“食利契约”的利益性互动环境,以全社会对王族和政府决策的政治默许换取经济奖励。(23)Islam Yasin Qasem, Neo-Rentier Theory: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1950-2000), p. 112.
二、 “食利契约”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社会
在“食利契约”的基础上,海湾君主制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被认为是现代高福利社会。有些学者认为,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社会构建与西方模式有共通之处,甚至是对西方国家现代福利制度的移植和发展。但事实上,二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很大差异,这决定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福利社会在发展路径、表现形态以及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具有独特性。
从事福利国家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早期的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兴起于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对社会福利事务的干预是基于资本主义的需要。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流民和乞丐,教会承担起对他们的救济工作。此后,英国政府发布公共援助计划并逐步为流民收容所中的乞丐提供服务,国家开始介入社会的福利事务。(24)David Denne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7.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及随之产生的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促使德国颁布了社会保险法,同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25)谢圣远:《社会保障发展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二战后,西方及世界范围内的福利国家体系普遍建立,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社会支出的增长非常迅速,1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用于公共支出,特别是用于教育、健康、收入维持和其他福利服务等社会支出。(26)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al Expenditure, 1960-1990: Problems of Growth and Control, Paris: OECD, 1985, p. 14.
在这些福利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欧诸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类型,有学者也称它们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类型。在这些福利国家中,国家承担的社会治理职责主要是通过税收重新分配经济财富,进而以这些财富构建福利国家体系。北欧的福利体制覆盖了全体公民,因此被称为普遍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公民权思想。(27)潘屹:《国家福利功能的演变及启示》,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第17页。此外,西方福利国家中还有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缓介入的原则,即只有在家庭福利功能无效的某些情况下才会施以援手。在这种模式中,市场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养老保险等在福利体系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28)潘屹:《国家福利功能的演变及启示》,第17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西方福利制度自身缺陷的暴露,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平均主义、社会迟滞效应等问题的反思,反对发展福利国家,甚至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主张维护自发秩序和捍卫个人自由,否定通过人为设计的集中控制社会秩序的政治理论,反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对个人生活的过分干预。(29)Vic George and Paul Wilding, Welfare and Ide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pp. 15-45.
相比较而言,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社会保障机制深深地根植于本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中。(30)Zakariya Sultan Mohammed, “Social Insurance Schemes in the Gul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 55, No. 4, 2002, p. 157.事实上,福利制度在阿拉伯半岛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阿拉伯半岛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幼童、老人、寡妇及独身之人的生活起居由本家族及部落负责周济,贫困群体也可以从传统的施舍行为以及好客之风中受益。可以说,在阿拉伯半岛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互助的需要与行为是原始福利观念的最根本出发点。
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德于麦加创立伊斯兰教后,逐渐将半岛上传统的福利风俗议定为教义条款,强调行善的重要性以及对孤寡穷人的接济。如《古兰经》(31)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出自马坚译本,参见《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所记:“凡作恶而为其罪孽所包罗者,都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2:81-82)“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获得的战利品,无论是什么,都应当以五分之一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者、旅客,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两军交锋而真伪判分之日,我所启示我的仆人的迹象。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8:41)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以及此后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半岛的福利制度基础也从血缘向地缘转化,进而成为具有固定机构和流程的地方性、社会性的公益事业。(32)黄民兴:《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福利制度》,第67页。每个穆斯林都有缴纳天课(zakat)的义务,即每人每年需要将自己收入的2.5%交予征收者。(33)Zakariya Sultan Mohammed, “Social Insurance Schemes in the Gulf Countries,” p. 157.同时,清真寺也起着慈善机构的作用,负责照顾并周济有需要的民众。甚至早期伊斯兰教有关男子可以娶四妻之规定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解决当时战争频仍导致的大批寡妇生活无着的社会问题。(34)黄民兴:《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福利制度》,第67页。
从海湾君主制国家福利制度传统和其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海湾君主国在建构各自的现代福利国家体系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建立福利制度的动机来看,海湾君主国基于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和阿拉伯半岛的传统文化观念,但西方国家不仅基于宗教信仰,还基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更加注重资本主义对于社会安定的需要。第二,从福利制度的类型来看,海湾君主制国家的高福利制度近似于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类型,但与北欧国家不同的是,海湾君主国基本没有实行税收制度。换句话说,国家并不是通过调节和分配社会创造的现有财富来推行福利制度,而是依靠配置外来财富以保证社会福利,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社会财富不平均的问题。第三,从福利制度的实施主体来看,西方福利国家强调国家与市场责任并重,保险和基金在英美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发挥着较大作用。海湾君主制国家则主要依赖于国家发挥作用,缺乏市场机制,福利事务基本上仍属于政治范畴,与经济关联甚微。
在“食利契约”的框架下,海湾君主制国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福利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是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为民众提供工作岗位和直接工资援助;二是以社会福利项目为基础,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基本保障。
公共部门的就业是海湾君主制国家提供给民众的最主要福利,也是社会公众最为看重的社会福利途径。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支出都是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公共事业机构每月的工资收入成为了绝大部分民众期望并依赖的收入来源。(35)Mishary Alnuai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audi Middle Class: A Preliminary Study, Dubai: Gulf Research Centre, 2013, p. 36.海湾君主制国家的青年即使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也无法满足私营部门的雇佣要求,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公共部门岗位,认为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36)Justin Gengler, Group Conflic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Bahrain and the Arab Gulf: Rethinking the Rentier Stat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3.。在沙特,公共部门提供的工资福利均比私营部门高。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公务人员在社会中较为体面,这导致许多沙特青年拒绝每月1,000至1,500沙特里亚尔工资的工作,宁愿依靠国家福利及父母亲人的接济度日,为轮到一个政府工作岗位等待很长时间。(37)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in Jean-Francois Seznec and Mimi Kirk, ed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ulf: A Socioeconomic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48.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湾君主制国家确实创造了大量的公共部门就业岗位。但随着青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近年来海湾君主国公共部门的职位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海湾诸国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的增加最先从沙特阿拉伯开始。从1965年至1966年,沙特政府部门总共增加了66,460个职位,此后数量直线上升,内政部的工作岗位几乎增加了两倍。与1950年沙特国内仅有数百名公务人员相比,1965年公共部门的人数已经达到101,909人,公职人员的工资开支差不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38)Islam Yasin Qasem, Neo-Rentier Theory: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1950-2000), pp. 90-91.在海湾君主制国家,过去几十年间国家通过公共部门就业而建立“食利契约”下的福利制度仍在持续推进。根据科威特国家银行统计,2009年海湾君主制国家公共部门中就职的民众数量占整个地区就业人口的58%,其中卡塔尔超过90%,科威特占84%,沙特占50%,巴林占43%。(39)Mohammed Zaher, “GCC: Fiscal Stimulus and Reforms Are Optimal Choice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GCC Research Note, National Bank of Kuwait, April 2, 2009, https://www.nbk.com,登录时间:2018年12月12日。在公共部门就职的人口持续增加,自2006年至2007年,海湾君主制国家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增长了5.2%,其中阿联酋和阿曼的增长率达5%,科威特达4.4%,沙特达2.9%,巴林达2.4%,而卡塔尔的增长率更是飙升至33%。(40)Mohammed Zaher, “GCC: Fiscal Stimulus and Reforms Are Optimal Choice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海湾君主国公共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再次升高,阿曼2011年私营部门雇佣的国民数量比前一年降低了4%;科威特2011年民众入职公共部门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2012年该国公共部门的工资开支相当于石油收益的85%。(41)Suliman Al-Atiqi, “Laboring Against Themselv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26, 201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51044,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3日。
就社会福利项目而言,海湾君主制国家向全社会提供基本食品和商品的价格补贴,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住房贷款等公共产品。(42)黄民兴:《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福利制度》,第67页。在沙特阿拉伯,自费萨尔国王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十点计划”以来,国家逐步建立了全面的社会福利项目并奠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43)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18 Country Report: Saudi Arabia, Gu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8, p. 24; Moneef N. Mlafekh, Power and Autonomy in the Saudi State: Case Study Analysi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0, p. 4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实行的社会福利补贴主要针对小麦和大麦的农产品价格以及电费、社会保障金等与社会服务相关的各类补贴。更最重要的是,沙特民众几乎不需要纳税。1970年,沙特的补贴支出达1,700万沙特里亚尔,1984年增加至121亿沙特里亚尔。(44)Ministry of Planning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Plans, 1970-1989, Riyadh: Ministry of Planning, 1989, p. 55.此外,沙特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和医疗,婚后每对沙特夫妻都有资格申请无息贷款建造住房。(45)David S. Sore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Middle East: History, Religio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2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4, p. 143.然而,数目庞杂的社会福利项目不仅使沙特财政背负了巨大压力,还带来社会服务灵活性不够和水平偏低等问题。因此,沙特政府开始尝试推行社会保险项目以辅助社会福利项目的施行。比如2011年,沙特开始施行失业援助保险项目,为失业者提供12个月的生活补助。(46)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18 Country Report: Saudi Arabia, pp. 24-25.
巴林等其他海湾君主国的情况与沙特类似,不仅为民众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而且还有门类繁多的政府补贴。巴林于1976年建立的社会保险服务体系覆盖了全体国民以及在巴林定居的其他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民众。巴林的社会保险服务包括老年退休金、养老金、伤残人士补助金、遗孤抚恤金以及丧葬费用。社会保险的缴纳金额为月收入的15%,由雇主和职员分摊。由于近年来石油价格震荡,巴林、阿曼等国政府受困于社会服务和商品补贴的高额开支,开始限制某些群体的社会福利权利。2015年初,巴林卫生部制定并实行新的私营部门外国雇员社会保障计划,要求雇员少于50人的私营公司每年为每位外籍雇员支付189美元、为每位巴林籍员工支付58美元的政府医疗服务费用。(47)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18 Country Report: Bahrain, Gu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8, pp. 22-23.
三、 现代福利制度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对于“食利契约”下现代福利国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学界大致存在两种观点。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社会被纳入到“食利体系”之中,无力也无太大愿望反对政权,“食利契约”可以有效保证社会稳定。换句话说,石油收入及政府分配石油收入的举措压制了社会中不安定因素的爆发。(48)Gwen Okruhlik, “Rentier Wealth, Unruly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3, 1999, p. 308.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食利契约”及高福利制度与社会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尽管贝布拉维和卢西亚尼等学者为‘食利契约’对社会稳定的有效性进行辩护,但持久的社会稳定似乎并不依赖于持续存在的石油租金,政权并不能购买合法性。同时,经济衰退也没有导致石油出口国出现政权危机或不稳定的态势。”(49)Benjamin Smith, “Oil Wealth and Regime Survival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60-1999,”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Issue 2, 2004, p. 242.马蒙·范迪(Mamoun Fandy)认为,“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时,按道理会爆发政治动乱,但是该时期沙特政治稳定,而在石油价格上涨时期,该国的反对派数量却增加了”(50)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 26-29.。
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的共识是,如果没有基于“食利契约”建立现代福利社会,当前海湾君主制国家远不会实现相对平稳的政治局势。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财政支出确实分为经常性的项目支出和生产投资的资本支出。即使在1986年和1988年石油价格触底时,沙特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绝对价值计算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3%,很大程度上是优先保证了福利制度的经常性项目支出的花费。(51)Islam Yasin Qasem, Neo-Rentier Theory: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1950-2000), p. 44.巴林的公共管理支出也从197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增加到1990年的22%。(52)Zakaria Ahmed Hejres, The Prosp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ahrain Trough the Services Sector,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8, p.155.虽然巴林的福利制度难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标,且在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政治与社会动荡,但动荡与“食利契约”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实际上,“食利契约”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作用还在于危机时刻的财富输出效用,国家在政治及社会动荡时期购买合法性以平息大部分不满民众的怒火。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当属中东变局。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时,突尼斯、埃及等共和制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权相继倒台,但除巴林之外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基本保持稳定。回顾这一系列事件,海湾君主国并没有推行彻底的改革,而是面对民众潜在的不满,回归并加强了福利制度的功效,以“经济礼物”平息社会不满。有学者评论道,海湾君主国对危机的本能反应,是通过大量增加的石油收入加强财政资助,或多或少地利用安全力量进行压制,“食利者”的慷慨似乎也是一种诡计。(53)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p. 29.这些措施包括增加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工资,提高私营部门雇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强制性增加国内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就业岗位。例如,沙特新增的公共机构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阿曼新增5万个就业岗位;(54)陈小迁、韩志斌:《中东变局以来阿曼国家治理转型述评》,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115页。巴林则在国家机构内新设置了2万个工作岗位,(55)Martin Hvidt,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GCC States: An Analysis of Aims and Visions in Current Development Plans,” in 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26.增幅超过50%。(56)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p. 29.此外,海湾君主制国家还宣布实行新的市民补贴标准,降低公共服务费用,新增福利开支项目及公共住房补贴项目。2011年2月和4月,沙特政府宣布新增福利项目的财政预算总额估计为1,30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整个国家预算的两倍。(57)John Sfakianakis, Daliah Merzaban and Turki A. Al Hugail, Strategy Shift: Saudi Spending Swells, Oil Price Jump Evens out Fiscal Balance, Banque Saudi Fransi Reports, April 2011.2011年巴林局势陷入动荡后,在沙特的动员下,海合会国家同意为巴林和阿曼紧急拨款200亿美元用于以经济手段购买政治合法性。(58)Hadi Khatib, “Can Saudi or the GCC Save Bahrain?,” AMEinfo, November 2, 2017, https://ameinfo.com/money/banking-finance/will-saudi-save-bahrains-neck-nick-time/, 登录时间:2018年12月26日。
海湾君主国的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稳定,但也造成了许多其他问题。“食利契约”以国家为社会提供福利项目换取民众的政治默许,但福利项目的实施需要依赖石油收入的水平。在石油价格波动以及整体经济震荡时期,如何维持福利制度是摆在海湾君主国政府面前的一个治理难题。此外,民众的政治默许与社会风气关系密切,如何确保民众一直服从于国家,或在民众沉默的情况下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是各国治理精英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体而言,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制度造成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现代福利制度使民众养成了“食利者”心理,缺乏劳动积极性,同时滋生了懒惰狂傲的态度。有学者认为,“食利者”心理深深根植于海湾君主国民众的思想中,大部分人好逸恶劳,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希望支付很少的税收,但却想要获得大量的利益。(59)Paul Joyce and Turki Al Rasheed, Public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Public Governance of in the Gulf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8.此外,由于外籍劳工承担了大量生产服务性工作,而海湾君主国的国民很大程度上可以清闲无忧,这使他们普遍存在一种“主人—仆人”心态,这也是贝都因人部落文化的遗产。也有研究者认为,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民众因处于支配者地位而产生“老板心理”,石油收入为各国民众带来了大量财富,这使得他们将自身视作拥有财富的老板,平日对那些外籍劳工颐指气使。(60)Karen Leonard, South Asian Workers in the Gulf: Jockeying for Place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144.
第二,现代福利制度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就业机制扭曲,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人力资源的雇佣规模差距加大。(61)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p. 32.在海湾君主制国家,民众的主要生计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的公共部门就业,如沙特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比私营部门多4倍左右,这造成了人力资源分配比例极不平衡。各国的私营部门普遍存在低工资水平的现象,而公共部门又因福利制度而拥有高工资和隐性收入。如沙特公务员每月平均工资为9,000沙特里亚尔,私营部门则只有3,000沙特里亚尔左右。(62)Messaoud Hammouya, Statistics on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Methodology, Structures and Trend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1999, p. 34.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海湾君主国民众寻求私营部门工作的积极性。此外,海湾君主制国家普遍缺乏推行与基础收入和税率、劳动力市场积极性相关的措施,更缺乏实行财富二次分配的政策。(63)Philippe Van Parijs, “Basic Income: A Simple and Powerful Ide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2, No. 1, 2004, pp. 17-39.过于平均主义给了民众“搭便车”的机会,却使其丧失了前往私营部门工作的积极性。(64)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pp. 43-46.
第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制度还造成能源过度消耗、民众生活奢侈浪费的状况。海湾君主制国家水、电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并不彻底,基本属于国有企业,政府为民众提供廉价或免费的电力和淡化水反而导致较高的人均能源消耗。例如,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电力人均消耗量相当于欧盟国家的两倍多。2007年,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家庭住宅耗电量占国家总耗电量的42.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26.8%,非经合组织国家仅为17.5%。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电力补贴数额较高,巴林与沙特的补贴支出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和3%。此外,自1986年以来,海湾国家的人均石油消费量增长了三分之一,总消费量则增加了158%。(65)Steffen Hertog, “Redesigning the Distribution Bargain in the GCC,” in Michael Hudson and Mimi Kirk, eds., Gul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32-35.2010年,沙特国内消耗的石油数量相当于德国这个更加富裕且人口三倍于沙特的国家消耗量。按当前趋势预计,至2028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每天石油产量需要达到830万桶才能满足国内需要,这一数字基本与石油出口量相持平。(66)Steffen Hertog, “The Sociology of the Gulf Rentier Systems: Societies of Intermedia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2, No. 2, 2010, p. 302.
第四,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耗费了大量钱财,致使国家财政出现高额赤字,成为各国政府卸不下的重担。海湾君主制国家各种福利项目及公共部门工资开支所造成的每年庞大的财政支出在此无需赘言,但其所造成的问题却是影响深远,即签订了“食利契约”的海湾统治者逐渐意识到,“食利契约”基本上没有退出机制可言,一旦卸下责任将面临重重困难以及政权不保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海湾国家爆发财政危机,公共就业和廉价的社会服务无疑成为政权不敢轻易触碰的最后一条底线。即使廉价的社会服务涨价也会在抗议声浪中回调或采取其他福利措施弥补。正如有学者感叹:“权利一旦被创造,便很难解除。”(67)Steffen Hertog, “Lean and Mean: The New Br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ulf Monarchies,” p. 42.
事实上,海湾君主制国家治理本质上是在“食利契约”下运行的,近年来这些国家推进治理变革,目的在于提升效能,将治理职能交归市场,实现国家财政开源节流,最终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源为辅助的“治理契约”。在这一过程中,海湾国家主动调整政策,逐步卸下“食利责任”,注入市场原则,建立新型现代福利社会。各国纷纷加征了5%的增值税,同时在保证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减少补贴。近年来,巴林、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纷纷在粮食、肉类、副食、电力、水资源、油气能源等方面削减国家补贴,沙特2016年国家财政预算的发布,被认为是海湾君主国慷慨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终结。(68)“Saudi Budget Marks End of Era for Lavish Gulf Welfare Handouts,” Arab Business, December 30, 2015,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saudi-budget-marks-end-of-era-for-lavish-gulf-welfare-handouts-616798.html, 登录时间:2018年9月20日。
然而,海湾君主国的改革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政策落实艰难,易流于空谈,不仅受到各方的抵制,还会在社会局势震荡的情况下推迟或取消相关政策;(69)Ibid.二是政策经常遭到变相推翻,如巴林在取消食品补贴后,为应对社会压力改为直接向民众发放食品补助金。(70)Sarah Townsend, “Focus: The Impact of the Bahrain Food Subsidies Row, What It Means for the Wider Region,” Arab Business, September 18, 2015,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focus—impact-of-bahrain-food-subsidies-row-what-it-means-for-wider-region-606590.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12日。实际上,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食利契约”与海湾国家现代福利社会的本质悖论,即通货膨胀、物价增长、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君主制政权的执政基础遭到侵蚀。这种情况便是所谓的“短期内改革没有一方能够真正获利,改革伤害民众利益,更伤害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困境。
四、 余 论
海湾君主制国家基于“食利契约”建立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历史传统与石油地租经济发展模式辩证统一的结果,更是世界现代福利国家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现代福利制度有效保证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成为海湾诸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和手段。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现代福利国家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海湾君主制国家对于现代福利制度的承载压力逐渐增大,各国亟需在最大限度保证“食利契约”的基础上对现行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和修正。但对于现代福利社会而言,过于刚猛的改革显然具有“回潮倒水”的不切实际性,也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找准政策切入点并确立正确的长远战略目标,才是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福利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
根据福利国家的相关理论,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和商品化的程度是衡量福利国家本质的一个关键指标。在技术手段上,只有优先弥合商品实际价格与补贴价格,公共部门工资与私营部门工资,国家福利项目与民众商业保险基金等方面的双轨制差距,才能平稳地推行改革。例如,对水、电等日常资源采取重叠税率体系(stacked tariff system)的加价方式,进阶价格随着消费的数量而增加。目前沙特的某些居民和商业领域已经实行了电力重叠税率,但部分地区的政策实施并不彻底,且面临难度。此外,国家也应当采取扶持力度增加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对公共和私营部门区别征收个人所得税款,刺激民众向私营部门流动和劳动积极性。
上述探讨仅限于技术层面,而问题解决的关键仍在于政治层面,即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治理的成功取决于统治者是选择开拓思路更新“契约”,还是重走老路抱残守缺。事实上,不仅是海湾等中东国家,世界范围内对福利国家的反思都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对国家福利功能的批判,要求国家责任的退出;二是以削弱国家责任为前提,进行公民社会建设;三是在公平竞争旗帜下,以倡导福利多元化之名,行福利私有化之实。(71)潘屹:《国家福利功能的演变及启示》,第22页。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精英最理解本国统治的基础,国家退出或削弱国家责任,无疑意味着政权的瓦解,此条道路断然不能保证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威权治理体系长治久安。与之相对应的是,海湾君主国既要明确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也要加强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如何将社会治理的重担分摊在社会力量不断发展的道路上,而非变为旧有治理模式的越发沉重的包袱,才是海湾君主国政府最应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