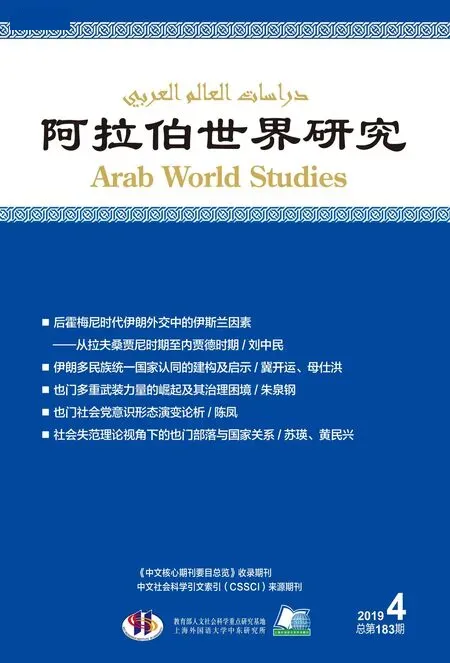马克西姆·罗丹逊的伊斯兰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探索*
2019-03-15周思成
周思成
一、 导 论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来,对宗教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完成的,并得出了宗教不过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神是人”的结论。[注]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520-521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宗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须从国家自身的本质中,进而从各种观念形式构成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即“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寻找根源。[注]同上,第169页;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关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参见N. Lobkowicz, “Karl Marx’s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6, No. 3, 1964, pp. 319-352;W. Post, Kritik der Religion bei Karl Marx, Muenchen: Koesel, 1969。国内相关研究参见王珍:《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万斌、金利安:《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探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方面,正如列宁所言:“宗教对人类的压迫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如果需要在现实斗争中批判宗教,就必须先“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注]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4-135页。,而不是去直接抨击宗教教义、仪式或神学本身。[注]特别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这个“日常生活的宗教”,才是他毕生致力于祛除的魅影。参见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另一方面,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特定时代条件和地缘环境下论述宗教问题时,往往更多地关涉犹太教和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官方形态(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注]列宁虽然有更多机会接触原帝俄境内的穆斯林,但列宁的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后来在苏联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制度化,仍主要涉及原为俄国国家教会的东正教,而伊斯兰教由于被视为穆斯林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则更多与苏联的民族政策实践相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等译,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45页。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宗教及其现实根源的批判具有某种普适性,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以下事实:他们的著述很少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社会、政治、教义学或历史地位进行系统分析和思考,[注]相关论述散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论断。参见马福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阿拉伯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唐晓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近百年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总体面貌与重要程度,已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截然不同。
其实,正是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本身,而不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相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至原帝俄境内的高加索、鞑靼斯坦和中亚的穆斯林民族中,促使以米尔赛义德·苏丹-加里耶夫(Мирсаид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为代表的“穆斯林共产主义者”对受压迫穆斯林的“无产阶级性”、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的共存形式、穆斯林在社会主义东方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注]参见[日]山内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イスラム世界とロシア革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164-189页。然而,这种理论火花只是昙花一现。二战后,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埃及和叙利亚等国一些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或“伊斯兰社会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如穆斯林兄弟会的西巴伊(Mustafa al-Siba’i),试图以《古兰经》和“圣训”来证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的神髓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及三者对社会正义与平等的共同追求等。[注]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p. 177.晚近一些欧美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将伊斯兰教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敌人或社会主义的潜在盟友,认为伊斯兰与社会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性不平等、资本和西方价值观的霸权,等等。[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Michael Pallis, trans., London: Zed Press, 1979, pp. 34-35.这类观点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为严格而科学的理论思考却付诸阙如。已故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马克西姆·罗丹逊(Maxime Rodinson, 1915~2004)关于伊斯兰教的历史著作和评论文章,恰恰——特别为中国学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马克西姆·罗丹逊生于流亡巴黎的俄国犹太人家庭,1936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继而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习伊斯兰教,又长期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从军和游历。二战后,他相继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高等实习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就职,1983年荣休。罗丹逊的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在1937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继续坚持斯大林路线,1958年罗丹逊与法共分道扬镳。[注]关于罗丹逊的早年生涯,参见Sébastien Boussois, Maxime Rodinson, un Intellectuel du XXe Siècle, Paris: Riveneuve, 2008, pp. 119-120。这本题为《马克西姆·罗丹逊:一位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文集,汇编了罗丹逊逝世后多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亦可参见罗丹逊的回忆录:Maxime Rodinson, Souvenirs d’un Marginal, Paris: Fayard, 2005.不过,罗丹逊一直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神论,同时积极声援第三世界受压迫民族特别是巴勒斯坦民族的解放事业,终身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著名左翼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评价罗丹逊是“领先于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de ces communistes en avance sur leur temps)。[注]Sébastien Boussois, Maxime Rodinson, un Intellectuel du XXe Siècle, p. 29.此外,不少评论者都注意到他身上具有法国知识分子的“多面手”(touche--tout)特性,[注]Ibid., pp. 22-23.罗丹逊不仅通晓30多种语言,且研究领域覆盖伊斯兰研究、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历史、埃塞俄比亚研究,等等。法国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历史学家贝伊(Farouk Mardam Bey)在回忆文章中曾评价罗丹逊既是“百科全书式学者”(encyclopédiste),又是“多个特殊领域的著名专家”。[注]Sébastien Boussois, Maxime Rodinson, un Intellectuel du XXe Siècle, pp. 49-50.
罗丹逊在伊斯兰教和中东研究领域出版过多部经典作品。1960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穆罕默德传》(Mahomet)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罗丹逊的这部早期作品已经显示出他后来的治学特色,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罗丹逊承认,这部传记并不提供任何新的史实,其特色首先表现为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引入了当代阿拉伯社会运动这一现实参照系,其次在于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呈现为一种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创建者,并聚焦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运动中某些恒定的因素(les constantes)。[注]Maxime Rodinson, Mahome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4, pp. 9-10.在罗丹逊的其他学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当属《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IslametCapitalisme, 1966)以及汇编了作者各时期论文的《马克思主义与穆斯林世界》(MarxismeetMondeMusulman, 1972)和《伊斯兰:政治与信仰》(L’Islam:PolitiqueetCroyance, 1993)。这几部著作被认为是“对于理解真实穆斯林世界不可或缺的作品”(des ouvrages indispensables pour comprendre le monde musulman actuel),[注]Sébastien Boussois, Maxime Rodinson, un Intellectuel du XXe Siècle, p. 105.尽管它们大多完成于20世纪,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及局限性,却仍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伊斯兰教历史和穆斯林社会的认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批判和借鉴。
二、 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伊斯兰教
罗丹逊对自身基本理论立场的反思,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但总体来说,他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学”维度出发来审视伊斯兰教的。罗丹逊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批判虽然自有其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学或社会史学——尽管马克思并不使用“sociologie”一词——才是最犀利的批判武器。[注]Maxime Rodinson, L’Islam: Politique et Croyance, Paris: Fayard, 1993, pp. 14-15.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预设出发,罗丹逊一方面批判结构主义将社会视为人类思维结构派生出的各种制度之总和的谬误,另一方面也反对那种认为特定的宗教教义和哲学能够“直接地和自动地”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推演出来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社会基础的变迁主要是通过影响特定意识形态“被构建、阐释、刺激、动员和体验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注]Ibid., pp. 10-11; 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p. 188, 190-192.
今天人们往往认为,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还是穆斯林的一种身份认同、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首先仍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一神教,而罗丹逊对伊斯兰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宗教社会学”(Religionssoziologie)研究。罗丹逊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复合体,应该区分出两大层次:一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一是以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为基础的伊斯兰思想,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意识形态结构(les structures idéologiques),这些思想的系统化和精密化及其传播、接受等问题。[注]Maxime Rodinson, L’Islam: Politique et Croyance, p. 12.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伊斯兰教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mouvement idéologique),这种意识形态运动在历史上建构出一个新的共同体(全体穆斯林组成的“乌玛”)及其自我认同,同时也产生出一种建构某种理想社会的思想。[注]Ibid., p. 30.在另一篇文章中,罗丹逊还用“隐含的意识形态”(implicit ideology)来称呼伊斯兰教,强调它绝非中世纪以来就确立的一套固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根据不同时期穆斯林人群的实际需要和愿望不断被重新诠释和创造的传统。[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 44.
应当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伊斯兰意识形态?尽管在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将现实加以歪曲、“异化”或“神秘化”的思想体系,不过他们并不否认存在一种广义的、不具有歪曲特征的意识形态。在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分类中,前一类(狭义的)意识形态是特权阶层企图通过粉饰现实来维持现状的一套观念和信仰,而后一类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旨在超越现状的“乌托邦”。[注]Ibid., p. 37。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准确扼要的综述,参见[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孔兆政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4页。罗丹逊指出,伊斯兰教为穆斯林提出了一种社会改革方案,一种“在地上而非天堂实现的规划”(un programmeréaliser sur terre),这一点使其区别于基督教和佛教。换言之,伊斯兰教并不是信仰同一真理的信众的集合,而是一个“总体社会”(société total)。[注]“总体社会”是一种既具宗教性质又具政治体性质的社会组织,罗丹逊认为伊斯兰教不同于基督教,成为穆斯林就意味着同时成为信众(croyant)和臣民或国民(sujet)。参见Maxime Rodinson, L’Islam: Politique et Croyance, pp. 30-32。这里罗丹逊实际上是从意识形态侧面解释了人们常说的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和“政治宗教”特征,或用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的话说,伊斯兰主要是“要求人们按某种方式生活的宗教”,而不必然要求承认某种教条或学说。[注]顾德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视域下的当代中亚伊斯兰政治化研究》,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3页;[英]凯伦·阿姆斯壮:《伊斯兰》,林宗宪译,台北: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页。罗丹逊进一步认为:“一般而言,伊斯兰意识形态具有曼海姆式的狭义上的意识形态性,在整个历史时期直到今日都是如此。但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在诞生之初是乌托邦式的(或者部分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化出不同的形式,并且在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甚至在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运动中,也呈现出乌托邦性质。”他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对人类在世界上处境和地位、社会和世界的本质的某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从而为个体的公共和私人行为提供了一套指导规范;其次,这种意识形态带有某种极权色彩,即它的规范和判断延伸到了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再次,这种意识形态通常有一组神圣化或半神圣化经典作为外在表现形式;最后,一旦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运动取得了成功,就极易完全或者部分地从“乌托邦式的”转变为(狭义上)“意识形态性的”。[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p. 37-39.
在回答作为一种“宗教—伦理的意识形态”(l’idéologie éthico-religieuse)的伊斯兰教究竟对现实中的族群关系、国家、经济制度和文化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一疑问时,罗丹逊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具有根本性:伊斯兰教自诞生伊始就不曾阻止人类社会的初级共同体——部族或者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分裂,反而常为这类冲突提供口号(slogans)、象征(symboles)或者意识形态名分(l’étendard idéologique);伊斯兰教赞成实践这种或那种性质的经济行为,只要这些表面上符合伊斯兰精神,但极少有意废除或者改革那些在它看来是自然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例如奴隶制(这与基督教如出一辙);伊斯兰教在现实中通常屈服于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则,它通常被权力驯服(逊尼派国家),或者不得不与之“共存共谋”(什叶派国家);相似地,伊斯兰教给特定社会带来的文化转型仅仅是局部的,在这一过程中它自身也受到影响。[注]Maxime Rodinson, L’Islam: Politique et Croyance, pp. 48-58.
三、 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 文化决定论的贫困
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可视为这种宗教意识形态与某一特定生产部门、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甚至是一个全球体系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注]通过综合马克思和韦伯的分析,罗丹逊在《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承认,自己正是在“生产部门”、“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三个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参见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p. 6-9。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讨论过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注]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7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新教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带来的经济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注][英]安东尼·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何雪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韦伯则指出,新教伦理,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职观念、禁欲主义等,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从这一观点再前进一步,就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驱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理性精神是否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独有的?东方社会未能发展出工业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否因为本土意识形态(如儒家思想)的“阻碍作用”?[注]关于“文化决定论”及其批判,参见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载《学问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327页。
事实上,伊斯兰教因在教法(Shari’a)中明确禁止“里巴”(rib,利息或重利)和投机性契约,通常也被认为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罗丹逊的《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是较早对这种观点加以批判的代表作。[注]笔者管见所及,此书已有日、德、英三种译本,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许多晚近著作讨论相关问题时亦频繁引用此书。罗丹逊首先关注的是,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传统是否反对采用现代的、进步的经济模式?伊斯兰传统究竟有利于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还是反对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因而阻碍进步?伊斯兰传统是否天然倾向“封建经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还是能够发展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注]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p. 2-3.可见,在罗丹逊看来,关键是要意识到探讨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非是出于某种纯粹的理论兴趣,它其实是关于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现实问题。
首先,在宗教的经济伦理层面,罗丹逊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对于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的态度,他认为《古兰经》的根本精神并不反对私有制或雇佣劳动,但谴责为富不仁,强调在真主对世人的审判面前财富毫无作用,反对高利贷。在罗丹逊看来,“圣训”也承认和保护私有制,反对高利贷,提倡缴纳天课,从事慈善,等等。总的来说,“在穆斯林传统和《古兰经》中,追求正当利润、贸易以及为市场生产商品的经济活动都没有遭到贬低”,而在对财富的一般性谴责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并无太多差别。[注]Ibid., pp. 14-16.罗丹逊进一步指出,《古兰经》、“圣训”或教法学中大量采用理性论证和推断,这与资本主义要求的理性化并不矛盾,[注]Ibid., pp. 78-99.伊斯兰教与欧洲在近代的“大分流”——我们不妨借用美国学者彭慕兰名著的标题——不应该从人类对于某种特定思想的从属关系中寻找根源:
“韦伯将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有且仅有欧洲才具备的某种特殊理性(specific rationality),这一看法是毫无根据的。一旦我们观察那些不曾产生出资本主义的文明,包括伊斯兰,并不难看到它们同样具有理性,只是程度较低……因此,我们毫无理由认为,穆斯林的宗教妨碍了穆斯林世界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伊斯兰并没有给信仰它的人民、文明和国家规定或强加任何一种经济发展道路,而中世纪伊斯兰的经济结构与同时期的欧洲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其实,直到遭遇欧洲冲击之前,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结构也是如此。”[注]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p. 116-117.
其次,从历史发展进程出发,罗丹逊研究了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都具有外来输入性质,先是在欧洲优势(European supremacy)、后来是在欧洲模式(European model)的主导下艰难发展起来的。直到20世纪之前,埃及、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均依附于英、法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外国资本通过不平等条约保障的低关税和债务等手段压制民族工业,当地多数工业企业也实际由外国资本或者买办资本控制。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上述已实现独立或仍保持殖民色彩的伊斯兰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发展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但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薄弱、劳动阶级受教育程度低,私有部门不发达,这一努力最终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注]Ibid., pp. 121-131.
罗丹逊进而指出,一方面伊斯兰思想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泥古不化,它容许所谓的“异端”(bid’ah),对现代技术和现代社会新事物至少抱有消极的容忍态度;又如,对于利息的禁止,在现实商业操作中产生了大量的(甚至为一些教法学家所支持的)规避手段(hiyal)。另一方面,不应忽视穆斯林社会自19世纪以来经历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伊斯兰教法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民法和商法的采纳等方面。这两方面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事实上,综合传统经济伦理和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层面提出“伊斯兰传统对资本主义在伊斯兰国家的现实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可以看作罗丹逊对传统研究理路的一种矫正。许多研究者——或许是受了韦伯研究新教伦理和强调“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专注考察伊斯兰教义中与资本积累(利息和利润)、企业家精神或自由市场规律有关的抽象伦理,很少把二者的关系还原到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具体社会这—历史进程中加以思考。[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最近的概述,参见Vassili Joannidès de Lautour, Accounting, Capitalism and the Revealed Religions: A Study of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Isla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26-31。罗丹逊的上述分析,尽管局限于工业化时代,而未延伸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毕竟极大地拓宽了“伊斯兰社会学”——借用当代土耳其学者图鲁·凯斯金(Tugrul Keskin)偏爱的一个术语——研究的视野。当代“伊斯兰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体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关注到了全球金融体系、石油经济、新自由主义、消费文化、城市化和社会运动等新问题,并且可细化为以不同区域、国别或特殊穆斯林社群为对象的社会学个案研究。[注]参见Tugrul Keskin, ed., The Sociology of Islam: Secularism, Economy and Politics, Reading: Ithaca, 2011, pp. 1-18。然而,罗丹逊对解决基础问题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基础问题上,罗丹逊认为仍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夸大社会心理的反作用。在《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罗丹逊总结说:以前的研究者往往认为,伊斯兰教对重利和投机性交易的禁令、宿命论思想或者近代穆斯林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遭遇的冲击,往往压抑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上述因素在现代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趋于弱化,而伊斯兰国家中的经济个体和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个体并无实质区别,如实证研究证明,在使用童工和劳动立法方面,穆斯林资本家绝不比基督教资本家更加仁慈。伊斯兰教中的所谓“反资本主义”因素,如对私有制的限制、互助制度、共同体团结等,也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相反,若过分鼓吹这些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既有可能动员穆斯林民众去实现一个没有特权和剥削的社会,也有可能掩盖、确实也常常掩盖了近代各伊斯兰国家中特权阶级与贫困的被剥削阶级共存于一个“乌玛”内部的残酷现实,在对这类现实的揭露上,马克思的思想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注]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p. 137-184.
四、 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从冲突到调适
在《马克思主义与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两本著作中,罗丹逊尝试对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或许尤为重要,然而它较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更为复杂。为了客观理解和评价罗丹逊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我们必须首先廓清以下两个方面的基础认识。
第一个基础认识是,除了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个别思考,对于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个连续性的思想史传统,或者说,不存在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伊斯兰思想、穆斯林社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才再次为某些西方研究者所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埃及、阿尔及利亚或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建立的一些政权,先后采取了某种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本国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口号;[注]关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参见Heinz Gstrein, Marx oder Mohammed? Arabischer Sozialismus und islamische Erneurung, Würzburg: Verlag Ploetz Freiburg, 1979;郁景祖:《什么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载《社会主义研究》1982年第1期,第40-46页;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42页。另一方面,人们也观察到,冷战格局下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外溢到第三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包括美国著名的中东问题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内的研究者更注重探讨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是否兼容的问题。1958年,刘易斯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文章中指出,“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质在于:考虑到西方民主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在争夺穆斯林世界支持上的竞争,在伊斯兰传统和现代伊斯兰社会中,有哪些因素或特征能够使在思想和政治领域活动的各组织采取共产主义政府的方法和原则?又有哪些因素或特征使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接受这些方法和原则?”[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 35.从上述背景再结合罗丹逊的自述来看,[注]Ibid., pp. 2-3.就不难理解他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情境,因为罗丹逊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主要是苏俄模式的“共产主义”。
第二个基础认识是,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总的来看,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分别加以考察,而罗丹逊思想的精髓部分,主要集中在逻辑的或者说潜在的维度。从历史维度看,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社会变革中展开和接触的客观过程,而不是社会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建构。例如,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共产主义与原沙俄统治的穆斯林族群的接触,产生了以苏丹-加里耶夫为代表的“穆斯林共产主义”,这种思潮其实是少数族群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的策略性结合。研究苏俄民族问题的法国学者亚历山大·本尼格森(Alexandre Bennigsen)撰写过多部相关著作,他的基本结论就是,苏联突厥—穆斯林民族中所谓的“穆斯林共产主义者”虽然部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反帝路线,但并非真心接纳共产主义,而是看重布尔什维克政党在秘密组织方式、群众动员策略和争取外部援助等方面的短期利益和经验,他们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者,其事业最终未能成功。[注]Alexandre Bennigsen,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the Coloni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 13-15, 125.本·佛凯斯(Ben Fowkes)等人重点考察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苏联为了切断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生命线”而采取的“东方政策”,即争取穆斯林的支持,同时对泛伊斯兰主义保持强烈警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些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遭遇挫折后采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即一套以独裁政党和国有化为标志、接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苏东剧变后,伊斯兰世界的共产党纷纷从社会主义纲领转向“阿拉伯传统”和伊斯兰主义。同时,左翼阵营和穆斯林面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也出现了进一步走向联合的趋势。[注]Ben Fowkes and Bulent Gökay, eds., Muslims and Communists in Post-Transition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53.罗丹逊虽然也像本尼格森和佛凯斯一样,关注过伊斯兰教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历史的——实际相当于现实策略的或者战略的——联系,并且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系统和全面,[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 45.但他认为,这一历史表象其实是二者更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和内在逻辑(inner logic)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在罗丹逊看来,对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脱离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孤立考察,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立后的时代环境对伊斯兰世界提出了严峻挑战——成为工业社会,或者被工业社会统治;选择工业化,又必然面临两个更加根本的抉择,即选择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注]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p. 215.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意识形态主要是曼海姆狭义上的“意识形态”,用来粉饰真实世界: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享用特权寻求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劝说被压迫阶级满足于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一定的社会流动性。然而,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只适用于很小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获益者,对于包括中间阶级在内的大多数民众而言,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要达到工业社会的生活水平,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因而,资本主义宣扬的“平等”、“自由”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太大吸引力,社会动员能力不强,[注]Ibid., pp. 219-220.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罗丹逊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更多社会和人类发展意义上的“乌托邦”要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在基本的价值预设(essential values)上有一致之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人本主义(humanism)和创造性乐观主义(creative optimism);[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p. 2-3.不过,他反对将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者的价值体系进行肤浅的、机械的比较,如区分三者对待信仰、家庭、财产、经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表面差异。[注]Ibid., p. 34.
罗丹逊进而尝试探讨了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理想及运动可能发生关系的三种模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模式都超越了特定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层面,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学分析推导出的。
第一,冲突模式。这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相遇而产生的最寻常、最自然的反应,因为共产主义通常视一切宗教为一种歪曲的、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压抑了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意识,社会革命主要以阶级为基础进行;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中,宗教被视为阶级社会的残余,易受失势的统治阶级或国外敌对势力的利用。同时,由于视宗教为一种依附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运动也强调要变革旧的社会基础,而不是单纯反对宗教。在现实历史中(例如前苏联),以上两个层面的考虑往往同时并存。反过来,伊斯兰思想家则往往指责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包含“物质主义”或“道德放纵”,指责苏联的共产主义宣传旨在摧毁穆斯林群体的“道德品质”,以便让穆斯林亲近苏联帝国主义。不过,罗丹逊认为,尽管理论上伊斯兰教有不少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思想资源,实际却未得到充分的动员或者收效甚微。[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p. 46-48.
第二,调适模式。在共同战略利益的驱使下(但非必要条件),伊斯兰思想借用了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思想,例如广泛接受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甚至双方都有可能将某些共产主义要素重新阐释为伊斯兰传统内含的理念和符号,从而出现一种罗丹逊所谓的“伊斯兰—共产主义协约”(Islamo-Communist Concordat)。在这种“协约”模式下,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一些宗教权威在发布的宗教教令中,伊斯兰教被看作一种“追求人民幸福,反对垄断,反对高利贷和资本主义”的宗教,并不敌视同左翼运动共享的那些价值;相应地,伊斯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也试图重新发现伊斯兰的伟大传统,驳斥西方右翼甚至左翼对伊斯兰教“宿命论、反进步、静态停滞”的指责,将伊斯兰教呈现为一种“进步的社会运动,尽管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却是民主的、反对富人和压迫者的”。当然,这种“协约”在某些伊斯兰国家也可能呈现为一种试图超越左和右、超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线——类似西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或“民族社会主义”,这一路线被认为是独具穆斯林特色的,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最佳选择。[注]Ibid., pp. 48-50.
第三,和平共存模式。在这种中间形态的模式中,双方地位平等,意识形态冲突退居幕后,和平共存、和平竞争成为主流。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甚至可以组成联盟来实现共同目标,但是不触及双方理念和原则的内在分歧,因而区别于第二种模式。这一模式通常要求双方有某些共同的、哪怕是消极的目标,如反法西斯主义、反抗外国统治和殖民主义等。在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抵抗运动时期和战后的三党联合政府时期,法国共产主义者就倾向于这一路线。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方面,这是一种过渡模式,非常有可能演化为第二种模式,即形成“协约”;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困难,双方意识形态中那些互相难以调适的矛盾一旦公开化,容易使群众无所适从。同时,这种模式也要求共产主义阵营一方维持较为恒常的战略,以便提供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基础,这一条件也是相当难达致的。[注]Maxime Rodinson, Marxism and the Muslim World, pp. 53-55.
归根结底,罗丹逊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利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传播,而亲共产主义的和敌视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思潮都有可能兴起,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 结 语
2008年,塞巴斯蒂安·布苏瓦(Sébastien Boussois)评价说:“今天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准确地重新审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为了避免陷入最为贫乏的文化主义和善恶二元论的泥沼,历史学家的作品尤其不可或缺。我们恰恰需要罗丹逊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各伊斯兰国家发生的一切,以及近几年来自杀式炸弹事件冲击下的西方国家发生的一切。”[注]Sébastien Boussois, Maxime Rodinson, un Intellectuel du XXe Siècle, p. 121.2015年,社会学家哈什(Thorsten Hasche)在《君往何处,政治伊斯兰?体系论视阈下的正义与发展党、“基地”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QuoVadis,PolitischerIslam?AKP,al-QaidaundMuslimbruderschaftinSystemtheoretischerPerspektive)一书中列举了当代重要的伊斯兰研究专家[注]原文为“核心伊斯兰研究者”(zentrale Islam-Forscher)。,只举出了两位法国学者,其中一位就是罗丹逊。[注]Thorsten Hasche, Quo Vadis, Politischer Islam? AKP, al-Qaida und Muslimbruderschaft in Sys ̄tem ̄theo ̄re ̄tis ̄cher Perspektive,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5, p. 26.尽管在西方的伊斯兰研究同行中获得了较高声誉,但即便是在欧美学术圈,罗丹逊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路径探索伊斯兰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迄今仍缺少详尽的专门研究和评价,本文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宗教现象的研究,以其唯物史观的本色,首先是“宗教社会学”式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考察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信仰密切联系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以“有神—无神”、“唯物—唯心”来对待宗教的简单思路。尽管我们并不一定赞同罗丹逊的所有结论,但他的基本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确符合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他的独特贡献更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拓展到伊斯兰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展示了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伊斯兰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历史研究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思想特质。
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传统相比,罗丹逊更喜欢用这样一句源自尼采格言的话来形容当代伊斯兰世界中的伊斯兰传统:尽管世俗化和祛魅一步步侵蚀了人们对传统宗教意识形态的深切信仰,但“真主在此间尚未死亡”(Dieun’yestpasmort)。他紧接着补充说:“虽然对真主的深切信仰已经很大程度上为对伊斯兰的信仰所取代(指事实上而非口头上)”,也就是说,信仰本身更多让位于对信仰的外部形式或穆斯林共同体的认同。[注]Maxime Rodinson, L’Islam: Politique et Croyance, p. 113.暂且不论当代伊斯兰教已多大程度上远离了其原初形态,又如何能够完成对“传统”的复归,罗丹逊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足够清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立后,在全球化时代,对当代伊斯兰世界来说,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宗教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重要的。这一观点直至今天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