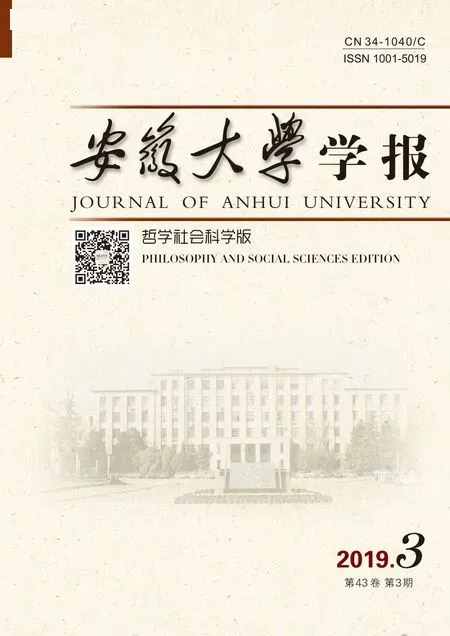网络时代数据隐私的搜查干预
——从滴滴顺风车司机抢劫、强奸、杀人案切入
2019-03-15高磊
高 磊
一、切入案件刑法适用之外的问题意识
2019年2月1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滴滴顺风车司机抢劫、强奸、杀人案”(以下简称顺风车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4日13时28分许,被告人滴滴顺风车司机钟某开车接上乘客被害人赵某。当车行至山路时,钟某采取持刀威胁、胶带捆绑的方式,对赵某实施了抢劫、强奸,后为灭口将其杀害。法院判决,被告人钟某犯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并处死刑[注]余建华、温萱:《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一审宣判》,《人民法院报》2019年2月2日,第4版。。法院的定罪量刑并无争议,而在此之外的更多的案情细节更具研究价值。媒体报道的细节事实如下:
2018年8月24日13时30分,被害人赵某告诉朋友已坐上顺风车。14时09分,赵某在微信群中表示进入无人山区并发来“怕怕”“这个师傅开的山路,一辆车都没有”的信息。14时14分,赵某发出“救命”“抢救”的信息。赵某的朋友多次联系赵某未果之后,于15时42分、16时、16时13分、16时28分、16时30分、16时36分、16时42分七次联系滴滴平台。滴滴平台回复:“一线客服没有权限。”16时左右,赵某的朋友向永嘉上塘派出所报案。其间,警方、赵某的父亲和朋友要求滴滴平台给出司机的具体信息,但被滴滴平台以泄露用户隐私为由拒绝。直至20时,滴滴平台通知赵某的朋友称,已将该名司机的车牌信息提供给警方[注]康佳、薛星星、陈奕凯等:《女孩乘滴滴顺风车遇害,五问滴滴平台安全》,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8/26/c_112332897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09-19。。但是,解救为时已晚。
二、转变隐私观念:从保护视角到风险视角
隐私权具有宪法价值。宪法虽无隐私权之明文但并不影响隐私权的基本权属性。例如,隐私权源自美国法,“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隐私权的保护,其对隐私权的保护是来自于对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引申而来”[注]陈法彰:《数位经济时代下个人资料保护的冲突与欧盟个资保护规则显示的意义》,《月旦法学杂志》2017年第264期。。又如,“隐私权实质内容于德国法制发展上由起初不予承认,到列入‘一般人格权’之内涵予以保护,进而列入个人资料保护专法,最终被承认为基本权利,并被赋予宪法位阶予以保护”[注]吕昭芬:《论医疗资讯电子化与隐私权之保护——以美国为借鉴》,《军法专刊》2018年第2期。。至今,基于人性尊严、个人主体性和人格自由发展的宪治原理[注]参见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中)》,《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隐私保护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然而,重视保护的隐私观容易造成隐私权的过度膨胀。由此,隐私权视角应当由隐私保护向隐私风险转变。
(一)保护视角隐私权的过度膨胀
保护视角的隐私权源于隐私的控制利益。传统的隐私权理论强调隐私保护,保障个人的自主控制[注]参见张陈弘《新兴科技下的资讯隐私保护:“告知后同意原则”的局限性与修正方法之提出》,《台大法学论丛》2018年第1期。。“隐私权保护的强化与现代信息社会具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信息社会使个人成为所谓的‘透明人’,甚至裸体化。”[注]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隐私的保护需求因而愈加突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隐私权保护基准是美国最高法院所构建的“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一是主观要件,该人(已通过其行为)展现了对隐私的实际(主观)期望;二是客观要件,社会承认该隐私期望是合理的[注]See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361 (1967); Smith v. Maryland, 442 U.S. 735, 740 (1979).。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诸多具体判断规则即以控制利益为基本原理。
控制性原理发展出了以告知后同意为核心的隐私保护规则。所谓告知后同意原则,是指在告知隐私权人并经其同意获取其隐私之后,其才不再具备隐私控制的合理期待。后美国最高法院又发展出第三方规则(又称第三方假设及风险承担理论),即宪法“并不禁止政府获取已透露给第三方并由该第三方传达给政府的信息,即使该信息透露给第三方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该信息仅用于有限目的且放置在第三方的秘密不会被出卖”[注]United States v. Miller, 425 U.S. 435, 443 (1976).。换言之,一旦隐私权人自愿地将隐私信息交付至第三人手上,则其就失去对该隐私信息的合理期待。因为该隐私权人能够合理地预测该第三人散布该隐私信息,即该隐私权人无法再合理期待对此隐私信息享有控制利益,其被假定要(或者基于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被要求)承担第三人对外揭露该隐私信息的风险[注]See Smith v. Maryland, 442 U.S. 735, 750 (1979).。此外,“不应以个人所处之空间有无公共性,作为决定其是否应受宪法隐私权保障之绝对标准。即使个人身处公共场域中,仍享有私领域不被使用科技设备非法掌握行踪或活动之合理隐私期待”[注]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7年台上字第3788号刑事判决书。该观点是对隐私保护判断规则“公私领域二分法”的限制。根据公私领域二分法,公共场域不存在隐私。除了第三方规则,公私领域二分法、“自愿公之于世”规则、“过去已结束”规则、马赛克理论等隐私保护规则都体现了隐私的控制利益。。其中的“控制即须保护”思维非常明显。
控制性原理所发展的隐私保护规则虽然有其积极意义,其控制利益的隐私观却具有保护过度膨胀的隐患。在控制性原理之下,隐私权总是在保护视角下被定义和判断,以家长的姿态保障绝对的个人自主性。在顺风车案中,从控制利益的保护视角讲,赵某和钟某因将用户信息归由自己和平台共同掌管,所以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正是这种隐私保护理念支持滴滴平台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向公安机关提供用户信息,只注重保障用户隐私的自主控制,并不关心该隐私在个案中是否受到侵害。其实,如后文所述,规范地来看,被害人赵某不会认为滴滴平台向公安机关披露其用户信息是对其隐私的侵犯,社会也不会认为滴滴平台向公安机关披露行为人钟某的信息是对其隐私的侵犯。因此,从隐私侵犯的风险视角讲,赵某和钟某都可被认为因没有隐私侵犯风险而不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二)风险视角隐私权的规范判断
风险视角的隐私权源于隐私的亲密利益。隐私除了具有控制性利益,还具有亲密性利益。所谓亲密性,是指个人通过隐私揭露的选择来调整亲密关系的能力。亲密性原理认为,隐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护个人的自主性,而且在于个人对亲密关系的塑造。个人可以通过降低隐私的流出,而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亦可释放隐私(更多揭露自己),经营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与秘密性着重于个人本身不同,亲密性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秘密性的重点在于个人自主性的保护,而保护的效果可能产生阻绝他人进入自己世界的结果;亲密性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经营,保护的效果可能产生他人(自己)愿意进入自己(他人)世界的结果[注]参见张陈弘《新兴科技下的资讯隐私保护:“告知后同意原则”的局限性与修正方法之提出》,《台大法学论丛》2018年第1期。。可见,与“向内”的强调控制的秘密性相反,亲密性具有“向外”趋向。
隐私因亲密利益的外向性而具有社会性。根据亲密性原理,“隐私权所保护的不仅是个人对所处社会体的‘自我’回应态度,其最终所保护的应是包覆‘自我’的‘社会有机体’对于该自我的回应态度。自我的隐私期待,必须是社会所接受的合理期待,而非纯粹的‘自我’隐私保护”[注]张陈弘:《隐私之合理期待标准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的操作——我的期待?你的合理?谁的隐私?》,《法令月刊》2018年第2期。。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客观要件,即来自隐私的社会性特征。进而,隐私的风险视角从保护视角的反面认为,由于隐私的亲密利益,个人在输出隐私或者接收隐私的过程中,具有对该个人造成情感或者其他伤害的潜在可能性。隐私风险理念将个人隐私置于社会背景之下。“隐私作为一种权利,个人得用以主张其所身处的社会能给予符合对个人隐私流通的期待”。“从隐私伤害或隐私风险角度出发的隐私概念,其优点在于帮助隐私与个人所处社会脉络间的互动调和。亦即,在个案中虽有个人的抽象隐私利益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对该个人必然产生社会所不可容忍的客观隐私伤害;隐私伤害的存在与否,取决于隐私权利所处社会脉络下的认知”[注]张陈弘:《新兴科技下的资讯隐私保护:“告知后同意原则”的局限性与修正方法之提出》,《台大法学论丛》2018年第1期。。总之,根据风险视角的隐私观,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适用需要规范地判断有无隐私风险。
隐私风险理念在顺风车案中可发挥巨大作用。从前述隐私权的保护视角出发,隐私保护是“一刀切”式的绝对保护,这种家长主义保护不分情境场合,但实则有时公民并不需要这种保护,或者不值得拥有这种保护。而从隐私权的风险视角出发,隐私保护应是规范判断的、情境化的保护,是根据国民和社会需要的有限保护。具体到顺风车案中,行为人钟某不值得拥有隐私保护,而被害人赵某则不需要这种隐私保护。由此可见,网络时代隐私体量的增加不但不意味着要继续甚至强化传统的隐私保护,反而要减少不必要的保护。
三、重构搜查法理:从财产基准到隐私基准
基于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如上所述,隐私保护与搜查行为具有密切关系:在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搜查并进而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宪法原则时,总是伴随着相对人是否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判断。最初,根据“在场”“有体”的形式说,搜查与隐私并无亲和关联。但是,随着形式说向实质说的转变,尤其是以财产权为中心的实质说向以隐私权为中心的实质说发展,搜查[注]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论搜查皆以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宪法原则为前提。就成了必要的隐私侵害。换言之,隐私保护的法律限度(亦即隐私干预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搜查,国家唯搜查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与形式说相比,实质说能够认定顺风车案中公安机关向滴滴平台调取用户信息的行为性质为搜查,从而消除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的制度鸿沟,因而值得肯定。
用微量移液管控制分取体积小于0.5mL,准确分取1.2中0、0.10、0.50、1.00、2.00、5.00、10.00ng铼标准工作液于盛有1g氧化镁的坩埚中,90℃烘干,研为粉状,再加1g氧化镁,搅拌均匀,覆盖0.5g氧化镁,以下操作同1.4样品的处理,以铼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质谱信号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a,用于测定铼质量分数低于10ng/g的样品。
(一)“在场”“有体”的形式说
反对顺风车案中的公安机关向滴滴平台调取用户信息的行为系搜查的观点,主要理由是搜查行为之构成在于“在场”和“有体”二者。具言之,构成搜查行为,一方面,搜查者和被搜查者及其他相关人员出现在搜查现场;另一方面,搜查之物为有体物,搜寻查找无体物者,不构成搜查。然而,该“在场”“有体”的形式说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
有关“在场”理由源于物理空间的搜查事实与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首先,在物理空间,搜查须搜查者出现在搜查现场。其次,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通常规定被搜查者或其他有关人员在场原则。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第1款规定:“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执行搜查,容易产生争端,会同他人在场见证,并令其于搜查笔录签名,一来可以减少违法搜查情事,二来可以增加以后争执时的证明管道[注]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总论编)》(第六版),台北:作者自版,2010年,第417页。。据此,有学者认为,数据信息得以远程传输之方式取得,搜查者、被搜查者等相关人员不在场,故而其非搜查[注]参见王士帆《侦查机关木马程式:秘密线上搜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BGHSt 51, 211译介》,《司法周刊》2015年12月25日,第1779期。。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构成要件是具有实质内涵的规范评价的类型化形态”[注]刘艳红:《实质的犯罪论体系之提倡》,《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但“在场”并非搜查行为构成的本质特征,仅是为了从程序上防止违法搜查不当侵害被搜查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根据现行法律之规定,“在场”原则也有例外。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存有例外之特征,不宜作为概念的核心内涵。
关于“有体”的理由源于物理空间的搜查对象与宪法法律的明文规定。例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民的身体、住所、文件、财物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注]See U.S. Const. amend. IV.。据此,有学者认为,搜查的法律意义,“乃为发现特定人、‘物’,对于一定场所、物件或人的身体所为之强制处分,或强制取得‘物’的占有。由此法律解释似可理解,原本刑事诉讼法有关证物保全的机制设计,乃转移、占有、处分过程中,以物理上管理可能‘有体物’为前提”[注]参见林裕顺《电磁记录之证据保全——检讨日本代表性判例的启示》,《法令月刊》2007年第10期。。然而,如此解释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对立是一种方法论和法律观的对立[注]参见刘艳红《形式与实质解释论的来源、功能与意义》,《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与实质方法相比,形式方法无法有效应对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而产生的新事物,正如这里的信息网络时代所产生的隐私数据。根据实质解释论,认定政府机关的行为是否构成搜查,首先需要探究搜查行为的保护法益(规范目的)[注]参见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02~105页。。毫无疑问,当政府机关“扣押”公民财产时,所侵犯者为公民的“财产权”。但是,当政府机关“搜查”公民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时,所侵犯者为何,不无争议。
(二)以隐私权为中心的实质说
美国最高法院最初的论证逻辑体现了以财产权为基准认定搜查行为的构成。在1886年的Boyd v. United Stat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Miller法官在协同意见书中认为,宪法并非禁止所有的搜查和扣押,制宪者所关注的是搜查和扣押不能被滥用,因而只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特别描述了搜查的场所(place)和扣押的人(person)或物(thing),那种授权搜查任何场所、扣押任何东西的普遍令状(general warrant)是不合理的,因而应被禁止;根据写明搜查事物的令状而进行的搜查是允许的[注]See Boyd v. United States, 116 U.S. 616, 640-41 (1886).。当时,禁止普遍令状的原因是,根据普遍令状而为的搜查严重侵犯公民财产。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法益是“物”或“场所”,以“财产权”或“物理侵入”为中心的搜查法理得以构建:以是否物理侵入宪法所保护的区域(身体、住所、文件、财物)、有无财产权的侵害作为是否构成搜查的标准[注]参见王兆鹏《重新定义高科技时代下的搜索》,《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93期;李荣耕《科技定位监控与犯罪侦查:兼论美国近年GPS追踪法制及实务之发展》,《台大法学论丛》2015年第3期;刘静怡《政府长期追踪与隐私保障》,《月旦法学教室》2012年第116期。。根据搜查的财产权基准,顺风车案的公安机关向滴滴平台索要用户信息,既无物理侵入,亦无财产损害,显然不能成立搜查。然而,如此一来,公安机关便失去了从滴滴平台取得用户信息的制度渠道。
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Katz v. United States案中将搜查的财产权基准推向隐私权基准[注]需要注意的是,隐私权基准并没有完全取代财产权基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尽管法院不时以“宪法保护地域”(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areas)[注]宪法保护地域理论和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搜查法理相契合,即强调搜查的物理场所入侵性。这一术语作为其结论,但这一概念并不是解决所有第四修正案问题的灵丹妙药。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仅仅是“地”不受不合理的搜查、扣押,其范围不能取决于是否存在特定圈占之地的物理入侵。例如,政府电子收听并记录个人在公用电话亭内打电话所说的内容,因侵犯了个人在使用电话亭时所仰赖的隐私而构成第四修正案所规定的“搜查和扣押”,而用来收听的电子设备没有穿透电话亭的墙壁这一点并无宪法意义[注]See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351, 353 (1967).。据此,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核心不是“财产权”而是“隐私权”,从而形成以“隐私权”或“隐私期待”为中心的搜查法理:只要公民欲保有其隐私,就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障,即使政府没有物理上的侵入行为,一旦侵犯个人的隐私期待,也构成搜查。
根据搜查的隐私权基准,一方面,搜查制度构成隐私保护的法律限度;另一方面,顺风车案中的公安机关调取司机信息就应当评价为搜查行为。其理论优势在于,为顺风车案中的公安机关获取用户信息提供了制度渠道:搜查作为一种强制处分,滴滴平台必须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用户信息。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新增电子数据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就已为隐私权基准的搜查埋下伏笔。根据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3条和第7条的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即电子数据取证,具体包括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现场提取电子数据、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冻结电子数据和调取电子数据等五种收集、提取措施或方法。虽然该证据规则未在电子数据的场合直接使用搜查的法律术语,但实质上已承认了数据搜查的事实,其具体规则也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搜查程序没有本质区别。
四、搜查适用:以隐私的紧急干预为例
根据以隐私权为中心的搜查法理,顺风车案中的公安机关向滴滴平台调取用户信息的行为可定性为搜查。然而,根据我国现有的刑事侦查司法实践,在顺风车案的现行犯的紧急场合,公安机关尚无法对滴滴平台实施紧急搜查。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搜查的立法规定过于具体化、程序化、形式化。当然,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该立法缺陷尚有以解释方法克服之可能。
(一)程序立法的形式性应兼顾实体法的抽象性与实质性
在顺风车案中,从被害人赵某通过微信与朋友的反复联系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紧急。在紧急情况中,一般的搜查因批准等程序耗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而要适用特殊的紧急搜查。然而,通说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紧急搜查仅适用于遇有紧急情况的逮捕、拘留场合[注]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据此,顺风车案因不“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而无法适用紧急搜查。鉴于信息网络能够使公安机关得知非当面的远距离紧急情况[注]如新闻媒体报道的“朋友圈炫耀非法捕捞被抓”“男子肇事逃逸后还发朋友圈炫耀被抓”“女子朋友圈炫耀卖枪被抓”等就能够说明网络时代搜查法制中紧急情况的特点变化。,网络时代的这一特点倒逼我国搜查法制的立法与司法反思。
一方面,我国搜查程序的宪法规定较具体,缺乏抽象性。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该条直接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干预主体和干预事由,而程序由法律保留。然而,这样的具体规定并不一定能充分发挥隐私权保障作用。例如,在《监察法》实施背景下,纪委监察机关仍实施了隐私通讯调查措施[注]参见刘艳红《〈监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9年第1期;蒋菁《微信回应“纪委提取被删除聊天记录”:从用户手机端通过恢复文件提取》,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80429/444544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09-20。。较为理想的状况是,该条的权利干预主体、权利干预事由同程序一起由法律保留,改为规定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权利限制原则。例如,只有出现增进公共利益、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防止妨碍他人自由等事由,宪法才可基于比例原则以法律保留的方法限制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我国搜查程序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较形式,缺乏实质性。受传统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分范式的影响,一般认为,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尽可能作出程序性、形式性规定,而实体性、实质性规定属于实体法的立法任务。该思维定式在尽可能追求程序法的明确性原则的同时,也极大压缩了司法的自由裁量权,顺风车案即为适例。与《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作为实体法的《刑法》反而并不排斥程序性规定,如“告诉才处理”即为犯罪成立的程序性要件。此外,域外搜查法制除了程序性规定,也多有“必要”“相当理由”等实体性、实质性规定[注]参见张斌《我国无证搜查制度法理之构建——〈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二款质疑》,《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我国部门程序法立法应摒弃程序法中不能有实质要件规定的观念,以加强司法的规范判断和价值评价功能。
总之,顺风车案问题的最终解决须建立能够适用的紧急搜查制度。搜查原则上需要搜查证,“但警察维护治安、侦查犯罪,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常常需要马上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此种情况与法官于审判时能仔细地翻阅参考书籍、衡量已发生事实的轻重缓急而从容地作出事后判断有本质的不同,若情况急迫或有其他特殊情形,仍要求执法人员”申请搜查证始得搜查,“乃极不合理”[注]参见吴巡龙《新法下紧急搜索之心证门槛、要件及违法搜索之证据排除》,《法学丛刊》2003年第1期。。所以,搜查法制体系有必要具备以“紧急情况”为实质要件的紧急搜查的例外。
(二)形式立法的实质解释:现行犯场合紧急搜查的适用
即使我国搜查法制具有上述立法缺陷,仍可通过解释论的路径予以弥补。“法律规则的优化和调整,归根究底是为了塑造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可靠法律规范,法律解释、补正、修订等无疑都以完善法律规则为目标,探寻法律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不仅是立法者的任务,也是解释者的工作”[注]刘艳红:《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正是在法律领域,通过新的解释,使得概念适应需求的变化”[注]储陈城:《人工智能时代刑法归责的走向》,《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通过将《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2款所规定的“情急情况”实质化,即由通说所认为的程序性情形解释为紧急搜查的实质要件,就可解决问题。
顺风车案的紧急情况具体属于现行犯的场合,行为人钟某系属现行犯。紧急情况下不需要搜查证的实质理由有三:“第一,为防止罪犯或嫌疑犯之逃脱;第二,为防止证据之湮灭;第三,为保护警察、他人或公众之安全。”[注]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台北:作者自版,2007年,第226~227页。而所谓现行犯,正是指正在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刚刚实施过犯罪行为的人;现行犯规定的立法目的正是防止逃亡或湮灭罪证和维护公共秩序[注]参见王兆鹏《论拘提或逮捕相关问题》,《日新》2004年第3期。。现行犯分为以下类型:(1)正在追赶呼喊行为人的场合;(2)正在持有赃物或者其他明显意图用于犯罪的凶器等物品的场合;(3)身体或者被服有明显犯罪证迹的场合;(4)“受到盘问而试图脱逃的场合”。该场合因可“明显被认为是实施了犯罪的情形”而视为现行犯,这种类型一般被称为“准现行犯”[注]三井誠、酒巻匡:《入門刑事手続法》,東京:有斐閣,2017年,第10、34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的通讯功能使得现行犯不一定仅是指面对面看到的罪行。
国外如现行犯之紧急情况的搜查实例有很多。例如,2009年8月22日,David Riley因驾驶标签过期的汽车而被加利福尼亚警察依法扣留,随后被搜查出两个隐藏的枪支。在进一步搜查中,David Riley被逮捕并查收其一部手机[注]See Callie Pippin Raitinger, Warrantless Search of the Digital Data on Cell Phones, Journal of the Missouri Bar, vol. 71, 2015, pp. 39-40.。该案的紧急搜查始于汽车标签过期,行政临检模式与刑事搜查模式能够顺畅切换,由此可见其紧急搜查要件之灵活与宽松。相比之下,如上所述,我国紧急搜查较为机械而苛刻。由此,我国紧急搜查刑事司法应当确立通过实质解释实现扩大解释的基本导向。在顺风车案中,公安机关应当以现行犯之紧急情况对滴滴平台实行强制紧急搜查,以获取用户信息。依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2款的通常理解,紧急搜查须在执行逮捕、拘留时遇有紧急情况,自然于本案中无法得出公安机关可以紧急搜查之结论。然而,该传统见解未免狭隘,极大限缩了紧急搜查的适用范围,而无法充分实现紧急搜查的立法目的。该条之“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与“遇有紧急情况”中间以逗号之标点符号相隔,二者能够被解释为并列关系,而非修饰关系。换言之,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得紧急搜查;在遇有紧急情况之时,亦得紧急搜查。该条规定了“执行逮捕、拘留”和“遇有紧急情况”得无证搜查的两种情形[注]第二条可能的解释路径是,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在现行犯的场合,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进而能够适用紧急搜查。但是,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5条的规定,由于由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该解释路径的实践效率较低。如果《刑事诉讼法》第82条所规定的“先行拘留”能够解释为可以无证拘留,亦即公安部2012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21条的规定,虽可避免效率之低下,但有混淆制度性质之虞。由于搜查的侦查措施与逮捕、拘留的强制措施二者的性质和根据不同,还是以各自拥有属于自身性质的紧急情况为妥,即使二者适用的紧急情况存在重合之处。。如此一来,公安机关就能够对顺风车案施以紧急搜查;而且,司法机关也就能够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司法实践不断丰富“紧急情况”的具体情形,从而使形式的紧急搜查规定实质化。
五、结 语
科技与法律以社会为媒介相互形塑。科技变革通过影响社会交往而为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课题,法律制度通过回应社会问题而为科技变革划定理性界限,因而法律立场的理性选择极为重要[注]参见储陈城《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和功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根据相对性原则,权利既有需要积极保护的一面,也有需要消极限制的一面。网络时代在强调隐私保护的同时,也应警惕其过度膨胀。隐私风险理念从隐私保护理念的背面理解隐私价值,有利于促成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有限的隐私保护。隐私权作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只有搜查制度才能构成隐私保护的法律限度。搜查作为一项强制处分,在受到程序规制的同时,也应具备实体要件。以“紧急情况”为实质标准的紧急搜索为顺风车案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方法论上,虽然我国程序立法具有形式性缺陷,但仍可寻求解释论路径对相关条款进行目的解释和价值填充,以增强机械程序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