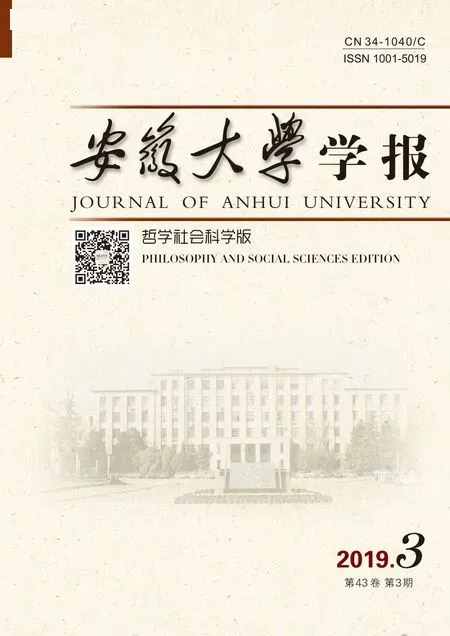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
——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2019-03-15李哲罕
李哲罕
自然权利学说在古希腊时代关于“自然”与“约定”的争论中有其传统的理论来源,中世纪的经院法对此也有大量涉及,其基本观点经过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出发点。正如古希腊时代无法平息“自然”与“约定”的争论一样,在一种后基督教上帝的世界观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中所假设的自然状态也并非完全从先天的基础上推演而来,而是基于经验的。由于经验本身是杂多和流变的,所以基于经验之上的理论必然会产生各种分歧,这也正是康德的法和权利哲学为追求普遍必然性而竭力避免的。康德为追求普遍必然性在纯粹去经验的进路上将自然权利学说推演到了极致。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则对经验主义和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行了一个双重批判。他们不仅揭示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所寻求的普遍有效性与其经验品格所具有的特殊性之间的内生性矛盾,还洞察到,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乃至康德的法和权利哲学所诉诸的乃是一种被形而上学化的人类个体和人类理性,由此它们就失去了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真实状况的能力。他们二人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经过从康德到马克思的批判,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最终走向了解体。
正如在早期现代语境中的讨论一般,目下国内许多囿于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理论内部的讨论因为接受了其理论前提,所以无从认识到这些前提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从康德到马克思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并非是一个十分新颖的主题,但这确实是一个现下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理论盲区”。我们非常有必要将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在此论域中批判性发展的脉络进行进一步的厘清和重申,指出这一学说在论证方式上存在的瑕疵,并进而实现对它的拒斥。
一、康德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与发展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以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荷兰的格劳修斯以及德意志的普芬道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虽然这些思想家的理论有所分殊,但是它们共享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理论—逻辑结构:首先构建出一个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状态正如后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一样是一种理论假设),继而在此自然状态中的人通过社会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从而进入社会状态。正是由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中社会契约的存在,他们的理论主张也被称为“社会契约论”。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中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类历史上——历史学、考古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真实和普遍存在过的事实,而只是从那些理论家们所处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反推出来的一种理论假定状态。他们希冀从这种状态反诸实际社会生活,通过这番操作以求得指导社会的规范性意涵。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社会契约论“通过宣称自然状态相比社会状态是显著地存在缺陷的,从而证成了国家权威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注]Robin Celikates, Stefan Gosepath, Grundkurs Philosophie Band 6: Politische Philosophie, Stuttgart: Reclam, 2013, S. 40. 引文中的“Staatszustand”字面意思是“国家状态”,但为了上下文的统一而使用了“社会状态”的译法。。早期现代自然权利论者为了追求作为规范性理论所要求的充分普遍必然性,以及以此为基础推演出普遍必然的伦理生活和法与国家制度,他们就必须要将自然权利学说“削薄”,即尽量地除去经验性的内容,以达至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作为理论起点的“阿基米德点”。这在方法论上类似于笛卡尔从“普遍怀疑”达致“我思故我在”。因此,自然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人类进入社会之前的状态,而这就要求他们对哪些事物是属于人类进入社会之前的,哪些是之后的有一个评判标准。这个理论在此毫无疑问是留有后门的,正如李猛所指出的:“在霍布斯这里,自然状态中的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我们眼前的人’没什么不同,这并非因为霍布斯将二者混淆在一起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状态中人的生活凭借的正是‘我们眼前的人’的‘经验’。”[注]李猛:《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霍布斯的两个证明与对人性的重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正是这些理论家从自身所在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出发对人性所做的某种预设导致了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经验性的,并且也是任意的。由此出发,也就可以解释他们产生理论分殊的原因了,因为经验本身是杂多和流变的,所以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理论也就呈现出了多样性。当然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并非自然状态本身是显著地存在缺陷的,而是因为事实上的社会状态是显著地存在缺陷的,所以从其反推出来的自然状态才必然是显著地存在缺陷的。
康德的纯粹形式性的自然权利学说可以被认为是对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否定。不同于前人从一种理论拟制的自然状态出发,康德在自身的实践哲学中使用了在理论哲学中用到的方法,即从先天的形式中演绎出后续的原则,将一种人的理性规定的纯形式施加于经验之上。在康德看来,这样也就可以克服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经验品格,从而保障理论与实践都可以立足于一种普遍必然性之上。这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的:“道德形而上学不能像关于人的经验科学那样,建立在人类学之上,但却可以应用到人类学中去。”[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7页。换言之,破除早期现代自然权利观念的第一个转变点出现在康德那里,这也像海因里希·罗门指出的:在康德之后,“作为自然法的起点和首要原则的、纯粹形式化性质的自由,使得实质性自然法,即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自然法成为不可能了”[注]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3页。。
不过康德形式主义的自然权利观念在论证路径上其实也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康德以建构人类个体之间理性同一性的方式化解了个体之间的冲突。卢梭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这个基本分类深刻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在卢梭这个分类之下,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然人就是进入社会之前的人,社会人是进入社会之后和其他人共存的人。在自然人的领域内,作为个体的人追求理性(或者在某些理论家看来是情感、意志或欲望等)支配下的行为;而在社会领域内,作为个体的人必须自我约束以与他人在社会中共在。但是康德哲学以建构人类个体之间理性同一性的方式调和了作为复数的理性存在者,换言之,他者之维在康德哲学中是虚置的(或者说是实质上缺失的)。同时,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我和他者的情感、意志或欲望等感性维度被遮蔽了。当然,康德并不否认在实然状态下人类可能会产生种种冲突,只是他在其理论内部试图通过应然的规范去解决这些冲突。
其次,康德取消了早期自然权利学说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正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中所说的:“自然权利体系最高一级的分类,不应该(但经常如此)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和‘社会的权利’,而应该划分为自然的权利和文明的权利。第一种权利构成私人的权利;第二种为公共权利。”[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51页。此书中译本译者在上述引文这一页所加的脚注中非常妥帖地标明了,这两种权利也正是“私法的权利”和“公法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私法的权利”和“公法的权利”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也被康德取消了。在康德的法和权利哲学中,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最大差别是私人性领域的逻辑扩展适用范围到公共性领域。依照康德的观点,由于人类个体理性具有同一性的原因,上述这个差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康德是从私法权利与调整私法权利的角度来切入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建立在私法之上的,也即基于所谓社会和国家的同一性、道德和法与国家背后逻辑的同一性。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自然的或无法律的社会状态,可以看作是个人权利(私法)的状态,而文明的社会状态可以特别地看作是公共权利(公法)的状态。在第二种状态中,人们彼此相互间的义务,并不多于和异于前一种状态下可能设想到的同样性质的义务,个人权利的内容在这两种状态中其实是相同的。”[注]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33~134页。正因为康德认为自然权利是通过先天原则引申出来并且在社会状态中也同样有效,所以他据此也将自然权利称作是天赋权利。
最后,康德法和权利理论中关于自由和平等问题基本演绎的出发点其实是历史性的,而非是先天的,他只是将这种历史性的内容形而上学化了。康德认为,在从占有向所有权过渡的阶段,才会产生与他人的权利关系以及公共权利(力)的介入。不过这里的问题是与他人的权利关系以及公共权利(力)的产生事实上要先于所有权的产生。正如桑希尔所指出的:对康德来说,“在法治标志着从第一自然转向第二自然时,它同时也标志着在自然状态下通过对抗与暴力抢夺的财产转变成了一种普遍合法的、稳定的所有权体系”[注]克里斯·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陈江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个人本位以及以所有权为代表的权利体系等并不是人类在早期社会就充分具备的,而是在人类进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生活后才逐步产生出来,再被进一步理论化和抽象化为一种“天赋”。康德法和权利理论实现的背后隐而不显的预设其实正是人类已进入到市民社会这一阶段(虽然“市民社会”这个术语在当时还未产生),只有在这一阶段才能使得他的观点在理论上获得想象的空间和在实践上获得建制性的权利保障。这正如韦尔默所指出的:“按照一种潜在地包含在绝对命令中的预期共识来行动的原则最终被证明同时就是一种处理主体间关系的规范原则。康德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表达了这一观念;但他并未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可能的目的王国的成员行动的能力与这种目的王国的局部实现有关,而且,只有当这种目的王国成为现实时,获得这种意义上的实践知识的独白式的建构才是普遍可能的。”[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作为康德后继者的费希特在他中后期的《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式的法和权利学说,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费希特是尝试将康德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哲学人类学的互主体性之上[注]参见李哲罕《早期德国法治国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主要对象的考察》,《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费希特认为法权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相互关系中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在自己用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限制自己的自由的条件下,用那个关于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概念,来限制自己的自由;这种关系叫作法权关系,这里提出的公式是法权定理。”[注]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文集》第二卷,谢地坤、程志民译,梁志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8~309页。费希特认为,法权经历了“原始法权”“强制法权”以及“国家法或一种共同体的法权”三个阶段,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就是实定法权或国家法,认为唯一真实的自然状态就是国家状态”[注]张东辉:《费希特的法权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9页。。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费希特的理论相较康德而言,更具人类学而非形而上学的成分。费希特的理论其实颠倒了原先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进入社会状态这个论证,这让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认识到自然权利学说中的弊端。
二、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
一般而言,黑格尔与他之前的康德和费希特分享了共同的论域和立场。只是黑格尔基于不同的理论方法,得出了形态上相较康德和费希特而言具有明显差别的理论。很明显,黑格尔并不满足于康德式的只有形式普遍性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是要寻求一种具有历史现实性的“具体普遍性”的法和国家学说。
在早年的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中,黑格尔就已经展开了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在他看来,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两条进路的自然权利学说都是成问题的。黑格尔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承接的是自康德以来的传统,同时也有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理论对手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进行论战的现实原因。他在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中指出:“经验主义首先在下述问题上缺乏标准,即,在偶然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何在,因而,在自然状况的混乱中或在人的抽象中,什么东西必须持续,什么东西必须被丢弃。在这里,引导性的规定只能是为了叙述在现实中被找到的东西而同样地需要保存下来;那种先天的东西的方向性的原则是后天的东西。”这就指明了经验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任意性之上,它是缺乏充分规定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充分普遍的必然性。而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他指出:“形式主义能够把它的一贯性扩展到如此的地步,就像它的原则的空洞性一般地所允许的那样……形式主义为此也有权利自豪地把完整性所缺乏的东西在经验的东西的绰号下从它的先验性和科学中排除出去,因为形式主义把它的形式的原则宣称为先验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因而把它通过这些原则不能掌握的东西宣称为非绝对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注]黑格尔:《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程志民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黑格尔在这里指出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并不能理解和处理具有历史现实性的事物,其只能通过将这些事物排除出自己的视域来解决这个问题。
出于对历史现实性的关注,黑格尔——包括之后的马克思洞察到了自然权利学说与市民社会的密切关联。黑格尔认为,所谓作为市民社会的属性的个人权利体系与社会契约,是历史发展出来的(绝对精神的现实化的)中间环节,而非先天必然的逻辑起点。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康德和他所批判的早期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者殊途同归。正如韦尔默所指出的:“通过把国家的契约论拒斥为自然权利理论的不正当的应用,并断定那些原则的唯一正当的应用领域是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个人之间的私人商业领域,黑格尔从一开始就为这种应用领域施加了独特的限制。”[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26页。换言之,黑格尔指出,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者而言,经过抽象化之后的市民社会正是他们理论的出发点,而这个市民社会其实只是一个特殊领域,它并不足以成为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的一个基础。黑格尔非常具有现实感地指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97页。这也正是韦尔默所指出的:“抽象权利的领域,即自主地在彼此之间形成契约的私人个体的社会,首先只能通过已经得到制度调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把自身确立起来,可以说,它自己就是从这种共同体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正如黑格尔认识到的,现代自然权利的‘自然条件’事实上就是从封建制度和绝对君主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条件。”[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28页。正是基于黑格尔这种加入历史性与现实性维度的观照,我们才可以充分和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家其实是从自身所处的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立理论,他们所谓的自然状态只是对进入市民社会之前的人类状态的理想化,社会契约只是对作为资产阶级与专制统治者斗争产物的宪法性文件的理想化,而社会状态则是对市民社会的理想化。简言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究其实质只是对市民社会的抽象化、形而上学化和意识形态化。
不同于康德,在黑格尔的视角之下,基于私法规范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者属于依照截然不同的逻辑运行的两个有质的差别的领域。正如韦尔默所指出的:“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把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与公民的政治自由分离开来的人,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变得有效的自然权利形态的典型特征就是试图把政治自由和平等与民法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联系在一起。”[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51页。黑格尔否定了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以及康德的法和国家理论中基于私法权利和契约等市民社会的规范去构建国家的观点,而且认为国家作为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存在,其可以统摄市民社会,并防止因作为私法主体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所导致的共同体解体。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末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3~254页。黑格尔在之前还论述道:“国家决非建立在契约之上,因为契约是以任性为前提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83页。。依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高于社会,公民高于市民。换言之,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领域需要作为辩证法中的一个环节被否定并继而成为更高环节的一部分。按照韦尔默的分析:对黑格尔而言,“享有国家对其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权利的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的市民乃是现代国家的产物,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市民并不等于现代国家,如果现代国家在其制度结构上并不总是已经超越个人的私人利益的眼界,那么它就不过是自然状态的翻版”[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29页。。
三、马克思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拒斥
黑格尔的法和国家哲学中就人类的自由与权利展现出意识与事实两个层面,其并不仅仅是(事实性的)反思,也并不仅仅是(规范性的)谋划,而是两者的合一,因而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初现萌芽的“事实的规范性”。黑格尔以及之后的马克思据此才能够将自身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巩固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早期受到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和卢格)的影响,认识到人并非是作为“个体”(individual),而是作为“类存在”(species being)而存在的。恩格斯将费尔巴哈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里对应“终结”的德文词汇是“Ausgang”,这个词也有“出口”“出路”的意思。恩格斯在同一本书里也指出:“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依照俞吾金的研究,黑格尔才是真正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前期的费尔巴哈尚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内,而成熟时期的费尔巴哈则已经走出这个范围并成为“出路”[注]参见俞吾金《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思考》,《江淮论坛》2009年第6期。。与之相应,从一种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前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渐变线上。马克思后来则进一步完成了对“类本质”的批判,正如他在与恩格斯合作的《费尔巴哈》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换言之,马克思认识到,不是通过关于人(不论是单数形式的,还是复数形式的)的抽象观念,而是通过现实中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人(复数形式的)的实践活动才可以具有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真实状况的能力。这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所指出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3页。如此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之后的工作中为何会摆脱德国古典哲学概念框架的束缚,为何会有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以及为何还会去研究早期人类学问题。站在后来人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被彻底地“终结”和找到“出路”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现实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实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超出直接事实的建构性的理论概念。”[注]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研究是区别于实证性研究而带有规范性的内涵的,这种规范性就是“事实的规范性”,即从事实中探求规范性内涵,而并非单纯在实证主义理论中进行事实性的反映,或者在规范主义理论中进行纯粹概念的空转,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了之前一些理论家将某些经验事实形而上学化以作为规范性来源的做法。在黑格尔的法和国家理论中其实已经有这个“事实的规范性”的萌芽,不过正如霍克所指出的:“黑格尔试图证明已经发生的事物是应该已经发生的事物。”[注]Sidney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50.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一区别使得黑格尔的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而马克思的哲学则是高卢雄鸡的报晓。
马克思在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过一个批判,其在结构上非常类似于黑格尔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不过针对现实层面而非观念层面的批判使得马克思的批判相较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更为有的放矢和更为彻底。马克思和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着眼点并不一样,即马克思试图更进一步地从市民社会内部而非从作为外部的国家中挖掘变革的潜力,也因此他认识到之前理论中的问题所在:“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学说虽然以人类的名义主张自由和平等,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无产阶级不利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更为准确地说,这种虚假意识只是对既存的实质上不平等的剥削关系与事实的反映而已。这也如韦尔默所指出的:“正如马克思对等价交换的‘深层结构’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联系既是真实的,又是一种幻觉。因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联系决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理解自己的方式;作为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必然幻觉’,它代表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当性的天然基础。”[注]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44~45页。引文中的“合法性”改为了“正当性”。与黑格尔设定了一个中立的和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以作为解决方案不同,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及两者间同构性的关系,而且还认识到只有对市民社会本身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进行彻底变革才有可能有效地消解自然人与公民之间的差别,继而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这种理论建构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有现实危害性的。可以说,马克思更为充分和彻底地揭露了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本质,并且最终指明了在自然权利之外构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哲学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此也就实现了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彻底的拒斥。
四、结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
作为一种理论设计的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突破宗教与世俗专制的革命性进步意义,但是在市民社会成为现实之后,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进一步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束缚。因为,这一学说以及其所基于的个人、自由、权利或平等等观念的提出和发展实则是以市民社会为背景的,因此也是具有特殊性的。自然只是预示着各种可能性,其本身是缺乏充分规定性的,因此我们并不能从它之中得到规范性的“自然权利”。在引入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维度之后,也即在多元文化和权利的历史发展的双重视角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所尝试追求和锚定的非经验的普遍性,因为具有经验品格,或者是其将经验形而上学化,故而遭受到了质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本位以及以所有权为代表的权利体系等并不具有一个先在的内容或形式来保障它们的诞生,其是从具体的人类历史生活中生成、变化和拓展出来的。对原始人类而言,或者在农奴制尚未被取消的情况下,个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这些“天赋权利”并不实际存在,以生命权和财产权等为基础的关乎个人存续和发展的权利体系其实是市民社会自身要求的理论化与抽象化,当然还有更进一步地对它的形而上学化和意识形态化。
若在上文所述的一种更为彻底的关于历史生成的权利学说面前,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就表现出了自身的保守性与消极性。我们只有从以“事实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非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才可以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的真实状况。在从康德到马克思的批判中,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充分暴露出了自身论证方式上的问题。并且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认识到在早期现代自然权利之外构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哲学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此就实现了对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彻底的拒斥。换言之,因为一种更具有解释力和实践性的理论的出现,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
在面对目下兴起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自然权利学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从康德到马克思对该问题的批判。此外,我们在实践中考察人权和社会经济文化等权利的时候,也必须要警惕和拒斥那种将形而上学化的观点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