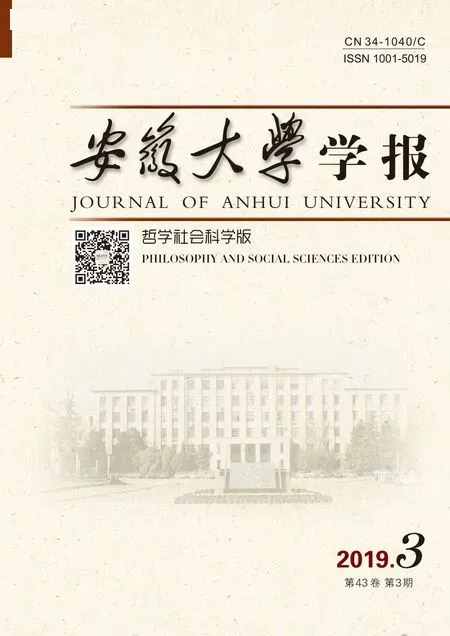身体意识与时空观念性
——早期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
2019-03-15陈永庆
陈永庆,王 恒
引 言
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性原理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核心论题,在《遗著》中康德称其为“先验哲学的钥匙”[注]Kant,Opus postumum,ed. by E. Förster, trans. by E. Förster, M. Ro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5.。王咏诗指出:“康德整个批判哲学正是基于两个核心词的关系而展开,即时空和自由。从论证策略来看,时空的观念性被他处理为自由实在性的必要条件。要想理解康德对启蒙时期人类自由本性的独特贡献,就必须先了解他对时空性质的说明”[注]王咏诗:《论康德的时空先天性论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在1770年的《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以下简称就职论文)中,时空观念性原理首次得到完整表述,就职论文因此被视为康德哲学转向批判阶段的标志。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第一批判)中,时空观念性原理作为“先验感性论”而成为该著作的开端。但海德格尔曾指出:“先验感性论如何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这本来是不可理喻的……先验感性论就其本身而言,不能是在可能性上封闭在其中的整体自身”。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不可能仅仅从其自身得到理解,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必须对之进行一种溯源工作,即必须追问“空间和时间在此是怎样亲临的呢?”[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7~138页、第137页。王庆节先生将“transcendental”译为“超越论的”,本文则根据康德中译的通行做法将其修改为“先验的”。
康德赋予了感官一种综观(Synopsis)能力:“如果我由于感官在其直观中包含杂多性,就把一种综观赋予感官,那就任何时候都有某种综合(Synthesis)与这个综观相应” (A97)[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参照学界通行标准,随文夹注AB版的页码。引文参考邓晓芒先生的译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并根据德语原文有部分修改,不再一一指出。。海德格尔则仅仅抓住感官的这种综观能力并指出:“纯粹直观中的‘综’的特性〈‘Syn’-Character〉并不从纯粹直观对纯粹知性的从属地位而来,相反,对这一‘综’之特性的阐释,就引向了从先验的想象力出发对纯粹直观进行溯源的工作”[注]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138页。。因此,海德格尔把作为纯粹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起源追溯至先验的想象力;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纯粹知性范畴的起源也追溯到先验想象力。因此,尽管康德只是猜测感性和知性“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基”(A15/B29),但海德格尔却明确主张先验想象力就是这种根基[注]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130~147页。。
本文所展开的也是这种溯源工作:基于历史的视角,从康德1760年代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出发,将康德的时空理论追溯至他对人的身体意识和身体经验的理解。之所以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出发,是因为时空理论是其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因此本文就包含两个任务:首先,梳理康德1760年代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揭示其将身体意识引入形而上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其次,基于这种方法批判,考察身体意识与其时空观念性学说的起源之间的隐秘关联。
一、身体意识与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
(一)数学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有着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在1765年致兰贝特的书信中康德说道:“多年来,我的哲学思考曾转向一切可能的方面。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所有这些努力,主要都是为了寻求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独特方法”[注]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在《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康德强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的意义:形而上学“之所以虽然有学者们的伟大努力却还是如此不完善和不可靠,乃是因为人们认错了它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像数学的方法那样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注]康德:《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本文涉及的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论文均来自李秋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引文根据德语原文有部分修改,不再一一指出。。事实上,这是康德对他1764年论文《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的重复,在这篇论文中,康德对哲学的方法与数学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并强调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康德看来,数学认识和哲学认识都要运用普遍的概念,而达到这种普遍概念的方法只有两种:“或者是通过概念的任意结合,或者是通过对借助解析而变得明晰起来的那种认识的抽象”[注]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前者是数学的方法,康德称之为综合的(synthetisch);后者是哲学的方法,康德称之为分析的(analytisch)[注]第一批判引入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以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但它们与作为方法的分析与综合的概念是不同的,为了区分二者,康德又把分析的方法称为“回溯的(regressive)方法”,而把综合的方法称为“前进的(progressiven)方法”。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由于本文主要涉及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文献,因此仍然使用了“分析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综合的方法的核心特性在于:“我所解释的概念并不是在定义之前就给定的,相反,它最初是借助定义才产生的”[注]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277页。。康德以不规则四边形的概念和圆锥的概念为例指出,如果我们不事先定义它们是什么,那么它们就可以意味着随便任何东西[注]《几何原本》开篇就首先定义了什么是点、线、面、角等。参见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燕晓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而适用于哲学的分析的方法则正好相反:“在这里,关于一个事物的概念是已经给定的,但却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不够明确的。我必须对它进行解析……使这一抽象的思想变得详尽和明确起来”。康德以时间概念为例指出,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却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分析使它变得清晰起来,但却不能通过综合的方法首先给出时间的定义,因为,“倘若这个概念恰好就是充分表达了给予我们的理念的那个概念,结果该会是怎样一种幸运的巧合啊!”[注]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277页、278页。
由此可知,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是被给予我们的,而不是像数学概念那样是由我们定义的;前者是含混的,而后者是清晰的。因此康德主张:“人们在形而上学中绝对必须以分析的方式行事,因为形而上学的任务事实上就是解析含糊不清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从解释开始,例如把必然的解释为其对立面是不可能的,而是“应该在自己的对象中首先谨慎地寻求关于该对象确定无疑的东西,即使还没有关于它的定义”。以空间概念为例,我们不能像牛顿那样把空间定义为自在的实体,或者像莱布尼茨那样把空间定义为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相反,由于空间这个概念是被给予我的,我应该首先寻找在这个概念中可以被直接想到的标志,包括空间的三维性以及空间中的事物彼此外在等等。不仅如此,康德还着重强调:“诸如此类的命题可以通过为直观地认识它们而对它们进行的具体考察来阐明,然而它们决不能被证明”[注]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290页、286页、282页。。可见,虽然康德此时还没有认识到空间的直观本质,但他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已经明确指出,关于空间的很多命题只能通过直观活动来具体地阐明。
在康德看来,分析的方法事实上与牛顿的方法是一致的,是一种经验的方法。但与牛顿不同的是,形而上学应该从内在经验和直接意识出发:“在形而上学中也是一样,人们借助可靠的内在经验,即直接的明显的意识,搜寻无疑包含在某种普遍性质的概念之中的那些标志”[注]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287页。。在1765年的《通告》中,康德再次重申了对形而上学的方法之批判的重要性。1766年《一位视灵者的梦》(以下简称《梦》)就是康德对这一批判的更加具体的展开,在这里,康德将身体意识视为内在经验和直接意识引入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中。
(二)作为直接意识与内在经验的身体意识
《梦》这篇论文是以反对神秘宗教为契机而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展开的一个批判。在康德看来,视灵者与形而上学家的亲缘关系首先表现在他们都使用综合的方法来获得自己的基本概念,而康德明确反对这一点,并通过直接的身体意识来揭示他们的方法带来的荒谬之处。
首先,视灵者模仿数学的方法,将灵神定义为一个拥有理性的存在者,然后声称人的灵魂就是这样一个灵神,这就会带来一个荒谬的问题,即人的灵魂在世界中的位置何在?康德指出:“一个物体,其变化就是我的变化,则这个物体就是我的身体,它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这就意味着,虽然身体也是一个物体,但与其他物体不同的是,它直接地属于我,或者说它与我是同一的,因此康德才会说,身体的变化就是我的变化,身体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因此,原初的、直接的位置意识是由我的身体决定的:“没有人直接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中的一个特殊位置,而是意识到他作为人就周围的世界而言所取的位置”[注]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27页、328页。。 这就意味着,原初的、直接的位置意识指的是我就周围世界而言所处的位置,而不是指人的身体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因此像视灵者那样追问灵魂处于身体的哪个位置就是非法的,因为这种提问“预设了某种并非凭借经验认识到、而是也许建立在想象出来的推论之上的东西:即我的思维着的我处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与属于我的身体的其他部分的位置不同”[注]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27~328页。。这个问题根本不能用经验来证明;相反,通过我们直接的身体意识,恰恰可以揭示它的谬误之处。
德国哲学家F. Kaulbach认为,康德在这里描述了现象学的身体意识,即身体被视为“非客观化的、我们的思维处境的主观特征……这个身体(与它的空间性的广延),我直接地把它体验为我的,我同样把它作为属于我的而谈及它,自我作为身体的—直观的体验者与自我作为被体验到的身体是同一的”,因此,康德对人类的认知处境和认知可能性的思考,是与人的身体的实存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那里,康德曾经认为我在物体世界中的处境是通过身体性(Leiblichkeit)得到规定的”[注]Friedrich Kaulbach, Leibbewusstsein und welterfahrung beim früen und späten Kant, Kant-Studien, vol. 54(1963), S. 464-490.。
其次,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也是通过数学的综合方法和单纯的概念思辨来获得超经验的知识,但与视灵者自始至终以为自己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不同,形而上学家在清醒的时候不会混淆由自己虚构、在自身之内的妄想和从外部感觉到的、处在自身之外的事物,那么,他们的这种内外之分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康德明确指出,“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对象被设想与作为一个人的他、从而也与他的身体所处的关系”[注]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46页。,即他们正是借助身体意识区分由自身虚构的幻想和从外部感受到的表象。但是,“如果他此时朦胧入睡,那么,所感受到的其身体的表象便逐渐消失”,基于身体表象的内部与外部之分也随之消失,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虚构的表象了。虽然此时形而上学家仍然有内部与外部之分的意识,但由于身体表象的消失导致没有真实的外部感觉“使人把原型与幻影、亦即外部的与内部的区别开来”[注]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46页、347页。,梦幻就产生了。可见,身体意识的消失导致外部感觉随之消失,真实与虚构、外部与内部就失去了区分的参照物,理性的形而上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梦幻者。
最后,康德通过对“感官(Sinn)/感觉(Empfindung)”概念的分析指出,对对象的感觉或者表象包含了对对象之位置的意识,这种位置意识是把事物设想为在我们之外的必要条件[注]参见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47页。。而康德在对灵神概念的批判中已经指出,原初的、直接的位置意识是我的身体意识,因为身体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我通过我的身体的位置才能把我与外部对象区分开来,并进而理解外部对象的位置。因此当视灵者和形而上学家自以为摆脱了身体,然后宣称有某物处在他们自身之外时,就是不合法的。
康德的分析表明,通过身体意识我们才产生了位置意识以及内在与外在之区分的意识,换言之,身体意识是对象意识与世界意识产生的前提。因此F.Kaulbach 认为,康德这里将身体意识与世界意识结合起来,表明“我的位置包含着在世界空间中的某个立场的条件,由此出发,世界及其中的物被认为源自我的主观性”[注]Friedrich Kaulbach, Leibbewusstsein und welterfahrung beim früen und späten Kant, Kant-Studien, vol. 54(1963), S. 464-490.。这就意味着,认识的对象及对象在其中被给予的世界之构造离不开我的主观性,并且,这种主观性首先是指我的主观的身体而不是灵魂,因为在康德看来,灵魂根本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甚至荒谬的概念[注]康德对灵魂概念的批判,不仅仅是出于思辨的需要,而且还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参见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75~376页。。而对象意识和世界意识与空间问题是分不开的。两年后即1768年,康德发表了唯一一篇专门论述空间问题的论文即《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以下简称《方位》),在这篇论文中,身体意识作为基本经验再次展示了其在形而上学批判中的核心意义。
二、身体意识与绝对空间
空间不仅是一个数学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因此,根据康德对哲学方法与数学方法的区分,空间概念是不可能通过综合的方法获得定义的,比如像牛顿把空间定义为独立自在的实体,或者像莱布尼茨把空间定义为位置分析的结果,而是应该通过分析的方法,借助内在经验和直接意识来获得。在《梦》中,康德把我们的身体意识视为这样的直接意识,在《方位》中同样如此。
在《方位》中,康德一方面主张,“方位并不存在于空间中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关系中,这本来是位置的概念,而是存在于这些位置的体系与绝对的宇宙空间的关系中”[注]康德:《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80页。,即把绝对空间视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康德又明示了方位区分与我们的身体的相关性:
在立体空间中,由于它的三个维度可以设想三个彼此都垂直相交的平面。由于我们只是就我们之外的一切都与我们自己相关而言才通过感官认识它们的,所以毫不奇怪,我们从这些相交平面与我们身体的关系获得最初的根据,产生空间中方位的概念。[注]康德:《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81页。
康德接下来具体解释了基本的方位是如何通过与我们的身体相关联而产生的:
我们身体的高度垂直立在其上的平面对我们而言是水平的;而这个水平面提供了区分我们借助上和下来表示的各个方位的理由。在这个平面之上,可以垂直立有另两个平面,它们同时也彼此垂直相交,使得可以在相交线上想象人体的高度。这两个垂直平面中的一个把身体分为外部相像的两半,提供区分左边和右边的理由,而垂直立在它上面的另一个,则使得我们能够有前边和后边的概念。[注]康德:《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81页。
康德在此以无可置疑的清晰性指出了,基本的方位概念,即上下、前后、左右源自立体空间的三个维度与我们的身体的关系。我们关于世界方位如东南西北的判断,同样如此[注]参见康德《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82页。。
因此,关于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根据,康德的立场似乎是矛盾的:既主张绝对空间是方位区分的根据,又主张我们的身体是方位区分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康德此处的立场与1760年代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联系起来,就能消除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从哲学方法与数学方法的区分的角度来看,康德虽然同牛顿一样使用了绝对空间的概念,但他不可能接受牛顿通过综合的方法所获得的绝对空间的概念,即首先把空间设定为独立自在的实体。相反,按照分析的方法,康德必然依靠内在经验和直接意识来获得绝对空间的概念,而在《梦》中,康德已经指出了身体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直接意识。因此,康德同时把绝对空间和我们的身体视为方位区分的根据并不是矛盾的,从其形而上学方法之批判的背景来看,二者恰好是一致的,因为绝对空间的概念正是通过直接的身体意识获得的。
在《方位》结尾处,康德称绝对空间具有“对于内感觉来说足够显明的实在性”[注]康德:《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386页。。这种内感觉指的就是作为内在经验的身体意识。虽然康德没有明示这一点,但我们基于其1760年代的形而上学方法之批判可以揭示这一点。F. Kaulbach通过现象学的分析指出,康德的绝对空间与牛顿不同,“绝对”在康德这里是个立场概念,它意味着自身与一个主体的立场相符,而这个主体是一个身体的主体[注]CF. Friedrich Kaulbach, Leibbewusstsein und welterfahrung beim früen und späten Kant, Kant-Studien, vol. 54(1963), S. 464-490.。M. Rukgaber基于图形—背景关系理论的研究同样指出,在《方位》中,康德证明了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终根据是我们的本己身体[注]CF. Matthew Rukgaber, “The Key to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Space, Time and the Body in Kant, Kant-Studien, vol. 100, no. 2(2009), pp. 166-186.。P. Woelert的研究则表明,康德在《方位》中的洞见在于指出左右手构造了空间的一种原初形式,从而表明某种原初的绝对空间的实存,并且,这种绝对的、原初的空间本身不是被设想为去身化的,而是与人的本己身体的在场有关[注]CF. Peter Woelert, Kant’s Hands,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pernican Tur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0(2007), pp. 139-150.。
由此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关于康德在《方位》中的空间观的争议。学界的最新研究倾向于坚持《方位》中的空间理论与就职论文以及第一批判中的空间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即在《方位》中,康德的空间理论已经具备了主观性和观念性的特征。例如D. Walford认为,在《方位》中,康德对绝对空间持保留态度,并且为观念论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在1770年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注]David Walford, Towards an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1768 Gegenden im Raume Essay, Kant-Studien, vol. 92, no. 4(2007), pp. 407-439.。P. Kauark-Leite则进一步指出,《方位》中的绝对空间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独立自在的实体,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感知物体的可能性的条件,因此已经具有主观性和观念性的特征,并据此批评了学界的通行观点,即康德直到写作就职论文时期才发现了空间的主观性和观念性[注]Patricia Kauark-Leite, On the Epistemic Status of Absolute Space: Kant’s Directions in Space Rea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 Critical Period, Kant-Studien, vol. 108, no. 2(2017), pp. 175-194.。
不过,如果从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方法批判的角度出发,就能更好地理解D. Walford和P. Kauark-Leite的立场。准确地说,康德不是对绝对空间持保留或者限制的立场,而是持一种与牛顿完全不同的绝对空间观,因为他们获得绝对空间概念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方位》中绝对空间的主观性和观念性的特征,必须从绝对空间与我们主观身体的相关性方面来理解;身体意识作为内在经验和直接意识,是绝对空间的主观性和观念性的根源。因此,正如不少研究所揭示的,这种理解是空间的先验观念性的基础,从而也是先验哲学的基础[注]除前述文献外,还可参见袁建新等《康德的心灵具身性思想及其意义初探》,《世界哲学》2016年第6期;Angelica Nuzzo, Ideal Embodiment: Kant’s Theory of Sensibi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1-44; Helge Svare, Body and Practice in Kant,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p. 61-78.。但在就职论文中,康德却不再提及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在批判哲学的开端处好像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身体意识与时空的观念性
在就职论文中,康德首先指出了数学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不是原初的时空概念,因为在数学中,空间和时间“就性质而言对可感事物没有规定任何东西,所以它们仅仅就量而言是科学的对象。因此,纯数学在几何学中考察空间,在纯力学中考察时间”,即数学仅仅就量的方面考察空间,但不涉及空间的质的规定。康德则从质的方面把时间和空间规定为“不仅仅是所有直观的形式原则,而且自身就是原初的直观”[注]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04页。,即康德规定了时空概念的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作为原初的直观,其次是作为直观的形式。因此,就职论文首次完整表述了时空的观念性理论。
但一方面,根据前面的分析,时空观念性理论并不是在就职论文中才产生的,相反,其形成有一个历史可循。另一方面,虽然康德在就职论文中不再提及原初空间与人的身体的相关性,但从康德1760年代形而上学方法之批判的背景出发,我们仍然可以主张,空间的观念性论题同样是通过分析的方法,借助内在的、直接的身体意识获得的。就职论文对空间概念的第一条规定包含了这一点:
空间的概念不是从外部感觉抽象而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把某物设想为处在一个与我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我就不能把它理解为被设定在我之外的,而如果我不把事物置于空间的不同位置上,也就不能把事物设想为彼此外在的。[注]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10页。
我把事物表象为在我之外,并把不同的事物表象为彼此外在,这预设了我的身体表象,因为,根据《梦》,我通过我的身体表象才产生内在与外在之分的意识。我之所以能够把某物表象为在我之外,是因为某物与我处在不同的位置,而我的身体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因此,空间关系预设了我的身体意识。
但康德在就职论文中几乎不再提及身体,而是频繁地使用心灵一词,并把空间和时间视为“从精神的活动自身得出的”[注]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15页。。根据黄毅先生的研究,这与康德1770年前后对牛顿晚期神学著作中的作为上帝之感官的空间理论的反思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康德吸收了牛顿把空间视为神圣心灵赋予对象的形式之观点,另一方面,康德又否定了空间依赖于神圣心灵,而认为空间依赖于人的心灵。因此,正如牛顿为绝对空间寻找一个神圣心灵的基础,康德也为绝对空间寻找一个人类心灵的基础[注]参见黄毅《论牛顿的作为上帝感官的空间理论及其对康德先验唯心论的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4期。。这就意味着,空间在就职论文中必然被内在化,即空间关系被还原为时间关系。
与第一批判的“先验感性论”相比,在就职论文中,时间被置于空间之前;但在第一批判中,空间在时间之前。这种安排并不是随意的,它反映了康德对时空关系的不同立场。在就职论文中康德指出,空间和时间“本来一个是为了对象的直观,另一个是为了状态的直观,尤其是表象状态的直观。因此,人们还把空间也作为形象运用于时间的概念,用一条线来表现它,用点来表示它的界限(瞬间)”。尽管人们能够用空间关系来形象地表达时间关系,但康德认为,这并不表明空间关系优先于时间关系,相反,“时间更为接近普遍的和知性的概念,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包容在自己的关系中,包括空间自身,此外还有未包容在空间的关系中的偶性,例如心灵的思想”[注]康德:《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14页。。
空间关系能够还原为时间关系,因此康德此时才主张,空间同时间一样是我们精神的产物,这也是康德在就职论文中把时间置于空间之前的内在根据。但在第一批判之“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将空间置于时间之前,也许暗示了空间的重要性。G. Bird指出,康德在空间的形而上学阐明部分诉诸的即是作为身体的存在者而不是作为空间点的主体概念[注]Graham Bird, The Revolutionary Kant: A Commentary o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hicago: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140-145. Matthew Rukgaber持相同的立场,CF. Matthew Rukgaber, “The Key to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Space, Time and the Body in Kant, Kant-Studien, vol. 100, no. 2(2009), pp. 166-186.。而第一批判之“驳斥唯心论”则证明了内部经验以外部经验为前提,从而间接证明了空间关系对于时间关系的优先性[注]Jacinto Rivera de Rosales以“驳斥唯心论”为突破口,将人的本己身体引入第一批判,CF. Jacinto Rivera de Rosales, Versuch, den Begriff des eigenen Körpers in di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einzuführen, Das Leben der Vernunft: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Kants, hg. v. D. Hüning, S. Klingner u. C. Olk, Berlin: de Gruyter, 2013, S. 109-130.,康德在晚期笔记中同样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比如:
正如我意识到我在时间中的实存,我必然也意识到了外部之物的实存……事实上,为了认识某个人的内部状态,他不能仅仅拥有内感官,然而唯心论者却这样主张。[注]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ed. by P. Guyer, trans. by P. Guyer, C. Bowman and F. Rausc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60.
这就意味着,作为外感官的形式的空间关系是原初的,它不能被还原为时间关系和心灵属性,否则将导致唯心论。唯心论把自我视为一个灵魂或者思维实体,康德在《梦》中借助直接的身体意识对之进行了驳斥,在第一批判的“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部分,康德借助先验观念论再次对之进行了驳斥。在一篇驳斥唯心论的晚期笔记中,康德明确指出,自我首先是一个身体的存在者:
我们自身事先就是外感官的对象,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知觉到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且不能直观到我们自身处于与其他物的关系之中。——因此,灵魂作为内感官的对象不能直观到它在身体中的位置,而是说,人的位置就是灵魂的位置……我自身是我的外部直观的(在空间中)的一个对象,否则我就不能知道我在空间中的位置。因此,灵魂不能知道它在身体中的位置,否则,它就必须通过外感官直观到它自身,这样的话它就在它自身之外。[注]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pp. 361-36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与《梦》中的论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康德在这里再次强调了,我们自身事先就是外感官的对象,即一个身体的存在者,借此我们才能产生位置意识与空间意识。晚近面世的“列宁格勒笔记”则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身体与空间的关系。
首先,“对我自身来说,我并不直接地是一个对象,而是感知某个对象的人。只是就我把握时间中的对象,尤其是空间中的对象而言,我才规定我在时间中的实存”[注]Kant, A New Fragment of Immanuel Kant: “On Inner Sense”, trans. by H. Robinso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3(1989), pp. 249-261.。
对我自身来说,我并不直接地是一个对象,既不是内感官的对象即灵魂,也不是外感官的对象即躯体,也不是灵魂与躯体的组合,因为二者的组合仍然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由此可知,一方面,此时[注]“此时”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因为时间意识仍然是个问题。我的身体不是作为对象属于我,而是直接地属于我;另一方面,由于此时我还没有规定我在时间中的实存,灵魂的我与思维的我都还没有获得自身的规定(二者都在时间中被给予、被规定),即它们都还是“无”,因此,此时我与我的身体是同一的,我就是我的身体。“只是就……才……”则表明,原初的自我意识是一种身体意识,而关于作为灵魂的自我的意识则是派生的。
其次,“我能够先天地意识到我处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甚至在我知觉到它们之前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的直观作为外部直观,在关于我的印象的意识之前,属于同一个意识,所有这些都是必然的,因为空间是关于这些现实的关系的意识”[注]Kant, A New Fragment of Immanuel Kant: “On Inner Sense”, trans. by H. Robinso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3(1989), pp. 249-261.。
一方面,我处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这就预设了我与他物处于不同的位置,而身体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这是康德一贯的立场,因此,康德强调我能够先天地意识到我处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表明我的身体的实存是先天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另一方面,康德强调,空间是关于我与他物之间的关系的意识,因此,空间意识就预设了我的先天的身体的实存。这表明,空间关系在康德那里不是一个非空间的、无身体的意识与空间中的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与他之外的物之间的动力学的关系。这种空间关系是先天的,因此,“我直接地并且原初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世界存在者(Weltwesen)”[注]Kant, A New Fragment of Immanuel Kant: “On Inner Sense”, trans. by H. Robinso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3(1989), pp. 249-261.,也就是一个先天地处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的有身体的存在者,而不是一个自身封闭的思维主体,空间关系就源自我的这种先天的身体之实存。
四、结 语
在康德哲学中强调身体的作用是相当异端的,因为传统的康德研究认为,人的本己身体在康德哲学,尤其在其理论哲学中是不在场的。近年来,不少新的研究试图突破这一点,本文同样是这样一种尝试。学界关于康德前批判时期身体观的研究,在文本上大都局限于《梦》与《方位》,但本文的研究表明,首先,只有从早期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出发才能理解,康德为什么会在形而上学批判中引入人的身体。其次,虽然早期康德并未对身体意识与时空观念性原理之关联进行专题的讨论,但基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方法之批判,我们可以揭示这一关联。这同时表明,康德的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出现批判转向并不是“灵光一闪”的结果。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返回人的主观意识与主观经验,将它们纳入先验哲学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身体的主观维度。在《遗著》中,通过将“经验的动力学统一”的问题纳入“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先验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康德最终将人的本己身体纳入先验哲学的体系之中,主观身体的哲学意义及其与时空观念性原理的关联由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晚期康德对人的主观身体的思考可以被视为其早期立场的延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