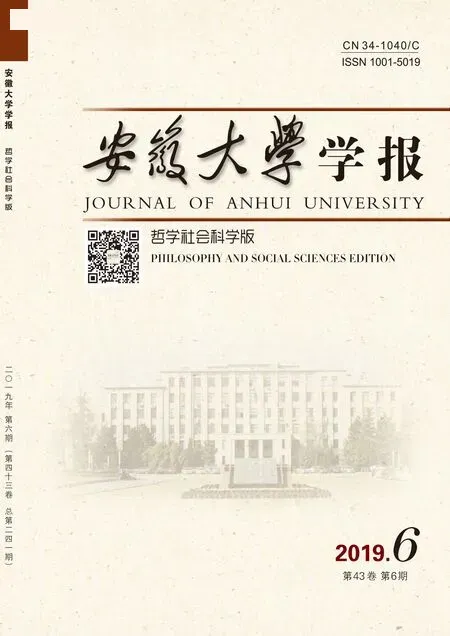从健全职业到服务抗战:抗战语境下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转向
——以上海“记者座谈”为中心
2019-03-14胡凤
胡 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记者群体寻求自由、独立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资格是中国新闻界的一股重要思潮(1)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57~286页。。与之伴随的是一系列旨在推动职业化的组织机制,诸如新闻团体、新闻教育、新闻学术活动等渐趋兴盛。职业化思潮的一个基本主张是新闻职业“非政治”“非党派”,而以“应社会之需”为追求。这也可以说是“五四”后新青年重视“社会改造”,并多少带有“非国家”思想倾向在新闻界的反映(2)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57页。。然而,这股职业化思潮盛行的时代也是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日益加快的侵华步伐,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是继续沿着职业化进路前行,还是对民族危机作出新闻人应有的回应,甚至调整自我的职业定位?此类问题是处在职业化前沿的上海青年记者们思虑的重心,显然也是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拷问的议题。
上海“记者座谈”是“现役职业记者们相互探讨新闻学术和工作上实践问题的一个集团”(3)陆诒:《“新闻学讲座”的开始》,《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0月3日,第3版。。它以同人聚会、切磋讨论的方式聚合成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团体组织。该团体成立之初衷在于健全职业、讨论学术,却在战争阴影下逐渐转向以抗日救亡为自我教育的中心议题。其中的转折和曲折,反映了1930年代青年记者在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纠结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背后的政党因素,值得深入探究。关于“记者座谈”的相关研究并不鲜见,或将其置于左翼记者群体中考察(4)蒋含平、梁骏:《转身之间:职业期许与救亡图存——1930年代的左翼记者群体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或关注组织职业化的方向和程度的转变(5)胡凤:《“记者座谈”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闻职业化》,《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或重点关注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立场和作为(6)徐基中:《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与自由守望——以〈记者座谈〉为中心》,《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已有研究多未能从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角度审视“记者座谈”的组织功能及在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的变化,也甚少论及“记者座谈”与中共领导的新闻组织的关系,以及其核心人物多系中共党员,忽视组织发展中重要的政党引导的因素。实际上,在抗战阶段,利用新闻教育培养新闻宣传干部和战地新闻记者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7)胡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才培养:以“青记”为中心的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第163页。。“记者座谈”对自我教育的探索和讨论应当成为“记者座谈”研究的重要视角,本篇即着力于此。
一、学术与职业导向:“座谈”式自我教育的诞生
“记者座谈”成立于1934年春夏之间,核心人物为恽逸群、袁殊、陆诒、刘祖澄、杨半农等上海在职新闻从业者。它以介绍新闻理论、新闻采写印刷技巧、地方新闻事业发展,以及探讨记者职业道德与修养、讨论新闻事件等为主要内容展开讨论,以促进自我教育。当时,这种非正式的新闻界同人群体非常多,上海的大部分新闻界组织都与“记者座谈”相似,属于“联谊性的俱乐部,很难看成严格意义的报业组织”(8)[澳]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第185页。。虽然参与者范围不是全国性的,人数亦有限,但是座谈通过比较有深度的研讨,尤其是后期筹办报纸专栏,汇集了当时沪上较有名望的记者、编辑和学者,对当时新闻记者和新闻学子的自我教育有明显的推助作用。
对于“记者座谈”的学术属性和职业属性,座谈发起者有过多次说明:“记者座谈,是新闻从业员(包括新闻社内外勤、内勤、印刷、经营各部门的人员),在目前这样现实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职业同人自己的生活教养的环境”(9)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4年8月31日,第1版。,是“一种职业同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10)陆诒:《“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页。。座谈的定位很明确,即以袁殊、陆诒等为代表的职业新闻人,实行非正规、非系统但颇具针对性的自我教育的平台,旨在促进“每个新闻记者对当前发生的事实现象,就可有一种了解,而对消息采访上,意得便利,不致多闹谬误”。此外,座谈开展的自我教育还有一层指向,即“记者的职业地位,亦将因技术和智识水平的升高而升高了”(11)沮沉:《现役记者与学术研究》,《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8月15日,第1版。,同时也推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发展。
“记者座谈”的产生也与当时新闻教育的弊端有关。刘祖澄认为院校新闻教育不仅培养出来的人数有限,而且偏重新闻学基础知识的培训“对于应付这所谓动乱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仍还是不够的”。为弥补院校新闻教育的缺陷,座谈同人认为现役新闻记者应当加强自我教育,即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互相配合,以获得较有系统和实益的‘学识’和‘能力’”(12)沮沉:《现役记者与学术研究》,《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8月15日,第1版。。因此,座谈期间的议题和讨论都以培养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为目标,偏向学术性和职业化。最初,座谈成员主要是通过工作或乡谊聚合在一起的现役记者。不久,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院校新闻系的师生也加入进来,如申报业余补习学校教员吴伴农、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学科教授宋哲夫、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授章先梅、参与创办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沈吉苍和沈颂芳,以及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施钧伯、顾迺湘、夏仁麟、凌鸿基等。以此为基础,座谈会与新闻教育机构的来往也愈发密切,座谈所举办的三次讲座均在沪江大学校内(13)《二次新闻学讲座》,《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0月17日,第3版。。与院校师生的密切互动使得“记者座谈”的自我教育从范围和形式上逐步发生转变。
当时,参加现役新闻记者的群体活动是新闻院系师生重要的学习方式。除“记者座谈”外,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师生还参加中国新闻研究会的活动。师生们希冀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报界现状,增加实践经验,学习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记者座谈”鼓动师生加入,也正契合其交换新闻智识、提高记者教养的宗旨。参加过座谈的复旦学生顾迺湘曾这样表述座谈会对自己的影响:“过去,我曾对一切现职的记者抱过反感,我很知道记者绝不是人人腐化,但我总是怀疑着他们为什么不运用青年的活力,对恶势力反抗呢?现在,我已得到答复了,记者座谈给我以很圆满的答复,尤其是X先生的一席话,更使我知道了这些有为的记者,是和恶势力在奋斗着。”(14)顾迺湘:《参加座谈会后》,《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4年11月30日,第4版。这种面对面对未来新闻人的培养和鼓动,效果尤为直接。
因为院校师生的加入,有了充足的参与者和合适的场地,座谈会的扩大版——“新闻学讲座”也随之产生。座谈曾邀请顾执中、成舍我、章先梅等知名新闻界人士开设新闻学讲座,且每次讲座都有明确的主题。如刚从欧洲考察新闻事业归来的顾执中,其演讲主题便围绕“欧美新闻纸最近动态,特别是新闻纸科学技术设备情形”。这些讲座的举办地点多在新闻院校内,所以它的受众群不再局限于在职新闻记者,在读的院校学生和“凡有兴趣于新闻学术的,都可自由参加”(15)《二次新闻学讲座》,《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0月17日,第3版。。这是同人群体自我教育的特殊性和优势,它的开放性保证了成员可以随时扩张,同时,与学院派新闻教育的密切来往,使得“记者座谈”在学界和业界学术职业导向的定位得到强化和凸显。
“记者座谈”座谈式自我教育从根源上是基于新闻记者职业化和新闻学术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时期“记者座谈”自我教育的职业化和学术化的偏向,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它与当时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以下简称“记联”)关系密切。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新闻学研究团体,除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该团体主要还是“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16)《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言》,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8页。,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建构和传播。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新闻研究会未能充分开展会务,其主要成员转而成立了“左联”的下属组织——“记联”。“记联”通过自己的刊物《集纳批判》及上海新生通讯社、远东通讯社等传播中共的抗日主张,批判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纳批判》在1934年被查封后,“记联”开始转变宣传策略。“一方面运用盟员在其所服务报社的公开合法的身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组织稿件通过种种关系分散供给报社登载。”(17)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9页。在这种策略的引导下,“记联”主要成员之一袁殊转而筹划“记者座谈”。“记者座谈”与“记联”的关联体现在:首先,“记者座谈”的核心成员和主要参与人员大多为“记联”成员。尤其是袁殊,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就是在他主持的《文艺新闻》作者群和读者群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他后来还成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干事。其次,活动的形式都采取座谈会、办刊物的方式。这两种方式被“记者座谈”沿用和执行之后,又被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继承发扬,并形成较大规模,达到了中国新闻史上新闻团体自我教育的巅峰。再次,在所办刊物的主题上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记联”出版的《集纳批判》较集中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传播和讨论,通过集纳理论探讨和新闻实践经验分享,教养在职新闻记者。“记者座谈”及其所办报纸专栏也是重点谈论集纳问题,培养职业同人。《记者座谈》专栏创办之后,还登载过“记联”组织的介绍苏联新闻事业的稿件(18)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国民党对上海的进步势力连续进行六次大破坏,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被破坏殆尽”(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上海的进步人士不得不以各种方式隐蔽起来。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报刊等大众媒介实行严密的检查与控制,重点在审查、封锁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信息(20)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第145页。。为了有效规避国民党的“围剿”,袁殊等遵循党的指示,“尽可能的变成一个小市民”。因而成立之初的座谈会也配合当时情势“打定主意不标榜任何党派”(21)丁淦林:《袁殊对“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46页。,将宗旨和活动定位为探讨新闻学术和新闻教育问题,坚持专业化和学术化导向。
诚然,“党派政治因素绝对不是左翼新闻团体活动的唯一动因或者根源所在,它只是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一元而已”(22)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记者座谈”学术职业导向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中国新闻职业化、新闻教育学术化发展的需求。这种学术化和职业化的导向,一直影响着座谈会早期的活动,直至1935年华北事变系列事件的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这一导向才开始有所转移——学术、职业导向弱化,政治导向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这个群体及其开展的自我教育。
二、职业化向政治化转向:《记者座谈》专栏的自我教育
偏向新闻学术探讨的座谈式交流开展不久,“记者座谈”就借助《大美晚报》中文版开设《记者座谈》专栏,开始以报刊专栏助推自我教育。从1934年8月开始,截至1936年5月,《记者座谈》共出版89期(23)专栏末期标注为第90期,但是第一次标注日期时应为第15期,误作第14期;第45期出现了两次,即1935年6月27日与1935年7月4日,重复了一次;第55期(1935年9月12日)与第57期(1935年9月19日)之间遗漏第56期。因此,专栏总期数为89期。。专栏开办基于“仅仅是在星期日的夜会的座谈,每感到零乱,许多谈过的话,没有记录,似觉可惜,许多要谈的问题,在热闹与匆忙的时间里,也有感言不尽意之处”(24)记者座谈会:《在“座谈席”上》,《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4年8月31日,第1版。,具有明显的学术化指向。除了可以利用专栏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新闻学理探讨外,同时也是期望利用《大美晚报》这个大众传播媒介,扩大自我教育的范围和影响。一经开办,《记者座谈》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不仅知名于上海新闻界,连北方新闻界亦有所了解(25)《三种报纸的出路——成舍我先生主讲》,《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0月17日,第3版。,成为中国出版史上较早研究新闻学知识、推进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新闻学专栏。专栏标榜“研讨新闻之学理”、“传布新闻之新闻”,目的是让在职青年新闻人“基于知识的和职业的共同的需要之下,有一个互相督促,互相训练和指示的机会”(26)编者:《我们的回顾与前瞻——关于周年纪念号的话》,《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8月22日,第3版。。因此,专栏刊登的内容以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国内国际新闻业发展为主,几乎囊括一个记者自我学习上的全部内容。对一个普通记者来说,这种专栏是进行自我教育、提升新闻业务能力的较好平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学逐渐朝着学科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步的还有新闻学研究以及新闻学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现。学术期刊的出现,使得新闻学研究成果有了发表、讨论和交流的平台,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学术化、职业化导向。早在1927到1928年间,北京新闻学会就连续创办《新闻学刊》《报学月刊》和《新闻周刊》三份新闻学专业刊物,以“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27)《第二卷的新闻学刊革新计划》,《新闻学刊》1927年第3期,广告页。。此后陆续又有《记者周报》《新闻学研究》《民国新闻》《报学季刊》等。《记者座谈》不是最早的传播新闻学专门知识的刊物,却是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专门介绍新闻知识的报纸专栏。和上述期刊不同的是,《记者座谈》依托的是面向普通大众发行的报纸,它的受众群体和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一般的新闻学刊物。受众不仅有新闻学研究者、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教育系统的师生,普通的大众也可以通过这个专栏了解新闻学知识和传媒界的行业万象。这种面向大众的教育不仅实现了新闻职业自我教育的功能,也具备某种宣传和推介新闻学术、新闻职业的功能。
此时,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日军一步步侵入华北,抗战救亡渐成大众媒介的主流话语。从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起,到该年12月,日军发动一系列侵占华北的军事行动。新闻记者们强烈直观地认识到“我们破碎的中华民国,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敌人得寸进尺的步步来侵略,压迫吞并全中国的计划,眼见即将完成”(28)沈颂芳:《新闻记者与民众运动——全国新闻记者组织之必要》,《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2月26日,第3版。。大敌当前的紧张和担忧也映射到“记者座谈”同人身上,他们开始通过专栏表达对日军侵华事件的反应。从1935年3月28日(专栏第32期)开始,《记者座谈》专栏对日本新闻界的态度发生了明确的转变。此前的第31期(实为第30期)上刊登的《新闻纸在日本》一文,还是以比较中立的态度介绍日本的新闻事业,从第32期开始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运用其毒辣的新闻政策”(29)《朝日新闻机访华之前后》,《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3月28日,第3版。这样明显带有倾向性的话语。以此为时间点对89期《记者座谈》进行分析,前30期专栏中与日本有关的内容仅有4篇,且基本以介绍日本新闻界为主,态度上多是将其视作外国新闻事业的介绍,如《日本现在的新闻纸总数》《日本朝日新闻的发迹》等;此后的59期中,直接以日本新闻界为大标题或小标题的文章有25篇,在文章中鲜明地提到日本新闻事业或者对日态度的有33篇。这58篇内容涉及日本新闻界、新闻团体、新闻宣传政策、新闻出版等等,开始从日本新闻界国际宣传和鼓吹的视角,全面审视日本新闻界。“我们对于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运用其毒辣的新闻政策,派朝日机来华访问,至少促醒一般平日里轻视新闻纸功用的政府官吏,而新闻界同人,尤应怎样的来加紧努力,积极奋斗,抵抗帝国主义的新闻政策,建立我们民族自救的新闻阵营!”(30)《朝日新闻机访华之前后》,《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3月28日,第3版。对日本新闻界操作规则的关注,一方面是为了让业界知晓和采纳其长处以促进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在中日矛盾日趋尖锐之时,掌握敌方新闻阵营的特点和动态。这两点,不仅仅是对在职新闻记者新闻业务和信息焦点的传授,更是对新闻记者在战时新闻活动中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外来侵略的教育。同时,座谈同人也开始关注日本的宣传政策和舆论操控,直指日本为配合其对外侵略扩张,在国际宣传上也欲打造“新闻帝国主义”,“普通报章杂志,由政府在最大限度内统制着,关于对外政策的言论,由外务省情报部供给资料,国内问题,那受内务省指导”(31)《日本新闻统制政策及其报章上言论之背景》,《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6年5月7日,第3版。,坚定地认为日本的新闻统制政策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
尤其是“何梅协定”之后,抗日群众运动自北向南风起云涌,迅速发展至上海。上海尚存的中共党组织“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32)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0页。。这一时期,中共对“记者座谈”固然不能完全做到像陆诒后来回忆的“采取教育、帮助和指导的态度,领导我们(记者座谈)冲破封锁,克服困难”(33)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第145~146页。,但是基于其“记联”的组织基础和核心成员与中共的密切关系,“记者座谈”显然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共的抗战政策。在中共的间接引领和鼓动下,座谈会同人不仅进一步认清了情势的危急,也更加坚定了鼓吹抗日的决心,并付诸行动。彼时,“由于抗战爱国运动的发展,形势迫使狭隘的左翼团体,真的变成了包括各爱国救亡组织的群众性大联合”(3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84页。。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比较集中,且主要参与者多为中共党员的群体,“记者座谈”也是转变中的一员。这种转变也证明了“记者座谈”同人对抗战语境中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认同。
同时,这种转变在新闻界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在其他新闻学研究的文本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以发行于1934到1935年间的《报学季刊》为例。在1934年创刊号中,《报学季刊》在谈论国际新闻的焦点时,仍然认为“在我们中国报纸的国际版中,目前有三个重要的牵涉到我们民族性的国际问题横在一般社会的面前:(一)希特勒登台以后德国问题;(二)美俄复交以后的日俄对立程度的估量;(三)以英国对‘伪满’实业考察为中心的复活英日同盟问题”(35)薛农山:《中国新闻纸中的国际问题与中国新闻记者的立场》,《报学季刊》1934年10月10日,第49页。,显然没有把中日关系视为国际问题的焦点。到1935年第1卷第2期,聚焦的仍是边疆新闻的报道问题。但是自1935年第1卷第3期开始,对日本新闻界的关注明显增多,仅这一期就刊登了三篇关于日本新闻界的文章,分别为《日本各报社采用社员的新倾向》《日本新闻界的动向》《握亚东新闻权威之日本通讯社》,另有两幅日本新闻机构来华的照片,国际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德、美、俄、英等转移为日本及其新闻统制问题。
三、抗战语境主导:“记者座谈”对战时自我教育和舆论动员的探讨
在非战时状态,中国报界的使命可归纳为:“第一,传达正确的消息;第二,建立公正的舆论。”(36)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今日报界的使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刊印,1937年,第21页。无论信息传播还是舆论建构都要求有职业化的新闻记者,然而抗战语境对新闻记者和新闻界的要求却有明显的变化,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成为普遍逻辑。对全面抗日要做的准备工作,马星野总结为三项,“第一,是军事的总动员之准备;第二,是经济的总动员之准备;第三,是意见的总动员之准备”,同时认为“宣传工作,最好是由新闻记者来做”(37)马星野:《战时宣传之应有准备》,《中外月刊》1936年第1卷第8期,第93页、97页。。新闻记者从职业化走向政治化,承担战时舆论动员和战时宣传的重任,当时是普遍共识。
“记者座谈”是较早开始讨论战时新闻记者社会责任的记者群体。首先,座谈同人对职业新闻人在抗战时空下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有明确的认知:“全国的言论界今天要抱着宗教家殉道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跟着上最前线去决斗……这是我们国难最尖锐化的时期,正是言论界殉道的时候!”(38)《国难最前线的言论界》,《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2月12日,第3版。其次,面对国难,座谈同人对特殊时期新闻工作的开展、新闻界在抗战中的特殊使命、民族自救中新闻工作者的自救提出自己的见解:建立一个新闻记者组成的“国难期舆论界同盟”,“由这同盟组合中,产生全国舆论界一致的共同意志,根据此公认的共同意志,表现舆论和舆论界的行动,各个单独舆论机关间,均实行互相策励、互相呼应,以表现新闻界整个具体的力量,与巩固舆论阵营”(39)祖澄:《国难期中的舆论战线应统一舆论意志和行动》,《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6年2月6日,第3版。。这个国难期舆论界同盟,有鲜明的整合新闻界力量、建立新闻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识,也为“记者座谈”发展为“青记”这一全国性新闻组织提供了舆论支持。此外,《记者座谈》专栏还刊有《中国新闻界的特殊使命》《民族自救的烽火中我们应加紧自励工作》等一系列探讨战时新闻记者功能的文章。座谈同人深感时局不稳,对于全面抗战的必将到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于平静无战争的前线,焦灼已久,同志们有的是脾肉重生,有的是锋芒未试,如今机会将近到临,准备着厮杀罢”(40)必行:《如何冲出记者的“苦闷圈”》,《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9月26日,第3版。,呼吁新闻界投身民族救亡事业。这种呼吁和讨论也是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一种。这种自我教育的所指,座谈同人用“记者道”的概念予以概括:“记载不欺骗读者大众的消息;说不违背大众利益的话;尽量暴露敌人各种侵略方式下的阴谋;严厉地批判欺骗大众的汉奸理论;尽量登载各地救亡运动的消息,并加以鼓励指示。”(41)袁殊:《记者道》,上海:上海群力书店,1936年,第1页。这些讨论一方面是对新闻记者进行广泛的关于抗战历史责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为战时新闻界自我教育的模式进行预设和归置,教育广大青年记者要联合起来,利用集体组织,在新闻团体中开展自我教育。
被迫休刊前夕,《记者座谈》对战时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模式又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勾画。座谈同人一方面深信“我们座谈同人所矢志努力过的学术的生活的自我教育运动,却决不因刊物的休刊而终止”,深信座谈会学术的、生活的教育势必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又深信“今后中国新兴的集纳运动,必然有更大的进展,而中国的新闻事业,也一定会从艰苦危难的环境里,奋斗出光明远大的前景”(42)陆诒:《写在记者座谈休刊的前夕》,《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6年5月7日,第3版。。这种新兴的“集纳运动”,是座谈同人在国难当头之时,试图构建适合于中国抗战需求的,有别于1920年代效仿欧美新闻理论、新闻实践的新闻观和新闻教育观。专栏在休刊之际,对于战时新闻理论和自我教育也有过不同层面的论述。这其中就发表了应该在各个新闻团体内部开展战时新闻教育和新闻理论研究的呼吁:“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同业们,各就原有的职业组合的团体,起来做一种研究学术技术,检讨理论,整饬风纪,充实力量的运动,把以前种种颓废、悲观、浪漫、萎弱、自私的行为表现,迅速的改变过来,建立起铜铁一般的新闻事业的战士集团,来和险恶的环境搏斗!”(43)陆诒:《民族自救的烽火中我们应加紧自励工作》,《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1月14日,第3版。希望在战时状态下,现役新闻记者可以通过自己参加的新闻组织,在职业组合的团体内,通过学习战时新闻宣传、研究实践技巧、检讨理论的方式开展自我教育。这一点在抗战时期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实际开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陆诒的回忆,这种讨论同时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战略开展的。“党及时教导我们必须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善于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并打击极少数的反动势力。特别批评了我们从《新女性》影片事件以后所滋长起来的小圈子作风,严重妨碍了团结工作的开展。”(44)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第148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引导下,座谈同人发表《新闻记者与民众运动——全国新闻记者组织之必要》一文,阐述建立战时新闻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认为新闻界“本身还没有健全的组织,过去各人都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即使各地有一二记者公会的组织,它的出发点的动机,往往是为着个人利益着想,从来没有见到能够替全体或是整个的新闻事业有个打算,更谈不上救国运动”。基于此,该文建议召集全国记者大会,整合全国新闻媒体的力量:“我们要联络努力新闻事业的纯粹分子……我们直接负责救亡的责任,但一地方记者的力量是很薄弱,所以要集中全国的记者才有伟大持久的力量,且可以在一致的目标下去奋斗。在开始救亡运动以前,第一步先发起召集全国新闻记者大会,以使对于整个新闻事业的改进及救亡运动,采取共同的行动。”(45)沈颂芳:《新闻记者与民众运动——全国新闻记者组织之必要》,《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12月26日,第3版。此时,正值1935年末,北平刚发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各地抗日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马相伯、沈钧儒等就组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认为“一切苟且因循的政策,都只有分散民族阵线,使敌人逐步的消灭我们”,明确提出要“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46)沈钧儒:《沈钧儒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建立民族联合战线,停止一切内战。“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抗日救亡、争取言论自由的主张,都表赞同。新闻界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步形成。”(47)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第148~149页。正是这种讨论和造势,才推动了战时全国性新闻组织的产生。
显然,1935年后“记者座谈”对战时新闻记者职能以及战时自我教育模式的关注,远远超出座谈成立之初“现役新闻记者如何从事新闻学术研究”(48)沮沉:《现役记者与学术研究》,《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专栏,1935年8月15日,第1版。的定位。它开始配合左翼文艺界解散“左联”以扩大文艺界联合战线的战略,为新闻界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的自我教育组织进行舆论造势。这表明以“记者座谈”为代表的上海记者群体开始主动适应抗战、配合抗战,自觉地完成了从学术化、职业化向政治化、军事化的转变。
新闻教育的这种转变显然具有普遍性,当时的大部分新闻团体都发表公开声明,指出新闻记者应当服务于抗战,有些新闻团体甚至是专门为讨论抗战时期的记者职责而成立,如“努力研讨,如何使中国新闻事业,能适应现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49)《平津新闻学会宣言:在平成立选出理监事,发表宣言提出四要求》,《生活教育》1936年第2卷第23期,第34页。为旨趣的平津新闻学会。这种转变甚至在相对远离政治的院校新闻教育上,也有明显的呈现。以燕京大学开展的新闻学讨论周为例,1931至1934年连续举办的四届讨论周,都是围绕具体的新闻业务开展讨论,甚至具体到“中学刊物”的刊行等问题,强调新闻教育的学术性。1935年后,第五届、第六届新闻学讨论周的主题分别设为“新闻事业与国难”、“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议题也紧紧围绕报人如何配合抗战形势,以及如何培养服务于抗战的有特殊使命的报人展开(50)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今日报界的使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刊印,1937年,第21~24页。。因此,总体而言,“记者座谈”的转变固然有政党引导的因素,但主导的政治因素,仍然是抗战时期大势下,新闻记者为国家民族图存而奋斗的使命感。
《记者座谈》专栏于1936年4月被迫停刊后,“记者们每周座谈的活动却从未停止”(51)方蒙:《范长江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并且“在这一时期,改变了过去狭隘的工作作风,放开手从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广泛交朋友,团结了更多的青年记者,扩大了队伍”(52)陆诒:《文史杂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第150页。。直至上海沦陷,“记者座谈”才停止活动。“青记”的成立,既有座谈前期的舆论基础,也有座谈会此阶段活动奠定的组织基础。因此,“青记”在成立之初,就认定宗旨是“(一)进行自我教育,(二)部分地解决当前新闻事业的困难”(53)陆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成立大会》,《新闻记者》1938年第1卷第2期,第17页。,显然是继承和实践了“记者座谈”对于战时自我教育的探索和构想。
四、结 语
从学术和职业指向来看,“记者座谈”以报纸专栏为输出平台,向受众传播新闻学理论和实务知识,这种知识传播和职业教育的意义,是普通的记者群体甚至新闻教育机构无法比拟的,它为新闻学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空间。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座谈同人开始将目光聚焦到日本及日本新闻界,关注日本新闻界为侵华战争做出的调整和准备,讨论抗战情势下中国新闻界如何在舆论动员的需求下开展自我教育,明显地呈现出学术化职业化向政治化的转向。这种讨论和转向,是内外因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职业新闻人和新闻团体面对民族危机奋起救亡的自觉抉择,另一方面也和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动“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的政治导向相关。“以政治学的视角,将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划归于党的政治领导,认为左翼新闻团体和其实践活动是党宣传战线上的整体部署”(55)倪延年主编:《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5页。的观点固然过于武断,但是作为以“记联”为基础成立,其核心成员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的“记者座谈”,它对抗战新闻教育的讨论与构想,必然“含有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履行政治使命的色彩”(56)徐基中:《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与自由守望——以〈记者座谈〉为中心》,《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第123页。。尽管基于斗争情势的需要,“记者座谈”前期的活动和“党的领导及‘左联’无关系”(57)丁淦林:《袁殊对“记者座谈”的回忆》,《丁淦林文集》,第46页。。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与左翼文化团体的密切联系,推动包含“记者座谈”在内的新闻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双重因素的本质是国家危难之际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选择,两者都是以抗战救国为根本出发点,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坚决抗战的政治核心。在大势所趋和政党引导下,兼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新闻界自我教育逐步实现了从学术化向政治化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新闻教育从学术范式向政治宣传、战时舆论动员的转变,也体现了自我教育的目标从培养职业的新闻人向培养战斗的新闻战士的转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引导下,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最终确立了以培养战时宣传和舆论动员为导向的新闻记者和宣传人才的定位,新闻从业人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新闻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记者座谈”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