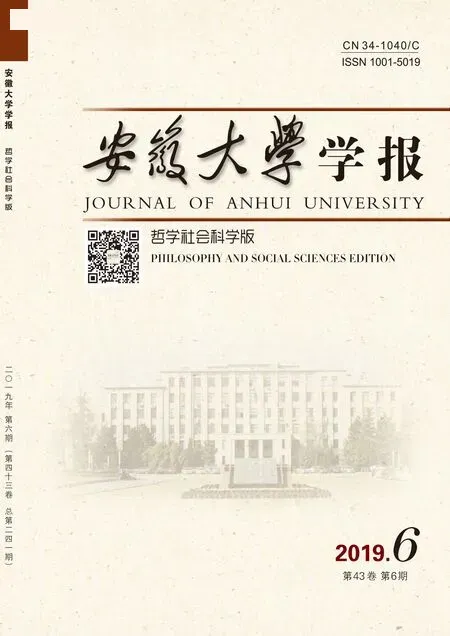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谜团:对笛卡尔道德哲学的考察及其结论
2019-03-14贾江鸿
贾江鸿
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否具有一种道德哲学的思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笛卡尔的道德哲学,特别是如何来看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和他的这种道德哲学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对学界来说,并没有十分完满的答案,而且考虑到笛卡尔自己的一些看似“奇怪的”做法,或者说他在表述上的前后矛盾,考虑到事实上笛卡尔并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道德的哲学文本,以及考虑到笛卡尔哲学本身的一种模糊性,因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类问题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笛卡尔哲学中的一个谜团(1)国内有学者注意到笛卡尔哲学的这个谜团,并把它称为“二重性疑难”,参见张柯《从“第一哲学”到“道德学”——论笛卡尔思想的“二重性疑难”》,《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一
当代笛卡尔哲学研究专家,巴黎一大的德尼斯·岗布什内(Denis Kambouchner)教授曾经谨慎地把他的一部研究著作定名为《笛卡尔和道德哲学》,而并没有像他的前辈罗迪·勒维(Rodis-Lewis)那样将其著作直接命名为《笛卡尔的道德哲学》,原因之一就是,在笛卡尔的著作中的确存在一些让人费解的表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性文本出自笛卡尔1648年在荷兰的埃格蒙德与一个叫弗朗索瓦·贝尔曼(François Burman)的年轻人的对话。贝尔曼在他关于对话的整理文稿中指出,笛卡尔曾经在对话中谈到他在1637年出版的《谈谈方法》中的“临时的道德准则”(une morale par provision)(2)关于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这个“临时道德”思想,可参见施璇《如何理解笛卡尔的“Morale par Provision”》,《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思想,他是这样来转述笛卡尔的话的:笛卡尔“不愿意写作道德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一些当政者或一些学究们,他不得不添加了一些道德的准则,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这些人就会断言他既不关心宗教,也没有信仰,并且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颠覆这些东西”(3)Descartes, Entretien avec Burman, texte présenté par CH. Adam, Paris: Vrin, 1975, p. 125.。另一个可能的支撑性文本出自笛卡尔在1647年11月20日写给夏奴的信,在其中笛卡尔写道:“的确,我总是拒绝写作与道德有关的思想内容,我有两个这样做的理由:一是,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从中一些机灵的人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去指责别人的借口;二是我相信只有君主或者被君主授权的人才有权去控制其他人的行为。”(4)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textes présentés par André Bridoux, Paris: Gallimard, 1999, p. 1285.考虑到这两个文本均出自笛卡尔生命的后半段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给予重视。依照这里的思想,笛卡尔一方面基于一些原因并不愿意写作有关道德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明确指出,十年前(1637年)的《谈谈方法》中的道德思想只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困难时局而写出的一种权宜之作。遵照这样的表述,再加上的确在笛卡尔的著名的文本中并没有明显的涉及道德哲学的内容(5)笛卡尔的《论灵魂的激情》被看作是笛卡尔唯一的一部涉及道德哲学的著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笛卡尔在这里的重点是描述激情的整个生理—心理上的运作机制,而不是提供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由于笛卡尔有意识的排斥,他在其哲学建构中并没有真正严肃地讨论过道德哲学方面的问题。
更为麻烦的是,似乎我们在笛卡尔早期的文本中也能找到相关的证据。在1619年那段对笛卡尔来说极为重要的时间里,笛卡尔在其著名的私人札记《内心的思考》中,曾经说过一段令后世的研究者费解的话语:“正如喜剧演员刻意遮掩自己脸上的肤色,以所扮演的角色的样貌出现一样,我在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世界舞台的时候,我戴上面具行走”(6)Descartes, Oeuvres de Descartes, V, textes présentés par Charles Adam et Paul Tannery, Paris: Vrin, 1996, p. 213.。笛卡尔为什么会在1619年初在自己的私人札记中说出这样的话呢?既然是私人性的札记,笛卡尔显然是认真而诚实的。在1637年的《谈谈方法》中,笛卡尔向我们指明,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及的“临时的道德准则”,实际上早在1619年左右就已经成形了。这样的话,一切似乎就顺理成章了,即笛卡尔在1619年,在自己准备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一种可能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因此,作为应对,他不得不临时制定一些道德准则,就如同是给自己带上一个面具来掩藏和保护自己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显然笛卡尔并不会真正严肃地对待和讨论道德问题,在其哲学中是没有道德哲学的位置的。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很快就显示出来。
在其著名的《哲学原理》中,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笛卡尔是这样说的:“全部哲学就如同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树干,别的科学就是在树干上生长出来的树枝。这些树枝可以分为三种: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我所谓的道德科学乃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善的科学,它以我们关于别的科学的完备知识为先决条件,因此,它就是最高等级的智慧。”(7)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66.我们知道,《哲学原理》是被当作教科书来写的,笛卡尔显然在这样的场合中也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而且,笛卡尔在这里还把道德哲学的地位看得极重,认为它是“最高尚、最完善的科学”,是“最高等级的智慧”。我们该怎样看待笛卡尔的这种思想?
事实上,把哲学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在笛卡尔思想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内心的思考》这个1619年初期的文本中,笛卡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科学也是戴着面具的……一旦卸下面具,它们将展现出极其美丽的面貌。从整个科学的链条来看,人们将发现,对于心智而言,掌握科学并不比掌握一些数字更难”(8)Descartes, Oeuvres de Descartes, V, p. 214.。在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的字眼“面具”,也就是说,依照笛卡尔的说法,在他当时的眼中,传统的科学是成问题的,它带着“面具”,遮掩住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而他自己则在探索一门“新的科学”。在1619年3月26日写给贝克曼的信中,他写道:“透过我这门科学的谜团,我已经瞥见了那难以名状的光明,凭借它,我想我能驱散最浓密的黑暗”(9)Descartes, Oeuvres philosophiques, édition de F. Alqué,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1997, p. 39.,这门新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像数字一样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那么,问题是,在这样的新的科学之中,有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的位置吗?
著名的笛卡尔研究专家、哲学家马里翁(Jean-Luc Marion)曾经在其《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和形而上学》中对1619年那段时期笛卡尔哲学的一些样貌给出过分析。马里翁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笛卡尔在1619年11月10日夜里所做的三个梦(特别是第三个梦)来判断笛卡尔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思想。马里翁指出,笛卡尔梦到的两样东西——字典和诗集是具有一定的哲学寓意的。在他看来,在笛卡尔所处的时代中,哲学并不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科学,而且由此,它也并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智慧。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伦理学,因为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伦理学本身在当时就是一门缺乏确定性的科学,它和哲学的其他组成部分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或系列。进一步来说,哲学这门科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就是十分零散和繁杂的,并不能达到真正的智慧的水平。但是,笛卡尔梦中的字典和诗集却体现了笛卡尔在当时的一个全新的想法,其中作为科学总称的字典代表的是作为统一的整体的哲学,而诗集则代表的是由哲学的统一性而达到的真正的智慧。马里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在1619年初的确已经在探索一门“新的科学”,一个科学的“链条”。不过,问题是,在这个时期的笛卡尔的思想中,伦理学真的已经被包含在他的科学整体之中了吗?
在此,我们是有必要再考察一番的。在1619年3月26日写给贝克曼的信中,笛卡尔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新科学的:“我正在构造、设想的并不是雷蒙·吕雷的那种简单的技艺,而是一种可以说是崭新的科学,它可以解决关于任何性质的连续的量和不连续的量的一切问题。”(10)Descartes, Oeuvres philosophiques, pp. 37-38.关于“连续的量和不连续的量的一切问题”,它仅仅涉及笛卡尔在后来提出的和量有关的广延性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在《内心的思考》中,他还写道:“正如想象使用形状来向它自己再现物体的形象一样,知性也使用为我们所感知的事物,如风和光等,来代表精神性事物”(11)Descartes, Oeuvres de Descartes, V, p. 213.。在这个被莱布尼兹评论为是“想入非非”的表述中,笛卡尔的观点是比较清楚的,即在这里精神性的事物也是可以被想象、被形象化的。当然,这样的观点笛卡尔在后来是抛弃了的,因为精神性事物的本质就是不可想象、不可量化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窥探笛卡尔在1619年那个时期的想法,即他的新科学不仅仅包含物体性的和量有关的对象,它还是包含一些精神性的内容的。在稍晚一些的1621年左右所写的《运用良知》中,笛卡尔写道:“智慧也就是伴随德行的科学,它把意志的功能和理智的功能混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是一条全新的道路。”(12)Descartes, Oeuvres de Descartes, V, p. 191.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笛卡尔在1619年左右所构想的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统一体的新科学,它是包含精神性事物以及和意志有关的道德科学的。
于是,我们面对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笛卡尔并不关注道德问题,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严肃的关于道德哲学的讨论,另一种则认为笛卡尔曾认真地把道德哲学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完全的不同声音呢?在笔者看来,在提供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去尽可能认真地审视一下笛卡尔对于道德问题的表述,以便搞清楚,如果存在这样的表述的话,那么笛卡尔到底在其中谈到了什么样的道德思想。
二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笛卡尔最初相对集中地处理道德问题的文本是1637年出版的《谈谈方法》。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中,笛卡尔指出,为了能切实地推翻之前旧的科学住宅,只是把房子拆掉,准备好新的材料,有了新的设计是不够的,因为在这时我们还需要准备好一所临时的房子,以便我们在建构新的科学大厦时可以舒舒服服地住着。“所以,当我受到理性的驱使、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地活着,我给自己定下了一套临时行为规范,一共只有三四条准则,我愿意把它的内容告诉大家。”(13)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页。为了能更好地分析笛卡尔的这种道德思想,在这里先简单地把他的这些准则转述如下:
第一,服从自己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的恩赐从小就接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约束自己遵循周围最明智的人通常在实践中采取的最温和、最不走极端的意见;
第二,在行动上尽可能地坚决、果断,一旦做出决定,哪怕它十分可疑,还是要坚决遵循,就如同它十分可靠一样;
第三,永远只求克服自己,而不是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而不是世界的秩序;
第四,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培育自己的理性,按照自己制定的方法尽可能地增进自己对真理的认识。
一些学者认为,笛卡尔的这套“临时的道德准则”之所以是临时的,首先就是相对于1647年笛卡尔《哲学原理》的法译本序言中的观点而言的。前文已经指出,笛卡尔在那里把自己的哲学描述为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有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并且道德学因为是以所有其他科学知识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也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智慧”,一种“最完善、最高尚的科学”。很显然,相对于这种作为“最高等级的智慧”的道德学来说,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这套“临时的道德准则”至少从表面上来说必然就是“不完善的”“临时的”。实际上,笛卡尔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在提到自己的哲学之树后,笛卡尔很快就写道:在《谈谈方法》中,“我曾经概括地叙述了逻辑的规则,和一些不够完善的伦理学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只是供那些尚未知道更好的道德科学和道德准则的人临时使用的”(14)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66.。不过,问题是,笛卡尔自己真的建立了一种依赖于所有其他科学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了吗?
大部分学者都对此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理想。比如笛卡尔研究专家白依萨德(J.-M.Beyssade)就曾指出:“笛卡尔总是保持着两种极端的观念,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笛卡尔的同一个道德目标的两个界限:一个是在理论上可以完美地控制的观念,由此,理智是完全得到彰显的,它具备了一个个无限的科学序列,可以必然引导意志去选择善的东西;另一个是在理论上有些混乱的观念,在这里科学是缺乏的,意志自身则得到了彰显,是可以自己来做决定的。但是现实的道德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15)J.-M. Beyssade, Philosppher par lettres, CF. Denis Moreau, Lettres Préface d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GF-Flammarion, 1996, pp. 41-42.。虽然白依萨德对笛卡尔的道德界限的划分本身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但是至少她的观点代表了一些学者的共识,即笛卡尔实际上并没有能完成一种他所谓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而是提供了一种所谓的“现实的道德”。那么这种“现实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就是笛卡尔在1637年的《谈谈方法》中的“临时的道德”吗?应该说从表面上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很明显,在17世纪40年代的时候,通过和伊丽莎白(Elisabeth)公主、夏奴(Chanut)、克里斯蒂娜(Christine)等人的讨论,笛卡尔在一些相关的书信和最后一个文本《论灵魂的激情》中,确实谈及了一种新的、相对确定的道德。这种道德似乎既不同于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提到的所谓的“临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同于笛卡尔在《哲学原理》法文本序言中提到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
一个可以支撑这种论点的最直接的证据来自笛卡尔的一封书信。笛卡尔在1646年6月15日写给未来的法国驻瑞典大使夏奴的信中曾经明确地提到,他在自己物理学的基础上找到了“道德上的一些确定的基础”(16)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1236.。很多学者,比如笛卡尔研究专家格鲁特(Matial Gueroult)由此就明确地指出,这种笛卡尔所谓的“确定的”道德,即笛卡尔在一些书信以及《论灵魂的激情》中建构的道德,其实已经真正地替代了那种所谓的最高等的、不可实现的、完全建立在确定科学基础上的理想性道德(17)M. Gueroult, Descartes selon l’ordre des raisons, t. II, Paris: Aubier, 1953, p. 255.。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指出了这样的理论事实,即虽然笛卡尔在谈论“临时的道德准则”的《谈谈方法》和谈论“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的《哲学原理》法文本序言中都提到了道德和医学的紧密关系,但是,其中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其实就意味着笛卡尔自己的一种思想的转变,或者更明确地说,意味着笛卡尔在这个时期对一种“明确的”道德的建构。在《谈谈方法》的第六部分中,笛卡尔提到了一种他试图建构的医学,他讲道:“我们可以撇开经院中讲授的那种思辨哲学,凭着这些看法发现一种实践哲学,把火、水、空气、星辰、天宇以及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认识得一清二楚……然后就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了。……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幸福,也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因为人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气质和状况的。……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各种疾病的原因,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药物,我们是可以免除无数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的。我自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精力用来寻求一门非常必要的学问,并且已经摸到了一条途径,觉得非常可靠,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找到;只是受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是生命短促,二是经验不足。”(18)笛卡尔:《谈谈方法》,第49~50页。相应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曾同样把医学看作是知识大树的一个部分,即看作是应该作为“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基础的一门学问。但是,根据这些学者们的观点,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哲学原理》中,实际上医学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或者说,“医学的那种高度的作用不再受到足够的重视了,而道德,尽管仍然需要依赖医学知识,但是,它和机械学以及医学一样都是哲学大树上的特殊分支”(19)D. Kambouchner, Descartes et la philosophie morale, Paris: Hermann, 2008, p. 31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在这些学者看来,原因就在于,笛卡尔实际上在详细地阐释他所追求的这种医学时遇到了困难,即仅仅通过研究人的身体,我们是很难真正弄清疾病的原因的。笛卡尔在1646年6月15日写给夏奴的信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转变:“我很有信心地跟你说……相比于其他的我曾经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加以研究的医学而言,我现在对于这个道德的基础更为重视了,因为不再是去发现保持生命的那些方法,相反,我找到了另一个更容易、更确定的办法,即对死亡不再恐惧”(20)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1236.。对笛卡尔来说,现在,更重要的不是研究与我们的身体有关的医学,而是要控制我们的激情,因此,道德对医学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了。
学者们给出的第二相关的论据是,笛卡尔的确从1645年左右就开始把研究目标转向了对自由意志的良好运用的问题,从而把那种基于其他科学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放弃一边了。在1647年11月20日写给克里斯蒂娜的信中,笛卡尔谈到一个和道德有关的主题,即人的至善(le souverain bien),在他看来,人的至善是和我们的灵魂或精神相关的,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运用,“灵魂的善完全相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认识,另一个是意愿那美好的东西;但是认识经常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因此剩下的就仅仅是我们可以绝对支配的意志了。我觉得,对意志的运用莫过于总是坚定而一贯地去做所有我们断定是最好的东西,以及运用我们所有精神的力量去很好地认识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有的美德正在于此;确切地说,我们值得称赞和骄傲的地方也正在于此;生命中最伟大、最坚实的行为正源于此。由此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至善”(21)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1282.。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的论据,学者们认为,笛卡尔最终为我们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基于自由意志,以及通过自由意志进而对自己的激情有所掌控(不害怕死亡)的“现实的”“确定的”道德。
但是,在笔者看来,学者们给出的这两个论据并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真的认为医学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吗?我们看到,即使是学者们所说的《谈谈方法》,在其中笛卡尔对医学的探索也是出现在最后一个部分,即第六部分中的,在这之前(以及在笛卡尔提供了他的“临时的道德准则”的第三部分之后),笛卡尔分别谈到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是”(第四部分),谈到了他对各种物质性事物的研究(包括人)(第五部分)。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就可以看到,笛卡尔的道德准则同这些知识,特别是医学的知识是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的。而且,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呈现的整个哲学框架发生变化了吗?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这从他对《哲学原理》这本书的布局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我这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包括人类知识的原理,可以叫作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至于其他的三个部分,则涉及普通的物理学,其中解释了自然的第一法则或原理,解释了天、恒星、行星、彗星以及全宇宙的构成。再其次,我还特别地解释了地球的本性……这样,我就似乎已经开始有次序地展开我的全部哲学了……我此后还应以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地球上较为特殊的事物的本性,即矿物、植物、动物,尤其是人类的本性。最后,我还要精确地探究医学、道德学和机械学。”(22)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67.很明显,这样的结构安排和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布局基本上是一致的,先谈哲学的第一原理(人类知识的原理),之后谈物质事物的本性(普通的物理学),再到谈医学。不同的是,在《谈谈方法》中,“临时的道德准则”是在之前就出现的,而在《哲学原理》中,道德则是和医学、机械学并行出现的(都是树干上的旁支)。
其次,笛卡尔是直到1645年左右才开始注意到对自由意志良好运用的重要性的吗?我们可以马上就给出两个论据予以反驳。早在笛卡尔写作《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时,他就讲过:“那试图严肃地追求事物的真理的人……仅仅想的是去增长自己理性的自然之光,这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或那个学派的困难,而是为了在每一个人生的场合中,让自己的理智能去引导意志做出该做的选择。”(23)Descartes, Regles utiles et claires pour la direction de l’esprit en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Paris: Vrin 1977, p. 3.在1641年左右完成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四沉思中,笛卡尔写道:“如果他没有给我由于我前面说过的第一个办法而不犯错误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我对于我所能考虑到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清楚、明白的认识),他至少在我的能力里边留下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下定决心在我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之前无论如何不去下判断。……而且,由于人最大、最主要的完满性正在于此,因此我认为我从这个沉思中还是获得很多东西的,我已经找到了虚假和错误的起因。”(24)Descartes, Médidation métaphysiques, présentation de J-M. Beyssade, Paris: GF-Flammarion, 1979, p. 151.当然细心的读者会反驳,笛卡尔的这两处表述,明显和他在1645年之后的表述是不同的,在《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37节中,笛卡尔是这么说的:“人的主要完满之处在于他能借助自由意志行动,他之所以受赞美,或受惩罚,其原因就在于此”(25)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87.。同样差不多的表述出现在《论灵魂的激情》中:“正是因为这样,其相关的补救方法就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即对所有显现出来的事物都要形成确定、坚决的判断,要习惯于相信,人们做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时,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尽管人们的判断也许并不正确”(26)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5页。。也就是说,在1627年的《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和1641年《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虽然承认了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但是都是在强调理智引导作用的前提下来讲的,即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谈到了人最大的完满性就在于自由意志,但是他也是在理智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克制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去盲目发挥作用的意义上来说的。而在《哲学原理》和《论灵魂的激情》中,笛卡尔却完全是就自由意志的运用本身而言的,它和理智的认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表面上看,这样的反驳是很有力量的,但是问题是《谈谈方法》这个文本,我们在其中的确可以看到笛卡尔这样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追求一样东西,只是根据我们的理智把它看成好的还是坏的;有了正确的判断,就可以有正确的行动,判断得尽可能正确,行动也就尽可能正确,就是说,可以取得一切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我们能够取得的好东西”(27)笛卡尔:《谈谈方法》,第22~23页。。这种表述是和他在《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以及《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表述是一致的,即强调的是理智对自由意志的引导作用。但是,不能忘记笛卡尔在这里提到的“临时的道德准则”,其中的第二条就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地坚决、果断,一旦做出决定,哪怕它十分可疑,还是要坚决遵循,就如同它十分可靠一样”。这样的表述不是和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的说法基本一致吗?
三
笛卡尔的哲学中有严肃的、认真的道德哲学的内容吗?很显然是有的。我们至少可以在其文本中找到三种关于道德思想的表述:在《谈谈方法》第三部分中的,被看作是一种为了建构一所新的科学大厦而设的临时的居所——“不够完善的”“三四条”“临时的道德准则”;在《哲学原理》法文版序言中的,以所有别的科学为基础的,被看作是“最高尚、最完善”、作为“最高等级智慧”的道德科学;在1645年之后的一些书信以及《论灵魂的激情》中出现的,具有“确定的基础的”、被学者们冠以“现实的”字样的道德。那么,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临时的道德准则”仅仅是临时的,因而后来被抛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相对于可能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来说,它显然是临时的,也是“不完善的”,但是,至少有两条道德准则在后来还是被明显地保留下来。首先是第二条准则,正如上文中指出的,其表述依然出现在了《论灵魂的激情》中。其次是第三条准则,“永远只求克服自己,而不是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而不是世界的秩序”,在笔者看来,笛卡尔的《论灵魂的激情》实际上仍然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书中的最后一条条目是“人生命中所有的善恶都只与这些激情有关”,笛卡尔写道:“那些最受激情驱动的人也能品尝到生活中最甜美的滋味。当然,在他们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激情,并且其命运也不佳时,他们可能也会体会到生命中最苦涩的内涵。但是,在这里,智慧是很有用的,它可以教会人们去做自己激情的主人……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所有哲学事情中感受到一种快乐”(28)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162页。。
第二个需要我们澄清的问题是,以所有别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被建构起来了吗?很明显没有,岗布什内所谓的在“实践上”(29)D. Kambouchner, Le vocabulaire de Descartes, Paris: Ellipses, 2002, p. 50.“完善的”道德,显然不是笛卡尔在这里所谓的作为“最高等级智慧”的道德。虽然,白依萨德所谓的“一种极端的界限”的思想失之偏颇,因为笛卡尔显然并没有仅仅把这样的道德称作是一种极端的理想,在《哲学原理》中他曾认真地说道:“那些能借以达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的真正原理,就是我在这部书中所提示的原理”(30)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62.,“至于我的这些原理的最后及最大的结果就是,人们在研究了它们以后,可以发现我所未曾发现的真理,并且会由此逐渐进步,屡有发明,久而久之,对全部哲学得到完全的知识,因而达到最高的智慧”(31)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68.,“我的最高希望是:后人或者会看到这个幸福的结果”(32)Descartes, Oeuvres et Lettres, p. 570.。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对笛卡尔而言,这样的道德还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可能会实现的理想。
第三个需要我们澄清的问题是,笛卡尔的具有“确定的基础的”道德,仅仅是一种相关于“实践的”、在实践上“完善的”道德吗?对笛卡尔来说,由于全部的哲学知识并没有被建构起来,因此,这样的道德肯定不能被称作是“完善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具有“确定的基础的”道德,也只能是一种“不完善的”道德。不过相比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三部分的“临时的道德准则”,或者说笛卡尔在1619年就建立起来的这些道德准则来说,它不再完全是“临时的”,因为在这里笛卡尔毕竟已经把握到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是”),把握到一定的相关于物体本性的认识,把握到人的一些本性(人是一个身心的统一体),进一步认识到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以及探讨过激情的内涵,因此,这样的道德是以一部分坚实的哲学知识为基础的,它不仅在实践上是可靠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依据的。
为什么在笛卡尔的文本中会出现看似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情况呢?进一步来说,该如何看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和他的道德哲学的关系?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明的,从登上哲学舞台的一开始,笛卡尔就是十分关注道德问题的。即使将马里翁的分析作为证据的做法在这里看起来有些不够合适,但是笛卡尔在1621年的《运用良知》中的表述——“智慧也就是伴随德行的科学,它把意志的功能和理智的功能混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是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例证,即笛卡尔在1619年11月10日夜里的第三个梦,其中有两首诗,第一首诗的题目就是“我将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由此可见,笛卡尔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十分在意人生伦理的问题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恰恰说明了笛卡尔在那个时期的一种焦虑的心理状态,即担心自己的“新科学”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才让自己戴上“面具”,为应对可能的麻烦而假装制定一些所谓的“临时的道德准则”。但是,很明显,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的这几条“临时的道德准则”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临时的应付时局的策略,因为,正如我们分析的,其中的两条准则实际上也出现在他后来的《论灵魂的激情》中了。
而之所以我们能在笛卡尔的文本中看到他所谓的对道德问题的回避和拒绝,可能会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这恰恰就是出于笛卡尔那为了应对时局的谨慎态度,即他不愿意轻易地(尤其是在还没有能达成他所谓的“最高尚、最完善的”道德科学的情况下)提供一些所谓的道德立场,以避免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说得很清楚,“我相信只有君主或者被君主授权的人才有权去控制其他人的行为”,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当时欧洲的宗教气氛之下,笛卡尔显然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过于高调地多说什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临时的道德准则”的确有应对时局的可能(比如第一条准则)。但是,第二,我们不能忘记笛卡尔在1619年11月10日夜里的第三个梦中的第二首诗《是与否》,对笛卡尔来说,真理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他的一个首要问题。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在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曾这样说道:“涉及意志的相关内容,我一向是将它在生活上的应用和它在思考真理上的作用非常严格地区别开。因为在其日常生活的运用中,我绝不认为应该仅仅遵照非常清楚、分明的认识才能做事,相反,我认为甚至用不着总是等待最有可能出现的事物,而是有时候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物中选择一个并且决定下来,在这以后,就如同是由于一些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而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就像我在《谈谈方法》的第26页中所解释的那样……然而,我的《沉思》一书的唯一目的是思考真理……我对待的不是日常生活,而仅仅是对真理的追求”(33)Descartes, Médidation métaphysiques, pp. 273-274.。
由此,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出现了。笛卡尔的目标是要建构一种“全新的科学”,这种科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整体性,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原理来推导和建构出整个科学知识大树。其中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涉及最基本的知识原理,道德科学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原理中进一步必然地推导出来的。但是为了建构这样一门“全新的科学”,在具体的行动中,笛卡尔需要准备一套“临时的道德准则”,或行动准则,而且,在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原理之后,笛卡尔可以在整个科学大树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之时,建构一种具有一定的基础的道德哲学。总之一句话,在笛卡尔那里,道德哲学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种是作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即以所有别的科学为基础的、作为一种“最高等级的智慧”的道德科学,一种是具体而现实的、不够完善的(临时的道德准则)但可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1645年之后的)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