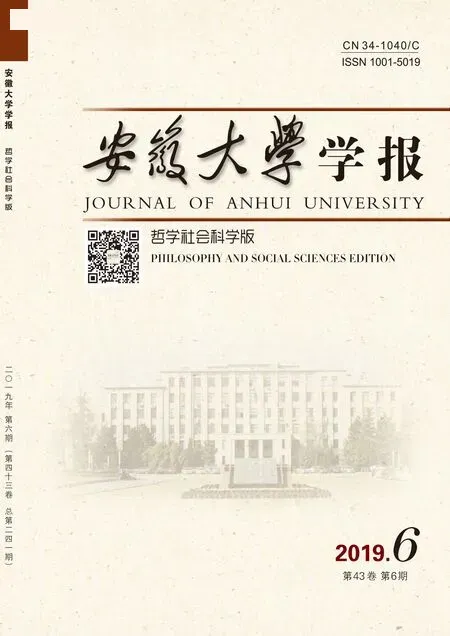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
2019-03-14孟义昭
孟义昭
山水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从山水中认识中国社会,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条必要途径。学界较为流行的研究范式,是探讨与山水相关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内容,如宗教、民间信仰、水利等,进而阐释山水与社会的关系(1)例如,魏斌研究了茅山道教的兴起过程及其与南朝社会的关系(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任双霞考察了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任双霞:《近代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以日照庵香会碑为中心》,《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王梓等梳理了福州西湖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王梓、王元林:《占田与浚湖——明清福州西湖的疏浚与地方社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但山水本身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实态,尚需进一步探索。山水史学,或称山水史,是一门研究历史上山水与人类社会互动实态的学问,这就要求研究视角既要放在山水本身,以山水史的视野研究山和水,同时又不能局限于山水本身,还需考察山水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山水所在范围内的人文景观,是人与山水互动的结果,也是研究山水史的绝好切入点。从山水的人文景观入手,览辑相关文本,探寻有关历史事实和人文故事,揭示景观背后的核心问题,分析山水文化形象的演进,解释山水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开展山水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徽州(2)唐至清代,徽州建置沿革较为复杂,为便于行文,本文统称其为“徽州”。山环水抱,山水之名闻于天下,同时人文荟萃,有“东南邹鲁”之誉,极其适合作为研究山水史的场域。作为徽州的名山,紫阳山上的紫阳书院颇受学界关注(3)张敏:《徽州紫阳书院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周晓光:《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类型分析》,《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张绪:《论施璜对清初徽州理学及书院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而对于紫阳山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紫阳山是如何成为徽州象征的,有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选取紫阳山作为研究对象,从其人文景观入手,在唐代至清代的长时段内进行考察,分析紫阳山由道教名山演化为儒学圣地的历史过程,揭示紫阳山与徽州社会的关系。
一、许宣平传说、紫阳观和紫阳山的道教形象
紫阳山位于徽州城南五里,“丰郁秀丽,端凝若堂,东向而峙。每将晓,日未出,紫气照耀,山光显烁,类赤城霞”(4)施璜编辑,吴瞻泰、吴瞻淇增订:《紫阳书院志》卷2,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4~455页。按,下引该书省去作者,仅注书名和页码。,因而得名紫阳。此山“高百九十仞,周四十里”(5)弘治《徽州府志》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93~594页。,因在徽州城之南,旧名城阳山,又称南山。
从唐代开始,紫阳山就有道士活动。朱熹在《名堂室记》中说:“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尝有隐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30页。此处“隐君子”,弘治《徽州府志》认为“盖指(许)宣平也”(7)弘治《徽州府志》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第51页。。关于许宣平的事迹,各类官私书籍记载颇多。最早记载许宣平事迹的当为南唐沈汾所撰《续仙传》,据该书记载,许宣平,唐代歙县人。景云年间,隐于城阳山(即紫阳山)南坞,结庵以居。隐居30余年,或济人艰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访之,多未能见,只看到其庵壁题诗:“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陇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8)沈汾:《续仙传》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9页。这些故事颇显离奇,却在徽州广为流传,从而生成大量神仙传说和人文故事。及至南宋,紫阳山名气日渐提升,许宣平传说也流传更广,在文人笔下此山异象迭出,据说“每夕有神光”(9)罗愿:《新安志》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82页。。
唐宋时期,徽州道教盛行,南宋徽州人罗愿所撰《新安志》说:“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聂遗风,以故人多好仙。”(10)罗愿:《新安志》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524页。在许宣平传说的影响下,徽州人更加重视仙道。徽州百姓在紫阳山上建立祠堂,作为祭祀许宣平的场所,是为许真君祠。北宋天圣二年(1024)四月,宋仁宗敕令将许真君祠改创为道观,并赐观额“紫阳”(11)罗愿:《新安志》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86页。,此即紫阳观。前引朱熹所说的老子祠,其实就是紫阳观。皇帝敕令以及赐额,奠定了紫阳观的地位,肯定了道教在紫阳山的合法性,使紫阳山名声大噪,成为道教仙山。
南宋淳熙五年(1178),徽州知州陈居仁“梦与许仙遇”(12)弘治《徽州府志》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第89页。,认为是许宣平对其感召,因访道观故基,重建紫阳观。嘉定年间,徽州推官赵希愬处事有方,不扰于民,“郡人立祠紫阳观祀之”(13)弘治《徽州府志》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15页。。徽州人在紫阳观为赵希愬立祠,说明紫阳观不仅是道教建筑,还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紫阳观毁于兵燹。此后住持黄毅夫重建三清殿、许宣平祠和玉枢阁,紫阳观再次恢复以往规模。
明成化年间,道士李本蓁在紫阳观东侧建楼七间,是为清隐楼。弘治十四年(1501),道士方本初创建凭虚阁(14)汪舜民:《紫阳观凭虚阁记》,《静轩先生文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8页。。为获得官府对紫阳观的认可与支持,方本初施展手段,一方面请徽州知府彭泽为凭虚阁题写匾额,一方面为徽州纂修府志提供场所。弘治十四年,在彭泽主持下,以汪舜民为总纂,开局紫阳观,纂修府志,此即后来的弘治《徽州府志》。彭泽选择紫阳观作为志局,是因为紫阳山远离市嚣,同时也考虑到紫阳观的宏壮规模可以为修志提供保障。汪舜民当时亲见该观规模:“观址东向,殿堂、门庑梯山而上。阁又据山椒最高处,凡十有六楹,雄杰明敞,几与山齐。试倚阑一眺,仰则青天白日如临目睫,俯则观屋参差万瓦如鳞,平山前出,群松如麻;远则大溪之东,问政、龙井诸山岚光掩映,如在帘栊之际。谓之凭虚,信乎!”(15)汪舜民:《紫阳观凭虚阁记》,《静轩先生文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第98页。可见紫阳观规模宏大,凭虚阁更是雄伟壮丽。
明代中叶,紫阳观远近闻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成化二年(1466),时任徽州知府龙晋命紫阳观道士柯永懋、仇道辅、钱启玄办理府城隍庙供祀诸事。此外,紫阳观还负责府城隍庙的管理事宜。柯永懋等修葺府城隍庙殿庑,“塑像创楼,焕然一新。买田立籍,令徒孙汪守清等相继居之”(16)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2页。。紫阳观势力所及,已经不再局限于紫阳山,还延伸至府城隍庙。明中期歙县人汪道昆说:“新都踞万山中,多列仙窟宅。”(17)汪道昆:《游城阳山记》,《太函集》卷37,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791页。紫阳观的兴盛,是与当时徽州道教的发展态势相呼应的。
受许宣平传说的影响,徽州一些隐逸之士也来到紫阳山隐居。如唐代歙县人张友正,结庐紫阳山下。贞元末年,魏弘简重其才,请他作《披云亭记》。张友正援笔立就,谢绝酬金,依旧隐逸山中(18)乾隆《江南通志》卷169,《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95页。。作为道教重地,紫阳山也是徽州著名道士的归葬之地。如宋代休宁著名的道教中人金野仙(名梁之),淳熙初年“坐化”后(19)罗愿:《新安志》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525页。,徽州民众将其葬于紫阳山,并在山上筑坛祭祀。道教仙山的名气,对致仕官员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万历年间,大学士许国致仕归里,在紫阳山辟地建屋居住。前来拜访的吴士奇说,许国为许宣平后裔,在宣平隐居得道之所结庐,实属机缘巧合。许国去世后,吴士奇为其构建升仙故事:“文穆仙逝之日,程生尝遇之九华巅,其与明奴家妪遇宣平于采樵之南山何异?”(20)吴士奇:《城阳山志叙》,《绿滋馆稿》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44页。吴士奇为许国构建的这套升仙叙事文本,使紫阳山又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紫阳山既是许宣平隐化成仙传说的发生地,又有紫阳观创立其中,引得众多士人寻仙问道、探幽猎奇,并留下不少诗文。
宋末元初,歙县诗人方回概括紫阳山道教形象:“将相共扶黄道日,神仙独隐紫阳山。云深夜注参同契,身在虚无缥缈间。”(21)方回:《桐江续集》卷2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560页。明初歙县人曹迁曾到访紫阳观,并赋律诗《紫阳观席上作》一首:“紫阳山中神仙家,青山绕屋生烟霞。枯林风过落黄叶,寒菊雨余开白花。只鸡斗酒自可乐,千驷万钟何足夸。兴阑携手过桥去,斜日稻田飞乱鸦。”(22)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55,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274页。曹迁所说“紫阳山中神仙家”,不仅是指紫阳观,也是对唐代以后紫阳山道教仙山形象的高度总结。成化、弘治年间,徽州人程敏政赴紫阳山游览,寻访许宣平、金野仙遗迹,留下“轩辕丹熟惟余井,太白诗高可配山”之句(23)程敏政:《游紫阳山寻许宣平金野仙二真遗迹次旧韵二首》,《篁墩文集》卷7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498页。。
嘉靖至万历年间,汪道昆约同友人游紫阳山,曾至紫阳观。据汪道昆说:“余童年谒仙翁祠,其像黄衣黄冠,仙仙如也。今祠视昔湫隘,尸祝乃摄世衣冠。土人谓旧祠灾,则皆更置。余从诸君子拜祠下,酌水献之。”(24)汪道昆:《游城阳山记》,《太函集》卷72,第1490页。昔日之盛况,今日之衰败,截然不同,反映了紫阳观在紫阳山生存空间的萎缩。这一时期,儒学在紫阳山居于主导地位,排斥道教,使其处于弱势。自宋代便开始的徽州儒士对紫阳山儒学形象的塑造活动,动摇了该山的道教仙山地位。
二、紫阳山儒学形象的塑造与道教形象的弱化
宋代紫阳山增添了两处重要的人文景观——紫阳书堂和祝确墓,尤以紫阳书堂影响深远。
徽州山川秀美,名山众多,紫阳山能在众山中脱颖而出,与朱松有着莫大关系。《紫阳书院志》即指出:“郡之名山以百数,而紫阳辟自朱献靖公韦斋先生,名遂冠一郡。”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徽州婺源县人,朱熹之父。据《紫阳书院志》载:“紫阳山在新安郡治南五里……献靖公游而乐之,为堂以居,肄业于中。后入闽,犹以‘紫阳书堂’镌为印章。”(25)《紫阳书院志》卷2,《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4~455页。朱松曾至紫阳山游冶,乐其山水之胜,在此建立书堂,以便读书起居。至于书堂之名,从“犹以‘紫阳书堂’镌为印章”可知,应当名为紫阳书堂。施璜更明确指出:“紫阳书堂,韦斋先生肄业之所也。文公自闽归,亦尝讲学于此,故后世尸祝之地,即为讲道之堂,志不忘也。”(26)施璜:《吴大司成陪祀紫阳书院记》,《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22页。朱松在紫阳山所建的紫阳书堂,是后来紫阳书院的文化源头。从此开始,紫阳山不再是道教独霸的天下。
祝确(1079—1161),字永叔,徽州歙县人,是朱熹的外祖父。祝氏家族财力雄厚,在徽州势力极大,号称“半州”。祝确不仅学问为人敬服,而且淳厚孝谨,乐善好施,“虽倾资竭力无吝色,乡人高其行”。据朱熹所撰《外大父祝公遗事》载:
方腊之乱,郡城为墟。乡人有媚事权贵者,挟墨敕徙州治北门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窊下,潦涨辄平地数尺,众皆不以为便。将列其事以诉诸朝者余二千人,而莫敢为之首,公奋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复取特旨,坐公以违御笔之罪。公为变姓名,崎岖逃遁,犹下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时事变更,群小破散,然后得免,而州治亦还故处,乡人至今赖之。而公之家资事力不能复如往时矣,然终不以为悔也。(27)朱熹:《外大父祝公遗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8,《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572页。
朱熹所说的“徽州徙州治”事件,或称“徽州迁城”事件,是徽州城市史上的一桩大事,罗愿《新安志》记有此事始末:
宣和三年,睦寇方腊既平,部使者迁其城于溪北三里,民不以为便。事闻,会除卢宗原为守,有诏同徐闳中相度。宗原以为新城地形不正,周四里有余,北皆重山,才能为三门。距溪数里,茶盐载卸者弗便。濒涧卑湿,为垒善崩,截山围筑,外高内卑,瞰临城中,又无濠堑,不足以为固。内之则顽石冈陇虚占其半,崚嶒峻仄不可以建居止,余皆荒草砂砾之地。夏秋山水暴出,灌注城内,雨雪则停潦为泥,盐米断绝。又顽石不可为井,土井六七,味恶易浊,汲溪则人以为苦,民以其故不愿。旧城据山下平原,大势端正,周七里三十步。左有长溪,春冬水面二十丈,夏秋阔一里许,湍流百尺,循城西南而下,便于载卸;其右则倚山为城,亦临深溪,绕城东北,不可逾越。市皆甓甃,民居宽广,井泉且千所。向特以城壁不全,故不能守。今若因故基修筑,足为险固,以此民情愿还。得旨:以旧城为州,以新城为歙县。且令以渐修筑,而新城亦卒不为县,今民间犹号新州。宗原城旧州毕,明年八月与士民复归于旧州。(28)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48页。
在“徽州迁城”事件中,徽州知州卢宗原捕捉时机,顺应民意,放弃溪北新城,将州治迁回旧城,从而奠定此后数百年徽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在卢宗原赴任徽州知州前,北宋朝廷就已经得知徽州民情。那么,宋廷是通过何种渠道获知下情的?在此过程中,祝确是关键人物。据朱熹说,公开反对迁建新城并诉诸朝廷者达2000余人,其为首者乃是祝确。正是在祝确的领导下,徽州民众的反对之声闻于朝廷,才促成迁城事件的日后解决。但对于祝确本人来说,此事无异于一场灾难。因此,徽州人对祝确极为尊敬和推崇。
祝确去世后,葬于紫阳山,紧邻后来的紫阳书院,成为山中一大人文景观。后世学子赴紫阳书院肄业,必至祝确墓前拜谒。《紫阳书院志》所录紫阳山图,就如实描绘了紫阳书院与祝确墓两大人文景观比肩相邻的情况(29)《紫阳书院志》卷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1页。。
南宋时期,朱熹曾至徽州,赴紫阳山游览,“留恋信宿,凄怆思慕。其山阿有处士祝公确墓,献靖公内父也。文公尝题祝氏山庄,有‘旧时山月’之感”(30)《紫阳书院志》卷2,《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5页。。览其父读书居住之处、外祖父埋葬之地,朱熹对紫阳山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朱松刻“紫阳书堂”印章,以示对紫阳山和紫阳书堂的思恋。朱熹不忘朱松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厅事”(31)朱熹:《名堂室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731页。,继承其父对紫阳山的眷念,人称“紫阳夫子”。
紫阳山是朱松游息之地,也是朱熹绍衣之区,其文化形象增入儒家因素,一变而成为儒家文化名山。正是因此,在紫阳山创立书院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紫阳书院志》即持此说:“紫阳山者,固献靖公游息之地,而文公绍衣之区也,两世灵爽凭焉。后之学者,俎豆宜于斯、肄业宜于斯矣。自宋迄明,建迁不常。而书院之归于紫阳山,则明正德时张太守芹之鸿裁卓识,为百世不敝之道也。”(32)《紫阳书院志》卷2,《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4页。在徽州儒士看来,紫阳山就是儒学的圣地。
尽管儒士将紫阳山塑造为儒学圣地,但在明代以前该山的道教形象仍较鲜明。一座紫阳山,道教、儒学形象兼具。现存关于紫阳山的诗文中,有不少综合其道教和儒学两种文化形象的表述。宋末元初,方回以紫阳山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诗文。在其诗文中,“紫阳山色好”“归老紫阳山”是较为常见的用语。方回在诗文之末,多署名“紫阳山方回”“紫阳山人方回”“紫阳方回”,可见其对紫阳山的钟情与痴迷。当其70岁时作五言诗,其中“紫阳山下住,问字足儒生……学师朱仲晦,诗友许宣平”诸句(33)方回:《桐江续集》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494页。,既表现其出世入世的心境,又反映出紫阳山作为儒学圣地、道教名山,可以将二者相融合的现实情况。
元代散曲名家张可久曾提出“新安八景”之说,即花屏春晚、练溪晚渡、南山秋色、王陵夕照、水西烟雨、渔梁送客、黄山雪霁、紫阳书声。张可久不仅品赏新安八景,还以其为素材创作散曲。其中,《南山秋色》曰:“华盖亭亭,向阳松桂荣。背立夜坛朝斗,直下看,老人星。地灵,风物清,众峰环翠嬴。千古仙山道气,谁高似,许宣平。”《紫阳书声》曰:“楼观飞惊,好山环翠屏。谁向山中讲授,朱夫子,鲁先生。短檠,雪屋灯,琅琅终夜声。传得先儒道妙,百世下,以文鸣。”(34)张可久撰、劳平甫校:《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外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738册,第287页、288页。由散曲内容可知,新安八景中的“南山秋色”正是紫阳山的胜景之一,其背后的人文意蕴是许宣平传说和紫阳山的道教仙山形象;“紫阳书声”则是以紫阳书院为主的景物,尽管当时的紫阳书院不在紫阳山,但作为新安八景之一,其与紫阳山儒学圣地形象却是一体的。
明初徽州人唐文凤选取徽州著名胜景,重新品评新安八景,分别为屏山春雨、练溪朝云、紫阳夜读、乌聊晓钟、渔梁夕照、古岩晴岚、黄山霁雪、白水寒蟾。其《新安八景诗》八首之《紫阳夜读》曰:“新安讲学尊紫阳,书堂夜永声琅琅。穆陵宸翰鸾凤翥,奎璧下贯晴虹光。上探孔孟继濂洛,道重泰山与乔岳。神游故国想归来,月明应化辽天鹤。”诗前有序:“紫阳山势若飞凤,昔我徽文公寓闽南,犹以是山名其读书之楼,以表其不忘桑梓之意。后之学者面山构书院,以为讲学地。”(35)唐文凤:《梧冈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559页。在唐文凤心中,“紫阳夜读”之所以能入选新安八景,关键在于其所承载的紫阳山儒学圣地形象。
对比两个版本的新安八景,在后者中“南山秋色”已消失不见,“紫阳书声”演变成“紫阳夜读”。由此反映出,经过明初徽州文人的有意塑造,紫阳山的道教形象渐趋弱化,儒学形象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三、紫阳山书院的创立及其对道教的打击
紫阳书院最初并不在紫阳山,而在徽州城。南宋淳祐六年(1246),徽州知州韩补奏建书院于城南,即紫阳书院,宋理宗御书匾额。院内明明德堂,作为祭祀朱熹的场所。此后,书院建迁不一,皆不在紫阳山。徽州士绅认为书院建在城内易遭兵燹,而“在山为可久,亡兵火患”(36)施闰章:《与曹太守言紫阳书院事》,《学余堂文集》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3册,第346页。,这成为明代在紫阳山创立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紫阳山和朱松、朱熹父子的历史渊源,在紫阳山建立书院的呼声不断。正德十四年(1519),在徽州知府张芹的主持下,在紫阳山新创紫阳书院。张芹认为:“朱子父献靖公爱其山而乐之,文公在闽犹筑紫阳书堂,而院不于山,名不称实。”(37)《紫阳书院志》卷1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59页。他将朱松、朱熹与紫阳山的关系作为紫阳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主张紫阳书院应当建在紫阳山,否则名不副实。
明代中期,紫阳山的道教形象虽远不如儒学形象突出,但当时山中紫阳观仍然较为兴盛,其凭虚阁内供奉朱松、朱熹之像,专设道士主持祭祀事宜。这种儒道混杂的情况,引起部分士人不满。胡缵宗专门就此致书张芹,郑重表达异议:“紫阳山以韦斋祀于其上,是矣。但在道家宫墙之内,而又以朱子斜坐之,于鄙见尤未安也。于书院之从祀者,详考而改正之;于道家宫墙,区别而改作之,是有望于执事也。”(38)胡缵宗:《与张文林太守》,《鸟鼠山人小集》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72页。张芹接信后十分重视,他本人对儒道混杂之情形也极为不满,决定采纳胡缵宗的建议。张芹打算直接将道观改为书院,既节省人力物力,又可打击道教,改变紫阳山儒道混杂的局面,维护儒学形象。但当时紫阳观势力兴盛,处置不当,恐生事端。他向南直隶提学御史林有孚提出该项建议,得其全力支持后,正式采取措施。《紫阳书院志》载录其事:
山故有老子宫,肖献靖公及文公像。公以位置不称,锐志改创,遂易老子宫为堂,以祀文公。而配享诸儒,则自勉斋以下皆如熊公制。旁为两斋,曰求志,曰怀德,以居学徒。其后高十余武,中为文会堂,号舍鳞列其下,周缭以垣。后即凭虚阁故址,为重屋,以祀献靖公。树崇正、仰高二坊,于从入之途。先上其议于督学御史林公,以吉报曰:“兹山兹院,名斯称,神斯妥。”盖至是始为紫阳山书院矣。(39)《紫阳书院志》卷2,《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7页。
文中所说“熊公”,是指徽州知府熊桂。正德七年(1512),熊桂将歙县县学后寺庙撤除,并把徽州城内的紫阳书院迁至其址。张芹撤除道观、改建书院之举,与此异曲同工,或许也曾受到熊桂做法的启发。在紫阳山创立书院后,张芹广受赞誉。其后紫阳书院设卫道斋,将张芹列为祭祀对象。《紫阳书院志》又载,经过张芹废道观、建书院,“正学昌明,异端屏迹”(40)《紫阳书院志》卷1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59页。,似乎紫阳观就此消失了。事实绝非如此,紫阳观虽受打击,却依旧屹立在紫阳山上。同是该志,另一处记载却说:“书院之建于紫阳山,自明世宗时太守张公芹始。其地基与黄冠为邻,此疆彼界,版籍未可淆也。”(41)《紫阳书院志》卷17,《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94页。按,此处所说书院创立于明世宗时显然有误,应为明武宗时。书院创立后,地址与道观相邻,显然紫阳观仍然存在。为了强调版籍,《紫阳书院志》专辟“院基”一栏,记载书院各建筑物的地块字号、四至(42)《紫阳书院志》卷17,《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94~595页。。该志纂修者特意强调紫阳书院与紫阳观的“此疆彼界”,既是保护院产的一种手段,更是对紫阳观存在事实的无奈认可。由此也可推论,由于紫阳观势力过大,张芹在改道观为书院的过程中,仅将部分道观产业变为书院,并未彻底拆毁紫阳观。直至明末清初,歙县生员许楚至紫阳山寻访许宣平遗迹,仍赴紫阳观游览。
紫阳山创立书院后,在历任徽州知府、歙县知县的主导下,不断采取措施保护院产,增添书院人文景观,使书院规模逐渐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嘉靖末年,何东序任徽州知府,选拔六邑之士70人入紫阳书院肄业,自文会堂至斋房皆次第修新。为保护院产,他下令稽查书院田籍,“悉钩其实,勒石于郡治堂左,以防隐没”。明末歙县知县张涛,亲登紫阳山,下令修葺书院,数月而成。他认为朱松不阿附秦桧,“启佑道统,而紫阳坊表不一及之”(43)《紫阳书院志》卷1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59页、560页。,实属缺典,下令拆除仰高、崇正二坊,修建新的三益贻谋、孤忠守道、父子真儒三坊,将朱松、朱熹父子形象与书院人文景观有机结合,扩大书院影响力。康熙六年(1667),曹鼎望任徽州知府,建邹鲁渊源坊于书院门外,从而增强了紫阳山儒学圣地的形象。
紫阳书院的创立,是官方意识主导下的儒学与道教在紫阳山争夺生存空间的结果。此后,紫阳观也曾试图进行反击,为道教争夺生存空间,并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凭虚阁移三清像”事件。
顺治七年(1650),徽州知府祖建衡大修紫阳书院,并在书院中段空处重建凭虚阁。凭虚阁原为紫阳观所有,后被征用,改归紫阳书院。祖建衡重建凭虚阁,为道教重夺生存空间提供了契机。道纪方承奇以书院临近紫阳观为由,将三清神像移入凭虚阁,供奉道教尊神。顺治十一年四月,朱熹十五世孙、婺源县生员朱烈赴紫阳书院谒祖,见到书院凭虚阁供奉三清像之况,极为愤慨。当时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孙登第按临徽州,朱烈绕过徽州府直接向孙登第具呈,说“书院为斯文而设,异端虚无之教久已摈绝,岂容溷杂宫墙”,要求“敕府廉查详复,崇儒培道”。孙登第批令署理徽州知府张惟养查实处理。张惟养详细调查后,令方承奇将三清像移出书院凭虚阁,并于五月初十日把调查详情和处理方式向孙登第呈报。五月十八日,在孙登第支持下,张惟养将这次事件的最后处理意见立帖存照:“仰本生遵照批文事理,一应紫阳书院春秋祭祀,原置山田基址,前后祠宇、中间凭虚阁等项,并听本生永远看守,督理修葺,以崇世典。嗣后如有混杂侵占情弊,许据实呈府,以凭严究,解院道正法,决不轻贷。”紫阳书院所有山田基址、祭祀事宜,均归朱烈督理。朱烈对此极为满意,赞颂孙登第、张惟养“崇儒卫道,攘斥异端”之功(44)《紫阳书院志》卷1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73~574页。朱烈本人将此次事件始末记录成文字,为揭开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线索。崇祯六年(1633),徽州知府陆锡明等大修紫阳书院,并捐置“资”字等号田塘16亩,永为书院司香之费,而“司启闭、任扫除,则遴黄冠之勤者”(陆锡明:《重建紫阳书院记》,《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17页),由道纪方承奇负责看守事宜。崇祯九年,方承奇开始垂涎书院田亩,“嘱族人方良堂呈代看守”。此后,紫阳书院田亩在事实上逐渐归方承奇所有。而经过“凭虚阁移三清像”事件后,紫阳书院所有田产皆归朱烈督理。由此可见,“凭虚阁移三清像”事件不仅是人文景观的属性问题,更是十分现实的利益之争。。
康熙四十年(1701),为彻底清除紫阳书院中的道教因素,避免紫阳观势力再次乘虚而入,徽州士绅对书院作了一系列调整,特别是对其中的人文景观进行改造。
撤塑像,易木主。紫阳书院供奉有朱松、朱熹等人塑像,以为祭祀。设像祭祀,与佛道无异,昔日方承奇将紫阳观三清像移入书院凭虚阁供奉,便是以此为由。大修书院之时,徽州士绅公议撤除塑像、改易木主。此议由吴苑之子吴瞻泰首先提出,施璜、汪芹、吴曰慎等人力主。吴曰慎还专门撰写《易木主说》,指出撤像易主的必要性(45)吴曰慎:《易木主说》,《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33页。。在徽州士绅的呼吁下,地方衙门表示同意。紫阳书院举行撤像易主设祭仪式,徽州名望皆赴紫阳山与会。施璜作《撤像易木主告文》,当众宣读,以告朱熹在天之灵(46)施璜:《撤像易木主告文》,《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30页。。
撤除凭虚阁,改建道原堂。紫阳书院中的凭虚阁,为顺治七年徽州知府祖建衡重建。吴曰慎指出:“中有凭虚阁,所以游目览胜,舒幽怀而寄清旷也。然其名近于二氏,非儒者之义。”(47)吴曰慎:《道原堂记》,《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21页。徽州士绅公议撤除凭虚阁,改建道原堂,消除道教影响。
调整人文景观布局,增强其与朱熹的关系。书院大堂祭祀朱熹,献靖公祠祭祀朱松,二者中间为凭虚阁,彼此皆有门户,各不相属,不利于平时管理。修葺书院时,徽州士绅将三者打通,使其前后联络、彼此相连,增强人文景观的一体感,便于有效管理,并防止道教势力暗中渗透。徽州士绅在大修书院之时,有意增强人文景观与朱熹的关系,从而对抗道教影响,消除道教痕迹。这方面最明显的举措,莫过于在献靖公祠悬挂“旧时山月”匾额。此匾系临摹朱熹之字制作而成,以符合朱熹在紫阳山的事迹。
经过徽州士绅的塑造,紫阳书院中的道教因素被彻底铲除,儒学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也促使紫阳山的儒学圣地形象更加彰显。
四、皇权加持与紫阳山儒学圣地形象塑造的完成
北宋皇帝敕令创立紫阳观并钦赐观额,肯定了道教在紫阳山的合法性。尽管在儒学人士的竭力塑造下,紫阳山的儒学形象远远盖过道教形象,但是作为儒学标志的紫阳书院始终未曾获得来自皇权的加持(48)淳祐六年,徽州知州韩补奏建书院于城南,宋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四字榜其门,始名紫阳书院。该书院不在紫阳山,和本文所说紫阳山上的紫阳书院并非同一书院。。在这种情况下,请颁宸翰就成为徽州官绅在紫阳山儒学形象中注入皇权因素的必要途径。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二十九日,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徽州歙县人吴苑具呈题本,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为紫阳书院请颁御书匾额:
宋儒周敦颐等,俱蒙御书“学达性天”之匾,悬挂各书院。臣按,朱熹系臣徽州府人,少年读书府城外紫阳山。宋淳祐间,郡守为建紫阳书院,宋理宗书额赐之,载在《一统志》,可考。朱熹别号紫阳,实因此山为名。今桥曰紫阳桥,城门曰紫阳门,地因人重也。后入闽建书堂,仍曰紫阳书堂,示不忘本也。今御书赐婺源文公阙里,而徽郡紫阳书院未蒙颁赐,臣请令五经博士朱坤,敬摹送徽州府,令知府制匾,悬挂紫阳书院,则先贤遗迹,咸有光矣。(49)《紫阳书院志》卷1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70~571页。
吴苑所题,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朱熹少年读书紫阳山显然有误,是将朱松事迹嫁接在朱熹身上。精通经史的吴苑当不会犯下如此错误,或许是有意将朱松、朱熹父子的事迹糅杂在一起,加强紫阳书院与朱熹的历史联系,提高紫阳书院的地位,以便得到皇帝的批准。六月初三日,康熙帝命礼部议奏此事。六月十二日,礼部认为紫阳书院离婺源文公阙里不远,“俟命卜之日,臣部行文该抚,转令徽州府知府照式敬摹,制匾悬挂紫阳书院”(50)《紫阳书院志》卷1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71页。。十四日,康熙帝正式批准礼部题本。
安徽巡抚高承爵接到礼部咨文后,檄行徽州府遵照办理。徽州知府朱廷梅寻觅精工好手,将婺源县文公阙里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照式敬摹,制成匾额。九月十六日,朱廷梅率同文武僚属、乡耆、五经博士朱坤等人,至紫阳书院悬挂宸翰。徽州父老子弟观者如堵,场面十分壮观。值得注意的是,高承爵在歌颂皇帝的题本中,同样沿用吴苑糅杂朱松、朱熹事迹的说法:“朱文公熹婺源阙里,已奉御书,颁之匾额。更以紫阳为诵读之地,岂宸翰有弗及之施?特允监臣,命之摹挂,诚旷古仅见之隆施。”(51)《紫阳书院志》卷1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72页。如此种种,皆为强化紫阳书院的儒学渊源,抬高紫阳书院的历史地位。吴苑费尽心力,题请宸翰,引起世人对紫阳书院的关注与重视,提升了紫阳书院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对其发展历程起了重要作用,“一时学道之士,鼓励奋兴”(52)《紫阳书院志》卷12,《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64页。。乾隆九年(1744),经工科给事中吴炜奏请,乾隆帝御书“道脉薪传”匾额,颁赐紫阳书院(53)《署理安徽巡抚准泰为报奉到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日期事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乾隆朝书院档案(上)》,《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
在康熙、乾隆二帝宸翰的笼罩下,紫阳书院得到更加强有力的护佑,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仅以其经费为例,乾隆十六年歙县捐纳同知徐士修独自捐银12000两,解交府库,发典生息,以供膏火之用(54)“江南司移为查明江宁钟山书院及徽州紫阳书院生息银两事”,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0702—041。。获颁宸翰的紫阳书院更受社会重视,经费也更加充裕。无论是“学达性天”匾额,还是“道脉薪传”匾额,都在皇权的荣耀下强化紫阳书院和朱熹的历史联系。在皇权的加持下,紫阳山的儒学形象达到巅峰。紫阳山作为儒学圣地的形象塑造至此彻底完成,其道教仙山的形象逐渐湮灭。
五、“紫阳记忆”的生成及作用
因为与朱熹的历史渊源,紫阳山不断被歌颂、美化,名气显扬天下。朱熹别号紫阳,实因此山而来。清代名臣张伯行就对此指出:“夫朱子之以紫阳称者,其先世韦斋先生以新安婺源人,读书于郡城南紫阳山,后官于闽,以‘紫阳书堂’刻为印章。文公居崇安潭溪,复以榜于厅事。两世不忘紫阳,此‘紫阳朱子’之名所由来也。”(55)张伯行:《〈紫阳书院志〉序》,《紫阳书院志》卷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45页。在紫阳山和紫阳夫子朱熹的影响下,人山合一的巨大文化影响力迅速彰显。
自朱熹赴紫阳山开始,关于朱熹的历史记忆,深深地植根于紫阳山,并日渐强化,这种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紫阳记忆”。“紫阳记忆”无处不在,徽州历史上的紫阳坊、紫阳门、紫阳桥,皆是其在徽州文化中留下的印记。
南宋时期,因“紫阳记忆”生成,紫阳山成为儒学圣地,被大批文人学士所歌咏。南宋文豪杨万里过新安江,望见紫阳山,作《晓过新安江望紫阳山怀朱元晦》:“紫阳山下紫阳翁,今住闽山第几峰。退院归来还行脚,被他强占一江风。”(56)杨万里:《诚斋集》卷3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0册,第371~372页。作为朱熹同时代人,杨万里所作之诗反映出紫阳山在当时就已深深烙上朱熹的印记,成为儒家文化名山。稍晚于杨万里,徽州知州韩补作《紫阳山赋》,其中有:“承嘉命以宅牧,实歙州之故封。览山川之明秀,怀典刑乎晦翁……繄先正之阙里,俨紫阳之孤峰。”(57)陈元龙编:《御定历代赋汇》卷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9册,第481页。该赋将朱熹与紫阳山并提,显示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宋末元初,方回总结紫阳山与朱熹关系:“紫阳山去古歙郡之南门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讲赠太师徽国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与人,称曰‘紫阳夫子’,若洙泗先圣然。”(58)方回:《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桐江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322册,第398页。可见“紫阳记忆”对紫阳山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影响之深。
明清时期,这方面的例子更是层出不穷。明代中叶,程敏政指出:“紫阳山在新安城南歙溪上,以朱子益名于天下。凡礼送行者,必载酒其麓,览观胜迹,上怀古人,足以脱尘氛、振遗响,发志士之气。”(59)程敏政:《紫阳纪别诗序》,《篁墩文集》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516页。与程敏政同时代的徽州人张旭说:“一山高出万山阳,北望尼丘去路长。天遣考亭开拓后,至今草木亦增光。”(60)张旭:《紫阳山》,《梅岩小稿》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44页。清初名臣吴苑也说:“紫阳山继尼山出,讲坛间世动天阙。徽国肇基始吏部,授学龟山探月窟……笃生文公续绝学,濂洛真儒此其匹。”(61)吴苑:《北黟山人诗》卷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82页。按,《四库禁毁书丛刊》将该书之名写为《北黔山人诗》,但书中皆作《北黟山人诗》。此外,书前录有潘耒所作序文,其中说:“黄山,古名黟山,高大甲江表,纯石而多峰,刚棱而不媚,吴子名其集曰‘北黟’,殆取以自况乎。”此序也可证书名当为《北黟山人诗》,而非《北黔山人诗》。《四库禁毁书丛刊》所写该书名称有误,笔者径改。程瑞祊谒紫阳书院,留下诗句:“宣平未著千秋业,徽国宜升上哲班。七闽便争争不得,一支封在紫阳山。”(62)程瑞祊:《谒紫阳书院》,《槐江诗钞》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6页。沈德潜赴紫阳山后,也指出朱熹和紫阳山的关系:“昔年子朱子,读书紫阳峰……至今小山名,仰止如华嵩。”(63)沈德潜:《紫阳山谒朱子祠》,《归愚诗钞》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第301页。
约自元代开始,紫阳山为朱熹“读书处”“讲学处”“居住处”的记载,大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对于真实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些文献记载显然是有所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其根源就是“紫阳记忆”。紫阳山因朱熹而名扬海内,后人知紫阳山多因朱熹,便将朱熹的许多事迹和其父朱松之事相杂糅,共同置于紫阳山上。随着时间推移,朱松在紫阳山的事迹稍趋淡化,朱熹在此山之事反而愈加彰显,甚至多有虚造。由于儒学之士掌握着话语权,关于紫阳山文化形象的书写方式中,儒学形象最为突出。汪舜民曾对此指出:“紫阳,古犹今也,得宣平而名始显于一乡,得韦斋而名始显于他郡,得晦庵而名遂显于天下后世。”(64)汪舜民:《紫阳观凭虚阁记》,《静轩先生文集》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第98页。朱熹和“紫阳记忆”对紫阳山名气的深远影响,于此也可见一斑。
在“紫阳记忆”的作用下,紫阳山的名气迅速扩大,成为可与各地名山大山相提并论的一座徽州名山。紫阳山高虽然有限,但徽州人却将其视为名山、大山、高山,可与武夷山、泰山并称。明代正德年间状元唐皋说:“徽紫阳,建武夷,皆名山也。紫阳之有书院,武夷之有精舍,同一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也。”(65)唐皋:《紫阳书院记》,《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11页。万历年间,歙县人洪文衡说:“新安峙万山中,群秀环拱,亘若天城。乃海内独重紫阳,几与泰岱埒。夫非以韦斋先生暨徽国文公,讲业其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地固以人重与?”(66)洪文衡:《重修紫阳书院碑记》,《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13页。明代官员和文人在提及紫阳山时,往往将其与黄山并列,被誉为“徽郡第一循良”的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在《重修紫阳书院题辞》中说:“黄海郁奇,紫阳峙望,遂使歙婺顿成邹鲁。”(67)傅岩:《歙纪》卷4,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40页。
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的形象愈益高大。宋末元初,钱塘人仇远叹服紫阳山的巍峨:“峨峨紫阳山,翼翼素王宫。中藏朱子书,颇有邹鲁风。”(68)仇远:《送杨志行赴徽州教授》,《金渊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4页。元明之际,云间人邵亨贞诗中也有“峨峨紫阳山,高广出奇观”之句(69)邵亨贞:《上武阳太守汪公国良》,《蚁术诗选》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602页。。至明中期,程敏政所作诗歌中,有诸如“巍巍紫阳山”的描述(70)程敏政:《送翰林庶吉士许启衷南归》,《篁墩文集》卷9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722页。,以示紫阳山的崇高壮观。许国更是赞颂紫阳山之高:“紫阳山高齐际天,英才辈出理固然。”(71)许国:《瑞莲歌》,《许文穆公集》卷6,《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08页。明末清初,歙县人胡渊说:“孔子陬邑生而钟自鲁,在鲁登东山。朱子尤溪生而钟自新安,在新安登紫阳山。紫阳者,乡先生祝公题其楼之名也。是山在新安,居中最高。朝阳初升,紫光凝聚,光烛是山,而后众山沐其光昭焉,因又名其山也。”(72)胡渊:《紫阳书院会讲序》,《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639页。经过徽州文人有意识的塑造,紫阳山成为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高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仍然离不开“紫阳记忆”的影响。
六、结 语
徽州紫阳山的人文景观,可以分作道教和儒学两类。前者以紫阳观及其前身许真君祠为代表,后者以紫阳书院及其文化源头紫阳书堂为典型,二者并存山中,成为紫阳山两种文化形象在人文景观上的鲜明体现。但这两种人文景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紫阳山道教空间的萎缩和儒学空间的扩张。
从元代张可久提出新安八景之说,到明初唐文凤重新品评新安八景,“南山秋色”和“紫阳书声”演变为“紫阳夜读”,紫阳山的道教形象渐趋弱化,儒学形象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至清代康熙年间,歙县人吴逸选录歙县境内著名山川景物,绘制成《古歙山川图》24幅,其中就有紫阳山。在图中,紫阳观已消失不见,紫阳书院、祝确墓、紫阳桥占据全图最为突出的位置(73)吴逸绘:《古歙山川图》,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雍正三年(1725)刊刻的《紫阳书院志》,录有紫阳山图,图中最为显眼的人文景观也是紫阳书院、祝确墓和紫阳桥(74)《紫阳书院志》卷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51~452页。。可见,经过地方士人有意识的长期塑造,儒学成为紫阳山最主要的文化形象。雍正元年秋天,时任礼部尚书张伯行应邀为《紫阳书院志》所作序文说:“黄山、白岳虽称灵秀,而嗜二氏之学者多托而栖焉。紫阳近逼两峰,而灵秀特异,恒不溺于其俗,士之惇崇正学者,延绵不绝,此有以知朱子之遗教未泯也。”(75)张伯行:《〈紫阳书院志〉序》,《紫阳书院志》卷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445页。在河南仪封人张伯行看来,佛教、道教之人多栖身黄山、白岳,使其佛、道之学兴盛,成为宗教名山,而紫阳山灵秀特异,虽然离黄山、白岳不远,但从未沾染其俗。从外地人对紫阳山的文化印象也可看出,徽州士人对紫阳山文化形象的塑造可以说相当成功。至乾隆时期,在清朝皇权的加持下,紫阳山作为儒学圣地的形象塑造彻底完成,其道教仙山的形象逐渐湮灭。
徽州山水出众,在历史上早已被认可,“大好山水”“山水幽奇”等皆是历史文献中形容徽州山水之胜的词语。地处万山之中的徽州,名山大山尤多,紫阳山的自然风光并不出奇,而它之所以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人文景观和人文历史为其共同铸就的崇高文化形象。在徽州士人的塑造下,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的形象愈益高大,竟被视作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与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根源在于“紫阳记忆”。
关于紫阳夫子朱熹的历史记忆在紫阳山日益彰显,并同紫阳山融为一体,演化成“紫阳记忆”。“紫阳记忆”生成于朱熹游览紫阳山之时,历宋、元、明、清诸朝而日渐强化,在地点上由紫阳山扩散至徽州乃至全国。徽州各处以“紫阳”命名的地方,全国各地以“紫阳”为名的书院,几乎都和“紫阳记忆”密切相关,离不开“紫阳记忆”的影响。紫阳山不止一处,而“紫阳记忆”的生成地则是徽州紫阳山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紫阳山的最重要特点。
在紫阳山名声日隆之时,其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愈加突出,再加上“紫阳记忆”的作用,使紫阳山成为徽州的象征,“紫阳”一词也成为徽州的别称。至少从南宋后期开始,每当提及徽州山水之时,紫阳往往成为徽州的别称。南宋徽州人方岳在《答赵倅》中说“恐紫阳山水未足久稽天下士也”(76)方岳:《秋崖集》卷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479页。;明初人孙杰赠诗朱同,有“紫阳山水盘蜿蜒,紫阳之裔人中仙”之句(77)朱同:《覆瓿集》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第726页。;程敏政在《送许国用南归》诗前说:“许君国用自钱塘来新安,尝从于紫阳山水间,甚乐。”(78)程敏政:《篁墩文集》卷7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541页。这些事例中所说的紫阳山水,皆指徽州山水。而在编纂徽州文献时,紫阳更成为具有文雅之气的徽州别称。南宋徽州人潘岩肖搜罗徽州名士之文,编纂成《紫阳名公文海天琛》一书,书名里的“紫阳”即指徽州。明代休宁人程曈编著《紫阳风雅》,专记徽州相关人物,而书名中的“紫阳”也指徽州。更有甚者,宋末元初人邓文原在为徽州人程逢午撰写的墓志铭中说“紫阳,朱先生之乡”(79)程曈辑撰:《新安学系录》卷10,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05页。,竟直接以紫阳代指徽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紫阳作为徽州的别称,可以说是得到时人广泛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