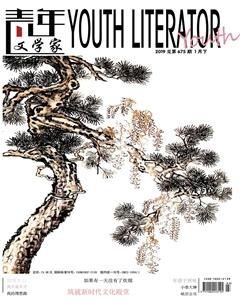徐訏小说浪漫主义问题研究
2019-03-13蒲敏
摘 要:徐訏的新浪漫主义小说继承了相对早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因为现代性的融入、充满细节的叙事等特征而具有了新的面貌与风格,在《鬼恋》中,他以具有现代性的人物形象,以及细节与现实的融入,在浪漫传奇中融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成分,使自身的浪漫主义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关键词:新浪漫主义;现代性;《鬼恋》
作者简介:蒲敏(1991.7-),女,汉,四川省南充市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打工诗歌和打工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自其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日暮之时”[1](p254)蜚声文坛起,便成为我们讨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无法绕开的存在。五四以后、建国以前的中国向来不乏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的狂放躁动,郁达夫的悲郁暴露,都足以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徐訏却以自己具有独特个性的浪漫主义,成为一个区别于文坛前辈的特殊存在,对于他的小说创作,评论家们更倾向于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词,用以概括他作品中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粘连与融合。
一、继承传统
徐訏的新浪漫主义无疑是继承了相对早期浪漫主义的传统的,与早前的浪漫主义作品相似,他的作品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注重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的心理体验。他曾说:“我作的心理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情感上憎厌、悯怜、爱恨、愤怒、焦虑、忧愁、苦闷都是内心生活。”这种“自我表现”式的心理刻画,使徐訏的小说与其它浪漫主义作品一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与浓烈的情感氛围。同时,作为传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的“理想化”,在徐訏的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他常常在作品中构造近乎完美的女性人物,设置唯美而富有神秘感的场景,并安排一场奇幻浪漫的邂逅。徐訏曾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但是在工作与生活上,我能有的并不能如我所想有的。”[2]现实生活是缺憾与不完满的,同时也从反面推动了作者将自己的“理想与梦”投射到艺术作品当中,“从人性中提炼真的、善的、美的成分,让它们在适当的作品中表现出来”[2],以“在空幻的梦想中”“填补生命的残缺”。因此,徐訏笔下的女性多是近乎完美的,如《鬼恋》中的“鬼”、《阿拉伯海的女神》中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海兰, 她们美艳绝伦、博学广才,或纯真或神秘,并且都心地善良,被成为了真善美结合的典范。这使得“他小说中大部分女性人物一看便知纯属虚构……每一个都可以打上某种极致美好的标签,视作某种理想化的呈现。”[3](p60)这种“理想化”便是对传统浪漫主义的一种继承。
二、新的突破
徐訏的小说继承了早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因为现代性的融入、充满细节的叙事等特征而具有了新的面貌与风格。
1.具有现代性的人物形象
徐訏曾留学法国,并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对西方康德、伯格森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行為主义分析学等都有较高的兴趣,这一背景使他的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叙事手法都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徐訏小说创作重要开端的《鬼恋》,便是三十年代在巴黎求学期间创作的。
小说写“我”在一个夜晚,于上海南京路上邂逅一名“有一百三十分的美”的神秘黑衣女子,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严肃而敏利”,她美丽异常,在“我”眼中甚至“有几分仙气”,却又坚决自称为“鬼”。“我”一直对她“鬼”的身份心存怀疑并互相探讨许多“于己无关”的科学和哲学,发现她极富智慧与学识,随后“我”不可自抑地倾慕于她,她却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表白,一再对以“人鬼殊途”。“我”只好黯然消沉,开始在凡庸的都市里追寻刺激,到最后终于决定“将我心底的情爱升华成荒谬的友谊”之时,她却突然离开。当“我”两个月后在一座寺庙里再次遇到她,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世:她曾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暗杀过许多人,坐过牢,也曾亡命国外,最后感到自己“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便决心把自己当作鬼,游离于世外,“冷观这人世的变化”。可是“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她,还是坚持要她做“我”的爱人。于是她选择在“我”病愈之后,彻底地离开,只给“我”留下无尽的忧伤和怀念。
中国自古就不缺少“人鬼相恋”的故事,也同样具有浪漫传奇色彩,而徐訏《鬼恋》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哲理性与象征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严重的性压抑之下,社会中下层的才子们往往通过“人鬼相恋”的传说,来寄托心理与生理上的寂寞,倾注些“红袖添香”的愿望。因此传统小说中的女鬼形象,往往容貌绝艳,知书达理,善解人意,还很喜欢自荐枕席,并且总是心心念念地想要做人,想要“长伴君侧”,真可谓“身是阴间的身,却有一颗阳间的心”[4](p57)。这一类旧式浪漫小说,在徐訏眼里,是“格局既狭,而情操低卑,爱之结果,也只是讨来做姨太太,上侍翁姑下奉元配而已”[5](p298)与此相反,徐訏笔下这个“超人世的,没有烟火气”的,“动的时候有仙一般的活跃与飘逸,静的时候有佛一般的庄严”的女“鬼”,生而为人却心甘情愿要做“鬼”,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人事都已厌倦的生存”。她曾经是最入世的人,却在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之后,感到“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6]因此发出“我要做鬼,做鬼”的誓愿。小说中的“鬼”对人世的失望与淡漠,已达到极端程度,在极度悲观中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鬼”的处境和选择,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折射与隐喻。徐訏通过夸张和传奇的手法,对这种失望、厌倦进行了极端的处理。《鬼恋》中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手法,使其不同于传统爱情浪漫小说,而成为具有现代性哲理的新浪漫主义小说。
2.细节与现实的融入
浪漫主义的作品“往往醉心于奇人、奇事、奇境”[7],徐訏的作品无疑是浪漫的,他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方,总是在“海岛乌托邦、马赛小旅馆、异国大别墅”[3],在茫茫的阿拉伯海上,与一位美丽少女发生缠绵的恋情(《阿拉伯海的女神》),或是在孤岛上的“世外桃源”,经历曲折而神秘的故事(《荒谬的英法海峡》)或是在巴黎富商的法式庄园,经历纠结交错的邂逅(《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都是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常常使主人公“分不清真幻”、“时时醒来还觉在梦中”,但徐訏又热衷于在浪漫传奇中融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成分,通过许多的细节描写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小说的情节似乎都是“虚构的谎言”,而他擅长在小说里添加“谎言中的细节”,使它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例如他的开场:
有一天,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Era,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欢,于是就送我两匣。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我们大家喝了点酒,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闲谈,直到三更时分方才分手。[6]
开场虽是作为为偶遇创造契机的一个存在,却是那般“琐碎的、温和的、如家常般的叙述语调”,就如同我们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和身边一个朋友的交往那样真实、平凡。以这样家常的开端,谁又会想到接下来会是一段奇幻的邂逅呢。接下来,在“我”与“鬼”的相遇中,作者“极认真”地交代了“南京路”、“斜土路”、“霞飞路”等地名,曾有研究者注意到:“画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鬼恋》故事的街道图”“将之与现今的上海街道图对照,竟然大致吻合”[8]。徐訏小说的细节,除了体现在物名、地名、房间布置的細心叙述上,还体现在对人物感情与心理活动与环境的真实刻画上,在描述“我”对“鬼”的无望的思念时,他写道:
但我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在湖边山顶静悄悄旅店中,我为她消瘦为她老,为她我失眠到天明,听悠悠的鸡啼,寥远的犬吠,附近的渔舟在小河里滑过,看星星在天河中零落,月儿在树梢上逝去,于是白云在天空中掀起,红霞在山峰间涌出……[6]
因为极度的思念,导致时间在感觉中发生变形,变得尤其缓慢起来,但在这缓慢的“失眠到天明”中所体验的每一道风景,从鸡鸣到星星的零落,从月儿逝去到红霞涌出,无不在淡淡的寂寥哀伤的氛围中透出日常的气息来。徐訏认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依照假想的逻辑,构造形象,以表现作者的理想与希望”[9],并通过浪漫故事的编织,对现实人生进行“自我疗伤”[10](p84)。
当然,徐訏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局限,从《鬼恋》之后便基本囿于奇幻爱情或是奇遇的写作,虽然兼顾了小说的文学性与易读性,使其在三四十年代得以一次次成为畅销的通俗读物,但是终归会限制作品的路数与格局,难以进行更具有创造性的改变。
三、结语
“现代主义就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11](p167)《鬼恋》中超越于一般奇情奇恋的哲学构思与人生思考,是徐訏对自身孤独生活的填补,他曾在《一家》的后记中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正是徐訏在奇情奇恋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融入了现实主义的成分,并表达不同于普通恋爱小说的人生哲思,才使他的小说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与更高的哲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朱曦,陈兴芜.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模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2]徐訏.风萧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袁坚.徐訏小说的细节与情调[J].书城2009年第3期.
[4]严明.文言小说人鬼恋故事基本模式的成因探索[J].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5]徐訏.两性问题与文学[C].徐訏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6]徐訏.鬼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7]茅盾.夜读偶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
[8]王璞.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訏小说研究[M].香港:香港里波出版社.2003.
[9]徐訏.徐訏给朱光潜的信[A].王一心.30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交往[C].新文化史料[J].2000.
[10]葛俊侠.论徐訏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3卷第1期.
[1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陕西:筛析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法言语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