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逼婚残疾青年的爱与梦
2019-03-12杨楠
杨楠

冲突升级。距离2019年除夕还有一周,何健决意离家。
他与父亲恶言相向,回了大姐一个巴掌,再用拐杖击向大姐的小腿。
导火索是结婚问题。半岁时,镇上暴发小儿麻痹症,何健没打上疫苗,右腿落下残疾。母亲在年前为他寻得一个姑娘,以11万彩礼为条件。早前有过两次介绍,一个是癫疯病人,一个是二婚。这是头一个健康女孩,何健怒斥母亲 “买卖妇女”。
沖突过后,何健宣布与家人断绝关系,跑到火车站旁的小旅馆,独自度过春节。出走时,除了几件衣物,只带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何健随后在豆瓣网成为热门话题“春节自救指南”中最热门的文章,甚至有自媒体平台向他约稿。
写作是梦想也是温室。何健喜爱文学,他高兴自己写的东西终于有人看了,又不甘心写些自己的故事才有人看。
他有过两段脆弱的感情,经不起细究,无疾而终。他不接受家人安排的婚恋,因为“对爱情还有向往”。作家史铁生将残疾与爱情比作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而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肢体的残缺,造就了何健的敏感与自卑。
“自卑,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爱的期盼,与怨愤的积累。”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爱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何健向往爱情,渴望走出躯体的囚禁,走向别人,盼望生命在那儿得到回应。而三十年来,何健的家人则怀着愧疚,小心翼翼地期盼着未来。
春节期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何健及其家人,试图记录残疾人婚恋世界中的一缕褶皱与微光。
一个残疾人被逼婚的始末
如果我爸只是敲门,我会打开。但敲门的同时他说:你妈买到一个云南女孩了,你快出来,女孩好手好脚,你同意就可以带过来了。
听到这话感觉自己像是海里的金枪鱼,一下子被捕鱼的人插穿。我死了,更想死,可是我又没死,只能装死。
我爸让我出去和那云南女孩视频,同意的话就买下来。他用“买”。我只好躺在床上继续装死。我姐从她午休的房间里出来:你出来先看看吧,不同意可以拒绝啊。爸妈都是为了你好,妈听说XX地方有女孩子,一大早带着大娘包车去给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对得起她吗?
这是我妈找来的第二个女孩了。离鸡年还有几天时,爷爷去世了,之后我内心世界空缺了一大半,心里开始松动,于是被安排了一次相亲(其实只是见女孩父母)。女孩刚满20岁,有精神疾病。我看到她坐在阳台上,一整天都在照镜子。
说服自己的时候,在想:娶了她吧,如果她嫁给别人估计病会加重,会被家暴,会被嫌弃,精神压力更大。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如果有了孩子怎么办?一个残疾父亲外加一个精神失常的母亲。孩子生病了怎么办?我能背着抱着他去医院吗?他的同学们是不是会欺负他有一个不正常的家庭?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要与孩子同学的父母去理论吗?我会在理论的过程里,被孩子同学父母侮辱吗?
还有介绍过一个二婚的,就在这次前十天左右。她让我发一张照片过去,我就故意发了一张全身的照片,拄着拐杖。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残疾。她说那算了,不要谈了。
那这次呢?如果我说不同意,他们会生气:人家好好的女孩,怎么配不上你,你别太自以为是。我说,不能买卖妇女;他们说怎么就是买卖妇女了,他们家穷,没办法才这样。结婚都要交聘礼的,他们那地方的男的交不起聘礼,我们给得起,人家女孩愿意,不是好事一桩吗?
我姐在门口骂我,没有同情心,不体谅父母,不孝,我打开门,骂她无知,没人性。她打了我一巴掌,我反打了她一巴掌。她拿手机砸我头并推倒了我,我拿拐杖重重地打了两下她的小腿。我后悔打她的第二下,但不后悔打她的第一下,这样她才对我彻底失望,不会再管这件事。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至少在除了这件事上,很多方面都在为我着想,为我担忧。
我爸敲门,说要杀了我,被我姐拦住,我姐也担心冲突进一步升级。我知道他不会杀我,但我会杀他。2016年也是因为成不成家的事,他把我揍得鼻青脸肿,我拿着菜刀追砍他。
我爸说了,说我这个人很阴险,如果他现在打了我,指不定晚上我就拿刀杀他了。我听到这句话心灰意冷,想了想,算了,还是走吧,与这家人彻底脱离关系。我问朋友借了点钱,带了一个小的箱包,装了两三件外套和裤子,还有就是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离家的时候二姐正好回来了,拦着不让我走,还给我塞了900块钱。
我先在家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一晚上一百来块钱。二姐夫发微信喊我去过年,我马上就买了一张去宁德的票。但后来我二姐发微信让我别去,我就退票了。我又问了一个以前在网上认识的,广西防城港的女孩,都喜欢写作。我问她可不可以去她那边,她先说可以,后来说让我先去南宁待着。我听到这话,又把新买的火车票退了。之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也不知道去哪里,交了一个月的房租。
豆瓣上有个网友,知道我没吃年夜饭,只吃了饼干和面包,就给我发了个66.66元的红包。她一直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知道我没吃年夜饭之后好像比我还难受。
这几天都是每天只吃一顿饭,因为懒,哈哈,我对饿的忍耐力挺强的。我床头有薯片。不是没钱,我现在钱很充足。你看过《饥饿艺术家》吗?我在看这篇的时候,有一种灵魂震颤,好像那个人就是我,好像专门为我写的。去讨好观众,损害自己,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和他说,不要删掉我们
二姐夫喊何健来家中过年,其实是二姐的主意。可她没想到自己这个当姐姐的,说了何健两句,何健就退了车票,删了她微信。“我是后悔说了他几句,他一个人在外面,我们也舍不得他。”
离家后,何健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布与家人断绝关系:“本人与何建国一家正式脱离亲属关系,此后不认他为父,我也不是他儿。买卖妇女是有违法律,违背道德,丧失天良的行为。”随后,他陆续删除了家人的微信,期望自己能够独立。这不是他第一次删掉家人微信。
二姐不明白为什么何健为人和善,偏偏和家人合不来,“小时候他生病,爸爸三更半夜去借钱,带他到处看,他不能不记得爸爸的好。”大约有半程的采访,二姐都在哭,“记者朋友,你和他说,他恨得不想娶也没关系,他自己又不是不能养活自己。到时候实在不行老了,跟我们在一起也没事,不差他一个人吃的。”
何健的婚恋事宜一直由母亲操心,她几次回到老家请人物色结婚对象,找着她满意的才敢给何健说。她希望何健結婚。为了抱孙子,也为了她死后还有人照顾他。
我儿子脑袋是好,可是脚不争气,我们对他是很愧疚。我都是偷偷地回老家,别人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娘家去,不说去找媳妇。人家问怎么不找媳妇,我就讲不找、找不到。那有坏人啊会讲,你看她儿子到处看,还看不到一个合适的。脚不好还挑,叫你儿子不要挑了,你也不要挑了,生得了小孩就可以了。我哪里行了!小孩子大了我可以带,但是坐月子总要妈妈带的,太糟了的月子都带不了,那不行的。这趟回去,车票钱,人情世故,花了三千多块钱,做媒要给钱的。

一共带我儿子看了两个。前年上半年看的那个有癫疯病,人家是可以,他家里就叫我交17万彩礼,就是怕我儿子反悔,怕我儿子不要她,我就有点犹豫了。我交那么多钱,但是嘴巴是在人家身上,不好讲的。我也怕我儿子不同意。我想带她去我这里的医院看一下,看那女孩诊得好不。我想同意又怕同意,怕她如果懂事了,又不要我儿子了。我儿子大她七八岁。我看到她很穷,她妈妈是后妈,有一点刻薄,我想把家里的衣服给她的。不是旧衣服,都是八成新的,现在人都不要旧衣服。
我回老家还给他看了二婚的,二婚的都有一点骄傲的。这次也是邻居介绍的。女孩子是很远的地方的,亲戚介绍,也是叫我交13万。我在这里和我女儿一起开个网吧,(我们老家)那里好像觉得我很有钱,就是直接讲叫我拿一点钱,就是彩礼。好像是你拿彩礼,就可以直接带女孩过来。
这个女孩子是正常的,我去了就对我笑,端茶给我喝。我说这个还可以,就叫我儿子看了。我说不是买,买我不同意。女孩子跟我说娘家是哪里人,她跟我说那边很可怜,我儿子他不听,就讲我是买,我说你来看一下,视频一下了,女孩子也要看你的,又不是看了就是你老婆。你自己这脚不好,不要再挑三拣四,一个人总归娶一个老婆了,你又不是没条件。
以前很可怜,几个月就脚不好,三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出来打工。一直打工,打得就是挣了一点钱,盖了个房子,就是给他的,就盼着他……
他谈过的那两个女朋友,好是好,但不可能嫁过来的。又年轻,又漂亮。我们农村里,带回去的要不是老婆,名声不好。我儿子说没事。人家来这里就是想到你农村里来玩一下,看一下你这边的风景。第一个女孩子走的时候,我给她两百块钱。我问她了,我说你跟我儿子交朋友,女朋友吗?她说,阿姨,现在还不能,大家都朋友,普通朋友也可以。我说要做女朋友哎。她说以后吧。
我说你以后要跟我儿子走动,她说可以可以,我说以后过来玩一下,她说了可以,然后又是那样。回去了说要租房子,要我儿子打钱,我儿子没钱,又叫我拿了,又要买手机,叫我儿子买一个,六千多块钱的,我们也都拿了一点。
这哪里靠谱。她们又年轻,又是读书,又是城市里面的人,都是骗钱的。他那么几年都是被她们两个女孩子骗了。去年他又谈了新疆那里的,我说要是要钱的你就不要谈,家里去找一个。家里有钱可以找得到,找一个好点的。
我一生中就一个儿子,我们做父母的哪里不牵挂。我和他说,你娶了老婆,人家给你洗衣服煮一下饭,你走哪里,我都跟你一起去,我在那边,在你旁边打一点零工,再给你煮饭。你老婆就陪你,洗洗衣服,收收东西就可以了。我说我丢着店不开,我都跟你走。但他就是不听,干嘛对我这样的?
他说不娶老婆要写作,你要写作我陪你咯。前年在家里写作,我也是陪他,陪了三天又不肯我陪,要我出去。我说你一天三顿饭总要吃,胃不好,你没有命,那你写什么作啊。他喜欢看书,每一本书我都跟宝贝一样,柜子里我衣服都不装,都装他的书。他讲要那个书干嘛,我说要传宗接代的,你这个花了钱的,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一本,我放起来,你有小孩了,我就给我孙子看了。我说有孩子多好,以后你老了,你老婆管不了你,还有孩子管你多好。
我讲他一下,微信又删了,电话又删了。初六是他生日,我发红包给他也发不过去,电话也不接。本来我是想拿一千块去给他花,我知道他没有钱的。你问他,每一年他自己挣钱,也至少要花我几千块。我周围每一个人都说我宠坏掉了,我哪里宠坏了,哪里能叫宠?
记者朋友,你能同他联系上,你和他说,不要删掉我们。不要想太多了,(腿缺是)没办法的事,叫他不要恨我们。
她们都以爱情要挟过我
帖子在豆瓣网引起关注后,有自媒体平台向何健约稿,希望他将这个残疾人因被逼婚而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故事扩写至五千字。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何健骗大姐夫说,对方预付了稿费,所以自己能靠写作挣钱了。
何健在QQ空间写下了许多与爱情有关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是文学创作。2011年,在一篇名为《我的爱情》的日志下,有人留下一句评论:“哥哥,加油。我看好你的,追逐只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对我爸,有时候好像是刻意生出的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确实想鱼死网破。我很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又怕我爸。从小他就嫌弃我,做错了事就会说你说个不停。我17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辆运货车,他邀表弟、二姐夫坐他的车,我也想坐,陪他出去运沙,他说,你跟出去干嘛。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村口闲玩,看到他开车回来了,其实想坐他车一起回家,他却骂了我,没有停车。前些日子我妈回老家,他给我炒了三次蛋炒饭,我感觉很别扭。他从来没这样对我,我只感觉到虚伪。
爸妈都想我结婚,想要我生孩子,但我想做丁克。
22岁的时候遇到了初恋。我从QQ邮箱的漂流瓶里收到了她发出来的信,怀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安慰了她的忧伤。她当时刚打过胎,男朋友的寡情让她倍感伤心。为了安慰她,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两百块左右的毛毛熊给她。她认我做了哥哥,有天两三点接到她电话,她说想自杀,我安慰到早上七点,然后就有了第一个女朋友。
她一放暑假就来我这儿,我去机场接她。在接到她之前,司机问我是接谁,我说表妹,当时心里想的是,以免他认为一个残疾人居然有女朋友。在车上,我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她的手,从电视上学的。怎么说呢?第一次摸女人的手,发现原来这么柔软,柔软得好像心头上的一块肉。
晚上住在宾馆,怎么都睡不着,像是担心一场火灾一样紧张。我抱着枕头去敲她的门,她给我留了一扇门,我打开了。剥她衣服的时候她哭了,“原来你和他一样。”我想起对她爱的承诺,也觉得自己骗了她,也哭了,哭得比她厉害,比她大声。
第三天早晨,她没有拒绝。中间她又开始哭,我感觉我在“强奸”她。这个词似乎成为一道压制欲望的符,又或者是手淫的问题。在一起八天,我一次都没射过。
送她离开的那天甬温线出了事,我看着网上的新闻,心里开始担心厄运什么时候会在自己头上降临。没有太久吧,有一天接到她妹妹的电话,她妹妹问我是不是带她出去了,我才知道,她还是和前男友在一起。她提了分手,然后我把第一笔工资寄给了她。
我缠了她一年,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到她的城市附近,求她见一面,她答应了。那天见到她,好像是连着阴雨下了几个月后,见到太阳,新生从腐烂里长了出来。我甚至想跑到柜台前,求店员将监控录像拷贝一份给我,想要将这刻永远保存。
残疾对我爱情的追求肯定有影响,不然的话,可能会追得到高中同学,就是第二个女孩子。其实我知道,真的是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但我就是想体验和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当作回忆保存住的。
2014年的时候吧,在高中的QQ群里,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头像很漂亮,就找她说话,然后就认识了。我就像是老师一样,经常和她说一些大道理。我觉得她喜欢听我说,她喜欢知识,而这是我唯一能给她的,我能看到爱的光亮。她当时在广东做文员,很苦恼,她也不想在家过年,没地方去,所以2015年春节我就带回家了。
我们不是恋爱关系,她没有喜欢过我。我跟爸妈说是女朋友,其实她就是在我爸妈面前表演。我们住一间房,但没有睡在一起。床下面有一个睡袋,她来之前我买的。本来我想睡睡袋,但她不让,她睡在睡袋里,我睡床上,然后我爸妈来的时候就把睡袋藏在床下。
第二年我也去她家过年,身份是朋友。回来之后,我发现她微博有一个好友,用和她亲吻的合影做头像,我就发现她有男朋友了。我心里感觉是一种解脱,喜欢她太痛苦了,不能在一起,又不能得到她,只能這样一直喜欢,一直喜欢着。我和她说了一句:原来你已经有男朋友了,很平静。
没有第三个女孩,那是个新疆网友。我妈一直问我有没有谈女朋友,说如果我自己谈了的话,他们就不会给我介绍,我就随便说了一个。
我和你提到过么,第二个女孩跟我说,如果不给她买苹果6plus就去做援交。第一个那时候找我借钱,说不给就去坐台。
啊,她们都以爱情要挟过我。
文字是一片烟火
在获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请求的当晚,何健和大姐夫发了微信,告知自己写了豆瓣日志,也将有记者前来采访。
“何健,你把你说得这么可怜和这么伟大,可是你没有把你的缺点写出来。自暴自弃,做事没有坚持,不懂感恩,这世界上比你可怜的人有太多了。”大姐夫回他,“你回顾一下你的人生,或许也就你在文章里写到反对买卖妇女这可怜的一点,是值得别人去称赞,你再去找找还有别的吗?”
“有一件事,我坚持下来了。但是,你们谁也看不到。因为你们不懂。”何健答。
十九岁到二十二岁,遇到初恋之前,在帮家里看网吧。网吧装下了小混混的敲诈,醉酒女孩的呕吐,工厂打工的少男少女的爱情,还有一群刷装备练枪技的少年们的青春。它禁锢了我,也饲养了我。我就是在这里看完了杰克·伦敦的文集,是网上认识的姐姐送的,还有《小王子》和《死神》。
那次和初恋分别没多久,家里的网吧被查了,起因是周边一家黑网吧的外挂空调漏电,触死了一个坐在空调机上的小孩。我去了二姐那边,做电话销售。我们销售彩铃业务,服务对象大多数是老年用户,很多连普通话也不会说。有经验的同事说,你不要管他听没听懂,把台本内容快速说一下,最后问“好吗?”他如果回答好或可以,你就直接成交。可这样,老人不知道开通的是什么,就白白每个月损失好几块钱。
我成交了几单之后,内心感到不安。后来只要听出来对方是老人,在最后确定阶段,我会把“每个月扣费”和“不用可以自动取消”说得很慢,好让他听清。老人听到扣钱都会强烈反对说不要,我就很高兴对他说:好的,那这边没有帮您开通,祝您生活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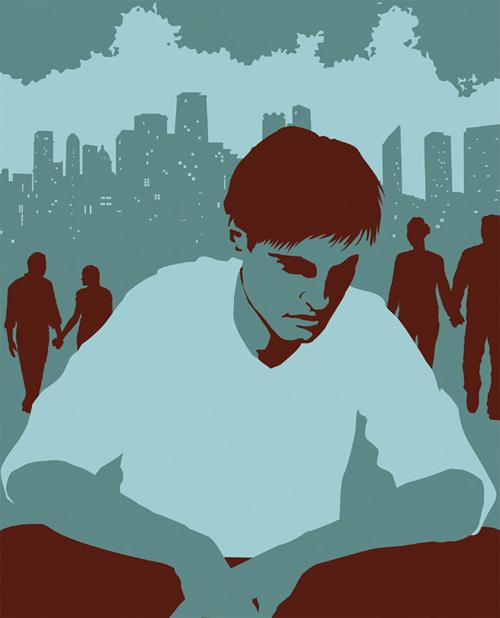
有一次拨通了一位老人的电话,跟他说了一遍后,问他,可以吗?他说可以。这样的回答让我有点惊讶,以为他没听清,于是又回到扣费的那段台本,重复了一遍。他还说可以,接着说,“你们工作也不容易,我要是拒绝的话,你们就少挣一笔钱。难得你们小姑娘能和我这老头子聊聊天。”我的声音有点女性化。
“看网吧、做客服、卖开关、当话务员,现在给淘宝写文案……家里人都尽一切可能去支持他了,可他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对何健,大姐夫是恨铁不成钢。他是福建人,寒门孝子,“爱拼才会赢”的真实写照,17岁便从一个小杂工做起,如今有了自己的外贸公司。
“写作这件事我们也很支持,可是他一直也没有一个成果出来。”大姐夫说,“他一直没去理解现实,还在幻想。他谈了两个,不还是拼不过现实么?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人家凭什么跟你?”
贫困带来的现实苦难,都有可能被克服,而身体的残疾难以改变。残疾人必须耗费更大的心力去突破桎梏,认清现实是一关,在认清现实后依然生机勃勃,又是一关。
文学是梦想也是温室。文学和网络,给了何健最初的安慰。在过往的近二十年里,他在文学里寻找安慰,退回写作中获得保护,通过文字弥合分裂的自己。写作是一件艰苦的事业,何健承认他并没有真的为写作付出过什么,但写作是他内心的出口。
唯有在文字构筑的世界中,何健与众相同,也与众不同。
初二的时候看了三毛,一下就喜欢上了。可能是那种孤独感吧,在她的《雨季不再来》里特别感同身受。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一直是个观察者。我喜欢猫,喜欢狗,喜欢鸡,小时候觉得人跟动物是能交流的,觉得我能看懂它的眼神,它也能看得懂我。三毛写自己拿了一本书去坟场上面看,就觉得是一个又孤独又很有趣,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一个人。那时候还下决心要去台湾照顾她的晚年生活,后来翻着翻着,翻到最后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初三的时候读了《挪威的森林》,直子那种用肉体祭奠爱情的执着,对我挺有影响的。那会儿养过一只蝴蝶,它是入秋之后迷迷糊糊从窗户里飞进来的。因为知道它出去会被冻死,就关了窗户让它在房间里飞,也知道蝴蝶是吸取花蜜为食,就咬了一节剥皮的甘蔗放在窗台上,还弄了一杯糖水。后来要上学,就把它锁在了房间。等到周末回家,发现它干枯了。没有难过,就想起一年级的时候,姐姐们带着我扑蝴蝶做标本的事。其实做得特别残忍,就是把蝴蝶夹在本子里,肚破肠流。
后来升了高中。我成绩也不好。离高考还差一个礼拜的时候,就辍学了。因为当时有个转学籍的麻烦,而且高考要交三百多块钱,我要问我爸要钱就很烦。反正我也考不到什么好成绩,就没去考。很洒脱的,不读书之后我就天天骑车在田野里到处逛,就乡间小路,自己好像有诗人一样的情绪。
和她分手以后,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以前想去西藏。以前覺得西藏是净化心灵的地方,但后来看透了,觉得心灵不用净化,可能就是自己疲倦了。
火车站旁的网吧五元一小时,每天花上个三四十,何健写了一个春节,最终被退稿。“我把稿子发过去了,他们说不行,应该还是要按照豆瓣上(拒绝买卖妇女)的故事去发展,但我写的是小时候的故事和初恋的故事。其实我没想过要写自己,可是,没想到一篇写自己的在豆瓣上引起了关注。”
从小爸妈对我说,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才能娶到老婆。为什么我一定要有出息才能娶到老婆呢?有人说,他认识一个残疾人,人很勤奋有自己的事业,最后娶了一个正常的女孩做老婆。虽然说是一种鼓励,但总觉得有哪不对劲。
正常女孩是残疾人的一种补偿吗?残疾人要娶到一个正常女孩才能证明他不比别人差吗?残疾人和正常人结合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身体区别之外的东西呢?我甚至觉得,残疾人婚恋这件事就不要过分关注,还有当作励志的例子。能有健全的伴侣当然好些,但也不拒绝彼此可以相互独立存在的残疾伴侣。
发帖后,在豆瓣上认识了一个朋友,她是心理咨询工作的,在纽约读书。从年前到年后,通过和她的交谈,心理得到了很大的舒缓。她问我:“那么残疾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是‘错的吗?你对这个生理上的缺陷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残疾对我当然是不公平的,为此我从小就怀疑并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现在,基本不会这样想了,也不想把这个问题转嫁到他人身上。是我就是我吧,我也习惯了。
其实现在也没什么向往的爱情,找不找女朋友都无所谓了。初八的时候回到工作的地方,也租到了便宜的房子。现在最想做的是挣钱,把欠老板的债还了。加上年前借的,欠了老板6300元。我现在特不想联系家里,不希望他们的建议或者他们的说法扰乱我的精神世界。我就想先在外面闯一闯,自己稳定下来。父母的观念如此,我改变不了,也没能尽早独立,其实是我的错。
发帖这件事,我想说,我把痛苦放到了一片陌生的海,没想到绽放出一片照亮天空也照亮我的烟火,让我孤身身处小旅馆时,感受到了温暖。也知道了我身旁另外的一些孤岛,希望大家都能看到绽放。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何健、何建国为化名。)
编辑 陈竹沁 rwzkzq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