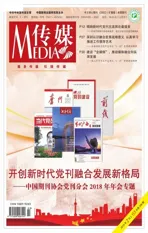移动互联网的场景建构与行为交互
2019-03-11孙桂杰
文/孙桂杰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认为,由于电子媒介所具有的传播特性,信息在流通过程中呈现出瞬时性和超地域性,它把发生在遥远的异地的事情传递到观众的眼前,这在信息传递的意义上“地点”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媒介创造了一种新的场景结构,人会根据这种场景结构创造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故而媒介本身也改变了人的社会行为结构以及人际交往的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梅罗维茨把媒介情境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媒介三喻”,即媒介作为容器、媒介作为语法、媒介作为环境,这种修辞学上的表达可能欠缺理论的严密性,但是对于在互联网环境中来思考网络媒介所产生的场景空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电子媒介中的信息流动改变了场景的定义,因为流动使得“地点”变得飘忽不定,物理的“地点”与媒介中的“地点”界限不再是清晰分明的,“地点”与“媒介”共同构建了人的交往模式和信息传播模式,形成新的社会场景。
社会的场景化
场景是一个影视用语,戈夫曼通过对戏剧中场景理论的转化,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术语,用于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境。在梅罗维茨的论述中,场景与电子媒介结合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交往空间——场景空间。这种交往空间以人的身体不在场为特征,通过电子媒介的中介行为而达到交往形态,他把场景的概念带入了主流传播学的研究中,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场景结构。
梅罗维茨在新的媒介场景形成之后,认为“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种特定的新媒介或者一种新的通用类型的媒介引进之后,媒介矩阵以及它对社会行为影响变化的方式”。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媒介矩阵的变化,它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变化,使得群体与个人界限变得模糊,原先分明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因为电视媒介所具有的流动特性,而具有进一步融合的倾向。
戈夫曼用戏剧来探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指出,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戏剧舞台上的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处,与戏剧表演一样,人们也会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合适的自己。在不同的舞台上,他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根据演出角色的不同展示不同的“自我”,这就是“场景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微观层面的探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社会行为与舞台上的表演类似,都需要在特定的场合调整自己的反应以寻求与他人的协调:演员要与台下的观众呼应,社会行为者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场景因素来调整对他人的态度;演员需要有一定的戏剧素养来赋予角色不同的含义,社会行为者则需要根据自我的个性以及社会情境因素赋予角色扮演的技巧及互动方式。
戈夫曼根据演员的表演舞台划分了剧场、前台和后台。当个体在特定的时间内进行表演时,为观众展现了一个情境,这里有标准的、有规则的设置和道具,是前台;为了不让观众看到,同时也要保持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限制观众与外人进入舞台部分,通常会有一个后台与前台进行间隔。在前台,演员表现了角色的部分,在后台则隔绝观众,保持了自身的神秘。
与戏剧舞台不同的是,电子媒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场景,它把个体的交往行为带入一个“身体缺席”的空间中,身体自身所具有的视觉、听觉与传播语境剥离开来,经过电视的中介,不同的场景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混杂的多元想象的场景空间。虽然身体不在场,但是可以通过虚拟场景空间与人展开交流。这种由电子媒介所制造的虚拟的信息交流场景拥有强大的社交功能,使人在不同的虚拟空间中任意穿梭。真如梅罗维茨所言“地域消失”了。而在后互联网时代的移动互联阶段,“地域的消失”更加突出,真实的社会空间被虚拟的场景空间所吞噬,社会进一步地场景化。
在虚拟的场景空间中,人的在场与环境因素并置存在,是一种非线性的并置状态,这是场景空间论的重要特征,移动通讯利用用户的移动性把实体空间随身携带,使得人际交往的互动性成为一种情感纽带,人与场景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既在里面,同时也在外面”的状态,从一种固着的空间中脱离出来,与移动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全新的流动场景空间。
“朋友圈”成为可见的“秀场”
在传统意义上,公共与私隐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隐私是一个极具个体化和私密性的信息,而公共性则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是非个体化的。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以“分享”为特征的平台,“过度分享”成为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共与私隐的二元对立模式受到了挑战。对于可见性而言,微博与微信具有不同的传播机制,故而二者所创造的社会场景也是不同的。
微信则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交网络,特别是朋友圈的设计,这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呈现隐私生活的个人生活“秀场”。微信的社交圈子主要有两类:朋友和公众号。朋友隶属于用户的个人生活圈子,大部分与自己都有现实生活的交往,有一定的现实社会纽带的关联,属于强连带关系的范畴。另一类则是微信公众号,其类似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由于微信数据的可视化,导致其传播范围的可控性,这种类似大众媒介的公众号,是信息的公开传播,它虽然具有了新媒体传播的特征,但是总体而言是一个以单向传播信息为主的数字媒介,其双向的交流性质欠缺。
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封闭的具有强连带关系的社会网络,其公共性的表现在于对信息的分享,而这种分享由于具有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的特征,故而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朋友圈“晒”的行为,将大量隐私信息打入公共领域,并放大某些生活的细节,由此形成社交生活的“前区”,而“后区”则逐渐消失。在人们习惯性地、主动地曝光个人隐私之时,“楚门的世界”就不再是一个幻想中的世界;而惯性地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使用LBS,则让用户及其空间信息全部暴露在LBS无处不在的监控中,整个社交关系的空间实践就被推向了一个“前区”暴露于公众眼前。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有交流和分享的欲望。在社交媒体上面,暴露自己与窥视他人成为一个同步进行的场景,人们进入了一个不设防的“表演”空间,点赞、转发、评论等是衡量用户影响力的量化指标,它们成为重塑自我的舞台,但是也通过将个人生活中的某个细节放大于公众之前而塑造了一个表演的个体。
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线何在?梅罗维茨认为电视把公共空间拓展到家庭会客厅,让个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同时也由于各类电视节目的样式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模糊了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线,从而形成一个介于公开的“前区”与私密的“后区”的“中区”。雷蒙德·威廉斯则认为由于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为了得到社会阶层的认同与交流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他需要一个私人空间,但同时也会通过对公共空间的考察而调整私人空间的范围,于是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人际交互维系了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
移动视频场景中的人际交互——深度私人化
2018年上半年,中国网络视频网站在版权购买和相关产业链打通方面充分发力,积极打造网络视频的完整生态系统。在收看设备方面,手机网民数量增长,视频用户不断向移动终端转移,视频网站的移动端流量用户占整体流量的73.4%,智能移动终端成为网络视频观看的重要工具。同时,随着智能电视的普及,网络视频的观看中,使用电视的用户数也在不断上升,视频场景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场景入口,且移动视频的收视行为与传统视频的收视行为相比特征十分明显。
第一,移动视频打破了原先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区别。在观看移动视频的过程中,他们构建了新的流动空间的模型,人的收视行为具有了分割空间以及空间流动化的特征。
第二,场景的划分:个体化的收视行为。电视作为家庭装饰的主要物品,在最早的收视行为中具有仪式的作用。网络视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仪式化,特别是移动视频使得收视成为一种个体行为。但是,移动视频往往是以互联网为中介的,所以当个体化的收视行为与互联网交互之后,就又具有了网络的虚拟仪式性,也就是通过移动视频的社交性来达到对视频的共同收视。他们倾向于对视频中的场景进行交互行为,如吐槽模式的展开,或者对视频场景本身进行评论,这就是视频弹幕和相关评论信息的作用。由于移动视频本身的可控性,自由控制的视频内容、随意设定的时间以及收看的环境的随意性,使得原先被迫公共化的私人空间重新陷入了深度的私人化,这也是梅罗维茨前区、中区、后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一个“深后区”,完全隶属于自身,但是又可以在身体不在场时与同时观看视频的其他个体发生关联,这是移动视频所具有的社交性,它改变了人们在对视频进行观看时的行为与情感模式的转变。
第三,“身体缺席”的弹幕场景,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弹幕对视频的再次加工,使得视频的传播模式不再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而变成多对多的模式,营造了超时空的集体观看体验,同时也形成了聊天室群聊的氛围,对于视频上传者、观众、弹幕评论者而言,他们都从中获得不同的社交体验,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存在和认同感。弹幕作为网络视频的新场景,不仅让物理空间与视频空间之间的界限消除,同时也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链接起来,使得观众在异时空之下居于同一视频中,实现了不同时空的混杂。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新的数字技术构建了新的场景,与此同时,新的场景也塑造了人与人之间新的交互行为。但是,梅罗维茨认为,社会场景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新的地点或者空间来替代原有的场景,而是会在新的场景空间中,通过移动互联网、VR技术等第三维度的媒介,塑造在其中活动的角色。移动互联网媒介融合了传统的人际交互模式与“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同时加入社交属性,从而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具有重塑的作用,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