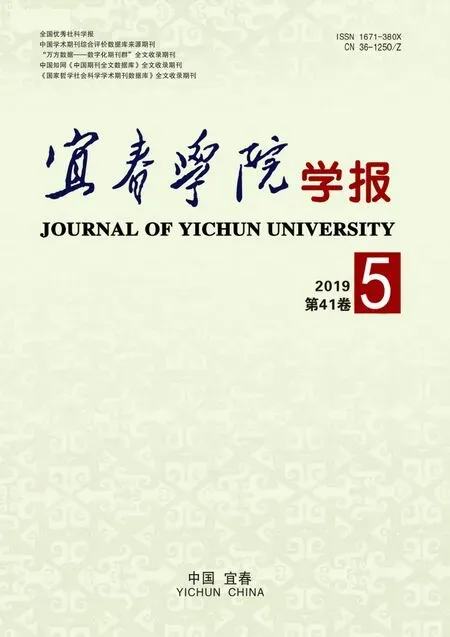礼乐文化起源的地域性及其当代意义
2019-03-05冯源
冯 源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历来探究礼乐文化起源的学者,多从时间着眼,少有结合地域来论述。考察礼乐文化起源的地域性,不仅可以发显礼乐文化滥觞及赖以发展的必备条件,而且可以结合其地域特征,揭示礼乐文化原初的价值取向。据此,亦可清晰呈现礼乐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内在关联。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礼乐文化起源的地域性及其当代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先秦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传统
历史文献与地下考古均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定都之地多集中在河洛地域,而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因此,有学者指出,“河洛文化的特质,概括说来,就是‘礼乐’宗法等级制度”[1](P71),笔者基本认同此观点。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皆与先秦河洛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夏、商二代礼乐文化的形成
学界多认为,礼乐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邹昌林先生在《中国礼文化·自序》中指出:“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古礼,实际是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经五帝时代(即父系氏族社会与早期文明时代)和三代(即所谓奴隶社会)两次整合,而发展定型的,以自然礼仪为源头、社会礼仪为基础、政治等级礼仪为主干的原生文化体系。”[2](P20)这表明,礼乐先于文字而存在。早期礼乐的概况,存于后世的文献资料中:
《通典》:“伏羲以俪皮为礼,作瑟以为乐。”[3](P1119)
《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4](P959)
《礼记·礼运》篇假托孔子之口,论及礼仪制度的功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5](P3062下)认为禹时已有礼,且礼仪制度已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
以上几则材料,将礼乐的起源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表明在古人的观念里,礼乐早已客观存在于上古时代的社会实践中,与人类早期的生活相伴随。当然,这些记载具有传说性质,礼乐在其时的真实存在状态,还无从一一考证。
关于礼乐文化较为可靠的记载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尤其是文字产生之后。最早记载“礼”的文献,是殷商的甲骨文,王国维先生据此考察“礼”字的本义:
《说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豊部》:“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禮之器,其说古矣。……盛玉以奉神之器谓之囲若豊,推之而奉神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6](P290-291)
按照王国维先生之意,“礼”之本义为行礼之器,用于奉神,后来涵义日渐扩大,泛指与奉神、奉人相关的一切事务。
对礼的起源及发展,郭沫若先生与王国维先生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他在《孔墨的批判》中亦指出:“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对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7](P96)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夏礼的存在,有着较为信实的记载:
《论语·八佾》载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8](P5357上)
《论语·为政》亦载孔子对夏礼的论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8](P5349下)
相似的记载还见于《礼记·礼运》篇:“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5](P3064下)
以上资料记载了夏礼、殷礼在春秋时期的留存情况及孔子为搜集夏礼、殷礼资料所做的努力,表明夏礼确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不仅如此,由殷礼、周礼对夏礼的承继,还可看出夏礼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尚书·商书》载《仲虺之诰》,提及殷礼:
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9](P341下-342上)
在仲虺之诰中,仲虺两次提到“礼”字:其一为赞美商汤对礼义的使用,即“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其二是对商汤的劝勉,将“有礼”与“昏暴”对举,并表明对二者的不同态度,此句孔颖达传曰:“有礼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由这则文献可以看出,至少在西周人的认知中,殷商已经具备了“礼”的观念,并用之成功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志自满,九族乃离”之语,表明殷人已经有了较深的宗法意识。与礼法观念相结合的,是殷商的尚德意识,其中的“佑贤辅德”、“德日新”之语,即是对伦理道德的崇尚。
从礼乐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来看,二者向来不分家,有礼必有乐,奏乐亦往往与礼有关。对于乐的发展情况,文献多有记载:
《尚书·益稷》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9](P302下)
《吕氏春秋·古乐》云:“汤乃命伊尹做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10](P126)
20世纪后期的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的音阶系统较周代成熟,已有完整的五声音阶,标志着商音乐的发展程度。
由以上对夏、商时代礼乐文化发展情况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夏、商时期,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一切,均为周代礼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
周代礼乐文化与河洛地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承继的是河洛地域夏、商二代的礼乐文化;其二,东周时期周代的礼乐中心仍在河洛地域的核心地带洛阳,孔子入洛向老子问礼即是明证。
周代礼乐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即周公在洛阳对礼乐的制作,最早对此事记载的是《左传》。《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之语:“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常,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11](P633)杨向奎先生指出,此语“出于季文子之口,他是鲁之世家子,鲁为周公子伯禽封国,且春秋去西周不远,这是可信的记载。礼的范围广泛,上述‘周礼曰’及‘誓命曰’的文词虽不见于先秦典籍及彝铭中,但不可能是后人伪造。”[12](P277)此外,还可征之于其他文献:
《资治通鉴外纪》引《尚书大传》叙周公居摄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于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13](P11)据《后汉书·郡国志》载“雒阳,周时号成周”[14](P3389),是知周公所营之成周即为洛阳。
《礼记·明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5](P3224下)
顾颉刚先生指出:“‘周公制礼’这件事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在开国的时候哪能不定出许多的制度和仪式来;周公是那时的行政首长,就是政府部门的共同工作也得归功于他。即使他采用了殷礼,也必须经过一番选择,不会无条件地接受,所以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既然有损有益,就必定有创造的成分在内,所以未尝不说是周公所制。”[15](P204)杨向奎先生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的历史作用:“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12](P136)
周公制礼的内容学界一直有争论,而关于周代礼乐对夏、商二代的承继,已为学界所共识。《新唐书·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16](P307-308)
此处欧阳修所谓的“三代”,即夏、商、周,此时“礼乐达于天下”,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与礼乐有关,表明周代以前,夏、商的礼乐文化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诚如邹昌林先生所云:“‘礼’——这个三代传留下来的东西,实际是夏、商、周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礼’不过是所有这些东西的一个总名。‘礼’在三代仍然是浑然一体的东西。”[2](P24)今人杨华先生明确指出,周人在礼乐制度方面吸取了“殷人的先进文化,包括以嫡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殷人和祭祀礼制等等;而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又作了损益,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统治对象。”[17](P64)
东周时期,周平王迁都洛阳,洛阳为当之无愧的礼乐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国的孔子曾入周问礼于老聃。《史记》对之言之甚详:
《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18](P1909)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8](P2140)
此外,《孔子家语》亦有记载:“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19](P541)
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传统,经过夏、商二代的酝酿,至周代时取得了集大成式的成就。“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是首次有意识的对于‘礼’加工改造,他用‘德’字概括了过去的‘礼’。”[12](P353)西周将三代的礼乐文化高度系统化、理论化,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孔子禁不住发出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8](P5358下)自此之后,历经《左传》、《荀子》、《孟子》、《礼记》等儒学经典对礼乐文化的不断建构与强化,礼乐文化作为强大的文化传统确立下来。试看后世对礼乐的认知: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1](P76)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11](P1266)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5](P3494下)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5](P3326下)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20](P5558)
以上资料代表着先民对礼乐文化的建构与认知。《荀子·王制》篇甚至提出:“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21](P90-91)表现出对三代礼乐文化的莫大尊崇。因此,春秋以后,虽然古礼、雅乐逐渐遭到破坏,而经历代先民的努力,形成、发展于河洛地域的礼乐文化传统始终得以保持不坠。
二、礼乐文化起源的地域性特征
礼乐文化之所以起源于河洛地域,基于夏商周三代以河洛地域为定都之地的传统;此种传统又催生了礼乐文化的内在品质——以德为核心的传统。由先秦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两种传统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以河洛地域为定都之地的传统,源于古人对河洛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的体认。夏启建都河洛地域是基于对夏禹建都之地的继承,商汤建都河洛地域是基于对帝喾活动地带的承袭,至西周时期,周人对都城选址又有了深入的考察与思考,其营建洛阳为东都的过程,体现出对河洛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及河洛为“王者之里”的文化传统的认知。
先来考察周人对河洛为“天下之中”的体认。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曰:“隹(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珷(武)王丰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逨玫(文)王,□玫(文)王受兹大命。隹(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22]据考证,此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意为周武王出兵伐纣灭商以后,认为洛阳一带是天下四方的中心(即“中国”),要以洛阳作为都城,在这里治理全国民众。[22]《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思量殷商覆灭的教训,不免忧心忡忡,“我未定天保,何暇寐!”[18](P129)“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18](P129)最后认定洛阳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便于其德教施于四方,于是确定洛阳为建都之地。具体的筑城方位,还要根据洛阳的地形环境来确定,《尚书·洛诰》篇记载西周初年周公旦卜建洛阳城的经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9](P454下-455上)孔颖达传曰:“遣使以所卜地图及献所卜吉兆来告成王。”[9](P455上)是周公旦遣使者将占卜结果告知周成王。周公将洛阳确定为地中的方法,《周礼·地官·大司徒》有详细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23](P1516下-1517上)
周代营建洛邑的过程,相关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
(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24](P525-529)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8](P133)
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4](P1650)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记载周代君臣对于洛阳地望的认知,此处的“中”,是为“中心”之义,即指洛阳居于中国地理区域之中心位置。
再来探究周人对河洛为“王者之里”的体认。左思《蜀都赋》云:“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此处的“王者”当指以王道治天下的君主。如《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邢昺疏曰:“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8](P5447上)史称洛阳为“都”、“中国”、“土中”等,即包含着把洛阳视为“王者之里”的意蕴。《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引刘熙语:“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18](P30-31)可见,把帝王所居之都邑称为“中国”,乃为自唐尧以来的观念。自上古时期,先民就把定都选址作为非常神圣的事情来看待,将之与对天命的绍继等同起来。《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殷后回到镐京,因国都未定,夜不能寐。他反复思考殷商覆灭之因,归结为“天不飨殷”。因此,他对天命至为敬慎。在选择定都之地时特别强调“依天室”。“天室”指天上星宿的布列位置,古代定国都、建宫室皆依之。洛阳南接三涂山,北临太行山,北有黄河,洛水伊水穿行其间,离天上星宿的布列位置很近,是为理想的定都之地。《尚书·召诰》篇很好地诠释了周武王的这一建都理念:“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孔颖达《疏》引《正义》曰王肃云:“旦,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称周公之言为旦曰。王者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继天使成,谓之绍上帝也。天子设法其理合于天道,是为配皇天也。天子将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称周公之言其为大邑于土之中。”[9](P451下-452上)由此可知,周武王所建立的王朝是“绍上帝”、“代天治民”的王朝,其为政理想决定了定都乃神圣之举,“必宜治居土中”方能上配皇天。更为重要的是,夏、商曾在这里建都,夏、商王朝的兴替是合天变应天道,周代定都于洛邑,就表明周代之政权是继天为治,周代与夏、商王朝是最为正统的继承关系。
既然选择定都之地是为了“绍上帝”、“代天治民”,那么,治理国家的凭借自然不是山河之险,而是顺天命、施德政。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洛阳一带地势平坦,交通四通八达,便于与周边诸侯国的交往,也促进了河洛地域商业文化的发达,所谓洛阳为“天下之大凑”,即指此。而此种地形的不利之处亦很明显,平坦的地势使得在军事上少有山河之险得以凭借。仅从军事战略位置着眼,“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18](P2716)地理位置自然优于洛阳。这一点,周武王当然了然于胸,他对周公分析:“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18](P129)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夏代曾经定都的地方。周武王意识到山河之险不足为凭,重要的是要顺从天意,他对周公说:“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18](P129)张守节正义:“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18](P130)周武王决定以德教布施四方,而不是仅凭军事和武力去统治天下。诚如西汉初年刘邦谋士娄敬所分析的那样:“(周)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职贡,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18](P2716)所以,洛阳作为“土中”之地,夏为之都,商、周袭之,“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相继在此建都,所承继的乃是施行德政的文化传统。
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制度化,其核心亦在“德”。在西周至春秋文献中,常常以“德”指代礼乐。如《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11](P317)又《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1](P445)“礼乐德之则也”,表明了先民对德与礼乐关系的理解。杨向奎先生指出:“周公之造‘德’,在思想史上,政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由此,传统的‘天人之际’,逐渐失去颜色,至孔子造‘仁’,遂以‘人人之际’代‘天’。”[12](P334)事实上,从三代以前先民对“德”的推崇来看,“德”并非为周公所造,只不过,周公着重将“德”提升出来,将其内化为礼乐制度的核心,确为一大创举。自此以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占主体地位的礼乐文化传统。
因此,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上,在河洛地域建都的传统与礼乐文化传统是一致的,皆体现着对“德”的尊崇与体认。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此两种传统往往交织在一起。在洛阳建都,不仅意味着王朝所接续的是最正统的统绪,还代表着一种施政理念,即推行“德政”,尊崇“王道”而非“霸道”。因此,后世诸多有“王者”理想的君主多醉心于定都洛阳,在精神理念上所承继的亦多为礼乐文化传统。
三、河洛礼乐文化传统对当下中原文化构建的意义
河洛地域是中原的核心,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主干,因此,中原应立足地域优势,充分发显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
其一,传统礼乐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原文化构建及创新的基石。
(一)应系统发掘礼乐文化传统的历史功用。从当下看,传统礼乐文化体系所依托的政治、文化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传统的礼乐形式与当下的社会发展更是相距甚远。然而,礼乐文化传统自先秦肇兴、繁荣,之后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作用,其历史功用亟待发掘。
(二)应精准阐释传统礼乐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传统礼乐文化原典丰富,应结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做好译注及普及工作,藉此,可使广大民众对传统礼乐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有一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认知。
(三)将传统礼乐文化精神融入到中原文化建设的多个纬度。比如,可以将礼乐文化中的德育价值、人文精神融入到当代教育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中原文化的创新亦应当立足传统的基础之上。
其二,构建中原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中原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原文化的传统、嬗变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嬗变与创新,构建中原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中原礼乐文化构建会在世界文化重组格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现在学界有一个热词“新轴心时代”,不论“新轴心时代”业已来临,或是我们正在通向“新轴心时代”的路途中,世界文化终将会有一个大的重组,而立足于深厚根基的礼乐文化亦必将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礼乐文化传统与当下融合后,必将焕然一新,如此,充满活力的中原文化不仅有根基、有当下,也有未来。
注释:
①囿于繁难字体,以上所引非为释文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