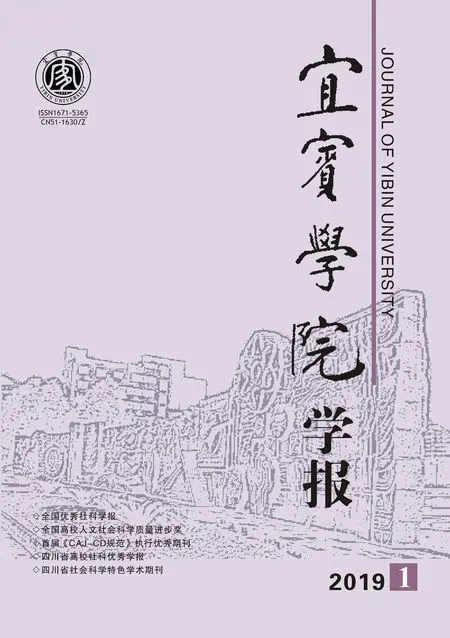反抗一切关于存在的命名
——鲁迅文学世界中的“影”及相关
2019-03-05张黎黎
张黎黎
(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四川宜宾644007)
作为文学意象的“影”要成为传达人自身孤独的道具,需要看它和主体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由于“影”和“形”不可分离的物理关系,作为群体动物的人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也有“影”的陪伴。但是“影”的陪伴不仅不能给人带来安慰,相反给处于此情境中的人带来更深的孤独与凄凉感,这种农业时代的文人情怀与自我想象为我们留下了一群叹息的身影。鲁迅的艺术世界中也有对使用“影”意象的偏好,但鲁迅的“影”却融合了更丰富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群/个、生存/死亡等交织作用下的绝望与黑暗性体验。
一、 “世纪末的果汁”沾染的现代体验
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影”的意象就传递出孤独与凄凉之情境。在古典诗词中,关于“影”的书写大体可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之“影”,毫无疑问,这是写作者本身体验到的孤独; 另一种是物之“影”,从诗歌文本的表达的情绪和意义看来,物之“影”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以写影获誉的抒情诗人是宋代词人张先,他因写影而被称作“张三影”:“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青门引·春思》)“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草树争春红影乱。一唱鸡声千万怨。”(《木兰花》)《青门引》中的“秋千影”是词人在伤春的时候,虽然伤春可能是由孤独引发的,但是隔墙送过来的秋千影以及秋千上少女的欢笑声却触动了词人青春不再的伤感。而“花弄影”“红影乱”传达的是春天万物纷纷的景况,其修辞效果与“红杏枝头春意闹”相差不远。也许,可构成一种小传统的是人之“影”的书写。“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晋·陆机《赴洛道中作·一》)“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赴洛道中作·二》)西晋灭吴,陆机被征,在路上的诗人思念家乡,又忧前途,返乡已不可能,顾影自怜抱影而寐,影子是孤苦的见证。“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唐·杜牧《早雁》)“影”虽为物影,但是孤雁却不是“雁”,而是被异族入侵烧杀之下四处逃散的黎民百姓的指喻。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境遇,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影”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意义指向,但是都没能突破农业时代生存结构提供的体验世界的模式。
鲁迅的“影”,既在这个小传统之中,也在这个小传统之外。小说《祝福》在写祥林嫂知道捐了门槛依然摆脱不了被分身的恐惧之后,文本写道“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1]21这里的“黑影”有两重暗示:一是让祥林嫂产生了自己将被锯成两半的幻觉;二是随形之影无声无息却时时相随无法摆脱,这让祥林嫂感觉到那种不详的命运。不管是哪一重意义,这都与祥林嫂内心的恐惧有关,这恐惧对象不断地幻化为日常生活细节并不断强化这种恐怖,最后导致她整个人的绝望乃至崩溃。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影”的书写充满感伤,但仍具有丰富的人间色彩和人情味,在审美上不失优美,甚至是生意盎然。而鲁迅先生对于“影”的描绘却是阴森恐怖、鬼气凌然。传统诗词中,诗人们最喜欢用的就是“花影”而鲁迅却独独喜欢用“黑影”,鬼影重重是人物内在精神状态和命运的暗示,也是创作主体自身体验向人物的渗透。
鲁迅一直的审美追求是冷峻的、凄厉的美。在鲁迅的世界里,他喜欢的不是鲜花而是野草,不是天堂而是地狱,不是神明而是鬼怪蛇枭。与“影”这一意象相关的意象还有诸如“黑色”(如《铸剑》中的黑衣人/玄铁剑、《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黑暗”(《影的告别》)、“黑夜”(《秋夜》《夜》)、“死亡”(《野草·题辞》《死后》)、“坟墓”(《过客》《墓碣文》)、“铁线蛇”(《死火》)、“地狱”(《失掉的好地狱》《伤逝》)、“无常”(《无常》)、“女吊”(《死》)。这些诡异的意象群说明鲁迅的审美世界是偏离于传统文学那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更多地吸收了“世纪末的果汁”的现代美学品质。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他们的风格都是对传统美学的反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主义确实是世界文学的主潮,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就翻译了安特莱夫(即安德列耶夫)和迦尔洵等的作品《墙》《谩》,“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也常常是文学史家评价鲁迅的常用语,鲁迅在致许钦文的信中对安特莱夫的评价是“全然的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根柢是: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2]517。 汪晖指出,鲁迅对于安特莱夫的“这种理解包含了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体验的某种认同”[3]44。这种黑暗性体验是主体通过叙述中介渗透到人物行动和意识感受中,或者作者自己直接书写死亡、鬼怪等否定生命实存的否定性力量。要理解这种现代风格的形成,仅从世界文学的视角是不够的,也许,我们应该探查鲁迅更深层的内心世界。
二、 立于无何有之乡
《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极诡异的篇章。其形式传统,恐怕不是陆机、杜牧,而更似陶渊明的《形神影》。它也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关于“影”这一意象的描写。
《影的告别》共有六节,以一个叙述性诗节为开始: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候来作的告别,对于影要对谁告别有着不同的理解。艾伯说“影的所谓告别是一种创伤引起的经验,因为告别实质上意味着死亡”[4]62。
诗的下面就是影独白的内容了。第二节是: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天堂”“地狱”代表了空间上的两端,“黄金世界”指向时间。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影”封闭了所有去向。钱杏邨说这把鲁迅“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5]186。理由就在于鲁迅拒绝去“将来的黄金世界”。“将来的黄金世界”被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赋予了相当的政治寓意。其实鲁迅在他小说《头发的故事》就写到,“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对被预设并被许诺为“黄金世界”充满了质疑,因为他有一种生命本体性的黑暗性体验,和这相比,在《呐喊》中所寄予的希望(如《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药》里的夏瑜墓上的白色小花、单四嫂子的梦)显得十分虚幻,甚至幼稚。“死亡问题或者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正是一切关于个体生存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恰恰是在这种终极关切中,人对自身与世界的怀疑达到了空前深刻的高度,而人面对自身命运和世界的态度又以这种怀疑的深刻性为前提。”[3]165汪晖认为是死亡问题让鲁迅有如此深刻的怀疑精神,其实应该是艾伯所说的有生命创伤更为合理。这种生命创伤来自历史与个人的生活世界。不过,鲁迅的确是在这样的怀疑中去探讨生命的存在,探讨个体的存在。影不仅“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不愿去,就连“你”也不愿意了。这是一种彻底地诀别。感叹句“我不愿意!”将这种决绝的心体现了出来。这一层次的反抗与挣扎仍是一种过去的失败带给个体的精神创伤。“影”要告别的“你”乃是在历史中的有限存在。“他”追求理想,许诺未来,然而“你”仍是终有一死者。“影”所要挣脱的乃是这些有限性。历史的循环感是鲁迅在判断这个国族的未来时无法摆脱的噩梦。历史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他。他洞悉了历史的这种游戏,也洞悉了自己和历史合谋的一面。因此,连“你”本身也是在告别的对象之列了。
诗的后面写到影“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而我由于“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选择了在“黑暗里沉没”。这是一种悲壮的选择,历史的“中间物”在体认了自己存在后作出的自由决断,“肩起黑暗的闸门”,与那黑暗同时沉没于旧时间。
诗的第五节中“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两种赠品——黑暗和虚空——不仅可以视为影的自然属性,而且也可以视作诗人内在自我的形而上的标志…… 影子处于光明与黑暗,未来与过去之间邪恶悖论之中,最终选择——似乎它‘自然’应该选择——虚无主义的出路……‘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结局形式,它传达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悲观主义。”[4]196用绝望、悲观来描述“影”所昭示的鲁迅对历史、时间、生命的复杂体验,是一种皮相之见。“影”确实“虚无”,因为拒绝时间和空间向度上的好/恶。但并不能说鲁迅是虚无主义,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默,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6]170黑暗乃是那无边无际的虚无的外相,它给个体带来的是那种被包裹的充盈感,。个体不是被动地接受虚无,而是主动地选择了它,因为他认识到它的实在性,它的无处不在性,虚无乃世界的本质。个体不再委身于那些被许诺的价值偶像来逃脱它。因此“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181。这是对大而且黑暗的虚无的毫无依凭的反抗。肉身直接对抗虚无,没有任何人类的价值依凭,上帝、神、理想、理性、各式各样的信仰在这里被放逐或已溃败。“肉搏”显示对抗者在绝望之极对它的反抗,但反抗者知道自己不是在反抗“绝望”,而是反抗历史与生命的本质——虚无(即“空虚”)。“绝望”,只是偶像的虚无本质带给个体的后果,而非虚无本身。虚无最终成为“实有”,可以“肉搏”。倘若“虚无”无法确定为实有,又何来“肉搏”。这是“无物之阵”之中的个体,只是这次连“投枪”都没有了。在《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尚有“投枪”可恃。到这时,历史中的个体两手空空,个体仍在虚无的深渊中坠落。
三、 反抗一切关于存在的命名
像“影”这样在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实在与虚无、光明与黑构成的世界里分裂、撕扯、纠缠,传达了鲁迅面对历史和个体生命诸层次的带有创伤性质的黑暗性体验。
鲁迅说:“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21黑暗性体验带来的对存在的理解最终结果不是虚无,而是虚无本体的不确定化和再虚无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207热/寒、天上/深渊这两组词构成一种互文关系:“浩歌”所歌的对象是“天上”,因为天上喻指着一切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不管这希望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人性的。因为对于“天上”的幻觉激起尘世中“人”的狂热,这是乌托邦的审美效果与人类的根性共同作用所致:“一切眼”中因为看到“天上”因而浩歌狂热。《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不就是鲁迅曾经的“浩歌”吗?然而那位呼喊“立人”“人国”的启蒙之子“荷戟独彷徨”时,反观自身,于是“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当年的浩歌者已经在虚无的深渊中寒的时候,历史仍在生产新的“浩歌者”——“身外的青春”,但是他们的眼中的“希望”却被看出“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并不是说无所希望后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走出新路。得救的前提是意义的产生,意义之根源乃是各种大的“希望”,各种形形色色的“希望”一直在被“人”生产、流播,永无终结的时候。“游魂”不愿附着“浩歌”描述的“希望”上因为它知道希望的本质乃是虚妄,“游魂”无所附着,得救(即探求存在的本相)不可实现。于是,只有向内转向自身,怀疑和质问,审判那已经颤抖的灵魂,以自啮其身的方式来获得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本质。“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然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旧,本味何能知……”[1]207“本味”应该理解为存在的真义。“欲知本味”,即要勘查存在的最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关于“本味”,有众多的命名,宗教式的、乌托邦式的、圣人式的。不外乎在“天堂”“地狱”“未来的黄金时节世界”之间修正搭配。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他感到了希望,也一样多地感到绝望。问题不是希望和绝望的交战,而是希望和绝望共同的虚妄。这使他终于惊讶与‘心’的空空如也”[7]164。《墓碣文》中的那个死尸“中无心肝”,因为“抉心而食”已经把心吃完了。但是“食”完后依然不知“本味”,否则有还要问“……答我。否则,离开……”那个“游魂”在悬置一切前在的意义体系下,以“自啮”的方式探求存在的“本味”。但是,“游魂”最终并无所得。这是孤独者用耗尽了他的肉身走出来的荒凉之境,“本味”依然高悬于词语的尽头。正如鲁迅告诉许广平,自己最终也无法证实“黑暗与虚无”是不是最终的“实有”。人类的自我意识产生终极性体验和救赎意识以来,就有各种“名”被各种各样的先知有意无意地描述出来。鲁迅拒绝这一切关于存在的命名,个体生命在时间的未知向度展开,它拒绝一切先在的描述,包括他自己。
结语
前文提到《影的告别》对于“黑暗与虚无”的确认,而《墓碣文》则否定了这一“实有”,作为“实有”的“虚无”被质疑,被“无”化。这已经不是什么“彻底的绝望”或“透彻的悲观”所能表达的精神状态了,生命已经能够无所依凭,它变成了悬浮在虚无之域的游魂,无所附着。在此,我们已经深入到了彷徨时期的鲁迅内心黑暗性体验的第三层,如果说在《彷徨》中的“黑影”只是审美经验偏好的话,那么后两层,乃是作为生存于历史中的个体对本真存在的勘查。这根源来自鲁迅独特的生存体验:存在即虚无,虚无本身仍是虚无,与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相反,鲁迅却虚无化了虚无本身。这已经跃出了绝望和反抗绝望所能划定的意义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