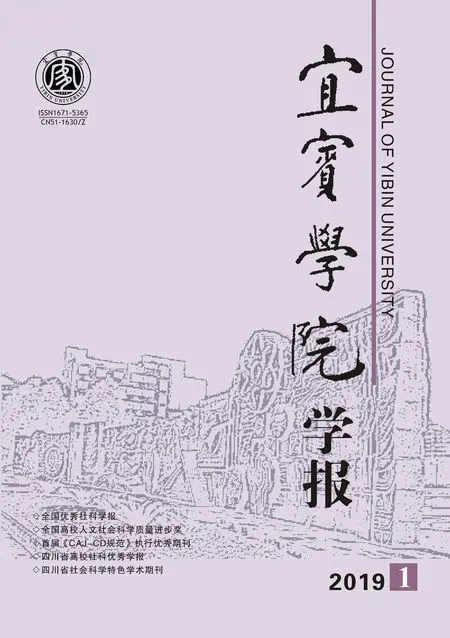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要做人
——论沈从文《月下小景》中的人性、自然与神性
2019-03-05郑依梅
郑依梅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
《月下小景》是沈从文佛经故事集《月下小景》之开篇,沈从文在其中讲述了一个优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折射出他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探求。结合沈从文创作《月下小景》时独特的生命体验,我们能从那片日月交映的光辉中一瞥湘西世界的自然与人,在那座爱的伊甸园中凝望彼岸世界的生与死、神与人,最终去发现人性的意义,从而解答“我们为什么要做人”的根本问题。
一、 纷杂之后的清净:《月下小景》的创作背景
1931年,可以说是沈从文生命中人事最为纷繁复杂的一年。是年年初,他得知挚友张采真不久前在武汉遭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消息,尚未走出悲伤,紧接着在1月17日,他的另一位好友、曾与他合编《红黑》《人间》月刊的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沈从文为胡也频多方奔走营救,数次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寻人帮助,要求国民党政府放人;可惜营救无门,胡也频于2月牺牲,沈从文与这位生命中最好的朋友生死相别。随后,他作为胡也频、丁玲夫妇的挚友,以武汉大学教师身份掩护陪伴丁玲母子返回湖南常德,一路倾力尽心,重担在肩,悲痛在心。
(一)纷杂与困厄的1931年
因路途耽搁,沈从文于4月才回到上海,等待他的却是武汉大学教职的失去。与此同时,沈从文在个人情感方面也不顺利,倾慕已久的张兆和迟迟没有回应他热情似火的追求,同时,师生恋引发的流言蜚语也让他颇为烦恼。事业与爱情的不如人意带给他精神上更深重的磨砺。
8月,沈从文返回青岛,应聘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过上了一段相对平和的日子。11月,噩耗再度传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沈从文于19日连夜赶赴济南,与这位亦师亦友的伟大诗人告别。[1]13-14
好友接二连三的离去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灵冲击,这引发他对人性与生命进行“抽象”的思索。沈从文在青岛的心灵状态,我们大致可以从《凤子》中窥见一二:
世界上一切仿佛正在把他忘却,每日继续发生无数新鲜事情,一切人忘了他,他慢慢地便把一切也同样忘去了。这一点,对于他自然是一种适当的改变。同一切充满了极难得的亲切友谊离远,也便可同一切由于那种友谊而来的误会与痛苦离远,这正是他所必须的一件事。一个新的世界,将使他可以好好休息一阵。[2]82-85
在遭遇如此多困厄之后,沈从文感受了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体悟出人性的弥足珍贵,此般思索构成了《月下小景》的创作底色。
(二)1932年的清净与转机
一切在1932年发生了转机。胡适和巴金与沈从文之间的真挚友谊让他重新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渐而走出大悲痛。这一年恰逢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返乡,8月初,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兆和,并与其家人见面,在此期间,张兆和默许了她与沈从文的恋爱关系,沈从文的苦苦追求终于在这个夏天尘埃落定,这为他带来无限欢欣。同时,他曾向张兆和的小五弟张寰和许诺,为他写一组取自佛经的故事,这便是《月下小景》集:
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年纪方十四岁,就在家中同他的姐姐哥哥办杂志。几个年青小孩子,自己写作,自己钞印,自己装订,到后还自己阅读。又欢喜给人说故事,又欢喜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去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3]215-216
这段话交代了《月下小景》集的创作动机之一。从表面看来,沈从文做这个集子是为了帮助小五读些故事,并希望他能够因此受到好作品的影响,能够知道“说故事时,若有出处,指明出处,并不丢人”的道理,并能“将各故事对照,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变成活的,简单的故事又如何可以使它成为完全的”[3]。不仅如此,沈从文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亦跃然纸上,即这些讲述人性的“故事”并非随意写就,而是意有所指——指向人性,拷问内心。
沈从文自认为1932年在青岛的生活逐渐接近一生中最旺盛的阶段。在青岛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沈从文收获了教学事业的成功、圆满美好的爱情和真挚动人的友谊,其文学创作也因之水涨船高。1983年,他在《小忆青岛》中追忆半个世纪前的岁月:“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他许多短篇也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4]174-175。可见,青岛确实是他灵感的源泉之一。
关于《月下小景》集诞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沈从文在题记中亦交代得明晰,因为在学校里教授小说史的课程,他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形体方面有所注意,同时发现佛经故事往往能够在短短的篇章中,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文体方面可资参考[3]。而根据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他对当年创作《月下小景》的心理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把佛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生命中属于情感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于是写成《月下小景》”“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另外一些方面作种种试验”[5]。此番表述似能更加贴切地反映《月下小景》集的诞生意义。
而笔者着重关注的《月下小景》这篇故事创作于1932年9月,是整个集子的序曲,集子也因此得名,其地位之特殊不言自明。经历了纷杂与清净的沈从文,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动人凄婉的爱情故事,在缠绵悱恻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人性深处的轻轻叹息,看到了人性在与自然和神魔间的沟通中闪现的夺目光芒,苍茫之中似有微弱却坚毅的声音在反复叩问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什么要做人?
二、 日头与月亮的背后:湘西世界中的自然与人
王继志在《沈从文论》中讨论《月下小景》集的归属时认为:“就故事本身而言,这些佛经故事属于异域文化,但就其对初民时代人生形态的描摹来说,不如说是对湘西古老民族的再现。”[6]171《月下小景》这个故事同样是以湘西世界的风土人情为背景,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相恋并相约自杀的故事,其中涉及大量对于自然的叙写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其间奥妙值得深思。
《月下小景》故事的开篇就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英雄追赶日月的故事。
这故事是这样的:第一个××人,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时,他还觉得不足,贪婪的心同天赋的力,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赶日头,找寻月亮,想征服主管这些东西的神,勒迫它们在有爱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点,在失去了爱心为忧愁失望所啮蚀的人方面,把日子又去得快一点。结果这贪婪的人虽追上了日头,因为日头的热所烤炙,在西方大泽中就渴死了……日月虽仍然若无其事的照耀着整个世界,看着人类的忧乐,看着美丽的变成丑恶,又看着丑恶的成为美丽;但人类太进步了一点,比一切生物智慧较高,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既不能用严寒酷热来困苦人类,又不能不将日月照及人类,故同另一主宰人类心之创造的神,想出了一点方法,就是使此后快乐的人越觉得日子太短,使此后忧愁的人越觉得日子过长。人类既然凭感觉来生活,就在感觉上加给人类一种处罚。[7]217-231
从这段神话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出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夸父逐日与“英雄”逐日
首先是关于这个英雄逐日的故事来源。英雄逐日让读者瞬间联想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8]224。《山海经·大荒北经》对此亦有表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8]299。《列子·汤问》中的说法与《大荒北经》篇相近,也认为夸父之举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但总体而言,大部分文献记载与后人评说均对夸父的行为表示了由衷的溢美,逐日被看作古代先民战胜干旱、影响自然的卓绝努力,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夸父的“道渴而死”无疑是为人类谋福祉而壮烈牺牲,可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但是,当我们把沈从文笔下的“英雄”逐日与《山海经》的夸父逐日相对照时,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对这个“英雄”的贬抑之意是不言自明的。“英雄”已经拥有超凡的智慧和武力,但仍不餍足,还希冀得到超越“人世一切幸福”的存在,即文中提到的掌握时间流逝急缓,进而主宰自然规律。如果说夸父对烈日的追赶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关爱之上,那么“英雄”的考虑则是完全出乎个人利益,甚至进而堕落成为贪欲的象征。从夸父的举动中,人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份不惜牺牲一切的、为理想而执着追求的探索精神;而从“英雄”的行径中,人们只能看到一种在个人利欲驱使下的对无上力量的扭曲而疯狂的追逐。再看两者结局的差异,夸父虽逝,其精神永远为世人铭记歌咏;“英雄”既亡,其行径却长久为世人敲响警钟。
(二)自然对人:凌驾主宰,不阿所私
人类作为万物中的一员,即使具有最高等的智慧和最发达的存在方式,他们也只不过是“刍狗”。沈从文在这里发现了一种触及人类本质、揭示人类命运的真理:在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自然凌驾于人类上方,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同时,“人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的主人,日月不单为人类而有”,人虽然是自然中最为高级的物种,但这不意味着他可以对其他物种任意压制、肆意凌虐;人类也不应用比其他一切生物更为严重的不道德来满足一己私欲,而应当在道德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一位伟大作家的创作是有一条明晰的精神线索的,前后作品应有相互照应之处,沈从文便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他1934年完成的代表作《边城》中看出他对自然对人姿态的关照,这与《月下小景》中所传达的自然对人的主宰是一脉相承的:
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9]66
“呆望”二字极为传神,将人类面对自然之神的那份无力匍匐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顺应自然的湘西子民,他们在自然面前也只能静默着感受其力量的不可阻挡。说到底,人类自始至终无法主宰自然,只能在自然的安排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正直地生活。沈从文离开古老湘西世界只身前往繁华都市,所经之处人性之丑恶与卑劣纵横蔓生,世间为工具理性与经济利益所充斥,实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他重返湘西也发现那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境界在城市文明的侵蚀下日渐式微,直至消失殆尽;但他相信,那些试图对抗自然、“剥削”自然以满足自己贪欲的人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走向人性的崩溃。
(三)人对自然:敬畏依赖,而非索求
面对自然的主宰支配,以常理度之,人类应当敬畏且依赖。在神话中,沈从文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太进步了一点,比一切生物智慧较高,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人类依仗自身作为万物中最高级的存在形式的身份,以及更加发达的头脑和更加复杂的思绪,所做之恶也就更多更坏。人类实在是一种劣根性很强的动物,一旦身居高位,就会想要摆脱自然规律对人性的限制,成为自然规律的制定者。此举实为本末倒置。
我们知道,沈从文内心深处对那一处自然、那一方生命无可怀疑的崇拜和对纯美自然人性无可遏止的追求,源于他对自然与人契合谐和的坚定认识,也源于他对现代城市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影响下的人性缺失、人心不古的痛切感悟[10]。沈从文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灵肉融合的自然人性,他将目光投向那片他熟悉而挚爱的湘西大地,将人性与自然的交汇点作为他关注的焦点。人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赖以存在的一切均源于自然,那么人在面对这份宏大的馈赠时不就应该心怀敬畏吗?人性中本存在一种“庄严意义”,是一种自然所孕育出的“人性的爱憎取舍方式,在这方式上保留下的较高尚的憧憬”[11]463-468。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沈从文在透视人类与自然关系之后,对民族社会现代启蒙的现实关怀,以及他对人类本身存在以及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寻的深刻思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韩侍桁对《月下小景》提出批评,并称沈从文为“一个空虚的作者”,是一个“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对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12]165,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沈从文在自然与人类的二元对立中强调对人性的高蹈并非浅薄,亦非将人性降格为人类的原始冲动,而是有自己的很深的意味的。
在卷积层,基于局部感受野的人体视觉原理,将输入图像或上一层的特征图与该层的卷积滤波器进行卷积加偏置,通过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输出卷积层的输出特征图(feature map):
他或许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去引领社会思潮,做一个“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只想透视人性,构筑起一座“精致、结实、匀称”、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让读到他作品的人感受到人性力量的伟大[13]1-7。人类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为物质肉体在时间空间尺度的存留,一为灵魂人性在生命深度尺度的保持。正如海明威《老人与海》圣地亚哥所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中人性之刚强,沈从文亦是发现了人性的不应磨灭性,从而对“我们为什么做人”的叩问进行了回答。人性与自然熔融,人性也就带上了自然的那份灵动与广博,万物与我相合,万物即我,我即万物。
三、 透析人神之辨:人与神各自的界限
在《月下小景》中,面对傩佑的赞美,女孩子有一句很美丽的回答:“还是做人好!你的歌中也提到做人的好处!我们来活活泼泼的做人,这才有意思!”[7]这里意指做人比做神要好。那么,在沈从文的语境下,神和人分别代表了什么呢?做人究竟比做神好在哪里?我们不妨从人和神各自的界限说开去。
(一)爱的伊甸园:凡夫俗子的世俗爱欲
我们在上文中说到,沈从文崇尚与自然熔融的人性,认为人性应当自然张扬而不受到外界环境的压抑,这在沈从文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他对自然纯真爱情的描写。他在《月下小景》中追溯了久远时代湘西的生活,凭借着常识和想象,把它描绘成性爱、宗教、自然三位一体的伊甸园[14]172。凡夫俗子们在世俗中往往为爱所约束,爱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与唯一性,这也是人区别于神的最重要差异。而在爱中,最为人唏嘘扼腕的当属一份不得善终的爱情了。
《月下小景》取材自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明月朗照,和谐雅丽,山寨、树林、平田、稻草与谷仓都浸润在这片宁静温和的清辉之中,而那一双小儿女也正在这月夜下,体验他们萌芽于春天,又成熟于秋日的爱情。他们表现爱的方式是传统的苗歌对唱,或纯真甜蜜,或忧郁感伤,爱情的纯净与执着似涓涓细流汩汩涌出,“幸福使这个孩子轻轻的叹息了”[7]。但是,正如逐日神话所叙述的那样,美好的月下时光总是短暂的,这对小儿女必须要面对本族人一个来源极古的风气,这风气让初恋的有情人不能得到灵与肉双份的爱:因为处女被认为是一种有邪气的存在,娶了这样的女人男子会遭遇不幸,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奇怪的规矩:“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地窟窿里”[7]。因此,倘若女子要与她所心爱的男子结婚,就必须要找另一个男子来尽一下“义务”。但是这种近乎宗教仪式的“初夜权”往往不为那些与自然的神意合一的年青男女所认同,“女孩子总愿意把自己整个交付给一个所倾心的男孩子,男子到爱了某个女孩时,也总愿意把整个的自己换回整个的女子”[7],因而常有人牺牲在这规定之下。他们两人试图用出走来维护爱的尊严,但是东南西北四方竟然都没有他们可以容身的地方,唯有死亡能让他们永远在一起。于是他们便相约服毒自尽,共赴黄泉了。
沈从文描绘的无疑是一个爱情悲剧,但是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并非痛彻心扉的伤感,而是一种哀而不伤的淡淡的情绪,似乎这注定的命运笼罩下的爱情就应当有这样一个恰如其分的结局。这与沈从文对故事的处理方式是分不开的。缠绵悱恻的爱情与凄美婉丽的结局,本该是对读者感官发起狠狠的冲击的,但是沈从文并没有一味渲染死亡的悲哀与绝望,而是将这份忠贞之爱的力量延续到死亡之时,甚至是死亡之后,留给读者的是无尽萦绕的对纯真之爱的感动。
爱情,常常被视为人生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沈从文在《月下小景》中围绕爱情谈了三个维度的问题:恋爱、欲望与婚姻,并以人性为线索,在这三个维度中注入了湘西人民特有的生命的鲜活与青春的激情,展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没有船舶不能过河,没有爱情如何过这一生?”爱情在沈从文的语境下是人生命的象征,是“生的一种方式”[15]3-29,而被视作自然自由的人性的体现。沈从文崇尚人性的自然张扬,人性不应当被他人、社会、习俗等外界环境所压抑,而应当在自然的规律下逐渐成熟:“秋成熟了一切,也成熟了两个年青人的爱情”。但是现实的残酷总是让一份自然纯真的爱无疾而终,古老习俗的压迫使得爱情与婚姻不能得到完满的对称。“这世界只许结婚不许恋爱”,一句喟叹,万千心酸。
海明威曾言:“最好的写作一定是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在前面提过,沈从文写作《月下小景》的时候,张兆和承认了与他的恋情,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沈从文后来在《湘行书简》中无不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同时,他还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16]143-145。现实中的爱情带给沈从文无尽的灵感,将一份张扬与肉感带入到作品中,流露出他理想中的爱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理想”并非取结局“圆满”之意,而是意味着《月下小景》这一类故事描绘的是湘西人民理想中的爱。这种爱情并非是因为现代物质文明对人性和爱情污染而失败,而是因为千年来的传统习俗以及湘西世界本身带有的愚昧与蛮荒,使得有情人最终只能在黄泉双宿双飞。在《水云》中,沈从文曾言:“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5]这些“乡愿蠢事”对爱情与人性的压抑,正为沈从文所深恶痛绝。
但是即便有了这样一个悲哀的结局,沈从文依旧让爱情的光辉普照人类生命的殿堂。在这个爱情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爱的纯真与热烈,其中透出的人本主义精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亚当夏娃生活的、不需要思索明天之事的伊甸园。或许爱情的确不需要那么多的考虑,活在当下不失为一种使人生无悔的生命形式。就像《雨后》中上山采蕨的四狗和阿姐,就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共赴黄泉的媚金和豹子,就像《阿黑小史》中婚前幸福的阿黑和五明,他们的爱情短暂却火热,人性的自由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恣意挥洒,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图自此徐徐展开:健康、优美而崇高。
(二)凝眸相望的彼岸世界:人类的生死界限
王德威在论述沈从文批判的抒情时,曾经对爱欲与死亡的关系进行这样的说明:“在他最好的浪漫小说中,爱欲时常献身于孩童般的天真之中,同时孕育一种非理性的狂暴力量。这种热情发展至其极致,便构成(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力量”[17]258。的确,爱情与死亡在沈从文那里是相伴相生的,爱情因为有了死亡的笼罩而拥有宿命的神秘,而死亡也因为爱情的相伴而不那么寂冷。爱情是人生的形式之一,而死亡终究是人类真正的终点。人或自愿或被动地奔赴彼岸世界,是自然规律使然,亦是人性安憩之归向。
《月下小景》中的青年男女为了成全那份不能得到的完满爱情而服药自尽,他们双双归向彼岸的画面是异常美丽的:
寨主的独生子,把身上所佩的小刀取出,在镶了宝石的空心刀把上,从那小穴里取出如梧桐子大小的毒药,含放到口里去,让药融化了,就度送了一半到女孩子嘴里去。两人快乐的咽下了那点同命的药,微笑着,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等候药力发作。
他们的结局正如那歌声中唱的那样,真的生存意义结束在死亡里,而战胜命运的只有死亡,死亡能够克服一切,因为在死亡的境域中一切都可以实现,世俗的规制在死神面前不过是人类的小把戏罢了。沈从文在这里将死亡或者说是自杀合理化,把死亡视作新的轮回的开始而非生命的终结,只要人性留存,一切都可以在彼岸世界得到延续。这一方面表现出人性最终战胜了魔性的世俗旨意,青年男女用他们片刻之间死亡的痛苦,来换取美的生命的永生, 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但是,沈从文并不是肤浅地认为归尘入土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作为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命状态的思想者,他对人活下去这件事其实是相当看重的:“人实在值得活下去,因为一切那么有意思,人与人的战争,心与心的战争,到结果皆那么有意思。无怪乎本族人有英雄追赶日月的故事。因为日月若可以请求,要它们停顿在哪儿时,它们便停顿,那就更有意思了”[7]。沈从文幼年和青年时期看杀人、数尸体的经历留给他的不是对生命代谢更迭的冷漠,他其实比谁都要热爱生命,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不仅表现在生命长度的延续,而更表现在生命深度的扩展,亦即人性层面的纵深,而且有时候为了扩展生命的深度,生命的长度也是可以暂时舍弃的,正如那对从容赴死的少男少女。这不是认命,不是匍匐在生命的藩篱之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直面死亡;这也不是向死亡宣战,而是承担与跨越死亡的恐怖与悲痛,而成为生的勇士。此外,即便此岸的人生种种受制,但做人的诱惑远远大于成神成魔。其实,正是因为了有些限制与不如意,人生才会那么有意思,人性的伟大才能显现出来。
(三)与人性交融的神性——神的界限在何处?
首先,我们要对“神”的概念有一个界定。在沈从文的笔下,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指“神”的存在本身,那种寓于自然的不可违抗的不可知的超越存在,是人们深深信仰的匍匐的对象;第二种是指“神性”,即一种抽象的美和爱的境界,它以人性的本真与自由为前提,是沈从文对前一概念的升华与重造。“还是做人好”中与“人”这一概念对立的是“神”的第一概念,而人所具有的极致人性则可理解为“神”的第二概念。
《月下小景》中多处出现人与“神”的比较,此处笔者摘录几句进行探讨:
1.他觉得神只创造美和爱,却由人来创造赞誉这神工的言语。向美说一句话,为爱下一个注解,要适当合宜,不走失感觉所及的式样,不是一个平常人的能力所能企及。
2.神同意的人常常不同意。
3.神的意思不能同习惯相合,在这时节已不许可人再为任何魔鬼作成的习俗加以行为的限制。理知即或是聪明的,理知也毫无用处。
4.痛恨日头而不憎恶月亮。土人的解释,则为人类性格中,慢慢的已经神性渐少,恶性渐多。
5.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张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如本地人所说的藏吻之巢窝,无一处不见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眫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神同魔鬼合作创造了这样一个女人,也得用侍候神同对付魔鬼的两种方法来侍候她,才不委屈这个生物。[7]
前三者属“神”的第一概念,后两者属“神”的第二概念,在比较中,“神”本身的局限性与“神性”的超越性被凸显出来。“神”本身的界限在于它对人类的主宰和对人性的客观抑制,这一点与自然对人的姿态是相通的,神以凌驾的方式将美和爱展现在人类面前,关于人类如何去体悟它、如何去获得它,则不是“神”所关心的事情,这与基督教中神的不可知性很相似,但是又有所区别,湘西世界的神重于自然,颇有春秋战国阴阳家之“序四时之大顺”的意味,而非基督教上帝那么顽固而超脱万物。
神性是一种生命的本质性规定,它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体现在一些具体而微之处,如人的性格、外貌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作为一个主体主动地去追寻美和爱的终极产物。美就在人的举手投足之间以及发自内心的话语行为之中,爱则以正直诚实为前提,以本真自由为法令,是一种“泛神情感接近的美”[18]。神性又体现在对神本身的反思,发现它的界限,攫取其超越性的部分与人性相融,以形成一种原始、单纯、雄健、热情的美好人性。
人的生命会受到爱与死的限制,而神的界限在于它无法体悟人性特有的纯净,两种存在都有自己的美好与局限。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选择做人,只因为人性可以超越人的生命本身,勘透生活中遭遇的磨难与痛苦,跨越生与死的界限,达到神性的境界。这种在残缺中追寻完满,在死亡中追求永生的生命哲学,正是沈从文作品中坚忍不拔的理性主义光辉的最佳写照。
结语
我们为什么要做人?沈从文借《月下小景》巧妙地回答了这个人性问题。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中,还是在人性与神性的融合结构中,人都能凭借其耀眼的人性光辉笔直地站立在生命的洪荒之中。这不仅是因为人能够具有一份源于自然、与自然同辉的健康人性,更是因为这份人性能在人生历练中,通过对彼岸世界的凝眸与对超越性存在的追寻而获得神性。倘若没有这份神性,那么沈从文只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人性主题潮流中的普通一脉;沈从文之所以为沈从文,正是因为他比别人要想得多一些,也要远一些。人性在自然中成长,在神性中升华。人性、自然和神性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三元范畴,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与精神主旨。而在这些背后,我们能读到沈从文对人性不存的深切担忧和对重造生命的热切愿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沉地爱着这个国家和它的子民。在战乱与磨难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渺小与脆弱,很多人面对苦难会轻言放弃生命,沈从文给这群人以精神力量;在和平与安乐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生活的无趣与庸常,很多人面对安逸会无所适从,沈从文便给这群人以心灵鞭策。这份澄澈纯净的对人性的执着追求,构成沈从文一生文学创作与生命姿态的真实写照,直至今天,我们仍能在其中汲取精神的养分,努力、正直地去做好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