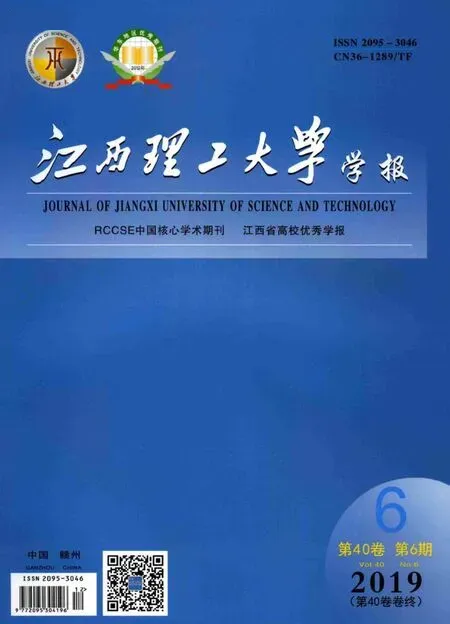“一带一路”背景下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现状及前瞻
2019-03-05李火秀
李火秀
(江西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341000)
巴基斯坦(全称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曾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 年6 月,印巴分治,同年8 月14 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巴基斯坦民族语言繁多,主要民族有旁遮普族、信德族、巴丹族、稗路支族等。巴基斯坦的语言繁多如:孟加拉语、旁遮普语、信德语、乌尔都语等,彰显出巴基斯坦语言系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概观
巴基斯坦的双语或多语现象十分普遍。巴基斯坦独立前,所用的教学用语为当地的信德语和普什图语。1948 年,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支持乌尔都语作为国语。 信德省有69 所学校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教学用语。1948 年6 月,巴基斯坦召开了第一次教育顾问委员会会议,与会人员呼吁小学阶段应该以母语作为教学语言。 之后,乌尔都语委员会成立,讨论乌尔都语取代英语的问题。 不过此时英语仍然占主导地位。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巴基斯坦的总统是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他赞同学校使用英语。 1959 年,国家教委宣布乌尔都语为普通学校6 年级以上的教学语言。 有些大学,如卡拉奇大学、旁遮普大学、信德大学,在考试中也使用乌尔都语。此外,乌尔都语成了所有中小学的必修课。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撼动英语的主导地位。 1966年,信德的一些大学使用信德语作为教学语言和考试语言,不过,政府随后将其禁止。 因此,信德语仅在一些农村学校使用。
20 世纪70 年代,穆罕默德·叶海亚·汗执政,他公开支持精英教育。乌尔都语团体提议教学语言改用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而其他各省则坚持使用本地语言来进行教学。 1972 年,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执政。 1973 年,《宪法》认定乌尔都语为国语,在《宪法》第251 条规定:巴基斯坦的国语是乌尔都语,在15 年之内应该安排乌尔都语用作官方语言和其他目的。布托此举对于奉行英语的精英群体无疑是一种挑战,而对于坚守乌尔都语的中下层阶级而言,则带来某些希冀。 1977 年7 月5 日,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实施军法统治。齐亚·哈克被称为“乌尔都语的保护人”,他命令从1979 年起,所有学校一年级开始采用乌尔都语授课。1978 年,巴基斯坦政府颁布新的教育政策,规定巴基斯坦教育分3 个阶段:小学和初中为初等教育;高中、中间学校为中等教育;专科学院和正规大学为高等教育。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初等教育,小学一般开设语言、数学、巴基斯坦知识、伊斯兰教、体育、艺术和卫生等课程。初中阶段增设英语和职业课程。“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采用英语授课,公立学校的教学用语多为乌尔都语。 ”[1]1983 年10 月11 日,齐亚·哈克强调英语的重要性。 10 月28 日《巴基斯坦时报》报道,教育部决定教学语言除了使用乌尔都语或各省地方语言以外,英语仍可继续使用。
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贝·布托执政,他支持使用英语教学。1989 年,教育部召开高层会议,讨论如何废除或缩小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落差。 同年5 月2 日,教育部声明“从一年级开始,所有课程都可以选择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如果教学语言是乌尔都语或各省地方语言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还必须另外开设英语课”[2]。 2000 年以来,乌尔都语在国内广泛应用,不过“英国在印巴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英语在大中城市相当普及”[3]。 因此,英语始终居主导地位。此外,伴随世界“汉语热”的兴起,巴基斯坦也“掀起汉语学习的热潮”[4]。 汉语作为巴基斯坦的重要外语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010 年访华期间,提出在信德省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计划。 2011 年9 月,信德省政府宣布从2013 年起在全省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6 年级以上课程设立汉语必修课,以推广汉语教育。2012 年9 月5 日,“巴基斯坦首个中文必修课在信德省海军附属学校正式开课。 校方把汉语课程开设在低年级,每个年级保证一周有三节汉语课。”[5]2015年,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颁发一个新的法令:乌尔都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取代英语,“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及4 个省份要在3 个月内完成官方语言转换工作”[6]。巴基斯坦政府通过积极的规划和措施,确立了乌尔都语作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重要地位,凸显国家意志在语言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
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迁延,表明巴基斯坦在服务国家战略、地方利益、民族关系、语言规划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首先,语言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一部分,不仅是多民族之间调节民族关系的有力手段,而且与执政者的执政理念、 利益权衡等因素关系密切。早期巴基斯坦语言政策主要考虑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 巴基斯坦独立后,其语言政策更多反映当权者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理念与利益诉求。巴基斯坦在各地学校所奉行的多种教学语言的冲突同样反映集团或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由于巴基斯坦的多语言社会背景,巴基斯坦官方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充满问题和冲突,语言政策、举措的颁布、实施总是引来争议。 “语言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变量之一,其中多民族国家在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及推广上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族际冲突,对其和谐关系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 ”[7]如巴基斯坦独立后,当权者试图弱化英语的影响,大力推广乌尔都语,推行“乌尔都语为国语”,这一举措不仅使奉行英语的精英阶层极为不满,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众也心生不满。 如信德族、俾路支人(Baluchistan)和锡耐基地区的民众,这些地区的人们坚持按照多种族原则,使用本地语言作为教学媒介。 由此引发统治阶层与种族和民族主义者之间长久的激烈斗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因‘国语’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即是突出的例子”[8]。
事实上,独立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本土语言作为国语,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国语、官方语言时,应该考虑基本诉求,尤其是依据本国语言实际,不能以强硬措施加以推行。 如巴基斯坦独立伊始,中央政府尝试阻止巴基斯坦本土语言发展,并确立乌尔都语为国语。 这一举措激起孟加拉人的民族感情, 民族关系矛盾日益尖锐。 当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在他们的母语遭到排斥后,他们则强调自己是孟加拉人,并使用孟加拉语言来宣示他们的民族身份,受孟加拉语教育的精英分子直接将孟加拉语用作反对霸权主义的手段,极大地唤醒了孟加拉人本土身份意识。而这一场语言运动的结果是逐渐发展成抵制巴基斯坦人的统治和内部殖民主义运动, 最后导致孟加拉国的诞生。 可见,语言教育政策作为民族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关系协调、维护社会稳定和捍卫国家统一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从本土语言教育来看,本土语言对于历史文化传承、民族身份认同发挥重大作用。 巴基斯坦已经认识到这点,并对此格外重视。 巴基斯坦独立前,信德语和普什图语是唯一作为主要教学的用语。 巴基斯坦建国后,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国语和中小学的教学语言。 不过,1973 年巴基斯坦宪法又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其中,信德省教学用语较为独特,该省中小学的教学语言是信德语,学习乌尔都语作为必修课程。 时至今日,信德语仅作为本地语言使用。 无独有偶,普什图语也只是作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 一份关于普什图语的报告指出:普什图语并不是初级学校的教学语言,使用普什图语教学语言的学校不如使用英语和乌尔都语的学校多。
第三,从外语教育政策来看,主要表征为:一是英语的普及化。虽然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应用最为广泛,但由于“英国在印巴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英语在大中城市相当普及”[3]。 因此,外语教育方面注重英语的学习。 尽管乌尔都语是宪法规定的国语,然而英语的地位却相当稳固,中上阶层都支持使用英语,在子女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他们更倾向于送孩子到英式教学的学校接受英语学习教育。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显而易见。 作为英殖民地,英语是巴基斯坦的教育、行政和文化语言。 1947 年,巴基斯坦建国以后,乌尔都语获得国语地位,但这只是个表面现象。 事实上,英语一直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语言。 二是外语使用的区域化。 巴基斯坦目前存在多种各不相同的语言教育形式。乡村和中小城市的中小学,一般都用乌尔都语或地方语言教学;在多数大中城市,小学仍用乌尔都语教学,贵族中学一般用英语教学,普通学校用乌尔都语教学;在大中城市的贵族学校一般使用英语来教学,乌尔都语用作必修课程,一些普通学校和宗教学校,英语则是外国语。 外语使用的区域化,展现了巴基斯坦语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同语言的地位存在着区域性差别。 可见,尽管当局采取立法和行政手段使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语言享有特殊地位,但多语现象仍然是巴基斯坦的语言现状。三是“汉语热”效应。据悉,“中国已在146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孔子学院526 所,孔子课堂1113 个。孔子学院总部在全球130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1100个。 ”[9]此外,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势头强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累计已在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304 所示范华文学校,帮扶294 所困难华文学校或新兴华文学校,支持25 个重点华文教育组织,设立607 个华星书屋。 ”[9]这些数据表明,未来汉语作为国际语言中沟通的“桥梁”的作用将愈益彰显。自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巴基斯坦设立汉语教学基地以来,巴基斯坦汉语教学有了长足发展。 “汉语热”已渐成为巴基斯坦国内新的语言动向。尤其是近十年,汉语在巴基斯坦得以迅速传播。伴随中巴经贸往来的密切,尤其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重要支点国家,汉语在各个阶层的使用也会更加频繁,“汉语” 将在未来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三、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的未来展望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10]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 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如何参与到这一伟大构想,推动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中巴的互联互通,是值得探索的命题。展望未来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的走向,归结如下。
首先,需要构建尊重多元的语言教育政策发展方略。 这里涉及母语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也涉及国语、官方语言与各地方言的关系问题。从政策规定来看,巴基斯坦对官方语言、国语和外语(主要是英语和汉语)在教育系统进行了规划,在全球化世界中,“学校正迅速成为复杂的多语言环境。语言教育政策必须在全国通用语言读写技能的较高要求和几种非母语语言不断提高的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语言教育政策不仅对于语言技能非常重要,而且对提高跨文化意识以及提高对‘他者’的积极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11]可以说,不管是从外部环境的推动,还是从国内自身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角度,巴基斯坦在推广国语、官方语言的过程中,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坚持多语主义政策,培养公民多语言能力,应当是其主导发展方向。
其次,需要积极重塑开放、国际化的外语教育政策。全球化的复杂性使我们认识到提高各种语言能力,以及扩展语言、文化和交流各个方面知识的重要性。关于外语教育,语言学专家王辉认为“英语无疑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最重要的语言”[12]。 这表明英语语言教育的普遍化与深入化,而国际化趋势,势必使英语在日后的国际交流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开放、国际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尽快适应世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是汲取全球化发展红利,在互利互惠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积极应对之策。
巴基斯坦国内近十年来兴起的“汉语热”是其呈现的语言发展新趋向。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也日益开放,应时而上。 目前,汉语基本是他们的第二外语甚至是第三外语。 2018 年3 月20 日,巴基斯坦官方发布通告:“考虑到中巴经济走廊框架(CPEC)下两国合作日益紧密,参议院鼓励当下以及未来中巴经济走廊人力资源培训项目都要开启学习中国官方语言的课程,以降低沟通的成本。”[13]种种迹象表明,巴基斯坦顺应国际形势在语言管理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不过,在语言规划格局趋于平稳的背后,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问题。 比如如何制定高效而具体的外语教育政策; 如何对待未进入语言教育系统然而在为地方所使用的方言等。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全球化的推动下,以国家发展目标及利益为驱动的巴基斯坦语言教育政策,特别是外语教育政策,必将迎来新的发展要求。 如何进一步加强或细化语言教育政策,寻求全面提高国内语言教育质量策略,是未来巴基斯坦亟待面临的重要题域。
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地缘、外交和语言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观察和阐析巴基斯坦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教育政策,可为中国语言政策提供启示。一方面,我国不仅要重视国内的汉语教育,提高国人汉语水平,同时,加大汉语国际传播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外语教育方面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目前我国面向非通用语种的语言资源储备明显不足,语言教育薄弱(国内大约只能开设20 门非通用语种的课程,其中很多语种只有1 所高校能够开设),语言人才奇缺,语言服务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14]。因此,“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应该覆盖沿线国家全部语种,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以英语教育为主,另增加一门第二外语选修课程。 高中阶段的外语教育课程可开设三四门外语语种,高中生可以自由选择两门外语必修课。 在高等教育阶段,除欧洲主要语言外,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官方语种,设置相关语言专业,为高校大学生提供学习多种外语的机会,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出国深造、专业发展、 职业规划提供选择余地,扩大发展空间,增加就业机会,扩大语言服务范围,提高语言服务质量,为“一带一路”发挥语言铺路的辅助作用。 伴随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多种语言和多语交流将是未来可期的发展图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跨国界、 跨文化意识积极融入并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