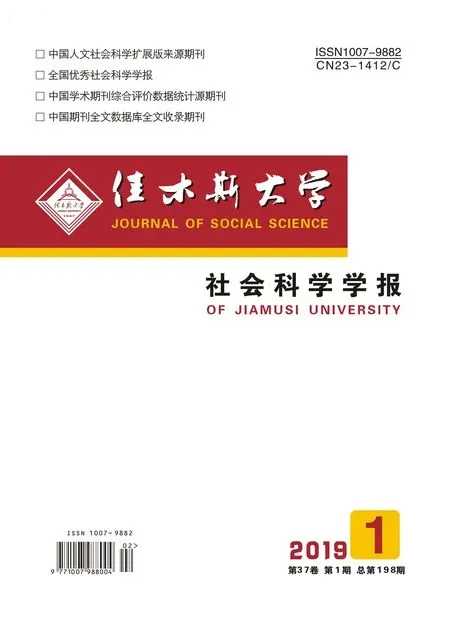《周易》与《中庸》的关系研究*
2019-03-05阴苏哲
阴苏哲
(吉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一、 《周易》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源泉
(一) 古今学者对《周易》与《中庸》关系之概述
在古代,研究周易、中庸两者关系的学者不胜枚举,尤其是在两者处于融合期的宋代,更是出现了一批以《周易》解《中庸》的理学先驱。正如魏了翁在祠记中记载:“一日,有讲授於学官者曰:‘伊洛之学以《中庸》为宗,诚敬为教者也。’仆闻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俱此理,而为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龙德而中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内。然则曰《中庸》曰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贯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1]228此外,程颐、程颢的《二程集》中也明确点出:“或问:‘系词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系词虽始从天地阴阳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不见,听之耳不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2]141等等,并且,此后的学者,如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利用乾、履、泰、咸等卦,对《中庸》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等著作中,大量运用以《中庸》阐发《周易》思想的方法,对后世之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近现代的中外学界对《周易》与《中庸》的关系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及论述,且观点大致相同,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庸》与《周易》的关系论述,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分内外探讨其关系,如熊十力认为:“中庸本演易之书。”[3]1萧箑父也认为:“《易传》与《中庸》义理相通。”[4]95第二类是分内、外探讨其关系,如李泽厚等人认为:“《周易》是世界观,《中庸》则将它转化为内在论。……所以,虽同为儒学正宗,二者在思想倾向上并不一致。”[5]130-131虽然学者研究的致思方向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易》与《中庸》的认识基础是一致的,即都肯定人性善。此外,《周易》与《中庸》在对于人的修养问题的原理以及原则性方法的理解上也是大致相同的。故而,金德建说道:“子思写作《中庸》时,明确吸取了《系辞》、《文言》、《象传》之词。”[6]174而国外学者对其关系研究较少,且着重点在于两者的成篇时期,其中,值得关注的著作有:(日)武内义雄的《易与中庸之研究》,在文中,他显然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割裂的关系。另外,(韩)南明镇的《关于孔夫子的时间观和历史哲学之研究》一文,他在文中对《周易·十翼》及孔门诸子所著的《中庸》《大学》等有关资料进行考察比较等等。可见,国内外学者均认为《周易》与《中庸》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子思与《周易》的关系概述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学界对于《中庸》的作者,基本形成了共识——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这也是对“子思作中庸。”[7]1946的考证。然而,对于子思与《周易》的关系阐述较少,因此首先,就其师承而言,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其师一般不出子贡、子夏、子游、曾子等人,而以上几人均与《周易》有着紧密关系,故其思想定对子思有重要的影响,如:《缪和》、《昭力》中明确提出了,孔子以《周易》教子贡、子夏。[8]尤其是子夏,学界根据出土资料对子夏学易、作易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证明子夏作《子夏易传》。[9]而根据郭店楚简,对曾子的《天圆》进行研究,可知其思想不仅与易有关,而且表明儒家早将《周易》纳入理论体系且涉及人伦。[10]可见,子思之学必然与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子思不但学《周易》,而且在其著作中常用《周易》;甚至作《周易》。学易在师从上已有提及,并且从其著作《表记》《坊记》里均有提及;其用易,主要体现在其《中庸》一书,金德建曾“举出十二例,来论证子思曾用易作《中庸》。”[6]172-173而(日)武内义雄也曾讲到:“在现存的儒家底文献中,称引易的,最早恐怕是认为子思子底残卷的礼记中的表记纺记缁衣吧。”[11]而子思作易的直接证据,则是在帛书《衷》篇的发掘、研究后而有所论证的,刘彬认为子思作帛书《衷》篇,[12]且其论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中庸》作为是子思中晚期思想的总结,其哲学思想确是以《周易》为根本的,因此,《周易》确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源泉。
二、《中庸》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一)《中庸》对《周易》爻象及爻数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周易》各卦均是由爻象和爻数这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爻象者,易卦之爻所象之事物也,只有阳、阴两种;爻数者,易卦各爻所居之位次,即爻位也。”[13]30-32两者作为《周易》各卦的基本组成要素,被《中庸》继承并且发挥。
首先,就爻象而言,《中庸》不仅体现了其社会性,还体现了其自然性。“阴”、“阳”两者的社会属性,直观体现在《中庸》的“君子”、“贤人”、“圣人”与“小人”、“不肖”之别。“阴”象征柔、顺,故而反应在社会属性上便是“才德薄弱”的“小人”之象,而“阳”则与“阴”相反,故而“阳”为“才德兼备”的“君子”之象,正是因为“阴”、“阳”两者所表现的社会性有所差别,故而,儒家后学著《中庸》一书,作为孔门修习之心法。但“阴”、“阳”所体现的自然属性并无差别,“阴”象地,“阳”象天,故而《中庸》提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懈,万物载焉;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14]35由上可见,《中庸》不仅继承了周易的爻象思想,还将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进行发挥。
其次,就其爻数思想而言,《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4]17就已经大致点出周易的爻数思想。爻数又称爻位,周易各卦均有六爻组成,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其总体表示着事物发展的本末始终。不仅如此,六爻还点明“三才”,其中初、二表示地道,三、四表示人道,五、上表示天道,这在《中庸》首句中有所提及,其中的“天”正是天、地两道;其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於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此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於学。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是由仁义行也。则是性已矣,故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2]30的表现;而最终便落到人之“修道”工夫上。除此之外,《中庸》对《周易》爻数思想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首先,《中庸》通过《周易》的爻数思想,进而点明中庸之道难行之原因。《中庸》的“过犹不及”,可能是对《周易》爻数中的初,三、四、上的深刻理解之后,而有所感悟。不及者初与四两爻,过者三与上两爻,占《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的2/3,并且以上四爻,少有吉者。初爻微而未显,故而《中庸》要求“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4]17而就三与上两爻而言,“三爻之不吉者,约为五十一卦,占三百六十四爻的13%,上爻不吉之卦约四十,占六十四卦的62.5%。”[15]44而对于不吉之原因,在《中庸》也有所点明:一是:“小人”的“无忌惮”;二是:“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其味也。’”[14]19综上所述,不过是难以适当地节制自身的欲望,故而“百姓日用而不知”[16]45,进而,难以达至“中庸之道”。因此,孔子发出“中庸之道”恐怕难以实行的感叹。《中庸》作为“孔门之修习心法”,继承并发扬了《周易》“中”的思想,其“中”在爻数中表现为二与五爻,而“在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中,二五两爻俱不吉者,无也。二爻凶者,仅剥颐井节四卦,六五爻不全吉者三卦:屯、师、小过。总共七爻,只占三百八十四爻的2%弱,中而不吉者九爻,仅占全部中爻(128爻)的7%强。”[15]9可见,二与五爻对“中”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作用恰恰被《中庸》所吸收,就其书名来源而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14]14可知,《周易》的“中”之思想,对《中庸》的意义尤为重大,并且,金景芳先生对爻数之二、五两爻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二、五之中,相当于未发之中,其特点是不偏不倚,恰在中道。”[17]这也是《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4]18的体现。不仅如此,(日)武内义雄也将“中”字作为《中庸》与《易传》成书之重要依据。[18]33-37可见,爻数思想对《中庸》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综上所述,爻象与爻数作为《周易》各卦构成的最基本要素,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论述《中庸》对《周易》的继承和发展,必然从《周易》的基础入手。
(二) 《中庸》对《周易》卦爻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中庸》与《周易》均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故而,对其关系研究应着眼于整体。因此,想要全面了解并研究其关系,应明确两者的系统结构,以免阐述过于片面或内容交叉重复。故而,以《周易》各卦的义例体系为基础,进而具体讲述《中庸》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周易》的义例体系是由爻象与爻数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是最能体现《周易》思想的桥梁,基本可以分成“时”、“德”、“当位”、“序”等四大义例体系。其中“时”最为基础,毕竟“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19]409同时,对“时”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时间或空间,要明确“盖时则能中,中则 能正,正则能顺,順则能应,此必至之符也。操此枢要,以御天下之变,自能因应无穷,而有‘位育’之功焉。”[20]91除此之外,其余三大义例体系只做简单阐述:“德”为吉;“当位”在于阴阳二爻所处的爻位,阴爻处奇数位为当位,阳爻偶数位为当位,反之,则为不当位;“序”指的是“义”。《周易》各卦的变化发展,均与义例体系密切相关,而《中庸》也是在对其义例体系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而对其思想进行继承与发挥。以下便以《序卦》为基础,以各卦所表现的义例体系,阐述《中庸》对其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乾卦(□)六爻皆为阳爻,无乘无比,且九二中而不当位,九五中正当位。虽然九二不当位,但其结果是“利见大人”,是吉,这正应了《乾·文言》中:“子曰:‘龙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21]8而此言中的“庸”之思想被《中庸》所吸收,并体现在“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也:……,君子胡不慥慥尔?”[14]23-24可见,九二虽然不乘不比且不当位,但其有“中”德,故而能“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21]13这与《中庸》“诚之道”的方法论之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4]32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论乾之九五,九五中正当位,为乾卦之主,虽与九二均称“大人”,但九二象“君德”,九五象“圣人之德”,故而唯有“圣人之德”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1]14这在《中庸》中的第二十九章、三十章、三十一章等有具体的体现,不过《中庸》中的“圣人之德”明确提出以“诚”贯通。其次,讲述《中庸》对《乾·文言》的继承和发扬,《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故曰:‘乾:元,亨,利,贞。’”[21]7此语明确提出了君子四德,且以“仁”为本,故而《中庸》提出修道应以“仁”的总纲,同时,《中庸》将四德明确并一体,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生也。”[14]28此外,《中庸》也将“四德”转化为“五行”,“‘宽裕温柔,足以有容’是仁的表现;‘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是义的表现;‘齐庄中正,足以有敬’是礼的表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是智的表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是圣的表现。”[22]从中可知,《中庸》将“仁、义、礼、智、圣”的外在行为转化成内心道德,将“德行”与“德性”明确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周易》中没有明确点明的,而子思将其建构成独特的儒家五行说。[23]最后,讲述《中庸》对乾卦用九思想的继承与发扬,用九在六十四卦中,仅有乾之一例,其《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21]4此句点明《中庸》“诚”之思想。周敦颐认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也。”[23]22这恰是《中庸》“诚”之道的合理解释,“诚者”是“天之道”故而出自“乾元”,“诚之者”作为“人之道”其目的便是“正性命”其方法便是“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唯天下至诚为能化。”[14]33进而“保太和”最终,与天地相合,参化万物。可以说乾之用九,正是《中庸》“诚”思想的来源。然而《中庸》是由人及天的修养方法论,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周易》的致思方法恰恰相反。但这正表明了“子思扬弃了孔子晚年以‘易’、‘乾坤’、‘阴阳’以及其构成的宇宙生成论来论证人性的思路,并重新使用‘天’,以代替孔子晚年‘易’,进而从道德性入手,来探讨人性的思路与方法。”[24]
蒙卦(□)讲教育之法,由四阴爻二阳爻组成,有乘有比,且九二与九五皆是中而不当位。首先,其《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16]137其中的“行时中”在《中庸》的君子之中庸为“时中”一语中有所体现。其教育方法及态度为“筮”即“诚”,进而能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儒家教育不外乎:“文、行、忠、信”[25]85,而“《中庸》下篇‘诚’字,作名词用,而作名词用之诚字,乃《论语》‘忠信’观念之发展。”[26]121可见,《中庸》以“诚”教人,合于四教之中。并且儒家常以诗言教,常以诗言德,而《中庸》中提诗共有14次,均不离“德教”一意。故而《中庸》将《周易》的教育思想具现化了。其次,《中庸》对九二之思想有所吸收,“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16]138九二为蒙卦卦主,且有刚中之德,与六五相应。故而,居九二之位,不能以明而自专,必定能纳天下之所善,获乎上之信,进而可发天下之蒙。这在《中庸》“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诚乎身矣。”[14]31已明确获上并治民之道。而其六五以阴居阳位,然能吉,就在于六五以柔居君位,下应于九二的“刚明之才”,故而为吉,不过居六五之君,要能至诚而任贤,而对于任贤之道,《中庸》已有提及“去馋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所以怀诸侯。”[14]30-31最后,其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16]141也点明了中庸之道的灵活性,上九为蒙卦的顶点,但阳居阴位,具有弱顺之质,要求击蒙时注意适度原则,正如二程之言:“教人之术,若童牛之牿,当其未能触时,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则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以难治,以百万制之,终不能使之改,唯豶其势,则性自调伏,虽有牙亦不能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须置其槚楚,别以道格其心,则不须槚楚,将自化也。”[2]14要“执其两端,用中于民。”[14]20进而才能达至上下相顺,最终成就治蒙之功业。
履卦(□)讲礼治思想,乃德之基也。其卦由五阳一阴构成,九二中而不当位,九五中正当位。首先,其《彖》曰:“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16]159该句点明礼之重要及用礼之法。其象辞表述更为明显“君子以辩上下定民。”[16]159这与《中庸》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生也。”[14]28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在《中庸》的第十八、十九两章中描述的极为细致。其次,履卦初九阳居阳位,无乘无应,且位于履卦之始,尚未被外物所迷惑,其“素履,往无咎。”[21]69的思想,被《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在上位,不陵下;……,反求诸其身。”[14]24的思想提出所借鉴,两者均是讲质的思想,在其位,行其义,不为外物所干扰,坚守本心正道而行。最后,履卦九五中正当位,无乘无应,其“夬履,贞厉”[21]17的思想,为《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14]37的思想所继承和发扬,因为九五处君位,且中正当位,故而,既可以“夬履”,又可以“贞厉”。因此,此卦九五含有非其位,则不得行其义,制其礼的思想,而此思想被《中庸》所吸收并发挥。
恒卦(□)讲久,乃是德之固也。其卦由三阴三阳构成,有应有乘,九二与六五皆是中而不当位。首先,其《彖》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6]254此思想在《庸》中描述相当生动,即“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14]20与“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14]20对比,而后其褒贬之意可知矣,进而得出“行道”或“择道”要恒久,唯久而能“不息则久,久则征,征择悠远,……,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14]34-35明显突出了人通过修道可与天道相辅,这与二程曾说:“颜子择乎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择?如博学之,又审问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择中庸也。虽然,学问明辨,亦所何遽,乃识中庸?此则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在学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择之则在乎智,守之则在乎仁,断之则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不能守,不能断。”[2]170意思一致。其次,恒卦九二为阳居阴位,本该有悔,然爻辞却称“悔亡”,究其原因在于,九二以其中德与六五相应,以九二之中而应六五之中,则其处与动都得中也,故而能恒久处于中道,故而《中庸》提出“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亲不惑,……,怀诸侯则天下畏。”[14]30要求上下均以九经为准则,进而上下以中德相应。
家人卦(□)讲述家庭关系,其卦由四阳一阴构成,有应有乘,六二与九五皆是中正当位。首先,其《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16]271其思想直观体现了儒家五伦观念中的父子、夫妇、昆弟,而《序卦》中的“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礼义有所错。”[16]95则将“夫妇”一伦提升至重要地位,故而《中庸》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4]23的重要思想。此外,《中庸》不仅继承了《周易》中所阐述的伦理思想,还对其有所创新,提出“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14]29这将后世定行“五伦”思想大致概括出来。而此“五伦”思想作为处理人们基本关系的原则,又被孟子发展且凝固成一个稳定的系统。[27]并且《中庸》将家人卦中“正”的思想,以“诚”来明确,正如周敦颐所说的“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28]32其次,家人卦九二与九五皆是中正当位,九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16]273讲求妇女主内不要自专,要顺从九五的一家之主,进而才能达到“王假有家,勿恤吉。”[16]274通过感格有家,最终,达到一家人的交相爱。该思想与“君子之道,辟如行远自迩,……,《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14]24-25的思想大体类似。
中孚卦(□)讲忠信之道。“中借为忠,诚也。孚,信也。”[13]477其卦由四阳一阴构成,成内柔外刚之象,且九二中而不当位,九五中正当位,有应有乘。首先,其卦辞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16]378以豚鱼祭祀,旨在言人以忠信对待鬼神。这在《中庸》第十六章“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诚之不可掩如此夫!”[14]25也有所阐述,并且明确提出了“鬼神之德”,这可以说对《周易》思想全方位继承,毕竟子思之后的孟荀二人极少或不再谈及“鬼神之德”。然而,金德建认为:“《中庸》里所涉及的尊天、明鬼、尚贤、崇孝的种种言论,显然出自墨子学说。”[6]170但这并不排除“《周易》作者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文化需要,进而对《连山易》《归藏易》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29]其次,其《彖》曰:“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16]378点明了“诚”的双层含义,一是:自诚明,讲“诚”的自然属性,此“诚”则为即“最真实无妄之仁。”[30]120故而,有“盡己爲忠,盡物为信。极言之,则盡己者盡己之性,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于天性有所损益,则爲僞矣。”[2]315一语;二是:自明诚,讲“诚”的社会属性,此“诚”则是通过“利、贞”而成的“诚之复”。[28]32再次,其卦初九阳居阳位,与六四相应,其爻辞“虞吉,有他不燕。”[16]379讲求“诚”在自身,不需外求的思想,要克己复礼,遂与六四相应,但不能被其干扰,这与“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14]34的思想类似。其九五中正当位,无咎,其爻辞曰“有孚挛如”[16]380,其思想内涵正是用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皆信之于上,故而固结的像拘挛一样,而此至诚思想在《中庸》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39描述更为细致。
总之,《周易》实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源泉,而《中庸》则是实现《周易》的方法论之一。《中庸》不仅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周易》的“时中”、“诚”等思想,还对其有所发展与创新。
三、研究《周易》与《中庸》关系的现实意义
《周易》与《中庸》作为儒家重要经典,对当下研究儒家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周易》作为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在儒学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湮灭的作用,其所蕴含的思想光辉,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扬。而《中庸》作为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以及孔门修习之心法,在儒家心性论及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故而,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运用《周易》解释《中庸》思想,不但有利于更为简便地纠正世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错误理解,而且对理清先秦儒学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