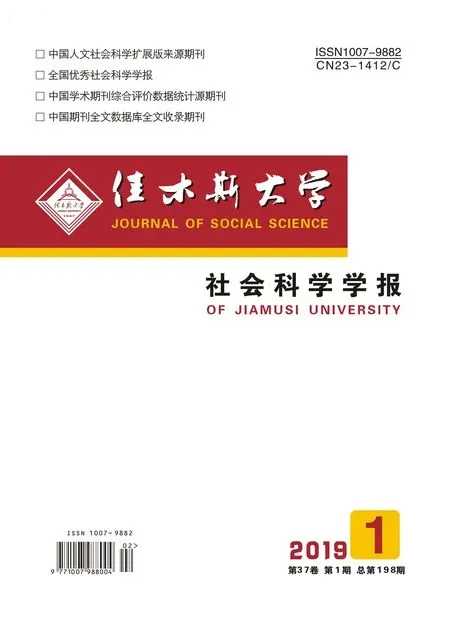明代各边镇马政机构研究*
2019-03-05石娟
石 娟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马政,指古代封建国家对官马的采办、牧养、分派、使用等一系列相关事务的管理制度。“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1]卷二零二:778,历代以农耕文明发展为主的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的战争中,战马作为主要作战工具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对军马的管理,明朝对马政的建设尤甚。
明代的马政,除了由中官所掌的内厩御马监,负责皇室所需马匹的提供之外,外厩的马匹主要分官牧和民间牧养两种。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始置太仆寺,在滁州”[2]卷五三:109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太仆寺也随之迁往北京,将原设在滁州的太仆寺改称为南京太仆寺。南北两京太仆寺主要负责近京各卫所军牧和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六府民间牧养的马匹,在太仆寺之下,于各府、州、县又有专管马政的官员通判、判官和县丞。在明代,由太仆寺管理下的民间牧养主要是为京师服务的,民牧之马匹仅供京营团卫军人骑操。正所谓“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3]卷九二:2270,有明一代,各边镇军人骑操的战马来源主要是在边镇地区设立的行太仆寺、苑马寺两官牧机构所负责孳牧的马匹,这也是本篇文章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各边镇马政机构的设立
明朝建立后,故元残余退守漠北,但蒙古部族始终是有明一代政权建设的较大威胁,为了增加与蒙古骑兵作战的军队战斗力,防止北边蒙古势力再次入侵,明朝初年统治者除了沿北部边防建立重镇,派兵驻守,还就近于边镇地区设立马政机构,专管马匹的孳牧,各卫所、监苑牧军因地制宜的逐水草放牧马匹,为军需战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成为明代作战的有力后备资源。
(一)各行太仆寺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沿边防之地“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3]卷九二:22700,牧马之地涉及到西起宁夏、河西走廊,东至辽东、鸭绿江的北部广阔草场。永乐十八年都城迁往北京后,将北京行太仆寺改称太仆寺,太仆寺的职权范围要比北京行太仆寺时期大的多,它所监管的牧马之地,从近京各卫所扩大到了京师、北直隶所辖的各府、各卫所,宣德、正统年间又扩散至山东、河南的部分府州县,牧养重心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民牧。剩余的甘肃、陕西、山西、辽东四行太仆寺一直存在至明朝末年。行太仆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属,主薄一人(从七品)”[3]卷七五:1845,统领所辖卫所的镇抚首领等官吏,共同负责各卫所营堡的官马牧养。其中,“甘肃行太仆寺所辖凉州卫、西宁卫等12个卫3个千户所;陕西行太仆寺,辖平凉卫、河州卫、洮州卫等30卫20个千户所,并将治所设于平凉府;山西行太仆寺,辖太原左、右、前等10卫5所;辽东行太仆寺,所属海州卫、盖州卫、辽海卫、复州卫等25个卫,初设治所于辽东城内”[4]卷一五零:544-546。牧养于这些沿边各卫所的马匹,平时由卫所驻军放牧,战时用于骑操作战。
(二)各苑马寺
为了扩大边地官马官牧的规模,增加马匹数量,明成祖在继承太祖时期马政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边地马政,又于各边镇广大地区设立苑马寺来大量孳牧马匹。永乐四年(1406年),在甘肃、陕西、北京、辽东四地设立苑马寺,各苑马寺统辖六监二十四苑。永乐十八年(1420年)裁撤北京苑马寺所属各监、苑,将苑马寺“并入太仆”[3]卷七五:1846,由太仆寺统一组织管理。正统四年(1439年),甘肃苑马寺被革。因此,至正统时期,各边镇苑马寺实际就仅剩下陕西、辽东两处,虽然在这期间陕西、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大部分监、苑也没有逃脱被裁革的命运,但仅存的几个还是一直延续到了明末。苑马寺,于各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属,主薄一人(从七品)”[3]卷七五:1845,率领各监之监正、监副、录事,责其所属各苑直接统领牧养马匹的圉长,共同负责六监二十四苑的马匹孳牧。设立之初,“陕西苑马寺辖长乐监、灵武监、同川监等六监二十四苑;辽东苑马寺,辖升平监、辽河监、永宁监等六监和新安、复州、清河等二十四苑”[4]卷一五零:544-546。牧养于这些监苑的苑马,是由专门的牧军集中孳牧的,他们春季于各苑放马,冬季归厩喂养。根据规定的牧场规模,上苑牧马可达万匹,中苑、下苑牧马也有四千至七千匹,可知明初陕西、辽东各苑马寺孳牧的马匹总数是相当乐观的,为各边镇战马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供给。
二、行太仆寺、苑马寺的职权
据《明史》记载,行太仆寺“凡骑操马匹印烙、俵散、课掌、孳牧,以时督察之。岁春秋,阅视其增耗、齿色,三岁一稽比,布、按二司不得与”,“苑马寺亦如之”[3]卷七五:1845。现将行太仆寺、苑马寺的职权归纳如下:
(一)孳牧
孳牧,即马匹的孳养放牧,这是苑马寺最主要的职掌,也是各边镇卫所军人在战争、防御之余所负责的主要职事。各卫所、监苑牧养的马匹来源除了通过茶马贸易、马市等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购买以外,大多还是靠自身牧养繁衍。洪武二十八年规定,一匹儿马(牡马)搭配骒马(牝马)四匹,五马组成一群,“每群立群头一人”[4]卷一五零:547,五群头由一群长率领。如此精细的分配,马匹的牧养权责到每一位牧军,使得明初各边镇牧马生生不息。
(二)科驹
科驹,即从各卫所、监苑牧养繁衍的马匹中科取马驹,主要供给边镇官军骑操作战。洪武二十八年规定,从搭配成群的儿骒马中,以群为单位,“每群两年纳驹一匹”[4]卷一五零:548,成化二年曾试图改为三年纳驹一匹,但紧接着下一年又立即恢复,因此,有明一代,几乎都以两年纳驹一匹作为马匹科驹的标准。所纳马匹除了一部分留在卫所、监苑补充病老倒死的种马之数,进行新一轮的搭配繁衍之外,大部分调兑给了边镇官军骑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马驹的生长,各苑马寺每两年交纳的一匹马驹须先留在各苑喂养大约三年方可调配,然后由行太仆寺卿负责将马驹分配给各卫所官军或牧养或作战,这一过程也可称为“俵散”。
(三)起解
各边镇孳牧的马匹除了大部分供给边镇官军作战之用外,每年也会征调一定数量马匹解送至京师,以备京师不时之需。这一任务始于正统十四年,正值蒙古瓦刺大举进攻明朝,为解京师燃眉之急以保卫国都,纷纷从各边镇地区征调马匹支援京师,此后起解任务遂成为定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起解马匹这一项并没有在陕西各镇执行,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西北边防任务也很重,各卫所、监苑牧养的马匹尚不足供给自身,已经无法腾出多余马匹运往京师了;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原因,西北地区距离京师较远,解送马匹较为困难。
(四)比较
对马匹的比较,顾名思义指对马匹数量、质量进行的核实和检查。起初,对各卫所、监苑牧养的官马的点阅直接由各管马官员负责,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他们需要将马匹的当前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造册上报给兵部。弘治四年(1491年),这一任务在各卫所“改由行太仆寺负责”[4]卷一五三:582-583,在各苑马寺则由朝廷派遣专门的官员进行,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国家对各边镇官马放牧之重视程度,边镇牧养之官马对明朝边防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印烙
印烙,即指在马匹身上加烙印以作标记。不同的烙印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官牧和民牧马匹的烙印、孳生马驹和牧养种马的烙印、优质马匹和羸弱矮小马匹的烙印等等。这些不同的烙印,标识出了马匹的不同来源、不同身份,也暗示着它们的不同去向和用途,对于那些不堪做种马,又不宜给官军骑操的老、疾、弱、小的马匹,要烙“退字火印”[4]卷一五二:575就地买卖。马匹的质量和分配关乎各地、各军队战马的数量、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地方的防守,在边镇各卫所、监苑牧养的马匹的印烙需要行太仆寺加都察院御史一名共同完成,以加强对边镇官马的管理,防止马匹的盗买、盗卖,保证边镇战马的质量。
综上所述,就边镇马政的相关事务而言,行太仆寺和苑马寺的职权基本相同,管理各所辖地区马匹的放牧、纳驹、起解等,然而与苑马寺统领所属监苑专职马匹的孳牧相比较,行太仆寺对卫所军牧更有一层监督检查的意味,职权范围也更广,负责了各卫所军马从牧养到分配使用的整个过程。
三、行太仆寺、苑马寺的关系
明初十分重视马政,就马政机构而言,除了太仆寺以外,还于各边镇地区设立了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作为明代官马牧养的管理机构,行太仆寺、苑马寺和太仆寺三者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它们都统一“听命于兵部”[5]261,两京太仆寺负责管理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地区的民牧,行太仆寺、苑马寺负责边镇地区的官牧。同为边镇马政机构,仆苑两寺虽无统属关系,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尤其在陕西、甘肃、辽东地区,既有行太仆寺,也有苑马寺,它们建立的初衷就是大量孳牧马匹以供各边卫所官军作战骑操,因此,苑马寺下的监、苑作为专门孳牧马匹的地方,孳生的马驹其中一部分就是直接供给作战军队使用,或在卫所军马不足的情况下给予支援,这样就转而成为行太仆寺管理下的官马了。如洪熙元年(1425年),辽军总兵朱荣向朝廷奏报:“开原马市官买到马二百匹,上命付辽东苑马寺以给诸卫。”[6]卷九:296
明朝廷于行太仆寺和苑马寺共同设立了卿、少卿、寺丞和主薄,官员的职称和品秩相同,因此两机构互不统属,其职责范围也是分工明确的。行太仆寺掌管各边卫所士兵牧养的马匹,其下再没有设立专门的养马机构,各卫所马匹由卫所军人在防御作战之余放牧,上有都指挥使、各卫指挥、各千百户直接管理,行太仆寺则“以时督察之”[3]卷七五:1845。苑马寺则掌管各监、苑牧军牧养的马匹,各监、苑作为苑马寺的下属机构,是专门负责马匹孳牧的马政机构,除此之外,各苑之牧军也是大多由从各地充发过来的有罪人犯组成,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负责官马的放牧。因此,相较于行太仆寺对卫所马匹的牧养和作战使用的管理,苑马寺则更集中于官马的孳牧。
万历时曾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杨时乔在其《马政纪》的序中写到:“各边镇行太仆、苑马、茶马均属马政”[7]505,茶马作为边镇马政一项推行于川陕地区,作为陕西三边马匹的又一供给源,自然与陕西地区的行太仆寺、苑马寺有着很大的关联。洪武中,明太祖朱元璋“在洮州、秦州、河州三卫各设立茶马司,与西番诸族进行茶马贸易”[8]165-167,用茶所换来的马匹大部分都是留于西北边防使用,或是直接给各边卫所骑操,或送苑马寺继续孳牧。正如《明世宗实录》中记载:“嘉靖年间,陕西洮、河茶马,岁易四千八百为额,以四千一百匹分给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以七百匹发苑马寺,令各苑与孳牧儿骟马一同牧养,专给固原”[9]卷四三三:7468,将陕西地区茶马司、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三个机构管理的马匹的互通关系为我们描述的一清二楚。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朝廷又以“马政茶法二事相须”[7]卷十二:632为由,允许巡茶御史提调行太仆寺、苑马寺官员,兼管马政事务并督理二寺。
四、边镇马政的衰落
明代边镇马政,在洪武、永乐年间,机构健全、制度完善,是边镇牧养马匹最为繁盛的时期。自宣德以后,边镇马政就开始逐渐衰落,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各监苑机构被大量裁撤。辽东苑马寺就早在宣德时期仅剩下清河和深河两苑;“陕西苑马寺也在正统二年大半监苑被裁革,剩下二监五苑,后经弘治十五年杨一清整顿陕西马政后,恢复为二监七苑并存留至明末”[10]卷二:57;甘肃苑马寺则更是在正统四年被全部裁掉。各苑马寺所属的机构从明初的大量建立到残缺不全,再加上各行太仆寺虽然一直存在,但机构松散、官员日减,边镇马政的发展状况可想而知,牧军大量逃亡,草场马匹数量急剧减少,边镇卫所官军无马可用,以致后期出现了各边向太仆寺纷纷奏讨马匹和马价银的现象。
边镇马政的衰落是多方面原因交织而成的,牧马草场被大量侵占,周边少数民族入侵对监苑的破坏,以及边境频繁的战争对马匹的不断征调,这些都导致了牧军因困于孳牧、负担过重而逃亡,从而造成马匹无人牧养。除了这些之外,在笔者看来造成后期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马政机构自身存在的弊端。首先,负责明代马政的多个机构官员地位平等,互不统属,这势必会造成行太仆寺、苑马寺和京师太仆寺三者之间相互牵制抗衡,马政事务最终难于统筹;其次,行太仆寺、苑马寺内多“择致仕”[3]卷七五:1845官员充任,这就为地方有司的无视、下属机构不受约束埋下了祸根,后期各寺官员不得不“兼按察佥事或直接裁撤由司道官员带管”[5]263-264,以致马政事务不再专理,日渐荒废。
明朝重视马政,沿各边镇地区设立的马政机构可谓是因地制宜、物有专攻,为明初抵制外敌,巩固边防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时代的变迁,马政机构固有的弊端日渐显露,边镇官牧无可奈何的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以致后期战马的供给多仰仗于民牧和马市。明王朝的最终灭亡,边镇马政制度的失败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