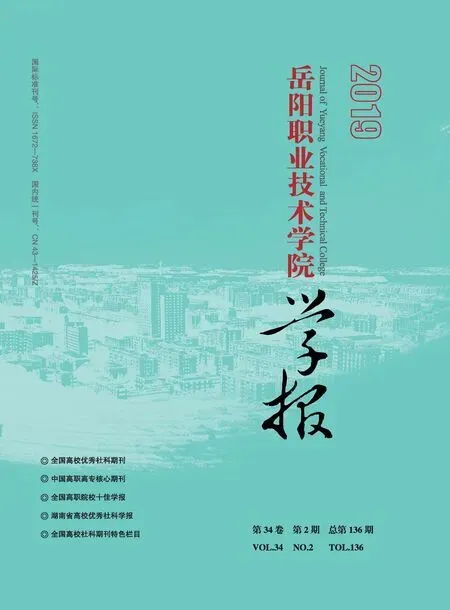“油滑”的“现代性”
——论鲁讯《故事新编》油滑与现代性的关系
2019-03-05郭佳乐
郭佳乐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的最后一部小说集,近年来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其油滑与现代性的专题研究亦层出不穷,但目前未有将二者并置进而探索其相互关系的学术成果。因此,本文将从既有成果、文本细读和生命体验出发,分别阐述油滑和现代性的概念、由来、特点和表现形式,从中探索油滑与现代性存在的紧密联系。
1 “油滑”的创作方法
对于《故事新编》的写法,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1]”竹内好认为与其称之为“历史小说”,不如称其为空想小说更妥当。人物、背景、道具一应俱全,但是舞台却是空想的,并不是历史先行于作者,而是作者的问题意识或者观念先行于历史,历史被视为材料为作者所利用。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到:“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2]”鲁迅对于历史材料的创造性认识和应用在写作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独到的对材料的把握成为鲁迅历史小说的显著特点,突出主要人物且淡化背景环境的创作风格则带有其鲜明的个人烙印。
对于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鲁迅起了个充满“意味”的名字叫“油滑”。郜元宝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写古人而忽然想到今人,一者让古人讲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二者虚构。一些次要和穿插人物,让他们直接代表现实中的某一类人。[3]”古人和今人“同台上演”的写法,鲁迅认为“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1]”但是,历时十三年的《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中,其坚持了“油滑”的态度,并未孤立地看待古人和今人,始终强调古今人物在精神上的联系,在主要描写古人的部分加入今人的言语、想法和行为,不能不说是他的自觉。所谓“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实际是鲁迅“有意为之”下的一种谦词。这是鲁迅一生一以贯之的写作习惯:先是自嘲,可内心对于自己的创作手法十分得意,只不过文人的清高要求自己先“自矜”一下。这种写作习惯带有一种“反语”的讽刺意味,成为“鲁迅式”语言的典型体现。
鲁迅十分欣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一文中专门辟一节来谈:“(芥川龙之介)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4]”由此观之,鲁迅创造“油滑”一定程度上受到芥川的影响。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将《故事新编》的写作称为“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以说明今人堕落的历史缘由。他自己说:“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1]”。正是在此心理背景下,鲁迅着力于“祛魅”,将人们心中的传统“神灵”“圣人”“英雄”形象解构和消解,重建“中国的脊梁”,以此完成写作的预设目标,在“没有把古人写得更死”的基础下给今人些许借鉴和启迪。另一方面,鲁迅认为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是一直在重复,所谓的“以史为鉴”只是给人类这一种族的兴衰更替增添一抹悲哀或荒诞。鲁迅面对这种荒诞、悲哀乃至绝望,他选择“油滑”,消解这厚重的暮气。无论是讥古还是讽今,都在于表达出跨越数千年不变的“民族印记”,使其以没有时空约束的“寓言”形式来展现,追求隐喻历史整体的寓言真实。换言之,“油滑”亦可视为鲁迅对于“象征”这一创作手法的延伸和探索,丰富了“象征”的内涵和外延。
油滑的具体表现方式可引入郑家建的“戏拟”说:“一方面,保持“拟”于“戏”之中,使得自己与旧文本语言保持着适当可调节的位置,即在新编中没有丧失故事的韵味;另一方面,借助于“戏”,即作家主题情感、思想、生命体验的投射、渗透、使得“拟”变得生动起来,使得故事中带着新编的新气息、新解读和新生命[5]”。
2 文本的现代性体现
首先考据源流,廓清“现代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流变。“现代性”是一个带有明显时间背景的词汇,而“现代”的具体指代范围需要明晰。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科建设受到苏联学界的极大影响。“近代”“现代”等断代史概念本身属于苏联的史学概念。苏联历史学家为了显示十月革命开辟了新纪元的重要意义,将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将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之间叫做“近代”,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命名特征。我国借鉴了这套学说,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近代与现代。以政治思想“切割”文学史,这样显然不尊重中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规律。因此,本文采用世界通行的“现代”概念来进行论述,即西方学界所划分的“16 世纪后的欧洲历史”为“现代史”,明确了“现代”的历时区间,具体谈“现代”概念引申出的“现代性”概念。现代性是一种支撑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但文学的现代性却恰恰相反。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对理性的超越、质疑乃至于否定,由文学的性质所决定。文学有两个基本层:一个是表层,在这个领域文学决定于社会、文化;一个是超现实的审美层面,在这个领域文学以其审美意义超越社会、文化,文学成为社会、文化的异质因素,它以自由的名义批判现实。审美是文学的最高追求,因此,审美意义是文学的本质,即当社会开始进行现代性转化,文学将与时代浪潮保持距离,它痛斥人性的异化、自由的丧失,反抗无理由的理性,质疑现代化和现代性。在这种对理性的质疑和追问下,文学捍卫了人的尊严,并揭示了生命的意义。文学的现代性只有达到如此水准的文学作品中才会有所体现。从20 世纪开始,诞生的现代主义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非理性化,它标志着文学现代性的确立。
我国最早提出以“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是严家炎,即1981 年发表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即所谓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最早始于甲午战后。(《剑桥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可推到更早的1840 年,自龚自珍始)。严家炎认为“现代性”并非衡量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并且现代性并不等同于现代主义,现代文学道路的广博包容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流派。
搞清楚了“现代性”概念,再聚焦《故事新编》的现代性体现。王德威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提到:“中国文学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特征,那就是现在与过去始终保持着回应和联系。即使在现代文学创作中,作家也没有切断她们与以往文学的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性就是从重新解读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和古文开始的。[6]”鲁迅则直接将时间线推至更古老的神话和先秦时代。
2.1 打破经典范式,创造崭新的历史小说形式
《故事新编》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充满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突破时间界限、井然有序的传统经典范式,创造出古与今混杂合一、想象与真实交相辉映的新艺术形式。鲁迅趣味盎然地按照内心行进的轨迹,将人们熟知的历史与最关注的现实以兼具直叙与反讽、写实与夸张、严肃与诙谐的手法融于一体,创造出崭新的历史小说形式。
2.2 小说文本中的人性体现
《补天》是以人性为标,演绎、重建了中国古代神话,尤其是对于女娲原初母性的细腻描写,生动地体现出女性魅力的熠熠光辉,并赋予了其现代意味。类似的处理还有将圣人、英雄拉下神坛,将权威“脱冕”,如作品中的后羿、孔子、老子等形象,去掉神性的一面之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所谓圣人英雄也逃不出凡人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以此彰显人的价值。
2.3 西方现代思潮的“鲁迅化”创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补天》中,鲁迅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性发生学,给古人故事注入了新鲜血液,再现了远古时代女娲造人的心理体验。同样,更具广泛性的则在于表现主义对鲁迅的影响。对历史材料的“信手点染”和充分运用表现主义的叙事技巧,显示出《故事新编》强烈的主观表现意味,亦寄寓了鲁迅针砭时弊(女娲胯下的小丈夫、文化山上的文化人等)、文明批判的现实立场。
2.4 鲁迅革命观在文本中的体现
革命话语本身归属于现代化语境中,王富仁对革命有着精辟的概括:“革命就是在当时社会上的弱者或弱者群体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对强者或强势群体的禁锢和压迫的反抗。[7]”“复仇”是鲁迅小说创作中喜爱的主题之一,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铸剑》一篇歌颂了勇于反抗的“眉间尺”,用复仇去反抗强权给弱者带来的伤害,这其中也寄寓着鲁迅对现代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和对被压迫者的殷切希望。
2.5 对绝对理性的质疑和嘲讽
绝对真理应该受到质疑,历史的本质是叙事,而所谓正史,也不过是状元宰相的文章、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一种修饰过、由人创造的宏大叙事。鲁迅用八则小故事完成“脱冕”,油滑颠覆了正史的神话和威权。《铸剑》中的“多头案”可以看出追求真理的困境。将三个头一起顶礼膜拜,展现出多元文化打败了一元真理,取得了滑稽的胜利。
2.6 对待传统的矛盾态度
鲁迅认为中华文明只是为一个更发达的吃人社会提供借口。然而鲁迅本身亦身中“老庄韩非的毒”,因而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犹疑和彷徨。他一生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执着追求和残酷现实下对前路的迷茫,展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化中面临的困境。犹如《起死》中的庄子,兴致所到复活了一个死了很久的人,可是被起死的人不曾感激却一味要求庄子赔偿损失,无疑显示出启蒙者面对庸众的愚昧和自私自利的本性而沦落尴尬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鲁迅本人的生存现状。
3 “油滑”的“现代性”
在一定程度上,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是一个“宏大叙事”,无数学者前赴后继探索“现代性”的奥秘,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仍未形成定论。因而对于《故事新编》的现代性探讨,本文更多是从几个点切入探寻“现代性”与“油滑”这一鲁迅特色的创作手法之间的联系,希冀为“现代性”研究增砖添瓦。
《故事新编》以一种“油滑”的形式来体现现代性。但“油滑”不意味着“失真”。孟广来、韩日新编纂,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编〉研究资料》中《有关古籍参考资料》一节中,详细考证了八篇小说的典故由来,基本可以认为鲁迅以坚实的古代文学功底进行创作。在此基础上,鲁迅选择一种独特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和当下。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是“涕泪飘零,感时忧国”,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鲁迅敏锐的洞察力使其看得更远,在热血激昂的年代仍旧保持着冷静与智慧。即便是曾经“呐喊”过,更多的原因也在于“听将令”。他认为单纯的现实主义写作远未完成对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命题的开掘,现代文学需要更加现代的创作手法与之相契合,“油滑”应运而生。它跳出了简单意义上的反讽或戏谑,将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中的精粹赋予崭新的现代意义,成为沟连古今的桥梁纽带。
现代性的厚重感和时代感经“油滑”包装后可以轻装上阵,使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对现代性的表述,肯定开拓出新的历史小说书写范式的意义,高扬人的本真价值,吸收西方先进文学理论,体会鲁迅革命观的现实意义,重新衡量理性的存在,最终以崭新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可以说“油滑”的“现代性”使蕴含意义得到更好的呈现,与此同时,“油滑”的“腔调”削弱了“现代性”的神圣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更易与读者达成“共情”。
鲁迅陷入“油滑”13 年无法不让人认为这是有意为之,其对时代的深刻把握和敏锐的洞察力需要一个宣泄的方式,在经历了“呐喊”和“彷徨”后,选择了“油滑”的“故事新编”,以此来承载其思想的锋芒,对现代性的体悟。油滑的创作方法在不失讽刺之锐气的同时增添了幽默诙谐的风味,嬉笑怒骂间便可领略鲁迅的深意,成为深深契合其本身写作风格的创作手段,更加益于作品的传播和扩散。同时亦可看到“油滑”同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关系,进而引起下层民众对作品的关注。
4 结束语
本文立足文本,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油滑”的“前世今生”细致梳理,明确鲁迅对于“油滑”矛盾中带着肯定的态度。在现代性解读上凸显新的认识,从6 个角度探索文本中的“现代性”体现,不断丰富对于《故事新编》内蕴的理解和阐释。同时将“油滑”和“现代性”并置,结合鲁迅生平,从其概念、由来、特点和表现形式多方面切入探索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进而发现“油滑”为表、“现代性”为里的小说书写模式,为《故事新编》专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