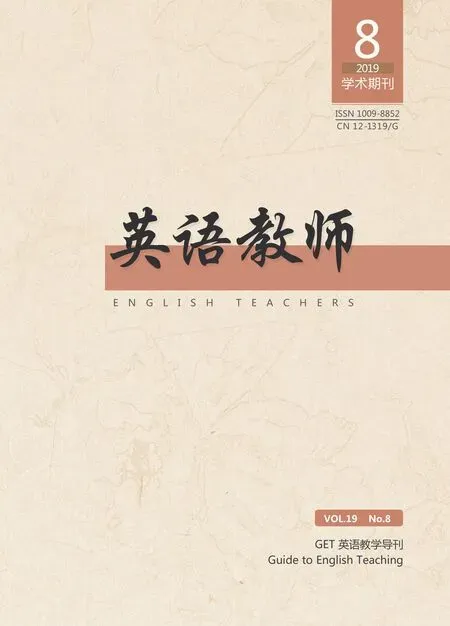翻译特性视域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探析
2019-03-05胡楠刘荣
胡 楠 刘 荣
一、汉语文化负载词
汉语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词组和习语,具有鲜明的汉文化意向,能鲜活地表现出我国文化的特性,成为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我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文化负载词在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准确英译汉语文化负载词,不仅能有效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还能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这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二、翻译的特性
众所周知,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等特性。
(一)社会性
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活动,翻译就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语文化负载词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语言,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国文化的个性特征,所以与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而翻译让人类社会迈出了相互沟通、理解的第一步,因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能够使得不同国家之间克服交流障碍,促进文化的传播。例如,在“一带一路”这个词的翻译上,很多媒体甚至地方政府举办的论坛起初都使用 “one Belt and one Road”来表达。然而,这样的翻译是不符合规范的,one 的确是“一个”的意思,但这里应该用定冠词the,因为这里的 Belt 和 Road 特指“丝路”和“海上丝路”。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进行了规范,译为“the Belt and Road”。又如“农民工”一词,指的是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劳动者,它具有社会性。在翻译时,译者不能简单地按照字面意思将其译为farmer workers,而应该思考它的深层含义,表达出它的本质意义。因此,“农民工”可以翻译为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同样的道理,“元宵节”被译成lantern festival;网络流行词“柠檬精”被译成sour grapes,而不是直译为lemon essence。这些充分说明了翻译是受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的。要将一种语言翻译得恰当、得体,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性
由于中西方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翻译很难传达原文的所有信息并找出目标语言,所以它的突破点文化问题日渐受到各界重视。在《翻译的科学探索》一书中,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奈达(2004)说:“对译者而言,由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远比语言结构带来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译者可以把汉语中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语用英语中能产生相同作用的词语来代替。例如,可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成Chinese Romeo and Juliet,把“七夕”翻译成Chinese Valentine’s Day。这样,用英语读者所熟悉的文化概念来翻译,可以缩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极大地促进沟通和交流。正如我国著名翻译家许钧(2008)所说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语言层面的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因此,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寻求目的语与源语言的深层共性,以减轻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三)符号转换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982)曾指出:“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特点。”这说明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而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只要源语言与目的语的符号意义功能完全一致,译者就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即在句子结构与语序上不作改动。例如,“寸金难买寸光阴”译为 Money can’t buy time,“事实胜于雄辩”译为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爱叫的狗不咬人”译为Barking dogs seldom bite。以上源语言符号如“金”“光阴”“事实”“雄辩”“爱叫的狗”“不”“咬”等在目的语中都可以找到符号意义功能一一对应的译文。所以,在符号转换时就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然而,在翻译中绝对的对等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如果原文与译文符号意义功能不完全一致或不存在对等的符号时,采用意译的方式就很必要。例如,“掌上明珠”这个成语多用来比喻父母宝贵的、疼爱的女儿。《圣经》中有一句话:“Keep me as the apple of the eye.”意译为“保护我就像保护眼中的瞳孔”。苹果和瞳孔的形状都是圆的,因此最初苹果被比喻成瞳孔。the apple of the eye 表示特别珍视的东西,所以“掌上明珠”被译为the apple of one’s eye,精准地呈现了原文的意思,更加便于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体现出英语翻译的意义。
(四)创造性
翻译不仅是将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活动,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的工作。这就要求译者必须了解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文化,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确保灵活、有效和得体地表达出源语中的文化内涵。所谓的“翻译是艺术”之说,突出强调的正是翻译的创造性。许渊冲说“翻译最大的乐趣就是创造美、发现美”。例如,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中有一句“不爱红装爱武装”,许渊冲将其翻译为To face the powder,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毛泽东诗中原句“红装”与“武装”相映成趣,是修辞中的同异格。本来翻译起来很困难,因为很不容易与原诗对应。而许渊冲的翻译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同源词语,传达出了原诗的趣味。第一个 face 是动词“面对”,powder 是名词,表示“火药”;第二个powder 是动词,“往……涂粉”,face 是名词,表示“脸”。也就是说,face the powder意思为“面对硝烟”,powder the face 意思为“涂脂抹粉”。这种高质量的创造翻译不仅可以准确传达信息,还能引发读者的文化联想和审美想象,同时弘扬我国的文化,起到加强对外交流的作用。
(五)历史性
在翻译时,译者要把翻译内容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遵循翻译的历史性特性,忠实于鲜明的时代特色。斯诺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译为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初看令人疑惑。因为green-tiered 应该是形容山的层峦叠嶂,莽莽苍苍,和磅礴不是一个意境;rounded steps 应该是指部队迂回行进,兜圈子,和走泥丸也沾不上边儿。翻译过来的英语整句意思就成了:层峦叠嶂里,是乌蒙山上红军迂回的脚步。按说,这句直译就可以了。为什么斯诺要这样译呢?是他理解错了,还是译错了?其实都不是。原来此句不是泛泛的描写,而是隐含了长征途中的一场经典战役——乌蒙山回旋战。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在多路敌军不停顿地围追堵截之下,采取疑兵战术,在乌蒙山来回打转,最后取得了胜利。斯诺对乌蒙山回旋战非常了解,因此,他没有按字面直译这句诗,而是把诗句背后的、诗人无法在诗里直接描述出来的东西表达。从记实、叙事的角度看,斯诺的这种表达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更加忠实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意图。
三、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应遵循的原则
在翻译实践中,对汉语文本进行意义再生需要遵循去桎梏、重组句、建空间等原则,从而获得更好的效果。正如许钧(2008)认为的那样:“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生。”
(一)去桎梏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想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意义,必须从源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源语字词的含义得到再生。例如,2018年网络流行词之“锦鲤”(意思是“幸运儿”)可以翻译为a lucky dog,从字面上看不到锦鲤(koi fish)的字样,而是用lucky dog来代替。这是因为在西方,狗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大量带有dog 的句子都是善意和褒奖的表达。同样的道理,dog 还适用于“身居要职的人”的翻译,即a top dog。以上翻译都更灵活、更地道的体现了翻译的意义。
(二)重组句
汉语被动语态用得少,而英语被动语态用得较多。这是由于中国人在表达时常以人作主语,或用泛称如人们、有人等作主语,也常把时间或地点置于句首,采用无主句的形式,而英语中常常用被动语态来表达这一类句子。因此在翻译时,译者不妨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重新组句,使得源语的字词意义得以复活。例如:“当地人发现印尼抹香鲸死亡,胃里有1000 块塑料垃圾”。译文为被动句:“1,000 pieces of plastics were found inside dead whale in Indonesia by local people.”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起强调作用。又如:“我认识一些大梦想家,他们都是成就大事的人。”译为:“I know some great dreamers who have achieved great things.”译文用定语从句而不是两个并列句来表达,增强了句子的紧凑感。再如:“你去,我就去。”译文为:“If you go,I will go.”译文用了条件从句,这是因为汉语仅靠句子内部逻辑联系就能表意,而英语句子结构严密,两个句子之间要用并列连词连接或用主从句来表达。
(三)建空间
译者在翻译时要努力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与原文作者相似的想象空间,创设出自然而然的语境,使得读者加深对语言的领悟。例如:“昨天晚上他们吃的是夫妻肺片。”译文为:“They had famous Sichuan food Sliced beef and ox organs in chili sauce last night.”译文中加上了famous Sichuan food,为读者搭建了一个中国饮食文化平台,使读者立刻了解到“夫妻肺片”是一种美食而不是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又如:“《焦裕禄》太感人了。”译文为:“The film Jiao Yulu is very touching.”译文中添加了The film,给读者营造了阅读的空间,取得了比较好的翻译效果。再如:“我属猪。”译文为:“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Pig.”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语境,使实沟通更加顺畅。
结语
总之,英译汉语文化负载词有诸多需要注意之处。译文既要传达出特有的源语文化,又不能偏离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在翻译时,译者既要考虑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等五大特性,又要遵循去桎梏、重组句、建空间等原则,对汉语文化负载词进行全面解读,从而克服文化交流障碍,达到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