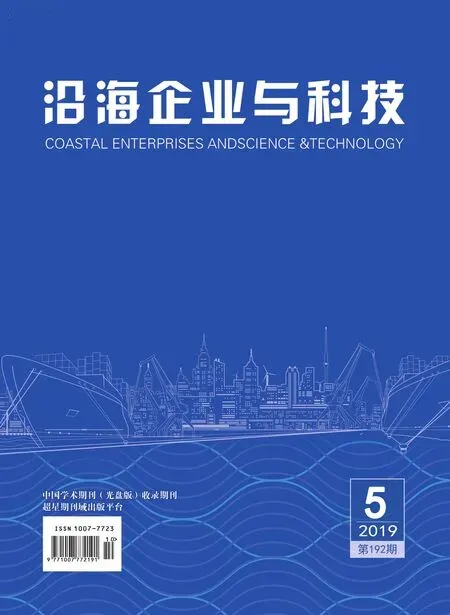以荒诞的形式呈现人心困境
——东西小说论
2019-03-03甘林全
甘林全
一、引 言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此言一出,让当时的国人都觉得难堪,认为其刻薄,甚至歹毒,然掩卷沉思,才发现鲁迅先生的深刻、通透,以及对于国人那份深沉的挚爱。我们需要寻找光明,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正视黑暗,鲁迅先生是勇敢的,他迈出寻找光明重要一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以启蒙主义,以文学之笔,孜孜不倦地改良社会人生与人心,由此完成作为“启蒙者”的作家形象的建构。
东西,作为晚生代代表作家之一,他对于中国人的人心问题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站在鲁迅这位“巨人”的肩膀之上继续前行的。当然,由于时代、个人经历、学识等方面的不一样,最终他们的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对于人心困境的呈现,东西更倾向于“举重若轻”,即用荒诞不羁的方式,通过不断地运用调侃、戏仿等手法,虚构一个个看似轻松愉快的喜剧故事,实则是对人心人性的一刀刀的凌迟问斩。阅读东西的小说,我们会有一种轻松的沉重。“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对心灵充满了好奇,喜欢窥视和打探,并把人隐秘的心理统称为‘秘密地带’。只有写到‘秘密地带’的时候,我才感到过瘾、有劲”。“我相信一个作家的好坏,取决于身体与心灵的距离,也就是自己离开自己究竟有多远”。[1]66东西以小说的形式,在轻松荒诞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情境中,像一个残酷的灵魂拷问官审问犯人一样,不断拷问着人心,直逼人的灵魂深处中所有的卑微和丑陋,让一切都无处遁形。这是对于人心深刻的发现,也是对于不能承受的人心之轻的书写,更是其“人心拷问者和人类前途命运思考者”的作家形象的建构。
二、文本内容:荒诞中的真实
季扎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俗话也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见,对于人心的把握是比较困难的。然文学即人学,优秀的作家是生活可能的发现者,总是喜欢、执着于以文学语言的形式,透过可能的生活现象,探索人心之本质。在近20年来,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深受解构之风影响的中国文坛,作家一本正经,正襟危坐地去虚构一个严肃的故事,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一个深刻的人心主题的写作,日益减少,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显得“另类”的方式来进行写作。阎连科的神实主义,余华对于平庸琐碎的现实生活现象的不信任,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等,作家们似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突破以往的现实主义,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以看似荒诞的形式,建构一个更接近于生活现实本质的艺术世界。作家东西同样也是这种写作的能手,以戏仿、夸张等手法,用看似冷淡绝望的笔调,通过一个个在城市、在乡村或在城乡结合部的故事,探寻人心本质,以达到整理人心的目的。
小说《后悔录》,以“后悔”作为切入点,写了一个人如何一生犯错,又如何一生后悔的故事,突出了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曾广贤,作为被历史强权政治损害的小人物,他的创伤是在特殊年代留下的中国式创伤,那是人性最深重的一种创伤。他的一生显得那样的可笑和可悲。小说始终保持着对自我和历史进行双重嘲讽,让读者在荒诞的快感中,又深切感受到人的身体和心灵难以言表的创痛。东西塑造了一个在人人自危,相互倾轧,无法坦诚相待的荒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人物形象,他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之中,因为种种错位的、荒诞的遭遇而造成的悲剧。这是对真实历史的表现和反思,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无法沟通”和“无处言说”的真实的现代困境,在这部小说当中也有显著表现。这部小说以“如果你没有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作为开篇,而文中的“你”是一个妓女,是“我”在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听我的“后悔故事”的人的情况下,只能花钱请一个妓女来倾听“我”的言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正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仿佛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座孤岛,彼此独立不相依。这是东西对于现实的反映,而且把这样的人心困境推到极致:当“我”向那个妓女提出只要她安静地听我讲,而不需要她其他的服务的时候,她非常吃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类似这样的有违常态的情节、滑稽的场景和人物荒唐的行为,在小说中都有不少的呈现,人生的状态和历史的真相在荒诞的故事和喜剧性的笔法中被淋漓尽致揭示出来。正如韦墨兰所说的:“《后悔录》是一部不屈不挠地直问本心的作品,它在历史、政治与人物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对中国人复杂的精神生活做了有力的分析和表现”[2]。《后悔录》是一次历史场景下的灵魂叙事,可以称为一部穿越历史场景的心灵史。
在作家东西看来,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荒诞远比作家的想象要多得多,他的写作也不是对生活的想象,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抄袭。因而,当他竭尽全力进行虚构想象创作的时候,小说中那些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羁的情节,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本质真实地呈现。张柱林认为:“这种真实就是艺术假定性的真实”,他将东西的小说称之为“真实的谎言”[3]。东西认为:“与其说作家在现实中发现了荒谬,还不如说是越来越荒谬的现实让小说不得不荒谬起来”[1]17。在东西的小说中,荒诞的情节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荒诞、黑色幽默已经成了其小说的重要标志。
小说《痛苦比赛》,仅仅从小说的名字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荒诞,痛苦居然可以用来比赛,这个比赛是用来征婚的,最终的胜利者,居然是那个说不出痛苦的人。可以说题目、情节,结局都显得荒诞不羁。荒诞引来一阵欢笑,欢笑之余却让读者陷入悲哀的思绪之中,这是对历史没有记忆的一代人,在迷茫之中惶恐不安,过着一种过于“轻”的生活,放荡不羁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承受不住这种“生活之轻”。这是东西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发现,没有历史的厚重,人终究会先入飘渺之中。
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家族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梦想,在城市经过种种磨难,如代替房产商林家柏坐牢,以跳楼讨工资,下体受损,妻子小文为了让儿子汪大志有更好的生活环境甘心当妓女,做皮肉生意等,终究徒劳,仍然无法改命。最后汪长尺为了改变他儿子的命,彻底绝望地就把儿子汪大志悄悄放在一对不育夫妻林家(也是汪的仇人)柏和方知之的门前,并把汪大志被改名林方生,实现了汪家几代人的成为城里人的理想。小说《篡改的命》用黑色幽默状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两极分化,把农民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那种卑微无助,面对阶层固化而改变无望的痛楚刻画得淋漓尽致。东西的其他的很多作品,如《送我到仇人身边》《救命》《反义词大楼》《我们的感情》《猜到最后》《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对于现代形形色色生活情态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我们的生活所见的,只是这些作品却在深层次的不同角度揭示现代社会的综合病症,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作品的命名和内容都呈现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米拉·昆德拉认为:“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4]6。作家东西总是从一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汲取创作的素材,然后通过漫画、夸张、反讽、戏拟等写作手法,营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氛围,让读者在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去“发现”生活的本质,把握和领悟到最深层次的生活本质内涵。
三、本质内涵:残酷的人心困境的呈现
东西的小说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整体而言显得比较冷酷,甚至是残酷的,他像是一个不依不挠的审判者,不断对人心进行审判拷问,也在不断把人心中丑陋和罪恶无情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然而,通过阅读,会发现在这些残酷的“人心拷问现场”——文本中,作家东西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进行书写呈现的,对于现实有深刻的揭示,却不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而横眉冷对,既对于这些人心的丑陋和罪恶表示同情并理解,更希望通过“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每个作家自己心中都有关于“现实”的认识,东西既以荒诞的表现手法刻画出人心现实的真实,这是全面的真实,包括真善美,当然也包含着丑陋、罪恶等,也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是经过夸张、压缩、想象等漫画式叙述而成的。苏童曾说:“最优秀的作家无须回避什么,因为他从不宣扬什么,他所关心的仍然只是人的困境”[5]。这种人的困境,指的是人心的困境,从东西的小说来看,他的创作观与苏童的观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创作的动力和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提供人生航标和精神出路,而在于勇敢面对残酷的人心的真实,以荒诞的形式虚构出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以对残酷人心和悲剧宿命的刻画去整理世界与人心。
东西的中篇小说《不要问我》,无论是小说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还是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人的人心困境与哲学思考,都显示出这是一部现代感相当强烈的作品。作品围绕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身份证的丢失到身份的艰难(无法)确认”展开叙述:大学副教授卫国酒后失态,在众人的怂恿下拥抱了一位女学生,因此名誉扫地,为了逃避嘲笑与屈辱,他只能被迫离开原来的学校,辞职南下,在火车上邂逅了一个叫顾南丹的姑娘,后来这个姑娘也给予卫国很多的帮助。他却在意外中遗失了装着所有钱物与证件的皮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无法证明自我的人。这样卫国失去了副教授的身份,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不能找到工作,不能结婚,就要处在别人的救济、同情、怀疑和嘲弄之中,受尽屈辱。现实的残酷使卫国完全陷入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和相当尴尬的困境之中。陈晓明认为:“东西的小说着力表现生活发生意外的那种反常状态,他的人物看上去都是被生活压抑扭曲变了形的家伙,他们有意和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作对,几乎是盲目地把个人的生活推上绝路。那些生活的意外,被扭曲的关节,强烈撕裂的边缘,都被东西磨砺得有棱有角,使他的叙述始终保持一种饱满的张力。东西无疑热衷于写作生活的苦难和不幸,但他的所有兴趣都放在扭曲后的生活所呈现的荒诞感,持续表现出的自虐性的快感,痛苦的本质实际上却被一系列的美学趣味所替代。痛苦的本质实际上被一系列的美学趣味所替代。东西的小说可以说是契诃夫与法国荒诞派喜剧最恰当的结合”[6]。在这篇小说中,东西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意外”,使原来日常的生活状态偏离原来的轨道,以虚构的荒诞情节表现同样荒诞的客观现实:国人往往重外表而轻实质,重“证书”而忽视人的真才实学,买椟还珠式的“幽默故事”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上演。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人是活在各种“符号”当中,人的身份必须需要通过外在的一系列的“符号”才能确认。人,始终无法通过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现象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这正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通病。这是东西一种形而上的思索,生命与身份、本体与符号的分离状态导致荒唐的结果。正如温存超所说的:“《不要问我》写出了在生命本体和身份符号分离之后,人的荒诞处境和离奇命运。从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常识意义上的生活现象,但对人的生存真相的拷问却抵达了同类题材作品所罕见的深度,已经上升到一种哲学的思考”[7]209。文学创作是对现实的刻画和升华,是需要虚实相结合,就如谢有顺所言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8]37,俗世的生活现实现象是“实”的,透过这些实实在在的“现象”,更需要由此而进行提炼思考升华,看到本质内涵,从而呈现人心困境和领悟整理人心。
《没有语言的生活》最初发表在《收获》1996年第1期,是东西最具代表作之一,曾荣获《小说选刊》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描述了桂西北贫困山区一个特殊组合的农民家庭的苦难生活。这个家庭由瞎子王老炳、聋子王家宽和哑巴蔡玉珍“三位一体”组成。对于这样奇特的家庭组合的书写,是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东西也觉得非常刺激和有挑战性:“他们所听不到看不见说不出的状况的描述,也是一种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描述。一旦战胜这种刺激和挑战,就获得快感”[9]。小说中描绘的是深处贫苦山区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家庭的生活,本身生活条件就很差,再加上他们又是残疾人,是弱势群体,让整个家庭就显得更加艰苦。这种艰苦既包括物质生活上的,也包括触目惊心的精神匮乏,而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严重。在他们的有限的生活区域里,我们看到他们沟通的困难与失效,一聋一哑一瞎的组合家庭,沟通是形同虚设的;也看到“人心不古”——王家宽央求小学教师张复宝替他给朱灵写求爱信,结果却被张复宝欺骗,信的落款人变成了“张复宝”,也就是说张复宝利用自己是个身体整全健康的知识分子的便利,非常不厚道,甚至有些无耻地欺骗和欺负了王家宽。王家宽家里还出现被人偷肉现象。后来,蔡玉珍生下一个健全的男孩,并取名叫“王胜利”。他们一家以为可以从困境中走出来,走向胜利了,以后可以家里有人跟周围的人过上有语言的生活了。但是孩子上学后,被人取笑:“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王胜利从此变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聋子哑巴没有什么两样。王家宽想与周围的人过上正常有语言的,可以正常沟通的生活的愿望彻底破灭。他们依然被排斥在正常人的生活之外,而且作为他们的后代和希望的王胜利,他最后也变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聋子、哑巴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家人没有语言的生活的精神困境是必将循环往复的,冲破不了的宿命,如西西弗推巨石上山,周而复始。这样的悲剧显得更加的悲壮和凄惨。
黄伟林认为:《没有语言的生活》充分传达了作家东西的后现代体验,准确形象地揭示了后现代生存状况,东西专注于对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揭示后现代最具本质意味的精神,东西小说呈现差异的形式不是历史叙事,而是语言[10]。无法实现的沟通,既源于生理上的残缺,更来源于人与人之间是充满隔阂的,缺乏信任,人心是冷漠的。不懂、不愿意、不能彼此沟通的现象在现代生活当中,尤其是在今天,当很多人都忙碌于沉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沟通是欠缺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今天很多人真正地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很多人的心是硬邦邦的,冷漠的。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是以一种极端的,极富想象力,甚至有些残酷的方式,把王家宽家庭中没有语言的生活困境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小见大,以寓言的方式,也让沟通的欠缺,人心麻木、冷漠、自私等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人心困境得以呈现。所谓“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东西是以人类学的视野来透视我们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小说作品实现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族的超越,具有胸怀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气魄。
四、作家形象:人心拷问者和人类命运思考者
东西在文章《近处的身体远处的心灵》中提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对心灵充满了好奇,喜欢窥视和打探,并把人隐秘的心理统称为‘秘密地带’。只有写到秘密地带的时候,我才感到过瘾、有劲”。“身体就在脚下,心灵却在远方。我相信一个作家的好坏,取决于身体与心灵的距离,也就是自己离开自己究竟有多远”[1]66。从这一段夫子自道的表述以及他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到东西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执著于对人心世界进行不断勘探、挖掘和呈现的作家,他把对于人心世界的拷问的深度作为评判文学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作家东西通过他的这些作品,建构了自己作为怀着悲悯之心而对人心不断拷问,并积极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的作家形象。
(一)人心的拷问者
作家是时代的良心,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文学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和人心的深度有关,没有成熟的精神,一定也产生不了成熟的文学。人成熟了,才能写出“灵魂的深”(鲁迅语),才能写出人心的真。作家东西通过以充满荒诞色彩手法虚构一个个具有含泪微笑效果的小说故事,这些故事的题材都是读者习以为常的,如父爱、父母的赡养问题《我们的父亲》、疯狂的沉重的母爱《原始坑洞》、底层小人物的心酸艰辛无奈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城乡间阶层固化的绝望反抗如《篡改的命》、无精神之根而发出漂浮流浪的沉重叹息如《耳光响亮》、对于往昔的不断追忆、后悔如《后悔录》、现代都市中青年男女在色欲和金钱中迷茫和放逐如《美丽的金边的衣裳》等等。在虚构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里,熟悉是因为故事里的人和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我们(包括作者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虚构或更高的真实;陌生,那是因为小说是经过作家的虚构,艺术化加工而形成的。我们看到,在小说作品中,东西化身为一位不留情面的,残酷的人心拷问者,对于小说的人心中丑陋的、悖论的、罪恶的等方面进行执著追问。我们也许觉得东西对于别人过于苛刻,然而就像鲁迅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11]284。当作家东西在拷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拷问着自己,甚至是更加严格无情地拷问着自己,他在创作的过程就是拷问自己的过程。东西在拷问着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比小说中那些人物更有人文关怀,更加的能够理解并同情别人的遭际,自己如果面临小说中的那些痛苦的遭遇,是否可以处理得更加合理……会不会由被迫害者,有机会的时候变成了迫害者等。
鲁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这样的:“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12]95。作家只有勇敢对人心困境进行不依不饶的拷问,才能成为一个内在的人,文学才能被称之为是找灵魂的文学。因为文学,说到底,是对人心的钻探。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3]288。人心乱了,一切都会变乱;心若清明,万事通达。人世的温暖,无不来自对人心的呵护;相反,人世的丑陋,也无不是从心的暗处发出。因此,当作家东西不断地、勇敢地怀着悲悯之心对于人心困境进行呈现,这是他试图寻找一种可能性,为建构更加合理人心文化而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的体现。
(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整个世界各个层面的顶层设计。作家历来被认为是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者,积极为人类的未来寻找更好的发展的可能性,也成了优秀的有责任担当的作家的集体无意识。谢有顺在《内心的冲突》中说到:“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14]154。作家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一定是根植于历史,还有此时此地的实际境遇的,也就是说作家是脚踏实地而有仰望星空的。作家东西通过自己的观察,他看到在那一段荒诞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扎,彼此迫害;他看到了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缺乏信任,却充满了虚伪冷漠;他看到了人如何地被异化成为一种“符号”;他看到了现在阶层固化,城乡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以这些观察和领悟为基础,创作了如《耳光响亮》《后悔录》《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不要问我》《篡改的命》等非常有代表性的小说。东西在《有一种生活被轻视》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精神工作也只能用财富来衡量的话,那就说明金钱已经成为所有工作的标准。一旦金钱成了标准的唯一,生活就会被金钱绑架。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强大补充,是一种能提高物质生活的生活。重视这种生活,是从意识到它的存在开始的。通过这些小说和文章,东西迫切想要提醒读者,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予以高度地重视,因为这些问题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会影响到将来的生活,体现了东西悲悯情怀和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王安忆在一次演讲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整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15]1。这里王安忆所强调的是现实世界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认为前者是基础性的存在,是小说飞扬想象的安稳现实基础。作家东西现实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关系也有类似的表达:“任何奇特的小说都不是凭空捏造的,它发自我们的内心,与生活血肉相连,魔力就蕴藏在我们的生活和内心之中[1]38。对于作家东西来说,他的创作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考,尤其对他童年所经历的艰苦的回忆,把这些经历进行重新地筛选、重组、夸张、陌生化等艺术加工之后,就是一篇篇小说作品。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受两次苦:经历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因此,可以看出,东西进行的创作其实是承受了两次的苦,这是为整个社会和人类而承受的苦,他在积极思考着人类的前途命运。正如他在《谁看到了我们》里所说:“任何文字的精彩都是依附在思想上的,就像所有漂亮的衣服都离不开身体”[1]32。东西以人心的拷问者,作为自我形象,不断拷问着人心,以小说的语言全面地呈现出人心困境,并以悲悯之心,积极探索解决困境的可能性,这是有责任担当的,具有人类大爱情怀的作家形象深刻体现。
五、结 语
文学是人学,是对于人心的一种省悟。文学是写人心的,作家通过形象、细节,以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其对于世道人心的感悟和态度。作家东西是个悲观的人心的拷问者,它的小说几乎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亲情也好、爱情友情也罢,似乎都是千疮百孔的存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心困境也似乎永远无法冲破,仿佛宿命般轮回存在。哪怕他已经足够的小心翼翼,以一种略带轻喜剧风格手法来呈现荒诞的人心困境,然悲剧的气息依然溢满纸张,粗看似喜,细看是悲。也正是对于人心困境的焦虑,东西在不断地探索一种更加合理的人类共同人心的建设道路,这是一种有担当有人间大爱情怀的体现,也是作家形象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