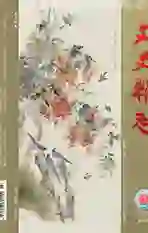论扬雄的思想 影响中国千余年
2019-02-27凤羽
凤羽

扬雄(公元前53—后18,画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史》记载,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1] 為什么给扬雄这样高的礼遇?因为扬雄是当时学界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就这样说:“扬子云真大儒邪。孔子既没,后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荀殆不足,况其余乎?”[2] 公开推尊扬雄是孔子之后第一人,孟子、荀子都无法比拟。
一、时代对扬雄的要求
扬雄,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扬雄所在的时代,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西汉、东汉交替,其间还有一个王莽的“新”朝。
西汉曾经非常地强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独领风骚。但是,到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尤其严重的是,封建统治理论遭遇到信任危机。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于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大大发展了儒学,而且为封建统治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学说与孔孟学说事实上是有差距的。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民本思想,孔子讨论的是人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孟子讨论的是国君应该行仁政,是君主对臣民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而董仲舒的新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要求,实际将孔孟学说转变成了君本思想。新儒学表面上讨论的是天和人的关系,实质上讨论的是臣民应该怎么对待皇帝的问题。董仲舒认为皇帝是天选择的,以忠于皇帝为顺而背叛皇帝为逆,并由此推导出臣民应该无条件服从和支持皇帝。
董仲舒新儒学主要表现在其所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这些都是要求人民服从君权的表现。新儒学弥补了儒学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方面的理论缺陷,加强了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但从其内在的逻辑而言,却是非常粗糙、肤浅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于内在逻辑上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政治功能力不从心。西汉末年的“异姓改命”以及当时农民起义的“受命”主张及弥漫整个社会的谶纬学说,都带有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影响。
正是因为汉家统治理论的上述缺陷,所以西汉之亡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统一王朝的覆亡都不相同:既非亡于外族入侵,也非亡于农民起义,而是亡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危机。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格于形势,少有成绩,从而在这一场运动中失去了主动权,使得士大夫群体对汉室大失所望,转而支持王莽,最终促成了王莽篡汉。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而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遂根据儒家经典而“托古改制”,开始在政治、经济、教育、祭祀、法律、音乐以及建筑、历法、漏刻、度量衡、车辆制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包括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王莽都不停地要求恢复到西周时期的周礼模式。

明嘉靖刻本《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书影
但是,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属空想,脱离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朝令夕改,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引起天下贵族和平民的严重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揭竿,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起义。更始元年(公元23年),新朝灭亡;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东汉政权建立。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理论,都产生于社会的动乱时期、变革时期、转型时期。
扬雄生于乱世。当他开始学习、研究儒家学说的时候,作为西汉统治思想的董仲舒的儒家理论已经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凝练,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扬雄必受其影响。但是,他因为身处乱世,也就更深深地体会到董仲舒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所以,扬雄作为两汉学术的领军人物,时代要求他去“圣化”儒家学说体系,而不再是过往的神化。
二、扬雄对儒家学说的“圣化”
扬雄对儒家学说予以“圣化”,目的是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
扬雄在他晚年所撰的《自序》中说:“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 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3]在扬雄看来,被董仲舒等时儒改造过的儒学,或经学化,或谶纬化,已经彻底歪曲了经典儒家的真面目。他期望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纠正儒学发展中的偏向,从而纯净儒学,重振儒家精神;而他最具体的行动,就是撰写了《法言》。在《法言》中,扬雄明确说,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4] 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勉励自己要像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在汉代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而要扫除塞路者,以张孔孟正学,就必须批判汉代的神学经学。
《法言》主张的是对儒学道统的正确承继,反对谶纬迷信和章句之学。扬雄的学说及研究方法,恢复了被董仲舒改造的儒学的本来面目并使其有所发展。
在扬雄看来,只有仰望过圣人的高度,才能够看到众人的微小,而只有孔子才称得上是最大的圣人。为什么?扬雄在《法言》的《问道》篇中指出,孔子之道是整个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中最大、最正的道,而诸子之道只能是小道,甚至是旁门左道。在《学行》篇中,扬雄还将人分为三种境界——圣人、贤人与众人;并在《修身》篇中对圣人、贤人与众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说:见识到贤人的高度,才能够真正地看轻众人;见识过圣人的伟大,才能够看轻贤人的不足;而对于圣人,能比他更好更高大的,大概就只有辽阔的天地了。这样看来,圣人不仅仅是能够高超于贤人与众人的,而且还是 能够通达天地之深远者。扬雄对儒学的虔信及对孔子的崇敬,使得他在《法言》中极力圣化儒家学说,尊孔子为圣人。

扬雄读书台(在绵阳涪城区西山风景区)
扬雄是一个大学者。在其著作中,他除了论及孔儒之道外,还对墨家、老庄、韩非、孟、荀、申、邹等其他多家学派多有讨论。他将孔子儒学置于最高地位,认为儒学之外的“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5] ,只有孔子儒学的经典才是最重要的经典。他在《法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6]《法言》的基调是尊崇孔孟的,扬雄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径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人。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7]“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8] 所以:“或问治己。曰:治己以仲尼。”[9]“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10] 扬雄明确表示要将孔子的学说思想奉为修身、学行的根本遵循。
虽然扬雄非常尊崇孔子,虔信儒学,但并不对其进行夸张的诠释。扬雄深知儒学是个包容的学说,从不故步自封而主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1]。扬雄主张:“有教立道,无心仲尼”[12],认为,有了教人成才的方法,就不必再拘泥于孔子。对于诸子之道,扬雄也并非彻底封杀,而是有所取舍。正如他所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缒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13] 他在其哲学著作《太玄》中提出“玄”的概念,这与《老子》“玄之又玄”的论述自当有传承关系。
扬雄与董仲舒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始终将孔子视作人而不是神——当然也不是常人,而是超乎贤人、俯视众人的圣人。扬雄还认为,即使是圣人,也不一定会长命不死。他指出,有生就一定有死,有始就必然有终,这既是事物的两面性,也是自然界该有的客观规律。在扬雄的观念中,孔子作为圣人,其“圣”体现在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体系里以及他于诗、书、礼、春秋的造诣上。
扬雄认为:“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14] 即是说,能学习并将学到的知识予以实践和推广,身体力行,是最好的;能够著书立说阐述它的道理,广泛宣传,是比较好的;只能教人理解其道理的,要求别人照着做的,是不太好的;以上三点都做不到的,那就只能是很一般的人了。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这一点显然与董仲舒之后的那些经学家有着本质的差异。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扬雄才会在《法言》中设置《修身》篇。以儒为本、援道入儒的思想、学术根基,使得扬雄始终能甘坐冷板凳,博学深谋,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
正因为扬雄真诚而辩证地去尊崇、继承孔儒之道,所以他阐述的儒学思想体系,就比董仲舒的儒学更为理性、更为完善。扬雄的思想学说为中华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规划出前进方向。
三、扬雄思想学说在历史上的影响
石晓宁先生在《试谈扬雄〈法言〉的思想倾向》一文中指出:扬雄《法言》的思想倾向是欲以“修身说”为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去建立纯而不杂的“纯儒学”体系;从思想史角度看,扬雄的“修身说”“开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5]扬雄的学说当是从孔孟到宋明理学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其实,从对儒家文化的贡献看,最能代表儒学发展环节的当属孔子、扬雄、朱熹这三人——孔子是儒学原理的创造者,扬雄是儒学理论的解析人,朱熹是儒学实践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原创、逻辑、操作这三方面。从这个层面讲,孔子、扬雄、朱熹三个人影响了中国2500年的文明进程。而扬雄的思想学说,从公元1世纪到12世纪,则是儒家学说的当然代表。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论扬雄:“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闺,究先圣之壸奥,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困,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16] 班固讲扬雄在理论上深究圣人之壸奥;同时又有藝术修养,游戏于文字之间,是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论:
(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昒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17]
除班固外,在历史上有许多学者都对扬雄发表了褒奖。例如:
西汉著名学者桓谭说扬雄之书“必传”,又说:“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18] 这里的“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就是说他将比先秦诸子更伟大。桓谭《新论》又载:
王公子问:“扬子云何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19]
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称赞扬雄有“鸿茂参圣之才”,说:“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同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为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20]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对扬雄都非常推崇。韩愈称赞扬雄是“圣人之徒”[21] ,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22] 。柳宗元说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23]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更有云:“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简直将扬雄推崇为圣人了。
北宋司马光说:“扬子云真大儒邪。孔子既没,后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荀殆不足,况其余乎?”直推尊扬雄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北宋“开伊洛之先”的“泰山先生”孙复评价扬雄是“自西汉至李唐,……以文章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艷邪哆之言,杂乎其中,……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24] 孙复认为,扬雄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上,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比肩。
明代的范涞入蜀主持四川民政大事。他关心扬雄的故居并予以恢复。为此,他查阅地方旧志,询问下属官吏,在实地察访,深入了解后,于丁酉(1597年)仲夏开工,戊戌(1598年)孟冬竣工,历时17个月。他还新建了“西蜀子云亭”。他在《新修扬子云草玄堂记》中说:“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休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25]
近代著名经学家刘师培写有赞扬雄之诗:“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26]
扬雄无疑是西汉时代的儒学大家。他和他的学说,自西汉起,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烙下深刻的印记。
注释:
[1](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礼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宋)司马光:《集注太玄经卷之序》,载《太玄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3][17][18](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4][7][12](汉)扬雄:《法言》之卷二《吾子》,见韩敬译注《法言》,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汉)扬雄:《法言》卷八《五百》,中华书局2012年版。
[6][8](汉)扬雄:《法言》卷一《学行》。
[9][10][14](汉)扬雄:《法言》卷三《修身》。
[11]杨伯峻:《论语译注》之《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汉)扬雄:《法言》卷四《问道》。
[15]石晓宁:《试谈扬雄<法言>的思想倾向》,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第3期。
[16](汉)班固:《汉书》卷一百《叙传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汉)桓谭:《新论》卷十五《闵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0](汉)王充:《论衡》卷二十九《案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
[21](唐)韩愈:《读荀》,载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唐)韩愈:《进学解》,载《韩昌黎文集校注》。
[23](唐)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载《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4](宋)孙复:《答张洞书》,载《孙明复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 。
[25]转见孙琪华:《扬雄宅的沧桑史》,载《文史杂志》2002年第3期。
[26]转见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成都市郫都区第四中学校长

扬雄墓(在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子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