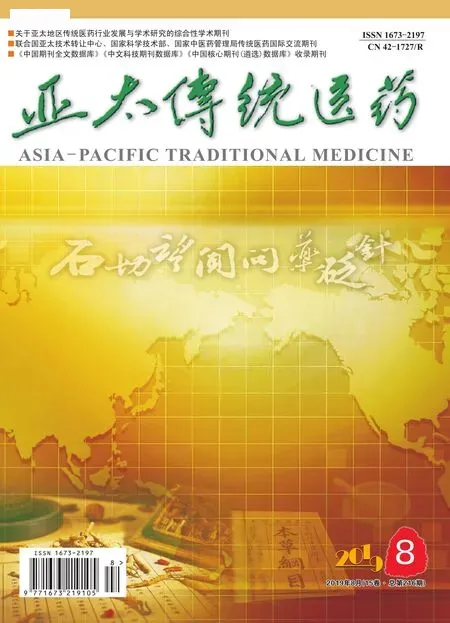阮诗玮教授治疗慢性肾脏病夏月外感临证经验
2019-02-26王雅仙阮诗玮
王雅仙,阮诗玮
(1.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福州350122;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建福州350004)
阮诗玮教授为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从医30余载,擅长肾脏病的诊治,创立了以病理为基础,以证候为先导,根据不同体质、时令季节变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肾脏病周期诊疗体系。倡导“六看”:一看天(天气情况、五运六气);二看地(地理环境、水土方宜);三看时(时令季节);四看人(体质禀赋、心理状况);五看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六看证(四诊证候)综合辨证分析,施于临床,每获良效[1]。雷丰在《时病论》中论述:“治时令之病,宜乎先究运气。经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五运六气学说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这对于研究外感病的发病和治疗具有指导意义。阮诗玮教授尤其在根据五运六气、时令节气、体质等方面遣方用药治疗慢性肾脏病夏月外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现将其临证经验报道如下。
肾主水,慢性肾脏病患者普遍存在水湿代谢障碍,津液输布失常。而夏月外感因其普遍夹暑夹湿的特殊时令特点,故慢性肾脏病的夏月外感的治疗在解表的同时应不忘从暑、湿着手。
1 夏月外感特点
1.1 外感夹暑湿
夏季气候炎热,天暑下逼,地湿上腾,暑湿交蒸,暑气既盛,且雨湿较多,湿气亦重,湿气与暑热相合,则易形成暑湿病邪,是故夏月外感以暑湿为多见。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暑湿伤气,肺先受病,诸气皆痹”,夏月感受暑湿之邪,肺属上焦,容易首先犯肺,肺失宣降,气失调畅,外则邪闭肌表,内则邪阻肺络。以恶寒发热、无汗为主要表现,兼有头胀、胸闷、身重肢酸,皮疹,甚则咳嗽等症状。
1.2 外感夹寒湿
《时病论·卷之四》道:“夫阴暑为病,因于天气炎蒸,纳京于深堂大厦,大扇风车得之者,是静而得之阴证也。”慢性肾脏病患者免疫力低下,夏季空调冷饮盛行,稍不注意就容易外感寒湿之邪,寒邪外束,暑湿内阻,寒湿夹杂,则表现为阴暑。寒湿邪易阻滞脾胃气机升降,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因此以腹泻、脘痞、纳呆,恶心欲呕等脾胃症状较为明显,兼具恶寒、身无汗、身形拘急、疼痛、舌淡红、苔白腻、脉浮紧等,故不可一见夏季外感即先入为主辨为暑湿热之证,临证上需多思辨之,切不可阴暑用阳暑之药。
1.3 外感夹暑湿疫
雷丰认为:“秽浊者,即俗称为龌龊也。是证多发于夏、秋之间,良由天暑下逼,地湿上腾,暑湿交蒸,更兼秽浊之气,交混于内。”故外感暑湿之邪易夹秽浊之气而为暑湿疫病,具有起病急、传染性、易于流行等特点。诸如夏季感受湿热毒疫之邪小儿的手足口病、急性病毒性咽峡炎、急性链球菌感染肾小球肾炎等都有暑湿疫病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反复高热、咽部红肿热痛伴有口干、小便黄、大便黏腻不畅、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
1.4 外感体虚夹暑湿
长夏暑热之时,慢性肾脏病中常有一些体质比较虚弱,外感暑湿缠绵不愈的感冒病人,投香薷饮这类芳香化湿剂疗效不佳。阮教授认为应转换用方思路,从扶正祛邪入手往往能取奇效。究其缘由,是邪不甚而偏于正虚之候,多为平素元气不足,复感暑湿之证;或暑湿伏于气分,损伤中气所致。临床上以疲乏、汗出为主要表现,兼有恶寒发热,舌淡,苔薄白,脉浮偏细弱。故临证时应当明辨其体质差异,尤为关注体质虚弱之人。
2 夏月外感治则及用方特点
2.1 夏月外感夹暑湿
夏月外感夹暑湿,如外邪明显,以发热无汗为主要表现,阮教授常用新加香薷饮加减之。新加香薷饮出自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上焦病篇暑温病的治疗中“手太阴暑温,如上条证,但汗不出者,新加香薷饮主之”,此方以辛温复辛凉为治法。方中香薷辛温芳香,既可辛温解表,又可芳香化湿,正如李时珍所说:“本品乃夏月发汗之药,犹冬月之麻黄。”金银花、连翘辛凉涤暑;鲜扁豆花芳香涤暑化湿,厚朴苦温,燥湿行气以除满。诸药合用共奏清热祛暑、解表化湿之效。如伴有咳嗽者,为暑伤肺经之轻证,阮教授常加入清络饮;如为湿热犯肺之咳则合入三仁汤以清热利湿以宣肺之气机。若伴有小便灼热,色黄,则合如鸡苏散清利湿热以利小便等。
2.2 夏月外感夹寒湿
夏月外感夹寒湿,如伴有脾胃症状明显者阮教授喜用藿香正气散加减之。藿香正气散方源于北宋年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文叙述可治疗“……反胃呕恶,气泻霍乱,脏腑虚鸣,山岚瘴疟……”方中藿香辛温芳香,外散风寒内化湿滞;白芷、紫苏加强其解表化湿之功;陈皮、厚朴、白术、甘草取平胃散之意燥湿运脾,行气和胃,加入大腹皮加强其行气化湿之意;陈皮、茯苓,半夏,甘草取二陈汤燥湿化痰之意;而桔梗宣肺,既外益解表又内助化湿;最后生姜大枣内调脾胃外和营卫。全方共奏“解表散寒,化湿和胃”之效而恢复脾主运化之功。若外感不甚,无明显表证者,则用《温病条辨》五加减正气散而治之。
2.3 夏月外感夹暑湿疫
王孟英《温热经纬》明确指出:“……甘露消毒丹湿温时疫之主方也,肢酸咽肿……”,故夏月外感湿热秽浊之邪,以身热困倦、咽肿、舌苔黄腻者明显,湿热并重之证时可用甘露消毒丹加减之。用药宣上、畅中、导下相伍,用藿香、连翘、薄荷、黄芩、射干、川贝清解宣透上焦热邪;蔻仁、石菖蒲畅中,木通、茵陈、滑石渗下,导湿热之邪从小便而出。全方共奏清热解毒、利湿化浊之效。若表现为高热者加入香薷、青蒿以加强解表,咽喉肿痛明显者,可合入银翘马勃散解毒利咽散结。湿热在表者,伴有皮肤皮疹者,则合用伤寒论之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使湿热之邪从表而发之。
2.4 外感体虚夹暑湿
《脾胃论》曰:“时当长夏,湿热大胜,蒸蒸而炽,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胸满气促,肢节沉疼……”故体虚之人夏月外感可用李东垣清暑益气汤加减之。阮教授认为治疗夏月外感不能一味的祛暑湿,还需考虑患者体质禀赋,元气不足体虚之人宜在扶正的基础上祛暑化湿。正气充沛则可一汗而愈[2]。故关于暑湿损伤气阴,尤其外感暑湿而兼有元气不足者,正是李氏清暑益气汤用武之地。方中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大枣、五味子、麦冬、培元以益气阴;陈皮、青皮、神曲、生姜理气运脾,补而不滞;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葛根、升麻芳香辛苦行散之性以通阳解表;当归养血而和阴;黄柏泻火清暑而坚阴,全方外可走肌肤经络驱暑湿于表,内可醒脾胃化湿浊于里。另外若是暑热之邪耗伤气阴较重时,阮教授则喜用王孟英之清暑益气汤,重在养阴生津。
3 经验举隅
3.1 新加香薷暑湿除
戴某,女,52岁,2018年7月28日就诊,患者诉3天前因在室内(空调房)与室外来回几趟受凉后出现发热,体温39 ℃,全身发烫,无汗,自行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后体温38.5 ℃后未予诊治。近2日体温波动38~38.5 ℃。辰下:体温38.5 ℃,鼻塞流涕,质清色白,纳呆,夜寐多梦易醒,小便少量泡沫,色黄,有灼热感,大便质黏,不畅,舌淡红,苔薄黄白腻,脉浮偏数。既往有“IgA肾病”20余年。辅助检查:2018年7月28日:尿常规:隐血1+,尿蛋白:微量,红细胞231.1个/μL,38.4个/HP。血常规:(-)。中医辨证为“感冒病”暑湿犯表证。方药如下,新加香薷饮合鸡苏散加减:香薷6 g,川朴6 g,扁豆15 g,银花15 g,连翘15 g,薄荷6 g,滑石12 g,甘草3 g,牛蒡子15 g,蝉衣6 g,桔梗6 g,丝瓜络15 g,西瓜翠衣60 g共5剂,日1剂,1日2次,早晚餐后温服。2018年8月4日复诊,患者诉服药2剂后发热已退,无明显鼻塞流涕,上述症状皆有好转。尿常规:尿蛋白转阴性;隐血1+,红细胞80个/μL。外感暑湿已愈,予改清心链子饮加减7剂善后。
按:患者于夏月外感风寒,内伤于暑湿,风寒犯表,邪滞肌表,正邪相争,卫闭营郁故见恶寒发热,鼻塞流清涕,无汗,脉浮等风寒之证;夏月内伤于暑湿伤脾胃,脾失健运故表现为纳呆,小便色黄,有灼热感,大便黏腻不畅,舌苔薄黄白腻皆为暑湿之象,故治当清热祛暑、解表化湿,方选新加香薷饮合鸡苏散加减之。
3.2 藿香正气疗泻泄
谢某,女,44岁,2018年7月28日就诊,患者诉昨夜沐浴后,在阳台吹风时睡着,半夜醒后出现鼻塞流涕,夜间腹泻4次,质前稀后如水样,伴有腹痛,服用黄连素后,今晨腹泻2次。辰下:鼻塞流涕,色白,质稀,稍有恶寒、恶心欲呕,乏力,无发热、咳嗽、咽痛。纳寐欠佳,大便质稀,今晨腹泻2次,小便调,舌淡红,苔白腻,脉弦滑。辅助检查2018年7月28日尿常规:尿蛋白2+。既往有“慢性肾脏病”病史7年余。中医辨证为“泻泄病”寒湿犯表证。处方用药如下:藿香正气散加减:藿香6 g,川朴6 g,陈皮6 g,大腹皮9 g,紫苏6 g,甘草3 g,桔梗6 g,苍术10 g,神曲6 g,茯苓15 g,白芷10 g共5剂,日1剂,1日2次,早晚餐后温服。 2018年8月4日复诊,患者诉服药3剂后腹泻已除,无鼻塞流涕,纳食无味,稍有乏力,寐可,二便调。舌淡红,苔白稍腻,脉缓。腹泻已除,予五加减正气散7剂善后调理脾胃。
按:患者阳台吹风时不慎受凉,风寒犯表,周身阳气不展故表现为鼻塞、流清涕,稍恶寒;风寒湿邪直中脾胃,脾胃失和,故表现为腹泻,如水样,恶心欲呕,纳欠佳,苔白腻,脉缓,皆为外感风寒夹湿之证。故治当解表散寒,化湿和胃,方选藿香正气散加减之。二诊患者表证已解,仅余脾失健运之证,故予五加减正气散调理脾胃以善后。
3.3 甘露消毒湿疫退
王某,男,45岁,2016年7月2日就诊,患者诉4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38 ℃左右,口腔溃疡伴疼痛,咽部红肿疼痛,平素体质较为怕热,未予诊治。目前体温37.9 ℃,症状大致同前,口干欲饮冷水,腹胀,纳寐可,二便调。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查体:扁桃体Ⅰ度肿大,色红,无分泌物。辅助检查:2016年7月2日:肾功能:尿素氮:10.2 mmol/L,肌酐198.24 umol/L,尿酸502 mmol/L。既往“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病史10余年。肝功能定期复查未见异常。中医辨证为“湿温病”湿热疫毒证。方药如下:甘露消毒丹加减:白蔻6 g,藿香6 g,茵陈15 g,滑石15 g,黄芩6 g,连翘15 g,浙贝6 g,射干15 g,薄荷6 g,六月雪15 g,甘草3 g共7剂,日1剂,1日2次,早晚餐后温服。患者于2016年7月8日复诊诉服用上方后体温未见升高,口腔溃疡及咽痛已愈。目前仍稍有腹胀,纳食欠佳,寐安,二便调。予以香砂六君子加减7剂后腹胀已除,纳食已转佳。
按:患者体质阳气偏盛,又遇夏月感受湿热疫毒之邪;湿热交蒸,蕴而化毒,充斥气分故表现为发热,口渴,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热毒上壅故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皆为湿热疫毒充斥气分之证。故治以清热解毒,利湿化浊。方选甘露消毒丹加减之。
3.4 清暑益气扶正气
黄某,女,64岁,2018年7月21日就诊,患者诉近1周来自觉体倦乏力、体温升高,但自测体温37.0 ℃,头部昏沉感,时有腰骶部酸痛,寐欠佳,大便3-4次/天,量少不畅,质稍粘腻,小便调,舌淡暗,苔薄白稍腻,脉细。辅助检查:2018年7月21日:尿常规:尿蛋白2+,隐血:微量。既往“慢性肾脏病”病史10余年。中医辨证为“暑病”气虚夹暑湿证。方药如下:李氏清暑益气汤加减:明党参15 g,生黄芪15 g,当归6 g,麦冬15 g,五味子3 g,陈皮6 g,青皮6 g,神曲6 g,黄柏6 g,葛根15 g,苍术6 g,白术6 g,升麻6 g,车前子15 g,甘草3 g共 14剂,日1剂,1日2次,早晚餐后温服。2018年8月4日复诊,患者诉上述症状明显好转,但时有困倦,纳寐可,二便调。继续守上方14剂。
按:患者有慢性肾脏病史10余年,平素体虚易感,暑易耗气伤津故表现为体倦乏力;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故自觉身热;暑湿犯表则头部昏沉,时有腰骶部酸痛。舌淡暗,苔薄白稍腻,脉细皆为气虚夹暑湿证。故治以清暑益气,除湿健脾,方选李氏清暑益气汤加减之。
4 结语
在治疗慢性肾脏病夏月外感时,阮诗玮教授结合夏月外感夹暑夹湿且易缠绵不愈的时令特点,在解表的同时祛暑利湿。同时结合病人的体质特点而辨证施治,以截断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预防因外感而加重慢性肾脏病病情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