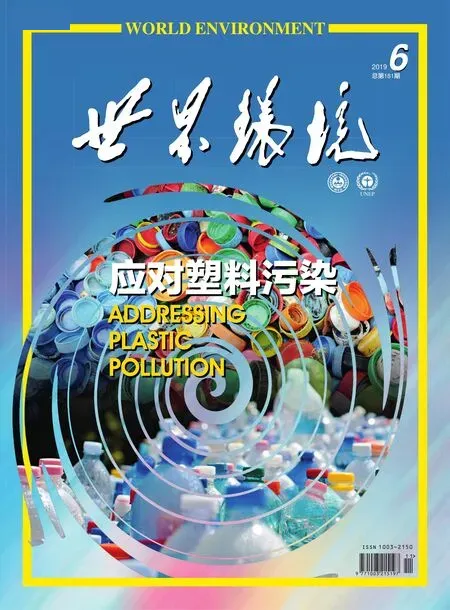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书:第三代环境规制的稳健起步
2019-02-26唐克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唐克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舒施尼对硝化纤维的发现堪称20世纪最糟糕的发现之一,造成了一个世纪后恼人不休的全球塑料污染。这种评价有失客观。舒氏发明塑料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其可重复利用性,以逐步降低使用纸袋对森林所造成的持续破坏,其出发点实际上是“绿色”的。因此,白色污染蔓延的根源,在于人类未实现对塑料制品循环利用的有效把控,而非发现塑料本身。
实际上,国际社会并非没有意识到该问题。联合国在2019年年初发布了有关各国对塑料的法律限制情况,在192个国家中,有127个国家制定了各类政策对塑料制品进行监管。从这样的结果来看,塑料污染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确实如此吗?答案是并不尽然。中国“限塑令”实施已经10年有余,零售企业借着政策的东风,却干着“卖塑料”的买卖,导致塑料袋的消耗数量只增未减,宣告了该政策已经“名存实亡”。限塑令的内容其实不过不失,实际执行也的确在全国铺开,这说明问题并不在政策层面,而是在原理层面,换言之,是第二代环境规制下对消费者的经济激励政策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白色污染危机,还需要引入第三代环境规制下的治理手段,从企业内部解决塑料污染问题。
从环境规制的更新迭代来看,2018年10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麦肯阿瑟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是一个顺畅的起步。目前已有包括联合利华、强生集团、可口可乐公司等巨头在内的290余家企业签署,占据全球塑料消耗总量的20%。《承诺书》将重点放在企业而非政府身上,确实下了一步好棋。其一,企业是塑料制品的产出大户,将矛头直接指向企业省去了通过政府转化为国内法的拖延,也能够降低各国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偏差;其二,塑料包装是各国社会生产的刚性需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通过第一代“命令—控制”型手段强行控制塑料产出将会与消费者利益产生严重抵触,而通过第二代经济激励政策来进行引导也只会将成本分摊到消费者身上,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只有通过第三代环境规制,与企业就塑料污染防治达成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承诺书》对第三代环境规制的采纳可以从两个维度观察:从内部来看,企业通过自主承诺设定塑料制品的淘汰量与回收率,并通过将目标写入公司规章来实现内部全程管理。从外部来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承诺企业基于对商誉的考量,尽最大可能实现塑料的减量与回收目标。同时,国际和国内普遍存在的第三方中立评估机构将定期对企业的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毫无疑问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塑料污染始终源于企业内部的自我规制动力不足,以第三代环境规制为契机,包括白色污染在内的大量全球性环境危机,都将寻找到更为有效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