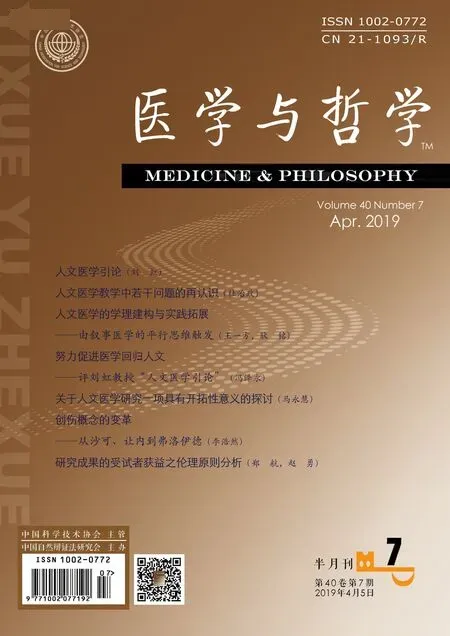中西医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比较研究*
2019-02-25张红霞
张红霞
笔者最近在做一项有关外国人为什么学中医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来自意大利并在中国已经学习中医六年的M先生,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学习中医的问题时说:“中医让我认识自己的身体,让我知道我的身体是我的!”当时,笔者追问了一句:“难道之前你的身体不是你的?”M于是讲述了他在认识中医之前,一直以来都是依靠西医来解决疾患的困扰。在就诊的时候,令他非常不舒服的是医生让患者做一堆检查,然后比较理性甚至没有多余表情地讲出几个医学术语,给一堆数据和药或者通知患者必须做手术。整个过程,患者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破机器,“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破了的东西,在接受检测,准备修理”。在医生的整个诊治过程中,病人的自感被忽略,除了“be patient”(耐心听从医生摆布),就是“be patient”(乖乖做一个合格的病人)。
在西医看来,病人就需要“be patient”,成为一个合格的病人。合格病人的基本要素就是要服从医生权威。显然,M不是现代医学的“合格病人”,作为病人,他的身体提出了“反抗”:不愿意做“被驯服的肉体”。可是,M对西医治疗方式的反抗在他经历中医诊治前只能是无可奈何,因为这就是他及其周围的人所熟悉的方式。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遇到了在意大利行医的一位中医师,由此他看见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师用一种古老的方式——脉诊来判断病情,这就像打开M脑洞的一道光。当这位中医师把三个手指轻轻搭在M的手腕,继而像朋友拉家常一样问询他是否睡得好?再让M张开嘴,看看他的舌头,辨别舌苔的颜色再问询最近身体的感受和变化。就这样,医生带着M犹如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一起探访一个与M无比亲密又陌生的世界——患者自己的身体。这个发现让M感到欣喜若狂,他第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灵敏,而不是默默无声,更不是一个供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的机器。“我的身体是我的!”M对自己身体的权利主张触及了中西医学对于身体和疾病的认知差异。而这个差异不仅是医学的差异,而且有其社会文化性。
比较两种医学模式在患者角色、医者角色、医患关系问题上的差异,尤其发现传统中医“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理念及其价值,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医学的“人”性。美国宾州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教授也指出,传统中医的医患关系是中医历史上最具有当代意义的一环[1]。
1 患者角色:被规训的服从者vs.主动修复的失衡者
作为疾病的载体,“身体”在中西医学中的地位和认知是不同的。西医主要是对人的物理身体的关注[2]。M厌倦的是西医把身体“物化”的一面完全抽离出来,把患者对疾病的自我感知忽略不计,让患者自己感觉降格为“一堆破碎的零件”。而在中医师面前,M感受到身体与患者是合一的,从而让患者获得“身体是我的”的支配权。
M对身体的权利主张其实反映了患者对现代医学意义下“病人角色”的一种主张。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引导下的西医重视微观与局部,躯体病了,就像机器的某个部位产生了故障,把这一部分拆卸下来修理就行。人体异化为一堆零件的组合,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中有过这样一段描绘:“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上来掌握它”。医生作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权威拥有者,他们规定了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的纪律就制造出了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在长期的“规训”下,患者们自觉地并习惯地去遵守那些纪律和规范,这些纪律和规范己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东西,而非一种压迫。西医的眼中,病和人不是一体的,驱壳已经不是你的,已成为他要来“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的东西。医生所拥有的医学技术和知识让他高高在上,患者的思想、情感都可以视而不见。西医的治疗过程其实就是病人对医学技术权威绝对服从的过程。
与西医不同,传统中医重视宏观、整体,认为人体就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有机整体,同时强调人的情志是影响疾病产生、发展、消退的重要因素。中医认为人体具有一个自我修复能力,《黄帝内经》中讲到“病为本,工为标”,肯定了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中心地位,病人对自己的健康承担首要责任;医生只是配合者和辅助者,医者就是用各种方式(如针灸、推拿、草药)来推动病人回复到身心内部和外部的和谐平衡状态,从而使患者的身心重新获得健康。值得指出的是,传统中医进行诊断治疗的焦点就是患者自感、自述,中医医疗行为的主体是患者。
2 医生权威:绝对治疗vs.选择治疗
曾经有一位叫胡美的传教士医生问一个中国病人:“哪位医生负责治疗你的病?”中国病人没有听懂。胡美那时就意识到医生权威在中国老百姓的认知中是不同的。西方人很早有“医学有限”的概念。这种“医学有限”的概念一方面来自于医学技术的有限性导致西医对“病名”认定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现代医学对患者不断“规训”与“驯化”的结果,使患者成为现代“合格病人”。因此,西方现代患者和社会对医生所承担的“责任”还是宽容的,甚至免责的。但是医生“通过他所选择的技术”,对于“疾病”是绝对权威,当然拥有对治疗的决定权。
中国传统文化里老百姓把能治病的视为“仙人”,觉得他们具有起死回生,无所不能的本领,故而也完全没有“医学有限”的现代概念。同时,传统中医治疗对象不是单纯的“病”,而是病人,这个病人还不一定是“合格病人”。他可以试探医生,如有些文章描述过去中医郎中“脉诊”,病人故意胡乱口述症状,为的是测试考察医生是否医术高明,真可以脉象来掌握真实病情[1]。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患者同时多处求医,以此来判断医生诊断是否准确。不仅患者自由择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而且患者和家属都会参与医生的诊治过程,而最终的决定权却在患者和家属手中。
这些事实都说明传统中国病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是有主动控制权的,而传统中医“责任、权利”完全不对等的。相比而言,西医的治疗过程对于病人而言是一个对西医医生作为高高在上的医疗技术权威的被动服从过程。西医医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去情感性的治疗过程对病人的身体和生命负责[2]。也许这个中西医差异可以解释为何当胡美医生问中国病人“谁负责你的病”时,中国病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3 医患沟通:器物术语vs.移情互动建构
西医的发展史就是伴随医学技术和医学仪器的突破而不断进化的历史。
从“床边医学”到“医院医学”再到“实验室医学”,西医离“科学”越来越近,却离人越来越远。传统中医师几乎没有任何医学仪器,中医治疗的过程就是一个“黑箱”,中医师必须把自己训练成高度灵敏的探测仪进行司外揣内[3],用外部的现象推测身体病因的本质。中医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是微妙的,中间没有冷冰冰的仪器隔阻,医生凝神聚气、气静心平地来感知病人脉息变化从而审判病情。当然,现代医学的精准仪器和设备在病情诊断和治疗中的优势可以被中医吸收用于微观诊断,在传统“四诊合参”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更好地发挥中医整体观的现代价值。
医学术语也在形塑医患关系差异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英国医学社会学家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曾指出,西医临床咨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医生的主导角色。医生接手患者的问题后,他就开始做好控制的投入,即控制或指导应该做什么。帕森斯病人角色理论也提出了一个医生享有最大限度控制的情境[4]119。通常,医患沟通的话题就被医生控制在医疗事务之内,而社会事务则被降格为边缘话题[4]130。但是,中医的医患沟通语言恰恰相反。引用一个中医看病的例子:一个病人去看中医,中医医生估计是肝火上炎;于是问病人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口苦口干;确认后进一步询问病人是否有压力,感到焦虑,脾气暴躁和急躁易怒?然后医生使用相应的调理手段,将其恢复平衡状态,随访确认患者康复,病人也告知服药后改善了睡眠质量,不再口苦,脾气变温和,工作压力也随之减少[2]。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中医的医疗是一种特定的“生理—心理—社会”建构过程:身体的问题也会导致心理和社会角色扮演上的问题。通过治疗之后,身体的问题解决了,心理和社会角色扮演也恢复了正常。
由上述中西医的不同医患沟通特点可见,中医“天人合一”的健康观念既讲求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又可视为个体和其生存的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疾病不仅意味着身体诸多要素之间的不和谐和不平衡,也意味着个人社会生活与社会角色扮演上的不和谐与不平衡[2]。这一点与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5]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书中强调的一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历,都可能进入他对具体病情的理解中。换言之,患病是一种社会状态。当医生把一个人的一种状态诊断为疾病时,这个诊断就常常会改变病人的行为。
4 结语
中西医在发展之源都走着相近的路,早在希波克拉底时代,西医界也流行“四体液学说”和自然疗法。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在19世纪之前,都维持着传统的医患关系:病人对自己病情和治疗方式具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1]。这一点在朱森(N.D.Jewson)的经典研究里就指出了。但是,现代医学的兴起完全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再用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病人的自感不再成为诊断和治疗的焦点,医生的“专业训练”让他把焦点聚集到“人”以外的病症、数据和检验报告上。从此,中西医的医患关系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传统中医的医患关系也正在被改变,中医师在现代医学培养模式下开始学习西医的专业制度和价值,同时被驯化为“现代医生”。值得思考的是,传统中医医患关系的价值正在引起当今世界主流医学界的关注,一些调查说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求助于包括中医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的一个原因就是患者感觉到“被尊重”。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今中国医疗环境下,难道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评价中医医患关系对现代医学回归“人性”的重要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