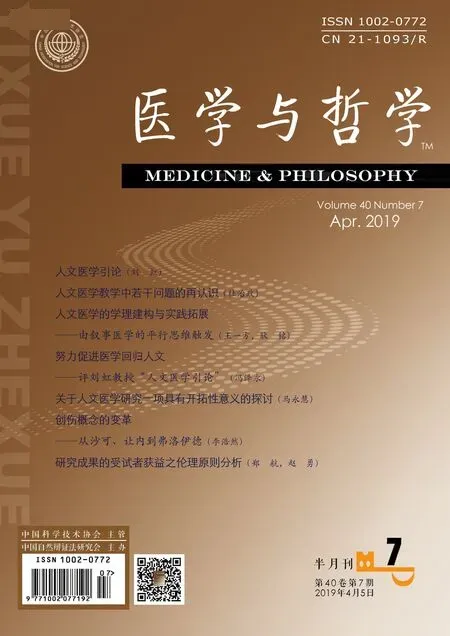研究成果的受试者获益之伦理原则分析*
2019-02-25郑航赵勇
郑 航 赵 勇
临床研究中的伦理原则贯穿了临床研究整个过程,包括研究结束以后。随着临床研究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关于临床研究结束以后的受试者获益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而目前在国内却少被关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基于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分析其相关伦理原则的发展演变,为我国的临床研究规范化发展以及伦理审查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1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相关条款的发展
临床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公正原则。临床研究受试者在参加研究中承担了风险,如果研究干预措施被证实对受试者是有益的,那么受试者就应该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益,否则是有违公正原则的。
早期的药物临床研究多由欧美发达国家发起,产品上市后也多在发达经济体系内销售。由于发达经济体之间比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药物临床研究的受试人群和上市后药品的销售人群可以保持基本一致,并且由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药品注册标准互认,药品上市的时间差异也不大。但是随着在发达国家进行临床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业化临床研究开始走向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和研究者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药物临床研究,利用发展中国家广泛的潜在受试人群以及临床研究的低成本和相对薄弱的临床研究管理。由此,关于临床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获益成为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这些新药上市以后,一方面,在其专利保护期和市场专营期内,维持高昂的价格,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很难负担;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当地药品监管政策和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也不利于这些价格高昂的专利药品的市场准入。最终导致为药品研发贡献了很大力量、承担了很大风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受试者却享受不到研究药物上市后的好处。他们无力购买或购买不到这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新药或获得最佳治疗方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承担和利益分配不公正问题在新药开发领域的反映。
为了强化临床研究的受试者权益保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受试者保护,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及世界卫生组织于1982年联合制订发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CIOMS),并在1993年更新版本里首次提出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问题。
1993年版CIOMS基于《贝尔蒙报告》的公正原则,在其“准则2:向未来受试者提供的基本信息”中,明确提到:“在评价疫苗、药物或者其他产品的研究中,应告诉受试者若这些产品经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应让受试者了解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应告诉受试者在他们参加的研究结束后和产品得到普遍供应许可期间能否继续得到该产品,他们是会免费得到该产品还是需要付费。”[1]正是这一条规定揭开了关于研究结束后受试者继续获益的讨论,并在此后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和争议。可见,1993年版的CIOMS已经关注到了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获益问题,涉及到研究结束后受试者能否以及如何继续获益,是否需要付费三个关键问题。但是本条款所指明的关于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益的这种义务不是必需的。这一条款把研究结束后划分为研究结束后产品上市前,以及产品得到普遍供应许可期间两个阶段,对于这两个不同阶段来说,其可能获益与潜在风险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的药品仍然是研究药物,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还处于有待验证的过程中,潜在的风险更大,可能的获益更不确定。
2002年版CIOMS在“准则5 获取知情同意:应提供给未来研究受试者的基本信息”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研究结束后,受试者将被告知总的研究发现,以及和个人特殊健康状态有关的发现;当研究结束且研究产品或干预措施已证明安全有效时,它们是否会提供给受试者,何时、如何提供,以及是否要付费。”[2]此版本关于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获益的伦理规定和1993年版的内容实质上基本一致,就是强调有义务告知、不强制提供。
2016年发布的最新版CIOMS里,在“附录2 知情同意:前瞻性研究的基本信息”中的相应表述是:“如何安排研究结束后的医疗护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试者能够在研究结束后继续得到有效的研究干预,以及他们是否需要为之付费。”[3]这个表述相比于2002年版的表述更加简洁,实质是一致的。另外,这一条款提出了“研究结束后的医疗护理”的概念,也就是把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的继续获益问题纳入了受试者作为患者的整个医疗护理体系考虑。
2 《赫尔辛基宣言》相关条款的发展
2000年版《赫尔辛基宣言》最早引入了《贝尔蒙报告》的公正原则,并首次对研究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问题做出了反应。其中第30条规定: “研究结束时,应该确保参加研究的每个患者受试者都能得到被研究证明的最佳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4]此条款实质上是对1993年版本CIOMS“准则2”的呼应,但不同的是,本条款的立场是有义务确保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药品监管当局和制药企业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研究结束后,谁来负责确保受试者继续获得治疗?如果把这个责任落在申办方的身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无力改变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的医疗卫生保障条件的差异,也无力落实在每一个国家实现统一标准的最佳干预措施。他们认为给参加研究的受试者提供被证明最佳的治疗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卫生系统和监管当局的义务。
面对争议,世界医学会在2004年第55届世界医学会大会做出了正式回应,对《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版第30条规定做出澄清注释:“必须在研究的计划阶段明确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获得研究中确定的有益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程序,或其他合适的医疗。研究结束后得到这些安排或其他医疗必须在研究方案中说明,以便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考虑这些安排。”[5]对第30条的澄清注释进一步强化了关于利益分配公正的立场,要求在研究方案里就要明确说明,并经过伦理审查。但是这个澄清注释没有再使用“最佳干预措施”这个有争议的词语,而是代之以“研究中确定的有益干预措施或者其他合适的医疗”,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药企的关注点。但是此版修订的澄清仍然没有回答谁来对这一系列安排负责的尖锐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这一条款在实践操作上的落实。
2008年版《赫尔辛基宣言》第33条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做出了修订:“研究结束时, 参加研究的受试者应被告知研究的结果,分享由此获得的任何受益,例如获得本次研究确定的有益干预措施或其他相应的治疗或受益。”[5]与2000年版第30条和2004年的澄清注释相比,2008年的第33条有两点显著改动。第一点是增加了受试者对研究结果的知情权。第二点提出受试者应该分享来自研究的“任何受益”,其范围包含并不限于研究确定的有益干预措施或者其他相应治疗。将受试者可以分享的研究利益扩大到“任何受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拿着这把剑向发达国家提出更多的利益主张,比如为实现本国受试者获益而要求跨国企业缩短专利保护期、降低药品售价等。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可以所谓的“任何受益”没有明确所指, 逃避任何义务[5]。
2013年版《赫尔辛基宣言》第34条对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修订:“试验开始前,申办方、研究者和试验所在国政府应针对那些研究结束后对试验中业已证实的有益干预仍有干预需求的受试者,就如何获取这些干预拟定条款。此信息必须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向受试者公开。”[6]相比过去,2013年第34条体现了三大理念。第一,首次提出了申办方、研究者和主办国政府应共同承担使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益的责任,并且要在研究开展前确定。这就引入了多方共治、事前设计的科学理念,为这一条款的落实打下了基础。第二,提出了在知情同意阶段就要告知受试者这一权利以及相关的具体规定,而不是在研究结束后才告知受试者。这和第一点的逻辑是相同的,把受试者在研究开始前纳入到对这一条的认知和落实中来。第三,没有再明确地要求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益的义务是必须的,而是需要“就如何获取这些干预拟定条款”,这就和2002年版CIOMS的准则5的规定内容接近了。另外,2013年《赫尔辛基宣言》第34条删除了关于“任何受益”和“其他合适的医疗”这样的模糊不清的表述,改为“在试验中确定有益的干预措施”这一简单明确可操作的表述。
尽管如此,落实这一条仍非易事,需要申办方、研究者和当地国政府在研究设计阶段就要协商达成关于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是否能够继续获益的一致性意见以及如何继续获益的解决办法,并在研究方案和知情同意书里做出相应说明。而当地伦理委员会也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做出审查,并在如果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假设下,从伦理上权衡在当地开展该项临床研究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3 实践与启示
由于关于临床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的伦理原则的争议以及在操作上的复杂性,人用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中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在ICH的E6(R2)的原则2.2中提到:“在开始一项试验前,应当权衡该临床试验对于个体受试者和社会的可预见风险、不便和预期的受益。”[7]另外在ICH的E6(R2)的原则4.8.10关于知情同意书中应向受试者提供的信息条款中提到:“可合理预见的受益,不存在预期的临床受益时,受试者应当知道这一点。”[7]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两处中提到的“可预期受益”应该包括研究结束后的继续受益。
在当前实际操作中,部分外资药企的临床研究项目会在知情同意书中对研究结束后的继续获益问题做出明确说明,告知受试者是否以及如何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得有效治疗。针对在临床研究阶段有确实获益的受试者,特别是罕见病以及肿瘤等重症患者,部分项目会在研究结束后持续赠药到疾病某阶段甚至药物上市,更多的是通过新的临床研究形式实现对这些患者的赠药计划。这类以赠药为目的的新的临床研究通常是在对原研究方案的修订简化基础上进行的,在保障受试者获益的同时,可以收集患者安全性数据,作为注册上市的数据补充。
但是,药品最终需要在当地国注册上市,并且以合理的价格为患者可及,才能得到广泛而且持续的应用,然而,长期以来,进口药品在中国的上市普遍比国外慢,并且价格昂贵,很多患者难以承受,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受试者及其代表的患者群体及时获得最新的有效的治疗手段,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受试者在研究结束后继续获益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从根本上讲,解决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问题需要申办方药企、临床研究者和试验所在国政府多方共治、协同努力,让好的进口药品尽快在受试者所在国家上市销售,并且以合理价格让受试者及其代表群体可获得、可负担。
过去的申办方多以向药监当局递交一份研究报告作为一个临床研究项目的结束点,而对于临床研究结束后受试者的继续获益关注甚少。在当前提倡将临床研究从过去的以研究药物为中心转移到以受试者为中心的背景下,构建临床研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新理念,重视临床试验结束后受试者继续获益的伦理问题成为了大势所趋。
随着新药注册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医药产业已经进入新时代。一方面,通过加快药品审评审批,降低进口药品关税,实施进口药品价格谈判等措施,促进外国药品在中国的同步开发、同步注册、同步上市,并且为患者可获得、可负担;另一方面,也鼓励更多的中国新药研发走出国门,去发起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开展国际注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顾并分析关于临床研究结束后的受试者继续获益问题的产生背景以及伦理原则的发展历程,对于促进我国临床研究规范化发展,提升伦理审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