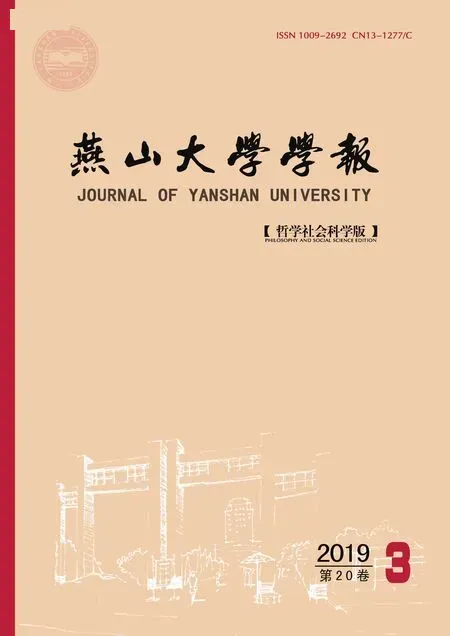英语世界的元散曲题材论
2019-02-25李安光
李安光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由于元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文人独特的社会境遇,包括元散曲在内的元曲作品与前代文学类型相比,无论是在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均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风貌。就元散曲丰富的题材内容而言,任讷将其概括为“博”“杂”,“若论二者之内容,当然为词纯而曲杂,词精而曲博矣。夫我国一切韵文之内容,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要之,衡其作品之大多数量,虽为风云月露,游戏讥讽,而意境所到,材料所收,故古今上下,文质雅俗,恢恢乎从不知有所限,从不辨孰者为可能,孰者为不可能,孰者为能容,而孰者为不能容也。其涵盖之广,固诗文之所不及”[1]13-14。
就国内学界而言,赵义山在其《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中第五章详细梳理了元散曲的各种题材类型,系统且全面,很有代表性。他把元散曲的题材内容共总结为四大类:叹世归隐、怀古咏史、恋情闺怨、自然山水等,并就其中代表性的论点作了扼要陈述。除上述题材内容外,经笔者梳理还有一些学人论文已论及很少被人关注的题材内容,比如刘博苍的《试论元散曲中的“四季歌”》、田同旭的《一个虚假的繁荣景象——论元散曲中农村题材的作品》、李春祥的《元人散曲中的讽刺时政主题》、奚海的《真实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士子壮志辅国精神的时代壮歌》等,均从不同侧面涉及了元散曲丰富的题材内容。
英语世界对元散曲题材(主题)内容进行详细论述的当数柯润璞(J.I.Crump)和克朗(Elleanor H.Crown)师徒二人,柯润璞的关注对象主要为小令,而克朗的考察重点则是散套。除此之外,黎得机(Kurt W.Radtke)对《阳春白雪》中的小令、王琳达(Linda Greenhouse Wang)对马致远散曲之题材内容亦有所论及。
一、柯润璞的题材研究
柯润璞是美国元曲研究名宿,研究兼攻散曲和杂剧,为美国本土第一代元曲研究之领军人物。柯润璞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旋即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直至1989年荣退,其间长达近40年于该校执教中国语文和文学,并培养了诸如奚如谷、章道犁、克朗等美国本土第二代元曲研究专家以及像彭镜禧、任友梅等华裔元曲研究学者,为中国元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柯润璞有关元散曲的论著主要为《元上都歌诗》(1983)和《元上都歌诗续》(1993),其对元散曲题材内容的论述就集中体现在这两部专著中;另有《兴盛时期的元诗研究》(The Study of Yüan Song Poetry Comes of Age)一文。此外,他还分别在《散曲的翻译》(Translating San-ch'u)、《翻译散曲的两种工具》(Two Tool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an-ch'ü)等论文中对元散曲的英译问题进行了详细且富有启示性意义的论述。
《元上都歌诗》一书的总体章节结构为:导言;第一至八章依次为,韵律学(Ⅰ)灵活性及措辞、散曲中的题材(主题)程式、张养浩(1269—1329)生平及其散曲、渔闻樵话、域外的汤姆·郝登(Tom Hoyden)或曰中国散曲及他处中的乡巴佬和傻蛋、韵律学(Ⅱ)、失落的爱情故事、雁字和篆香计时;附录、参考文献及汉字索引等。《元上都歌诗续》一书共分导言、爱情诗、讥讽和戏仿诗、机智、沉思和友谊之歌、雪日近京:冯子振及其散曲、索引等部分。通而观之,我们可依据这两本专著的上述内容将柯润璞的元散曲研究大致分为三大类:韵律研究、题材内容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研究。就题材而言,综合柯润璞上述两部专著中的关于元散曲题材内容的论述,笔者将其概括为闺情爱情类、道情归隐类、渔樵田园类、讥讽戏仿类等四类,现分述如下。
(一)闺情爱情类
在《元上都歌诗》第二章“散曲中的题材(主题)程式”中,柯润璞首先就指出元散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类题材是闺情爱情,并将其概括为“情色程式”(the erotic convention)。
早期曲作如同早期词作,多写与爱情有关的题材作品,后又扩大到其他感情。如同词一般,曲作起初主要是为室娱之乐,所以,毫不奇怪,曲作大都涉及歌妓、伶优职业,至少其起源时如此。柯润璞认为,所有时代的曲作都充满纱衣、床帏、丁香味香唇、香粉、珍贵青铜香炉、帷幔上的绣玉钩、小拖鞋、云鬓、蛾眉等这些极富情色意味的意象或象征之物;还有些有趣的乱象,比如蛾眉上的露珠、枕上香颊印,凌乱发型、薄纱便衣等。徐琰就有《青楼十咏》,其分标题为:初见、小酌、沐浴、纳凉、临床、并枕、交欢、言盟、晓起、叙别,极具特色,很有代表性。
当然,闺(爱)情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孤独的女人在青楼中等待有情人,这也是先前古诗特别是词作中常见主题,它被不同诗人以不同方式采用,已被程式化,可以认为,该主题内容与诗人自身的情境或经验无关。“曲作中,该主题仍十分有生命力且被广为采用,它和感情、美女和一些女性环境等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些主题相关的诗群,我把此简化称为:情色程式。”[2]31柯润璞特别指出,和词相比,元散曲主题转向高尚和英雄方面相对较晚,而且这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意义不大;然而散曲却从早期至晚期有一个一致的主题:涉及美女、情色、华丽妓院、懒散的淫荡人等。纵观《全元散曲》第一卷,大概有40首小令和散套关乎闺愁、闺怨,和春思、秋哀等主题连在一起构成了散曲的典型主题,这被克朗归结为“闺中的泣号”。许多著名散曲家均有这方面的作品,如张可久就有11首以“闺情”或其他类似主题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关汉卿也有艳俗之曲,白朴虽出身官宦之家,卢挚也身居官位,但也都有这方面的作品。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真正的儒者张养浩。郑骞就曾抨击任讷和其他学者将一些情词艳曲归于张养浩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他的玷污。但柯润璞认为,没必要如此机械地区分,泾渭分明,张养浩也可能写些俗曲以作为其早期新手时的历练。
这些俗艳散曲也有闪光的意象,很值得一读。“然而最吸引人的是其中的少许机智诙谐、人类脆弱的惊人闪现,还有各种富有新意的形式运用等。”[2]33就艺术形式而言,柯润璞就特别盛赞此类元散曲中“一半儿——一半儿——”诗尾形式。
在《元上都歌诗续》第一章“爱情诗”中,柯润璞又对先前的元散曲“情色程式”题材作了更通俗化的阐释。
彼此相爱是人之本性,亦是音乐和文学创作的母题。柯润璞认为,元散曲大概应是历史上所有文学类型中歌颂和描写此类主题最多的文类。
无论时空相距多遥远的人类,其对爱情的描绘都是一样的。散曲中有描写因爱生妒的,有因爱相思成灾、备受思念渴求等方面的折磨的;亦有对不忠和玩弄爱情的嘲讽、憎恶和哀怨。
柯润璞认为,在传统中国,浪漫爱情大部分局限于娼妓,因为在传统中国,人们一般认为浪漫爱情没有婚姻和家庭的基础,只是调情、怡情的闲话轶事。元散曲中的爱情描写大都是以娼妓歌女为主角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一般程式。歌妓一般具有出色的舞技和歌技,更出色的则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亦能在筵席之上与宾客之间作诗唱和。有时文人就会写散曲作品专给这些歌妓用以演唱,而歌妓亦能以歌其诗为一种身份和荣耀的体现,但这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文人间的某种“争宠”性的竞争。对于此类爱情,他认为以娼(歌)妓为内容的爱情程式具有固有的弱点和内在矛盾,也通常会导致此类爱情故事的悲怨结局,那就是商业利益以及爱情的分享性(而不是彼此爱情的独占性)。
当然,也有描写和反映文人与歌女间真挚深厚爱情故事的,比如苏卿和双渐之间的故事在元散曲爱情主题中的运用,既有对其歌颂、借题悲怨感慨的,亦有戏仿该故事的作品。对于闺情和闺怨诗,柯润璞认为,这类诗多与象征秋天的诸多意象相连,如菊、落叶、鸿雁、鸣虫等。对于有些男女间秘密幽会的爱情诗,他认为,“如果为上述所谓的文人间'争宠'而作的诗歌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学的话,那么写男女幽会的情诗则是中西共通的。”[3]50古希腊神话中有皮拉缪斯和忒斯彼(Pyramus and Thisbe)这样的巴比伦情侣,中国亦早在《诗经》中就有男女幽会的描述,特别是那种受家庭阻挠的幽会。
就创作层面而言,柯润璞认为元散曲中的许多爱情主题及其处理方法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属于文学创作的程式,其中不必有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散曲作品中的女性多为一般化了的娼妓歌女,但也有些生动具体女性形象的描述,如商挺的《[双调]潘妃曲》中的几只小令。虽然词曲较中国传统古诗而言多用了些人称代词,但是我们还是很难从曲作中分辨出,作品中的叙述人究竟是个全知全能的讲述人,还是其中的主人公,抑或是作者本人。
(二)道情归隐类
在《元上都歌诗》第二章中,柯润璞除提到“情色程式”外,还提到一种“道情、归隐类程式”,其典型的主题内容为弃功名、绝欲念,与山风野鹤相伴,归隐自然,逐退红尘。
对于道情散曲的由来,柯润璞认为:“曲由宫室之娱,转向后来的文人创作,也就使得道情散曲受乞食道士歌唱激发影响而形成成为可能。……但是否二者有直接的关系,不得而知。但因为文人应天生对其周围的何种音乐性质的声音敏感,道士行吟歌唱、引浆卖流之徒的吆喝、妓院青楼歌谣等等,都有可能被作家吸收到其曲创作中。”[2]40
对于道情散曲的意蕴层面,他认为,既有像张养浩那样真心归隐、虔心“归道”心境下创作的一种深层、超验层面的道情散曲,也有或更多的是一种躲避时祸、“及时行乐”、满口山林归隐但实心功名利禄的一种表面、伪装层面的道情散曲。而真正的道情曲特点应指一种超验的归隐,但有时“及时行乐”的道情散曲却又比那些描绘超验世界的道情散曲更具有当代的吸引力。
当然,柯润璞亦明确指出,归“道”更该是种内心的皈依,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皈依道门;有些散曲虽不自认为是道情曲,但实际上却传达的是一种真正道情曲的主题思想;道情散曲不是单纯的“道家感情”的倾泻,更是一种归隐心境的表达,这在元代是史无先例的流行主题。归隐类主题散曲也和情色作品一样,有大量的表述套语,或者是陈词滥调,诸如红尘、是非海、南柯梦、藜杖;绿肥红瘦、燕子衔泥筑巢、鸳鸯、桃花雨等等。而真正优秀的诗人,应是能熟练地运用其技艺程式,从而使其作品更具独创性。
(三)渔樵田园类
英语世界最早也是唯一向西方读者介绍渔樵这一中国文学母题的学者当为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他说道:“在改写故事这部分时,吴承恩保留了张梢的渔夫身份,但把李定写成樵夫。两人都被写成有学问的村夫,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就各自职业的利弊用诗歌进行论辩。这种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田园文学主要成分的论辩,在明代小说中并不少见。”[4]123
柯润璞认为,这种渔樵之辩中西皆有,它反映了人类对田园乡野生活的深层感情;人们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由来已久,并想象和创作了大量反映世外桃源、美好乌托邦的作品,竭力寻求这种美好图景的真实存在;不过,在西方文化与文学中,与中国渔樵地位相当的应是牧羊人,这是由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家,而西方则是根植于传统的地中海文明。
柯润璞指出,文人描写田园,羡慕田园生活,赞美田园单纯生活和乡民的淳朴德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想真正成为乡民中的一员。受教育、学而优则仕,才是他们及其家庭的厚望。其实,农民的真正生活是穷困的。渔人的生活也不比农夫好到哪儿去,有时生计会更受制于天气状况,他们无社会地位,其狩猎打鱼也会受到政府的种种限制等,而捕猎环境的恶劣,也使得渔人更具有迷信倾向。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作家文人对渔樵的理想化。渔人代表着独立、自由,能吃鲜美的食物,捕鱼亦是项充满思考的活动。而樵夫也是自由的代表,走动自由、免于农民的苛捐杂税。但柯润璞同时认为,樵夫遇见歹徒和不法者的几率也大,并与他们有勾结,盗猎当地牲畜,品性也不见得都好。
事实上,文人与樵夫几乎不打交道,很多作品纯属构想。有时这些归隐的文人有可能会成为渔夫,但文人本身是樵夫的却是没有,与其为邻倒是有可能的。所以,柯润璞推断,所有乌托邦式的田园描绘都是想象,而不是现实的描绘,真实的描绘反而令人不可信。所以,世外桃源更多人造成分。与西方的伊甸园不清晰描述相比,中国的“世外桃源”、道家仙境则是具体可感的,甚至会有具体地点。而渔樵对话,则成为一种田园乌托邦的象征代言。
除田园象征外,在另一种情况下,渔樵闲话亦会成为一种“繁华不再,一切虚空”的主题思想的代言。对ubi-sunt(现在何处?)的追问,中西皆有,只不过采取的形式不同,中国诗人惯用 “渔樵闲话”,而且已成陈词滥调,这在元曲中尤为常见。
(四)讥讽戏仿类
在《元上都歌诗》第五章中,柯润璞饶有兴致地探讨了元散曲中一类特有的题材内容:以乡巴佬或傻蛋为描述对象,以或讥讽或无恶意的戏谑之立场描述了他们的或愚笨可笑或天真机智的言行举止,从而使作品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是讥讽和戏仿类作品中特有的一类。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关于乡巴佬或傻瓜的传说和故事,人们从内心深处喜欢这类故事。它起源于人类城镇化发展而导致的乡下人——城里人、无知愚昧——文明这种二元对立城乡模式的出现,而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类故事又会不断推陈出新,以各种不同、层出不穷的面目呈现出来,“每一代人对这些故事都作了新的补充,尽管许多古老的故事有时就像埃及人或古希腊人穿上奇异的新衣服,被当作某些新的发明物。”[5]224-225这是一类别样的文学母题,其中既有带“种族歧视”意味的傻蛋故事,亦有充满机智和教益性意义的故事。
不管有关乡巴佬或傻子的地点是真实存在还是臆构,其功能都一样。而且,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才能很好理解的逸闻趣事、傻蛋故事等程式套语、典故等。柯润璞以中西文学比较的视角指出,英国伊丽莎白时期吉格舞中的一个人物汤姆·郝登,就是该类题材故事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善良的乡下人,他天真单纯地对城市的观察和体验已成为英国文学中的重要题材;类似于中国元曲比如杜善夫《庄家不识构阑》中的那位看戏的乡下人,该散套所反映出的金院本的剧场和演出情形,就类似于英国的吉格舞。
柯润璞指出,此类作品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情节突变(peripeteia)。这些傻瓜除可作为嘲讽的对象外,还可被视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天真汉形象。乡巴佬可能笨傻,但却也能向我们显示一种令人愉悦的简单的生活方式,至少和城市的压力与混乱相比是如此。在东西方,虽然乡野田园经常是世故、城市人的嘲讽对象,但通常我们发现这些描写田园生活的人都非常渴望、羡慕这种生活,这类田园诗或剧大都隐含着对田园生活的歌颂。这种既嘲讽又渴慕的矛盾心态在元散曲中表现最为明显,比如《庄家不识构阑》中,虽有单纯庄稼汉和世故剧场之间的幽默比较,但很明显,该套曲开头有关田园的描述如果没有真正的田园体验是写不出来的,它清楚地传达出曲作者对田园生活的深切体认感。
将整个CAD模型导入到ANSYSTM Workbench软件中对其进行有限元分析 [11]。定义整个膜片的材料为Solid187,并分解成13482个节点。根据实际情况,膜片的底面被施加完全约束,刻蚀腔里面的5个面被施加压强,如图5所示。经过计算,在压强为15kPa下的情况下,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薄膜的最大变形量为 1.831μm。
对于戏仿类散曲作品,在其《元上都歌诗》中,柯润璞特别提到王和卿的散曲作品《胖妻夫》与《胖妓》,其中《胖妻夫》就是对苏卿和双渐爱情故事的戏仿之作。再如唐毅夫的套曲《[南吕]一枝花·怨雪》,传统认为“瑞雪兆丰年”,一场大雪预示着来年的好兆头;但唐毅夫却以“瑞雪”戏仿,揭示了冬日雪天生民之痛楚、民生之多艰。
尽管讥讽主题的作品每个文类都有,但是和其前、其后的诗歌作品相比,柯润璞指出,元曲中则含有更多的此类作品,而且嘲讽对象(人物)多样,有歌妓、和尚、说谎者、纨绔子弟、色鬼、华而不实者等等。在谈到对此类作品的评价问题时,他认为,这些讥时讽时的作品,是独特个体看到其所处时代的独特视角,当然有其独特价值;元散曲不是没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政治的作品,但总体不多而且多在元初,大都是些温和、非激进性的作品;但是如若硬被阐释为某种政治或社会学理论的话,那么就会生出诸多谬论来。
综上而言,柯润璞的元散曲研究以题材内容为主体,兼论韵律、作家作品。与我国学界相比,他基本上论及诸如归隐、田园、爱(闺)情等方面的题材内容;而对讽刺戏仿类主题内容的论述,如中西纵横谈论乡巴佬或傻蛋主题程式、以“戏仿”之词来归结元散曲特有的题材内容,都更多地显示出了他特有的西方学术思维规训的研究路径;而对“怀古咏史”类题材的不经意忽略,则彰显了西方本土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膜。在英语世界,柯润璞是首位也是最全面论及元散曲(特别是小令)作品题材内容的学者,他开辟了元散曲题材研究的先河,拓展了元散曲的研究范围,在向西方学人和读者呈现元散曲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的同时,展示了元散曲摇曳多姿的艺术特质。
二、克朗的元散套题材研究
作为柯润璞的高足,克朗在其专研散套的博士论文《元散套宏观结构、内容及其与别种曲形式之比较》中,除探讨了元散套的联套特征、宫调与押韵等方面的艺术特征外,还集中讨论了元散套的题材内容。
首先,克朗同样认识到元散曲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对此,她说道,元散曲向来以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而闻名,这多是由于散曲作家都是在前人已经开拓并发展出的多种多样的主题内容的基础上创作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作家对过去传统继承多少,但有一点很明白,他们一定深谙并具有中国诗歌的渊博而优良的传统。
其次,对于其题材丰富性的原因,克朗解释为是元散曲对先前文学类型特别是诗歌及同期元杂剧题材内容的承继与借鉴。诗的疆域在宋代就被大大拓展了,新出现的词亦开始表达浪漫而温和的情欲故事。在写诗的同时,宋代文人也开始关注先前一些被忽视的主题,并将其融进诗歌传统中。华生(Watson,Burton)就言道:“这么多的文人创作了数量超多的诗歌,很自然地,其作品主题亦会异常丰富多样;如若不是如此的话,单调乏味的情形一定会让人难以忍受。”[6]198宋代诗人把诗歌从神坛拉下,而于其题材内容中融入了日常生活(甚至是其丑陋面)、社会反抗和公开坦白的幽默等方面的内容。除了传统诗歌的影响外,散曲特别是散套亦汲取了迅速崛起的杂剧传统。不论散曲还是杂剧谁先谁后,散套和剧套在结构上还是基本一样的,在散套作家们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吸收当时新兴杂剧和较早的准杂剧文学(如院本)中的主题内容。
对于元散套的题材内容的分类,克朗依据作品中的主题、人、风景、意象、引用及其他诗性手段甚至作品的标题①等因素将其大致分为五大类:情感诗(poetry of emotion)、自然诗(nature poetry)、玄理诗(poetry of ideas)、应景诗(topical poetry)和特类诗(special poetry)②,还有一种“多样综合性的散套”(miscellaneous suites)。
(一)情感诗
第一,该类散套又可细分为爱情和友情两类。
尽管有无望爱情的描述,但表达爱情喜悦的作品在该类中也很普遍。这类作品秉承了先前的宫廷诗传统,充满着诸如女性盥洗、梳妆打扮等方面的丰富意象,因而它们与词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此类情感诗以及另类“应景”诗中还包含着散套中较具情欲性的作品中的大多数作品。
另有些情感类散套是庆祝男人之间友谊的。常见主题是送友远行、归寺或辞官隐逸。它们的作者大都是晚元作者,作品程式化,类似于闺怨诗,缺乏创造性。还有一些作品声明以特别个人为主题,然而,大部分没有独特之处,多是充满陈词滥调式的意象及无创造性的程式之作;读者也很难看出其中的独特个性(它们中有些亦被归入“应景”类散套作品中)。
第二,克朗还总结了情感类散套的一些具体特征[7]26-28,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1)所写之人为广泛意义上的爱(情)人和朋友。意即,作者很少交代所写之人是谁或为谁而作之类的信息。文中所写之人的身份没有细节描述,关系和情境的独特特征都是暗示性的,而不是明白表出的。该类中的许多作品具有其读者所熟知的语调,而其中所呈现出的经验的普遍性又使得这些作品如同贴近作者的生活一样较易贴近读者(或观众)的生活。
元散曲另一个有趣的方面就是女性有时会被准予表达自身的情感,而这对早先的诗歌而言则是一种不恰当之举。卖弄风情,这在宋词和元曲中都是较常见的;但是,元曲的创新之处却在于女性能真实的发泄自己的愤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元曲中男人大都具有些固定化的特性,比如懒散、易怒、倦怠无聊等这些先前由女性身上所体现的特性。
(2)景观描写与现实性相比经常是更具象征性。诗中构建的地点是为了增强浪漫或情欲的心境,比如闺房、彩塔、空床或者是男人们追逐好运的孤独偏远之地。这类诗中充满着与爱和离别相关的地点,比如蓝桥、楚台等。我们在这些地点上看不出有关该地点特征的景观细节描写,它们只是“心境的体现”,而不是地理上的描绘。
(3)在情感类散套中,有大量的一整套固化的意象(就像在早期及其后的诗歌中一样),它们多因为其自身的文化或民间含义而不是原始意义而被选来运用。各种鸟被视为信使;梧桐和柳树,有种沙沙声而来的悲伤;还有燃尽的蜡烛、消逝的浓香等。
(4)还有些引用。最常见的两个就是“簪”和“瓶”;比如“合瓶”就一语双关,象征着同声的“和平”。
(二)自然诗
中国的自然诗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元代诗人主要继承了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传统,而他也确实在元代散套中扮演着显著的角色。有许多散套包含着自然诗和玄理诗的因素,所以界限不明,一些散套可以明确地归入上述两类中。
对于自然类散套的范围,克朗强调,除田园诗外,她归结的自然类作品还指这样的一类散套,即主要关注于自然现象、一个或多个季节、天气等等。许多散套的中心围绕着宴请、奢华的娱乐或适合于某一季节的日常活动等。上述这类散套作品通常就不属于田园诗的传统了,但它们都强调了自然现象对人类心境和活动的影响,都依赖于自然的描述而且都有种将人视为仅仅是环境的一部分的倾向。
自然类散套中还有些作品亦可视为“应景”诗,而唯一可能的标尺就是主题限制作品的程度。比如,四季或任一季节的主题对诗作就很少限制,而且一般而言,它们很少关注自身,只是对作品而言提供了一个整合统一的因素。与此相反,如果诗人特别将自己限制于既选主题,那么一首关于“雪”的散套就会有太多限制的范围。
对于自然类散套的特点,克朗总结道[7]38-42:
1.人物的地位和作用与其在其他几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
例如,在情感类作品中,尽管很少细节人物刻画,但人物仍被认为是个体或者与某些人相似,在这类散套中,表现的经常是诗人对重要人物的态度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身体描写。在自然类散套中,则恰恰相反。关于人物的身体细节被给与了详尽关注,然而这些个体自身的功用仅仅是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他们可和其他人有时是物之间相互转换。田园诗所常用的人物形象是老渔夫、樵夫、以及其他与诗人共享食物、美酒并交为好友的乡野村民等。这些人都是场景的一部分,而无法确认身份的这些个体亦是这场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其他自然类作品里,这些人物往往是些在其描述的季节中常见活动的一些人:宴会上的歌女、秋天里的织女、春日里的养蚕女等等,此种情形下,个体活动而不是人物个体是最重要的。
2.景观描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自然类散套的主要区别性特征之一
在自然类作品中很少处理个人自身的背景细节,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在自然类散套中不存在更宽泛的、不明确的有关个体方面的描述部分以及有关人物“心境体现”方面的独特原创;有时它们会同时存在且类似于情感类散套中的相关“描述”和“心境”,但是,自然类散套中的心境通常是完全不同的另种心境了。另外,这类散套大都在文首指出某种诗人于此中描绘自身的特殊情境。
3.这类散套中的意象比情感类散套中的更具自然特征
曲作者不是选择某些数量有限的、携带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自然意象,而是选用诸如树、植物、鸟、动物等,它们除自身的美丽、益处、在宇宙中的通常地位以及与人类的关系外,很少再有其他意义。对其中的自然意象给以任何象征性的阐释都是对作者原意的歪曲。
4.在自然类作品里亦有些数量有限的引用
田园类里最常用的两个引用就是陶渊明和邵平。陶渊明的黄菊,邵平的“东陵瓜”,均和归隐、闲逸的田园生活紧密相关,因而作为为数不多的两个常用引用,多出现在表现闲适归隐类的元散套中。
5.运用了一些诗性手段
(1)将自然景色与一幅画比较。大都是说明自然景致巧夺天工,非人为绘画所能模拟,更进一步引申就是对自然景观的文学描绘亦是不足的。
(2)运用有着相同开头字或相关词组的对仗性的词组,这很像西方修辞和诗学工具中的“首语重复法”(anaphora)。以贯石屏的散套《[仙吕]村里迓鼓·隐逸》中的几句为例:
闲时节观山玩水
闷来和渔樵闲话
闷来时看翠山
闷来独自对天涯
醉时节卧在葫芦架
睡起时节旋去烹茶
兴来时笑呷呷
自然类散套中很少有连贯(叙述性)的发展脉络,每部分都可单独成文。
(三)玄理诗
玄理诗在元代之前就有了一个多样而繁盛的历史了。元代的许多玄理诗都是以道教哲理为中心的,从道家宇宙观的陈述到用隐含的道家思想来对待田园生活等,而前面提到的有些田园自然类散套亦可归入此类,还有些政治和社会反抗类的散套也可归入此类。
克朗强调,必须指出一点,尽管散套有范围极广的主题内容,但其中很少有能启发人智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这里的哲理散套也主要是关注于大众化的情感,包括时光易逝、崇尚简约生活、命运的改变等,而不是形而上学观念的发展。她认识到,尽管宋朝的遗老和元代的隐士们在其他形式的诗作中表达了当下的哲理和政治抱怨,但是他们的散曲作品甚少,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用散曲来作为此种情绪表达的工具或手段了。“很少有散套在庄重性方面能达到这些人的诗作的,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元代诗人为其严肃写作选择一种工具时,尽管曲在当时是很繁盛的一种文类,但他们还是另选其他。这或许是由于从他们内心深处不情愿提升这种新文类(曲)至高贵的地位。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散曲只为娱乐而存在,而非娱乐性的主题则不会进入散曲的范围。”[7]51
她还提到,一个例外或许就是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它是社会反抗的记录,它描述了饥荒、瘟疫和死亡这类很少在当时散曲中被触及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对于该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克朗认为多为说话者和听众。在关汉卿的《[双调]乔牌儿》散套中,有些诗节是指导个人如何生活的,而其他诗节则是作者本人迈向精神和哲理理解的心路历程。
而该类散套中的自然环境经常发挥着类似于哲思上进步的作用。“当一个人学会了将自己解脱于财富、功名、地位和其他所谓'文明'等外界环境束缚的时候,他经常是将这些描绘成自身从大都市移向乡村、静谧的山谷和溪流以及诸如陶渊明所描绘的传说中的'世外桃源'等地方,在那儿,一个可以自由的思索。”[7]52在玄理类散套中,景观描写通常充满着道德上的含义。不是简单地描述自然,这些田园环境都被赋予了美好生活、静谧、祥和以及心灵的栖息和平静等方面的属性。这类作品所用意象也是十分标准的:如有着神圣身体的动物意象,鹤和松树是长寿的象征,时间流逝就如同白驹过隙、鸣箭或流逝的河水等等。
(四)应景诗
首先,克朗界定了“应景”的内涵。“如果这些散套作品是描述性的韵文而同时在本质上又受制于其主题的话”[7]55,即为“应景散套”。这类作品中,作者通过他所选主题事件的独特性、作文的目的、或者形式等方面的因素,十分严格地限制了其自身的自由,也就是说,他创造时的有限选择性,决定了其作品的内容等诸多方面。
应景散套特别类似于六朝时期的“题咏”诗,即在社会聚集场合以给定题目作诗。应景也好、题咏也罢,均源自于汉大赋,尽管汉赋的主题有叙述性的情欲幻想、想象性景观的铺陈夸饰,但它们在表面上都是关于特定物体的。
对于应景散套的类别,克朗认为,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散套也是创作于社会聚集场合上的,但散套本身却也说明确实有这种可能;有些散套就是纪念生日、夸赞某些表演者或庆祝节日的,如果不是写于上述事件中,那也一定是写来用以在上述场合中吟诵的。从这方面而言,此类作品数量有限。为祝贺生日而作的诗,一定要夸赞被贺者的过去丰功伟绩、并许以未来的幸福快乐的美好祝愿;为歌女而作的诗,如果是用来公开朗读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有关她优雅、貌美和作为歌者精湛技艺等方面主题的变奏曲;节日诗则承载着描述和介绍某节日蕴含的特殊意义等方面的构想。就艺术创造性方面而言,此类诗不缺乏这方面的创造性,但是也有许多作品都是些相当无想象力的创作,只是些礼貌性、礼节性意象的堆砌而已。
对于该类作品的主题及其创作中的程式化问题,她指出,应景元散套在许多方面都和其先前的此类诗相似:主题选择均选自同一类,即早期咏物诗中的动物、植物、昆虫、工艺品和人等。在运用历史和传奇方面的引用时,散套也和汉赋相似;散套还具有赋的灵活性,使得散套作家能如其所愿地进行细节刻画和描写。这些散套的主人公通常是抽象的和固定化的,在此类散套中,作者所描写的某一个体或情境基本能和其他的人或情境互换。如沈禧的两首散套,所其写祝寿的散套根本不适合年长者的生日祝寿,其与所祝贺之人关系不大;其所歌赞歌女的散套也几乎适用于任何女性表演者。
(五)多样综合性散套
具有上述四类散套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属于任何一类的散套作品,克朗称之为“多样综合性的散套”。
她特别指出其中一种散套就是关于某一地方、主要是城市的作品。此类作品在中国传统的诗歌传统中常见但在散套中却不多见。此种散套具有自然类散套中景物的繁茂描述,还详尽叙述人类如同光辉自然一样的辉煌业绩,从历史深度关注人类及其文明,显示出一种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还有些散套将自然描写或自然现象的重要性与政治或社会寓意结合起来,如张养浩的《[南吕]一枝花·咏春雨》。
(六)特类诗
克朗认为,这类散套不同寻常,但却无法以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来指代它,因而暂且称之为特类散套;该类散套非常不同于其他大部分散套,亦不同于其他任何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作品;它既是种类别,也是曲形式的特别有创造性的开掘,从而使其特性与其他种散套截然不同;还需指出的是,该类散套所依材料也为其他种散套所不用。
这些散套包括《庄家不识构阑》《高祖还乡》《皮匠说谎》《牛诉冤》《羊诉冤》和《代马诉冤》。
对于该类散套的特点,克朗指出:“首先应该明白,应将这些散套看作是叙述性的而不是抒情性的……该类散套毫无疑问也是高度叙事的,而且是以叙述逸闻趣事为特点。”[7]67-68她进而又详细梳理了该类散套的具体特征[7]68-70:
(1)长度
该类散套长度含有7至16支曲子不等。为了陈述一个复杂的逸闻趣事,作者利用了该文类的灵活性,即允许作家拉长作品长度,从而能承载其主题内容。许多特类散套的曲牌都是[般涉调]或[中吕],这两宫调都能包容较多的曲牌,从而也使作品容量加大。
(2)对话
在中国诗歌中准确地界定对话是件冒险的事情,因为在任何文本中,就形式方面而言,对话是看不出来的。然而在此类散套中,一些章段毫无疑问就是直接交谈的语言;当然不可否定其他散套中也会存在这种直接的交谈对话。
(3)个体化特征及叙述者
出现于此类散套中的人物都是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通常是漫画式的描述)。与诗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比,他们很像戏剧中的人物。在很多情况下,都有一个身份明确的陈述者。在一些散套中,还有一些先前诗歌作品中不曾有过的一种形象——动物叙述者。
(4)事件和行动
此类中的许多作品都关注行动和言语,而不是心境和感情。作者确实开掘了叙述者的心智,其视角提供了一种喜剧成分;然而,散套作品关注的是事件而不是叙述者的心境。
(5)高度原创性的主题材料
在先前的诗歌叙述和杂剧中,其故事通常选自于小说、流传故事、历史著作或其他资料。但是在该类散套中,此类逸闻趣事完全是独创,或者取自已不存世的口头或传统资料。
(6)特有的手段
该类散套采用了对古典作品、历史和其他资料的详尽引用,以及复杂双关语、谜语和其他手段等;该类散套的长度也使得其能充分运用上述在其他诗歌中很少见的各种手段。
(7)幽默
喜剧因素由世俗闹剧到老于世故的黑色幽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
此外,该类散套与院本(宋代喜剧短剧)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元杂剧中喜剧插曲也表明,院本、特类散套及喜剧插曲三者之间存有一定联系。而且,此类散套都是一种讽刺的形式,将动物放在人的位置,增强了喜剧效果和黑色幽默。
综上,克朗是英语世界首位详尽论述元散套题材内容的学者,她关于各种题材及其特征的论述系统而详细,也相当全面地概括了元散套的题材内容,足见其对元散套文本的细察及细读功力。在概括相关题材类型特征的时候,既有一般性的抽象概况,又有具体的文本细读,充分体现了克朗对元散套题材内容的熟稔程度与概括能力。她与老师柯润璞的元散曲题材研究互为补充、交相辉映,更进一步地深化了西方学者和读者对元散曲丰富题材内容的认识,从而更有助于他们对元散曲的正确评价和科学赏析,并加深了其对元散曲所反映思想主题的真正理解和认知。
除柯润璞和克朗外,黎得机在其博士论文《杨朝英编的散曲集<阳春白雪>所收小令之韵律和结构研究》(Yuan Sanqu:A Study of the Prosody and Structure of“Xiaolinng” Contained in the Sanqu'Anthology“Yangchun Baixue'Compiled by Yang Chaoying”,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第七章中,也提到了他所分的元散曲三种题材类型,即爱情类散曲,享乐类(酒醉、闲适和享受)以及“悟世”(不逐功名、虚空无为、咏史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散曲。大体而言,黎得机的这一分类法类似于刘若愚《中国诗艺》里的分类法,在《中国诗艺》里,刘若愚在第一部分的第五章“中国人思考和情感的一些观念和方式”中,他将中国诗按其思考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分为“自然、时间、历史、闲适、怀旧、爱情、醉酒狂喜”等几类[8]48-60。
王琳达在其博士论文《马致远散曲及杂剧诗研究》(A Study of Ma Chih-yuan's San-ch'u and Tsa-chu Lyr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第二章“马致远的文学主题”中,对马致远的散曲题材类型总结为五类,壮志未酬(unfulfilled ambition)、逃进杯酒(escapeintowine)、自然风景(natural landscape)、爱情(love)与幽默(humor),并列举了相关例作予以简略的论述。
三、研究的特征与意义
柯润璞、克朗和黎得机、王琳达的元散曲题材内容的研究,分类明确、论述详细,归纳总结系统而全面,他们是英语世界元散曲题材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些研究中,既有专著、也有博士论文,显示了英语世界学者对元散曲题材研究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思考。
第一,充分认识到元散曲题材内容的丰富性。由于元曲艺术形式上的灵活性、语言上的口语化倾向,遂使得它能够充分吸收容纳先前所有文学类型中的不同主题内容,并结合当下的实际创作,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题材内容上的丰富多样性。对此,英语世界的学者亦有深切的认识,在他们的论述中都首先无一例外地指出了元散曲较以往文学类型在题材内容上的丰富性。
第二,他们对元散曲题材内容的归结建立在扎实而细致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般地涉猎文本,特别是柯润璞、克朗和黎得机三人均对元散曲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阅读与考察。在他们的著作中均对所涉及的元散曲作品进行了译介,特别是柯润璞的元散曲翻译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最好翻译版本,这也是他的专著《元上都歌诗》及《元上都歌诗续》的突出特征。通过自身的翻译和深刻的解读,就能使他们对元散曲的主题内容形成较丰满立体的艺术感知,也使其相应的艺术鉴赏较为接近原作艺术面貌。所以,他们在此基础之上的元散曲题材内容的归结还是相当准确、全面的;对于每种题材类型的特征描述,他们都结合具体的散曲作品分析,具体生动而不乏真知灼见。
第三,题材类型归结全面、论述系统深刻。和中国国内学界相比,综而观之,除王琳达专对马致远散曲题材的研究外,其他三人的题材归结还是相当系统全面的,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散曲作品,而且对于各类型题材的相关论述也是细致深入,比如克朗针对每种题材类型具体特征的论述,条分缕析,就很有见地。
第四,他们(特别是柯润璞和克朗)独特的异域学术视野,使其对元散曲题材内容的研究不乏新颖别致之论。比如柯润璞以中西比较、互通的学术视野论述元散曲中的乡巴佬或傻蛋主题程式以及以“戏仿”之词来归结元散曲的题材类型,再如克朗“应景”和“特类”散套题材内容的归结,都是很富有新意的梳理论述。这些无疑都会拓宽中外元散曲研究的学术视野,亦能生成更具创新性的学术思维;它们与中国国内的元散曲题材研究互补互融,从而更进一步地加深了中外学者对元散曲丰富题材内容的深刻认识。
注释:
① 在归纳元散套的题材类型时,克朗将散套作品的标题考察作为其题材分类的重要标尺。她广泛抽样分析《全元散曲》中的套数,统计其中散套标题及类别的数量及其相关注释;同时还统计了各种专题文集中的散套及其所能暗示出的相关主题。如她所统计,共有22首套数,其标题或分类中含有“闺”字;有9首包含“怨别”;36首含有“怨别”或“别”“离”;另有标题含有“悟”字;马致远的标题如其小令一样富有诗性;汤式的一标题竟有43字,暗含着其作品的很多信息等。
② 这里,克朗把散套看作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笔者翻译时为保持其原文原貌,仍将其译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