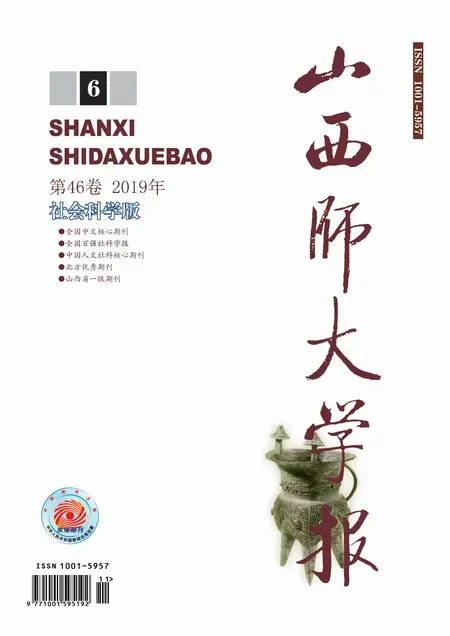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相关话题
2019-02-22彭兆荣
彭 兆 荣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是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也是世界农业大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超过20%的人口。中国人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土地是根,粮食是命。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政治家,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政见有何不同,几乎无例外地都把粮食问题放在首位,把农业当作国家第一政务——“农正”之政。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无论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变迁,这一历史逻辑不会变。
一、农本社稷
我国有“社稷”之称,原本就是指在土地上耕种粮食的国家。因此,粮食成了国家之首要事务。我国的主食由农业提供,即传统的粮食构成主要以土地种植的农作物为主,“中国人90%以上的食物来自谷物和蔬菜,2%~3%来自于肉类,而这深刻影响着中国农业经济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1]128“谷物食品”因此成为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从历史演化的线索看,食物的种类主要为肉类食物、谷类食物和鱼类食物,这样的粗糙分类原与地理情形与文明形态有关,比如在寒冷的地带或游牧文明类型中,动物肉类食物为主要,而在海洋、河湖地带则较多以食鱼为主。不过,我国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谷物食物无疑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强调,在三类食物中,最主要的是草木之实,即农业生产的作物,因为植物种类多,生长容易,故而素食。[2]208而我国的自然形态适合于农业生产。这种状况虽然在今天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肉类食物有直线上升的趋势,却因此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健康饮食问题,比如肥胖症以及许多疾病。但从全球范围和历史上来看,大多数传统饮食中75%~80%的能量来自于全粒谷物。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在鼓励食用全粒谷物。[3]92换言之,农业生产的食物作为人类食物的原真对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我国的农耕文明主要以北方麦作与南方稻作为代表。考古材料证明,小麦、大麦为外来作物,古代谷物从“禾”旁,唯“麦”从“来”旁,说明其为外来。[4]28大约4000 年前,小麦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原腹地推广,因为小麦产量是粟的数倍,小麦逐渐替代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5]24而稻作文明起源于我国,起源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2019年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获得世界文化遗产,为世界展现了5000年的中国稻作文化。“稻”作为粮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稻在五谷之外,稻列五谷之中,稻成五谷之首。[5]23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从黄河到长江的历史认知与评价语境。
无论麦作还是稻作,首先是土地问题。这也是土地本位的道理。土地本位首先意味着土地所具有的天经地义性质。其次,土地的权限归属。再次,特定范围内的人们对土地之于生产和保育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意味着生计的全部,所以,土地的所有权性质自古就是至上的。归根结底,土地所有制在根本上制约着农业。土地所有制检验着土地与人的归属程度与关系的远近。以最平实的表述就是:如果特定范围内的土地完全是“我的”,就像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如果土地部分是“我的”,就像住在亲戚朋友家里;如果土地不是“我的”,宛若住在客栈。从世界范围看是如此,从中国的历史观之亦复如此。
农业与食物生产首先是满足人之果腹(自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食物之美味体验(文化)。中国饮食的最大特点是,多元饮食本味与反哺之中和。从农业的角度,“和土”是要紧的。“和土—天时”配合,养育土地。所谓“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是为文化之核。“味”有一个前提,由“尝(嘗)”来实现。《说文解字》:“尝,口味之也。”张光直说,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6]250说的就是品尝食物。笔者增加一款,通过品尝食品体验农业。古时,“尝”也是一种祭礼,即在秋收时节祭天帝和社稷的礼数。《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在这里,“品尝”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生理“品味”,而成了一种对“时”的遵从。
二、农事协作
中国的农业是大农协作机理下的小农经济机制。以往在讲我国的传统农业时大都只说到“小农经济”,即自给自足的家庭作坊式的经济方式。这固然不错,却不周延。鲜见提到这种小农经济何以具有如此韧性,数千年基本不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农协作”。所谓大农协作指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农业本身就是协作配合型的;比如农业包含着耕织协作,故“农桑”的分工与协作自然天成。“耕织”是两个无法拆卸的有机构造的组成部分。故我国古代全书类农书说农必言桑,王祯《农书》即以“农桑通诀”贯通之:“《农谱》有蚕事者,盖农桑衣食之本,不可偏废。”[7]701其二,配合自然生态的耕作生产,什么样的自然条件生成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其三,乡村基本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互通有无的“互惠性”交流获得。其四,可以和可能与社会需求密切协作,机动灵活地进行调配。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说明农业本身具备着跨行业的内在机制与变通性。
水之于农业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没有水,便无农。对于人的生活和生产而言,水字当头;更有甚者,人类的文明是写在水上的。大禹治水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真实的历史。水包含着哲理与智慧,先哲们以水论理,大有人在,“上善若水”可谓极致。水之利害更是政治学,德国人卡儿·魏特夫甚至将“水利灌溉”与“东方专制”联系到了一起。[8]此学说虽极端,亦颇受学界质疑,却不妨碍其强调水利灌溉对于农业之重,而封建制农耕国家因基于此而重之,形成这一基本关系链条原理的立论。人类生存基于最外在的两个“生”:生存、生计。人要生存,首先依靠水。古人滨水而居,为的就是便于取水。没有滨水的条件,就凿井,有水方可成乡。故“井”与“乡”成为连带,“背井离乡”可疏之。没有水便无以生计。农业生产是生计之重者,而农业如果没有水,便无法维持和继续。因此,水利灌溉也是农业的基本主题;更为具体技术包括水土保持等。
我国的农艺是“艺术”的原生形态。在中国,欲述藝,先说“农”,因为“藝”从“農”,——即艺从农来;或曰,艺的本源为农。从汉字源流演化可知,“辳”(農)与“蓐”同源,后分化;“農”是“辳”的异体字。辱,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持锄下地,耕植劳作的“耨”。蓐,甲骨文 即 (草丛)加上 (辱,持锄劳作),表示锄草垦荒,而耨即锄草的农具,指从事农耕之意。[9]337说明艺在农中的道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农业价值,即“时—地—艺”的关系。在土地上植艺也是根据这一圭旨而进行的。虽然这里所说的艺术品已经超出了纯然的农耕背景,但置于传统的“农艺”而言,亦符合道理。在农业院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中就有一个“农艺”科系。
毫无疑义,农业遗产成为当世之“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农业既是世界榜样,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值得标榜之处,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与生态相谐的可持续性,比如梯田即为典范。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我国南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梯田入列,如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哈尼梯田等。梯田的水稻种植首先是生态智慧的反映,它们大都遵照生态循环的原理,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而梯田作为遗产,只是我国农业遗产之一范,还有大量遗产类型,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三、贫与扶贫
虽然中华民族文明类型本质上属于农耕文明,富裕的前提是农民必须富裕,因为农民是社会构造的主体。所谓“民富国强”,说的正是这番道理。就社会的行业分工而论,世界上没有一个理论家有胆量在正式的场合下做出这样的定论:农必贫。如果从事解决和保障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必然贫困的话,那么人类本身一定出了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贫困问题故为根本性问题,而贫困主要反映于“农”。今日之“扶贫”的主要对象是“农”。“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至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10]77对于中国农民的贫困化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剥削”派,各种对农民的苛赋税役太多,致使农民处于贫困中;二是“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导致农民贫困。此外还有诸如“天灾人祸”等问题。[1]153—154
但是,对于农民的贫困问题,学者大都从客体、客观、客位的角度去分析,无论是“剥削”论,还是“人口过剩”论,抑或“技术落后”论,都是没有从农民的主体、主观和主位的角度去分析。近来有学者提出了“道义经济”问题,其前提是生存伦理。[11]道义经济假定,人们创造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穷困的农民免受生存危机。另一个代表性的理论是理性原则。“道义”与“理性”成了不同视阈、不同学科、不同村落案例所产生的不同主张。近来我国也有学者开始更加关注这些问题,比如徐勇教授的所谓“生存理性”的观点,即以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出现的替代性机会时,基于生存理性,主动放弃了效率和效益十分低下的农业产业。[12]
这里需要厘清两点,第一,“理性”为舶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使用这一概念,比如美国哲学家李丹(Daniel Little)在《理解农民中国》一书中试图“通过关注农业社会,我希望能检验两个社会解释的一般模型: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13]2。即便在西方,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原有不少学者,概念亦不相同。[13]14波普金(Samuel Popkin)曾经对“理性”做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对基于其偏好和价值观的选择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据对结果概率的主观估计来预估每一次的结果。最后,他们做出自认为能够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选择。”[14]31事实上,理性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小农的描述、解释还是选择模式都是限制的。[13]288—291在我国近代乡村建设的运动中,也有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这一概念来阐释中国的农民,比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详尽地提出了“理性”问题,认为教化、礼俗和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15]45然而,笔者认为,“理性”是否足以真切地说明农民的贫困仍是个问题。简言之,“理性受限”。第二,如果说农民自愿放弃农业而投身到工业、商业、城镇化的事实,主要原因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社会主导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引导的。然而,进城的“农民工”是否以背井离乡的代价能够得以“富裕”,这也是个问题。而且,当代农民放弃农业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归的路。
四、人类学视野
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的学科。既然农业—粮食对人类如此攸关,人类学对相关的话题、问题必然不会视而不见。这一学科对“三农”研究原本擅长,乡土、村落、族群、宗族、世系等皆是在大的范围内属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长时段历史。
中国的历史形态中永远存在着区域差异,“三农”当然不能例外。有关中国区域体系的问题,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建构了多种多样的常规模型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农业的情形,特别是村庄、乡镇和城市的关系方面,创建了所谓的“地理巨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的体系和模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该体系对农民自身以及农民与其他群体间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义。”[16]65尽管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都承认这一理论相应的创建与创意。施坚雅通过对中国乡村的市场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13]85—86重要的是,传统村落和农业通过这一区域性的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以相对稳定的支撑。
西方人类学家对我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研究都围绕着这一基础的社会结构进行,比如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我国的人类学家大都自觉对“三农”进行调研,杨懋春、杨庆堃、田汝康等,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中国家庭制度的社会研究》,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等。此外,以萧凤霞为代表的对珠江三角洲的乡村研究,从早期的 “华南研究”升格成为今天的“华南学派”,如刘志伟、陈春生、罗一星、郑振满、科大卫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学家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类学“乡土社会”的本土范式。
在我国的乡土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村落构成是宗族世系。我国的村落,特别是汉族村落,典型的形制是由宗族分支所形成,即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呈现紧张局势,人们不得不离开原乡到外面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宗族分支于是形成。当一个分支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村落时,开创者就成为“开基祖”。所以,许多村落以宗族姓氏为村名,然后再不断地推展,姓氏、人群也随之扩大,而成了“族”。“族这个单位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成员资格是家。”[17]61—62所以,汉族村落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亲属性的人群共同体。
逻辑性地,乡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的“宗法制度”。就组织制度而言,宗族事实上承担着乡村的管理责任。在传统的村落社会,宗族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基层管理模式,它属于民众的自我管理,“基层社会的自治”式管理模式。[18]106费孝通先生将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称为“无治而治”,即“礼治秩序”,所遵循的是“同意权力”。[19]48—50也就是说,在传统乡村的重要事务由宗族代表在协商中解决,形成了各种乡规民约,大家共遵守。乡村中的“公共事务”,比如修路、修桥、宗庙的修建等,也由宗族自行解决,所需的费用,除了“公田”(族田)收成所产生的经费外,族内以捐款的方式集资解决。
实际上,传统的村落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形制。“公产”(族产)被特定人群共同体视为祖先遗产,具有家园所属关系,成为“家园遗产”,被特定群体作为集体认同的纽带和体现忠诚的对象。作为遗产的象征成为人们代际传承,且具有稳定的价值归属和纽带。[20]当今,传统的乡村形制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与变革,“两委”下沉到了基层乡村,这也为政府管理乡村提出了挑战,其中三个因素需要考量:一是下派的政府代表、代理如何与宗族、地方精英取得协同,特别是吸取传统的乡村管理经验。二是确认乡民为乡村的主体,毕竟那是他们的家园。如果他们失去主人翁意识,任何政府工程都将失败或事倍功半。三是调适、疏导因土地所有权变更引发的地方民众的危机感、紧张感和空虚感。
五、耕读传统
既然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自古以来也就形成了一个知识与教育体制,这也就是“耕读传统”。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构造和知识来源主要来自于耕读,所以“耕读传统”构成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知识性伦理价值。一方面,“耕”与“读”形成了一个难以分隔的关系链条;另一方面,仕绅阶层从来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即使是为朝政所御用,也必须俯身向下,关心体察民情。退而言之,那些读书人步入仕途,到了退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告老还乡;或因政见不符,可以隐居乡野,还俗于农;毕竟他们的父老乡亲还在原乡,他们可以将知识返还于乡土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教育科制进入我国,传统的耕读传统已经不适应于知识的“大批量生产”。然而,耕读传统毕竟是中华民族的教育基因与基型。
在我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宗族”是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也是所谓“宗法社会”的重要根据。逻辑性地,“耕读传家”也自然成为“宗族—家族”的地方性实践。“耕”,主要满足以宗族为基本构成的人群共同体的生养、生计、生产和生活为目标;“读”,主要以儒家伦理为内容的礼制,由此构成乡土性的社会秩序。在传统的汉族乡土社会里,家族主义构成了社会分析的基本视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血缘是亲属关系、职责、权力、态度和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村落生活的所有事务都与血缘有关。血缘是村落世界讨论的主题,也决定了理论社区的范围。在乡村生活中,“孝”与“祖先崇拜”是两个重要伦理视角,“孝与祖先崇拜的根本区别: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活着的人,次要关注的是去世的人;而祖先崇拜则反之。”[21]113这样也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园遗产”,既形成祖先崇拜的祭祀关系,又形成了现实社会关系以“孝”为核心的现实关系。
在耕读传统的体系中,农业知识也自然成为重要的、代表性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中国古代除了“农业全书类”著作,诸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还有大量的农业专书以及散布在各个时代、各类著述中有关农业的知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就有“为神农之言”的农家学派。事实上,诸子“百家”几乎皆有涉及农业,比如言及“月令”,必说农,管子的著述中就有大量的农业知识。至于历代的农书和涉农著述更是汗牛充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构造属于百科全书式,其中农业知识必在其列,甚至连《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都留下了《农桑经》《捕蝗虫要法》。[22]44—49而像古代的著名诗人、词人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等都有一批与农业有关的作品,他们熟悉农业。
六、粮食之悖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将土地视为根,粮食视为命。近时,粮食、食品骤然成为热议的话题。显然粮食问题是一个老而弥新话题,所谓“老”,指人类自成其为“人类”以来,食物就一直是追求的对象。这也是人类的生物性决定的。对于“人”而言,任何其他的属性都必须建立在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的基础之上,没有食物遑论其他。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境遇,粮食是一个制衡的指标,说明人类生存状况的基本数据。据联合国报告,现在世界上仍有逾8.2亿人在挨饿。迄今为止,全球实现“零饥饿”还任重道远。更有甚者,随着全世界人口增长,饥饿人口连续三年呈增加趋势。[23]也就是说,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类的温饱问题仍然未能解决,而且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所谓“新”,主要指食品安全问题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凸显。一定程度上,现代的科学技术在粮食食物的生产、制作、供给等领域的应用技术,比如转基因技术,一方面使得粮食食品在生产数量上达到了空前的提升;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奇迹”又带给人类史无前例的紧张感。具体地说,对食品产生了不安全感。因为转基因食物对人伤害与否或伤害的程度迄今仍然未能充分证明。其中包含着科技异化的人类“自残”情结,这种“自残”情结仿佛武器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升级,最终会残害人类自己。而历史越往后推,社会越是“落后”,这种“自残”反而越是轻微;反之,历史越是朝向现代,科技越是发达,“自残”就可能越是严重。
粮食食品除了供养人类的生计这一共性外,也羼入了不同文化的个性。中国的饮食文化极为独特,除了诸如“五谷”与“五方”之哲学认知,以及生态智慧、养育养生、地方菜系、烹饪技艺、品尝认同等。[2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饮食方面的粮食浪费已经成为一种变相的公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升魁教授的研究数据(2015年)表明,我国的食物浪费的组成为:蔬菜(29%),主食(24%),肉类(18%),水产品(11%),累计占总量的82%;其中,肉类主要剩余为猪肉(8%)和禽肉(6%)。值得特别一说的是,粮食的生产与食物的消费除了生存需求之外,还语境性地生成出许多伦理悖论和矛盾,其中食物浪费无疑最具有表象特征。
代表性的社会现象是食物浪费与“面子文化”,二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国的调查数据表明,仅“面子”一项就导致以下的后果:人均在外消费时多产生显性浪费28克/餐,约相当于全国每年因此浪费掉280万人一年的口粮。同时,为照顾请客人的面子,客人会比平时需求消费的多,造成约80克/餐的隐性浪费。(1)数据引自成升魁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饮食文化国际会议”(2019年7月6日)上的主旨发言“中国食物浪费变化与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悖论的是,当我们的成年人在餐桌上大肆铺张的时候,却没有忘记教自己的孩子背诵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国的稚童大都能够背诵此诗,成年后却实践着浪费。人类皆有“面子”,只是特殊的社会价值在“面子文化”加入了各种不同的“添加剂”,致使“食物—面子”之间成了一种特定文化的说明。
结语
“三农”是传统农耕文明之根本。习近平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是道理,也是逻辑。无论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文明的视野、中国农业的特点和范式以及当今面临的重大挑战等,我们都没有理由不更加关注“三农”。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只要土地—农民—农业—农村还健在、健康、健行、健美,天就塌不下来。这个道理,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