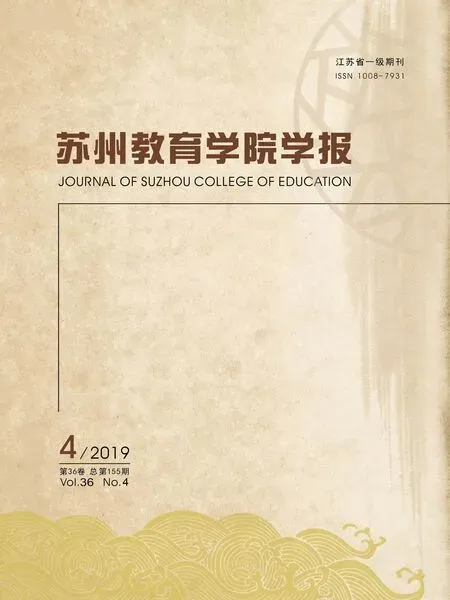诗人贵诚 诗心贵意
——论日本桂园派和歌诗人香川景树的“调之说”
2019-02-22李东军
李东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香川景树的“调之说”
和歌诗人香川景树(1768—1843)是日本江户时期“桂园派”的创始人,“桂园”是他的诗号。他主张个性自由的创作思想,既反对“朱子学”的儒家功用主义诗学,也反对贺茂真渊等日本国学者的复古主义,反对将和歌作为宣扬神道教的思想工具,代表作有《桂园一枝》《古今集正义》等。“桂园派”凭借优美、平易的歌风振兴了关西地区的和歌创作,直至19世纪晚期日本近代文学崛起之前,桂园派始终在和歌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与此相对,袁枚(1716—1798)科举中过进士,曾历任沭阳、江宁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畏权贵。后辞官在江宁筑室定居,号“随园主人”。袁枚的诗集很早便传入日本,儒学家兼汉诗人赖山阳(1780—1832)被誉为“日本的袁枚”,他非常喜欢袁枚的《小仓山房集》,并将其放在身边时常勤读,受益匪浅[1]。由于香川景树与赖山阳是好朋友,通过赖山阳接触过袁枚的作品的可能性非常大。
袁枚提倡书写性灵,反对形式主义,主张个性解放。香川景树也有著名论断:“和歌者,非关乎理也,在乎调也。”[2]所谓“调”,本义指“声调”“音韵”;香川景树首次将“调”与“诚”(真)结合起来,丰富了“调”的意蕴内涵。香川景树认为表现真情实感、有感而发的和歌便是好作品,诗美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之调”(天籁)。此外,他还说:“今世之歌,应有今世之辞、今世之调。”[2]反对拟古、复古的古典主义诗学。这种主张顺应了文化文政年间(19世纪初)“町人”—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
二、“天地之调”中的性灵思想
首先,我们看一下香川景树的作表作:
大堰河 かへらぬ水に 影見えて ことしもさける 山ざくらかな[3]136
译文:大堰河水东逝去,川流不息不复回。一年一度花倒影,今朝山樱分外艳。①译文皆为本文作者据原文译出。以下同,不另注。
通篇直白的诗句蕴含着深刻哲理,河水充满驿动的灵性,世间物事变幻不息,东逝之水不复还,年复一年盛开的樱花象征永恒不变的人间真理,对生命的礼赞则是不变的主题。流水与樱花倒影,一动一静,构思巧妙,意象婉丽。诗人站在大堰河边,望着流水中的樱花倒影,诗兴盎然,脱口而出,自成格调,浑然天成。“意高则格高”(王昌龄语),诗歌的立意高远,故直白平易的诗句也可以营造出意蕴深远的诗境,完全符合藤原定家的“事可然体”(道法自然)的审美理想,也暗合了严羽“吟咏情性”(兴趣)的诗学原理。
下面再举一例:
大比叡や をひえのおくの さざなみの 比良の高嶺ぞ 霞みそめたる[3]138
译文:逶迤比叡山,峰峦叠翠远。天边比良峰,朝霞春色染。
比叡山位于京都市的北面,“逶迤比叡山”是说山岭相连、起伏连绵的景象。比良峰位于琵琶湖的西岸,也是比叡山脉北延的最高峰。早春时节,比良峰笼罩在春光的雾霭中。京都的诗人目睹此景便会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这首和歌描写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境阔大,气象万千。这首和歌没有繁复雕琢的修辞技巧,胜在言简意深。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4]125备受历代诗家推崇。此句虽不精工,但出自诗人对春天的由衷喜悦,意在言外,堪称神来之笔,也是一种直寻笔法。钟嵘《诗品序》中举了几个直寻笔法的例子,如“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5],“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4]128等。这几首诗句的妙处就在于真情实感、情景交融,作者想表达的“喜春”诗题虽未明说,但已是象在言外、情蕴辞里,用鸭长明《无名抄》中的话说便是:“余情笼于内,景气浮于空。”[6]
香川景树特别强调“诚”对于和歌创作的重要性,“诚”指的是真情实感、毫无虚情假意。他在《新学异见》中说:“古代的和歌的调与情是和谐统一的,原因无非在于古代人的单纯的真心。发于真心的歌与天地同调,恰如风行太空,触物而鸣。以真心触发事物,必能得其调。”[7]1030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主情重真,学问与义理不是第一位的,而“诚”才是作歌的根本。同样,性灵派诗人主张以情为主,反对人为雕饰,推崇诗境的浑然天成,反对以理入诗,反对以学问为诗。
那么,“调”是怎样形成的呢?其实,“调”的概念是由日本国学者贺茂真渊在《新学》一书中首先提出。道,“调”就是用舒畅、明快、清新或者朦胧晦暗等各种感觉与感情加以音乐化……歌之调也对应于四季交替,而产生了丰富变化。②参见贺茂真渊:《贺茂真渊全集》第10卷,转引自王向远:《诗韵歌调—和歌的“调”论与汉诗的“韵”论》,《东疆学刊》2016年第3期,第1—7页和111页。贺茂真渊反对儒学(朱子学)思想,对“调”作了价值判断,他认为儒学传入日本是一种思想毒害,主张以神道教为核心的国学思想作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香川景树针对贺茂真渊的《新学》写出《新学异见》(1812)逐项进行批驳。再如,贺茂真渊认为“调”是指歌唱意义上的歌调、音调;香川景树认为“调”是广义上的自然形成的韵律或律动,可称天籁,是出乎天地的“诚”,非乎人工“有意识在创造出来的”[7]1031。在香川景树看来,贺茂真渊的“调”是用神道教代替儒教,换汤不换药,人的性灵仍然得不到自由。因此,他将“诚”引入“调”(音韵)的概念中,主张精神自由,摆脱伦理宗教的束缚,直视自我的内心,主张“诚”(性灵)才是创作的真正动机和灵感源泉。
香川景树的“诚”,其实质就是一种主情主义。香川景树《歌学提要》称:“由诚实之意而创作的和歌顿时成就天地之调,犹如空穴来风,物响其声,无不得其之调。无论何物,无论何事,感兴即发其声,感与调之间无隙可容一发,惟真心流出之故尔。”[8]大意是说,诗人要有一颗没有被功利玷污的真心(童心),当它感受外界刺激后便会激发回响,于是“诚”(性灵)便形成和歌的“调”(声律),而且“诚”与“调”之间还要通过“感”(感兴)的媒介作用,“感”与“调”密不可分,浑然一体,情景交融。古人论诗,无外乎“体格声律”与“兴象风神”。遗憾的是,香川景树并没有对“感”的获得机制作深入阐释,他只是强调“诚”的纯粹性,即绝对的“诚”便会产生“天地之调”。显然这是不缜密的逻辑。同样,袁枚提倡“性灵”,但也没有从理论上阐述清楚“性”(情)如何才能“灵”(升华),他只好强调诗人要有天赋。袁枚的性灵思想被后人讥为“空疏”“偏好艳体”。
当然,香川景树的“调之说”强调主“诚”,但实际上并非一味地主情反理。我们知道,日语中的“诚”与“真”“实”等汉字的读音相同,这源自日本上古时代的“言灵”信仰,出于对语言中的神明的敬畏,人们不敢说谎。此外,江户俳人松尾芭蕉也主张俳句艺术的真谛在于“风雅之诚”[9]。“诚”也即是“真”,诗人触景生情,主客观合拍,此情与此景契合无垠,诗人便会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往往可以达到“不须绳削诗自合”的艺术境地。对此,我们联想起钟嵘的“物感”、殷璠的“兴象”以及李贽的“童心”等诗学理论范畴。同样,日本古代诗学中也有类似的范畴,如“物哀”“面影”“景气”等。
香川景树的弟子八田知纪《调之直路》中称:“调者,姿也。”[10]这说明“调之说”并非只是音韵声调,必然也包括诗美的“兴象风神”,也必须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说明。“姿”的概念由藤原公任(966—1041)首倡,当“心”(内容)与“词”(形式)完美结合时便产生“姿”,和歌的“姿”可细分为“心姿”“词姿”以及“句姿”。因此,数百年后的香川景树提出“调之说”,虽然在诗学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创新,但他强调诗歌的音乐性和自我意识的张扬,目的在于反对儒家功用主义和复古主义诗学,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另一方面,性灵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11]情性即性灵,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袁枚的“性灵”包含性情、个性、诗才等要素,其中的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之外本无诗”(《寄怀钱屿纱方伯予告归里》)[12]247。其次,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个性,“作诗不可无我”(《随园诗话》卷七)[13]146。然而光有个性、性情是不够的,还应该具备表现这一切的诗才,“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馀藏园诗序》)[14],艺术构思中的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然而,袁枚只强调诗人的天分,而忽视学问的积累作用。
那么,香川景树的“天地之调”的诗学源头在哪里呢?王向远认为在于汉诗的“音韵”,古代日本人对和歌诗体学的认识源于汉诗,其中音律节奏一开始是套用汉诗的“韵”以及“歌病”。[15]不过日本人很快发现“四声八病”并不适合和歌,于是他们从“心词”与“心姿”等兴象对和歌意境论进行探索,开创了“幽玄”与“有心”的诗学体系;另一方面,藤原俊成(1114—1204)意识到和歌的“声律音韵”与诗歌意境、兴象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和歌不必象绘画一般处处穷尽其色,亦不必象作物所(作坊)的工匠一样穷尽其工,惟吟咏之时,(使人)闻之应有‘艳’与‘面白’(情趣)之‘姿’(兴象)”(《民部卿家歌合》)[16]。大意是说,和歌欣赏主要依靠听觉,节拍声调与意象兴象完美结合便会产生玄妙幽深的审美感受。同样,10世纪至12世纪的歌合判词中常有“音声和畅”(なだらか)、“声律优美”(歌めく)等用词,这表明平安后期的日本文人已经有了“调”的诗学意识[17]。
明清时期盛行性灵思想有历史的必然性。汉唐文学批评侧重于政治教化;宋代文学批评则注重内向性的心灵规范,将对“外王”的感性追求转向对“内圣”的理性追求,突出儒学所固有的理想人格追求,因而引起了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内向转化;金元之后的文学批评宗唐尊杜,主情贵真的诗学主张开始多了起来。[18]例如金人王若虚论诗主“真”,一是指性情之真,他认为诗歌的正理在于性情之真,在于诗人抒发真性情,写出胸襟怀抱;二是指事物之真,他要求诗歌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地叙事状物。但这时的“主真”还没有彻底脱离“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此外,李贽的“童心说”也为性灵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李贽肯定人的情欲和物欲的合理性,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假道学。随后,公安派“三袁”提出“独抒性灵”,反对明七子等拟古派给文学加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沉重使命。
总之,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文政年间,市民(町人)阶层的享乐主义思想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刺激下达到了高潮,他们肯定物欲,张扬个性,这些都是“调之说”产生的文化土壤。
三、“调之说”与“格调说”
“格调”是明代诗学批评的最基本的范畴,源于高棅,成于李东阳,盛于明代前后七子。使用格调品评诗文,应该注重诗文内在的气韵与外在的艺术形式的妙合无垠。最初的“格调”只是指“体格声调”,包括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中说:“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19]唐代以后的诗论家都很重视诗的格调,格调派创作讲求比兴、蕴蓄,不可“过甚”“过露”,以致“失实”,特别重视诗歌的体制、音律、章法、句法、字法,不赞成死守诗法,主张通变。清人沈德潜强调格调,不过他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强调伦理道德规范对于格调的重要性。他强调“学古”和“论法”,对诗歌的体格声调作出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诗歌内容体现“温柔敦厚”的宗旨,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才是他所倡导的格调说的实质,只要诗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那么它的格调就一定是雅正的。对此,主张性灵的袁枚予以猛烈的批判。这一点与香川景树批判贺茂真渊《新学》的复古思想的做法非常相似。
性灵派诗人袁枚强调作诗应抒写个人的性情遭际与实感,直抒胸臆,辞贵自然,主张个性表达,反对形式主义诗风。在这一点上袁枚表现得非常激进,他甚至说:“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12]228作诗可以“不用一典”[13]35,这容易给人造成不重法度规矩、轻视学力的印象。相比而言,香川景树的言论则要温和与灵活一些,他在强调“诚”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积学与法古,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思维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香川景树《新学异见》说:“(散)文以义为本,(和)歌以感为要。譬如,文华也,歌香也。华者语其容(貌),香者则说不得其芳也。”[7]1042大意是说,和歌与散文不同,其内容不能用理性分析加以说明,“诗无达诂”,不可句摘,不可句解。因此,他提出“诚”与“调”相结合,最高境界便是“天地之调”,即八田知纪所说“调者,姿也”[2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诗歌与散文不同,注重的是感性思维,但并非排斥理性。我国古代诗歌审美发展有两个维度,“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可换言之主情与主理。虽然香川景树说的“调”包含二种语义,其一是客观上的体格声调,包括“音韵”“声调”,以及“五、七、五、七、七”的和歌诗体;其二指审美情趣上的意象或兴象。
关于“姿”,按照藤原公任以及藤原俊成等人的观点,它是指让人可感受到兴象或意象,存在于和歌文词之外的风格或韵味,即“心”(诗意)与“词”(文辞)契和无垠所外溢辞表的风韵气象,或香浓或妖艳或清丽,如同美女的美妙仪姿,给人以美妙的感官感受。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中将“心深姿清”视为优秀和歌的最高审美标准,不过“心”与“姿”相比,他更注重“心”(意蕴诗心);相反,藤原俊成《古来风体抄》则更看重“姿”的有无。如果和歌诗句有“姿”,诗人根本不需要直白表达心曲怀抱,其意可含蓄地传达给读者。我们认为诗歌的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为思想内容服务,应根据内容需要灵活运用,不能不顾内容而炫耀技巧。然而,形式与内容往往紧密在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这是一种“调”,一种“腔调”,也可称其为“格调”。诗歌的格调由诗意(文意)所决定的,那么诗意就必须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要素。
如果将心中怀抱(感性)与文意(理性)圆融无碍地表现出来,必须要“积学”,光靠才气天分是不够的。日本古人自《古今集》之后,对和歌审美有了理论自觉,他们依靠“枕词”“缘语”“挂词”等修辞手法进行“心姿”“词姿”的诗美营造,“幽玄”“物哀”等诗学概念深化了“心姿”的诗美形成机制。一方面,“体格声律”构成了诗歌的音乐美,宫商角徵羽各成曲调;另一方面,“兴象风神”为诗歌审美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因此,香川景树意识到了“兴象风神”对于“调”的重要性:“古人言称嫩草,必指春日野;言鹿,必提小仓山;说月,必定是指音羽山更。”①参见福井久藏:《关于枕词》,(日)《心理研究》1919年第15卷88号,第357—381页。春日野、小仓山、音羽山更,都是平安贵族们游宴狩猎必去的风雅场所,更是吟诗作歌的歌枕(审美想象的场域)。“初学者往往不理解,为什么新奇的地方有许多,感觉这种作法愚笨(而不这样做);结果反倒是自己的作法很愚笨,不能生成调,算不上秀歌。并非春日野的地方嫩草就生长得好;更科这个地方的明月就格外地明亮,而是那些地名具有自然调(兴象意象),故不得不依靠这种方法。”(《木曾人小坂道贤咏草之奥》)[2]这段话讲得很直白,说的是“积学”的重要性,只有经历此种审美历练的阶段,才能做到将“诚”与“调”完美融合的境界。
为此,香川景树将“调”进一步细分为“型调”和“象征调”。他说掌握“型调”(雅调)必须学习古人。“诚者典丽雅正,欲歌陈诚者须雅正。……是则歌之稽古也。”(《某法师咏草》)[2]因为表现“诚”(性灵)的和歌创作必须具有才力、学识才能胜任。不过,他更看“象征调”,他说:“谣曲、浄瑠琉、音头,此外还有伐木歌、打舂歌,只要具备各自之调便不会混淆,更不会落入俗套。大和歌自有其调。”(《信浓国野泽人并木周子之咏草》)②转引自王向远:《诗韵歌调—和歌的“调”论与汉诗的“韵”论》,《东疆学刊》2016年第3期,第1—7页和111页。意思是说各种艺术体载都有各自特点,也即是艺术风格各不相同。香川景树说这段话的用意在于主张个性与创新,如豪放与婉约,壮美与阴柔,审美风格应该与思想内容相一致。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21]对于“型调”和“象征调”的体悟也是如此,只注重积学拟古是不够的,必须摆脱古人法度的樊篱束缚。为了不受古法所缚,香川景树提倡“诚真”,他在《法性寺水月之咏草》一文中说:“体得调之途有二,其一为精神训练;其二为学习古今集。会得调者,得自然之歌。自然者,即诚实也。”[2]在《答信浓松木良本之寻文》中他又说:“毕竟调乃诚情之声。偿试咏歌,此为捷径。若立此诚心,犹如入神之境,如入老庄之境,乃至入百技之境,皆成我之囊物。”[2]
贺茂真渊主张学习雄浑刚健的“万叶调”,以《万叶集》为宗,其实质是将和歌作为神道教的政治工具;香川景树则主张学习《古今集》的雅正歌风,但法古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心中应有自我之调,不惟古人。他在《新学异见》中强调:“今世之歌,用今世之辞,为今世之调。”①转引自藤平春男:《見聞くもののまにまに—景樹の「新学異見」と言道の「ひとりごち」》,《短歌(古典の歌論をどう読むか 特集)》1970年第第17卷第7期,第50—55页。香川景树强调学习《古今集》的目的在于“精神训练”,即思维训练。
现代美学思想认为,从古代的功用主义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实践美学以及生命美学,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审美活动的本质的探索。审美活动由两大层次构成,人类审美活动具有分属为不同层次的双重性质:既是受生理、心理机能影响的智能性活动,属于自然层次;又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精神性活动,属于观念层次。每一层次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每一具体的审美活动都是在这两大层次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审美活动是以非功利认知方式为智能基础的社会精神性活动。当然,还是黑格尔说得言简意赅:“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3]
当然,生活在18、19世纪的香川景树达不到现代美学的认识高度,但他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能作出科学阐释,只是用“天地之调”来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在与贺茂真渊论战时,香川景树是反对复古拟古、反对形式主义的,强调自我创新。他认为只有诗人的创作出自“诚”(性灵),发自肺腑,便自然有“调”,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调”是有高下等级的,最高级的“调”便是“天地之调”。同样的,“诚”也是有高下等级的。显然这种推论是有问题的,这只能说是“调之说”的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
四、结语
我国明清时期出现了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等众多诗学理论流派。其中主张主情重真、崇真贵诚的性灵派顺应了市民阶层主张个性的时代潮流,为陷入道统泥潭不能自拔的肌理、格调等诗派提供了新的气息。面对“从格调优先到性情优先”诗学转向的影响,格调派努力摒弃缺陷,尽力修正。例如注重“性情”与“学问”的重要,避免明七子徒讲格调、遗漏才学的弊病,强调才学的重要性。同样,日本江户时期,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小泽芦庵等人也对日本三大和歌集的优劣有过争论。强调个性、反对形式主义的香川景树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复古拟古不能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他强调和歌的缘情性和音乐性,认为“饮食、男女、语言”为天下三大事,符合时代的潮流,诗歌是表现社会文化的最佳载体。香川景树重视诗人情感的真实表现,强调诗歌的通俗易懂。但过分强调诗歌的通俗性,容易流于直白、俚僻浮浅,这是古典诗歌之大忌。他强调效法《古今和歌集》的雅正歌风,但其雅与俗的冲突却使他的理论体系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因此,为了弥补理论不足,香川景树引入日本古典文学中最上位的美学范畴“诚”,建构出性灵思想体系的“调之说”,也就是说诗人真实情感的“直抒胸臆”之作,其诗境会浑然天成,自合声律。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比,香川景树则显得灵活宽容许多,避免了只谈性灵而忽视才学的空疏,做到了性灵与格调兼顾,性情与学问兼顾,对日本近代诗歌的兴起有着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