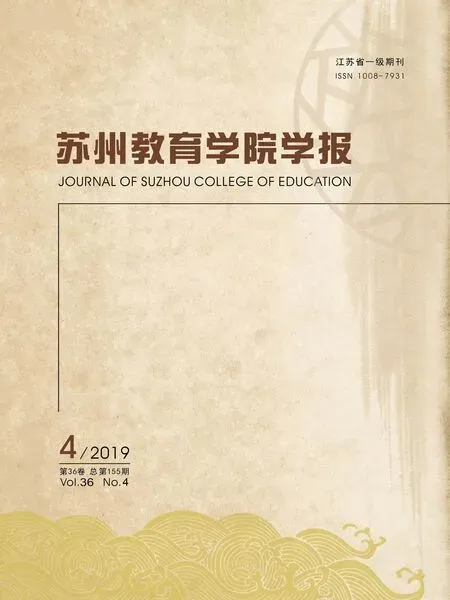反抗与救赎
——玉娇龙形象的再解读
2019-02-22伍荣华
伍荣华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1]的结局出人意料:玉娇龙以为父亲康复还愿的名义,投崖妙峰山,然后悄悄远走天涯。这样的结局是对一般英雄美女小说的超越。事实上,按照通常的小说逻辑,此时,玉娇龙由父母之命定下的夫婿鲁君佩已被制服,鲁家对玉家已不构成威胁,母亲已逝,父亲病情好转康复,家里也不再是一地鸡毛,罗小虎还独居于庙宇,等着她去团聚。玉娇龙在妙峰山跳崖,等于向江湖宣告死亡,江湖仇怨也即了结。但是,玉娇龙仅仅赶去与情人相聚一夜,而后便决然离开,奔向高山大漠的自由天地,此后的故事接续于另一部小说《铁骑银瓶》[2]中。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考察玉娇龙的选择,可以说这样的结局虽出人意料,但确实是出于玉娇龙个人的自由选择,抛开了情义、礼教和世俗眼光的羁绊,有不俗之处,且另有深意。
16岁时在大漠追杀劫匪,遇见罗小虎,可谓玉娇龙灵与肉觉醒的开端。由此开始,王度庐塑造了精神分裂般的玉娇龙形象。白天,作为玉府千金,玉娇龙用以示人的一面,永远是珠翠华服、温柔可人、知书识礼、弱不禁风;夜晚,却是青衣小帽、习武练剑、飞檐走壁、剑指江湖。白天和夜晚的两面,构成了既矛盾对立又有机统一的玉娇龙形象。公平地说,两面都是真实的玉娇龙:白天的玉娇龙是千金之躯,享受着九门提督小姐的荣耀和尊宠,这是她不能割舍的;夜晚的生活更接近她的本性,也是她刻意追求的。但是,玉府千金与驰骋江湖是根本冲突的两套价值体系,必须舍弃一个才能成全另一个,这两者的冲突也成为玉娇龙悲剧命运的根源。玉娇龙的一生“爱情梦”和“江湖梦”都是破碎的,母性成为她最后的救赎。玉娇龙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对自己命运的选择,背后都蕴含着深沉的性别政治,而其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表现、变化和反抗,无疑是个人命运变幻的昭示,也反映了她对权力意志既反抗又妥协的矛盾心态,下面将从身心两个方面试作分析。
一、身体的政治
在女性被客体化、对象化的时代,女性的身体无疑是社会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交换物。玉娇龙以九门提督之女的身份,从新疆回到京城,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卧虎藏龙》中有一段文字描写玉娇龙的出场:
她年约十六七岁,身材细高窈窕,身披雪青色的大斗篷,灿烂耀眼……天足……长长的辫子露着黑亮亮的鬓云,鬓云边覆着一枝红绒珍珠做成的凤凰,雍容华艳,无法可比,只可比作花中的牡丹……禽鸟中的彩凤……又如江天秋月,泰岱春云……[1]4-5
这段关于玉娇龙外貌风度的描写,是通过一个底层游侠刘泰保的视角观察所得。在小人物刘泰保的眼里,玉娇龙仿佛是嫦娥降临到凡世,而且他连当面和正眼看的权利也没有,仅能偷窥。玉娇龙的出场之所以如此隆重、如此令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她生得美丽,关键是地位尊贵,如刘泰保这等人物都不配瞻仰她的美丽。所以,刘泰保看到玉娇龙时自然而然联想起她那权势显赫的父亲,从而感慨自身命运:她的一只鞋都比我的命值钱!对权力又羡又妒,再加上惊艳于玉娇龙的娇美,这些复杂的情绪使刘泰保在瞬间产生巨大的晕眩,几乎把他击垮。由此看来,玉娇龙的美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有外表看得见的,表征物就是那些华服珠翠,还有背后看不见的,即地位支撑的尊贵之美。玉娇龙的仪态万方和身上的装饰也即权力符号和权力意志的体现。
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华贵雍容的背后,还有一套严格的规训法则,比如三从四德。按照社会学的观点,肉体具有驯服性,是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它可以变成政治的玩偶,是权力所能改造的微缩模型。对玉娇龙来说,从衣服首饰发型到一步一颦一笑都要合乎贵族少女的礼仪规矩。对肉身的限制,是对思想灵魂控制的前提和基础。一心想要追求自由的玉娇龙,夜间练武行走江湖时,必须乔装改扮成男性,这个男性身份还成为玉娇龙离开京城以后的固定身份,在西北地区独闯江湖时,她是当地闻之丧胆的“大王爷”。从衣饰到性别身份的改变,是非常疯狂的举动,普通百姓对她的恐惧,实质就是将其身份女巫化,玉娇龙几乎走上了耿六娘的老路,这从侧面揭示了性别的不平等及女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迫。
作为女性,无论出身如何高贵,玉娇龙的身体仍是社会阶层的展示物,是联结话语与权力的枢纽,可以当作维护阶层利益的工具,她的身体自主权掌握在拥有决策权的家长手里。玉大人看中鲁君佩的前途和家世,两家联手可以更好地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对于父亲看中的对象,玉娇龙厌恶至极却不敢有任何疑议。从本质上说,玉娇龙跟底层平民蔡湘妹的命运也没什么不同,即嫁人是最终的归宿。蔡湘妹失去父亲后,便半推半就地嫁给了年龄大她一倍的刘泰保,因为她急需一个依靠。个性倔强的玉娇龙以乔装、逃婚等方式来表达对命定归宿的不满和抗拒,她的抗拒背后是有资本支撑的,即她有武功在身,还有银两养活自己,所以她还可以选择,这又是她跟蔡湘妹的不同。
有一点儿选择权的玉娇龙,身体就有了一点自由。小说中多次写到玉娇龙梳头的细节。发型是女性社会角色的象征符号,如满族女性少女时代梳几根发辫儿,待到提亲年纪,要梳抓髻儿。玉娇龙逃婚以后,一个人在茫茫草原,不再梳发髻戴“两板头”,而是编几条发辫,发辫是少女的标志,这里的发型变化可视为追求肉身自由的象征。玉娇龙瞒着家人,青衣小帽,习武外出,也是争取最大的自由空间。她为了孝顺父母,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尽量隐忍,不敢有任何忤逆之处,希望罗小虎尽快发迹做官,光明正大地上门迎亲,取代鲁君佩。这样的设想未免太过天真,一个大漠里长大的强盗,没有后台背景,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入籍于上流社会?所以,玉娇龙把自己被逼婚的原因全部推到罗小虎的身上是不公平的。这种推卸也是她不能面对现实自我逃避的借口,是一种反抗的拖延。坚强如玉娇龙,也有懦弱之时,因为她要反抗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制度。直到正式成亲后,她终于意识到逃无可逃,毅然选择了出走,女扮男装,走出了父权制对她的身体和身份的禁锢。与此同时,玉娇龙心怀对父母的愧疚,还要面对盗走青冥剑的江湖追杀。女扮男装,身份的掩饰、四面楚歌的现实,都是源于她要追求一个自由身。
有关身体政治学,鲍德里亚有一段解释:身体是包括各种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自形成以来就遮盖着身体、分化着身体、破坏着身体,以便把身体组织成一个进行符号交换、与物体领域相同的结构物质,它的功能和策略都是派生于政治经济学的,而能打开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大楼钥匙的,则是女性的身体。[3]女性的身体是通向社会有机体的秘钥,是社会流动发展的一部分。而且身体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安排调遣,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难以避免悲剧命运。玉娇龙人生悲剧的核心事件就是被指婚鲁君佩,这个事件的运作与发展,背后的基础是双方家庭门第、政治和权力的联合和博弈。玉娇龙的身体被禁锢在这桩功利婚姻里,但又心有不甘,尽力逃离,这是她心理症结的渊源所在。逃离以后的玉娇龙,要面对众叛亲离的压力和流亡天涯的痛苦,这些压力和痛苦,表现为其精神上巨大的孤独。
二、灵魂的监狱与母性的救赎
对于玉娇龙来说,她的冲突和痛苦,除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还有内在原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灵魂被当成一种权力的工具,身体通过它被培养和塑造出来,即从某种角度来说,灵魂成为一种标准的和规范化了的理想,身体根据这种理想被规训,被塑形,被培养;灵魂本身就是权力驾驭控制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4]虽然玉娇龙对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奋力反抗,但是自小所受到的伦理教养,是不可能不留下印记的。玉娇龙有个江湖原则,就是绝不与官府为敌,这就跟她的出身和教养有关。她离开罗小虎,除了遵守母亲的遗言,还有她对罗小虎出身的在意,不愿把自己降低到“压寨夫人”的身份。她对孝悌之义的认可与服从,与行走江湖也是根本矛盾的,于是产生了深刻的罪恶感。可见,玉娇龙的“监狱”是自身和环境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如此牢固,深植于心,不易突破。然而她的反抗和追求自由的精神跟封建伦理之间的冲突又十分激烈,这让她时时处于孤独之境。《卧虎藏龙》中写到经过一系列争斗、挫折、屈辱,罗小虎制服了鲁君佩之后,玉娇龙所面临的孤独境地:
玉娇龙,这貌美多才,出于名门的玉娇龙,现今已被人目为一个可怕的东西。大家猜着她,就像是迷人的女鬼,美丽的毒蛇,连她的兄嫂,仆妇丫鬟中除了绣香一人之外,谁也不敢跟她接近,见了她的面就像立时能够躲开才好。[1]727
可以说,玉娇龙的真实一面大曝于天下之时,也是她与整个上流社会决裂之时,被污名化为毒蛇女鬼,被视为洪水猛兽,是其反抗的后果和代价。此时赖以傍身的《九华全书》和青冥宝剑、珍珠弩,都已全部失去,赤手空拳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天下之大,却无容身之处,独自品尝孤独,远走天涯变成必然选择。此时玉娇龙其实还有另一个选择,即与意中人一起归隐江湖,但是她仅仅与罗小虎一夜鸳梦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是主动选择的孤独,是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这样的孤独是深入骨髓的孤独,是一种生命之痛,也是一种生命意志力的体现,符合玉娇龙坚强独立的个性。
往前追溯,自16岁跟随父母离开新疆,玉娇龙突然自觉自己是只笼中鸟时,孤独就开始了。当她产生被囚禁的意识时,当然希望冲出牢笼。要想冲出牢笼就要积聚力量,而这样的准备工作,其实从跟老师高朗秋偷练武功便已开始。所以,孤独是玉娇龙的人生选择。她很早便有了个人的独立空间,晚上睡觉也是一个人,不似普通的小姐有仆人陪伴,更不同于一般柔弱的女性。玉娇龙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并努力实践它,对她来说,这个意志就是实现江湖梦,实现做侠客的理想。她逃亡时巧遇女侠俞秀莲,看到她生活安逸、莳花弄草的生活,也产生过艳羡之情。但玉娇龙是不可能过这样的生活的,她觉得力斗群雄的江湖快意才是她的选择。优越的出身使她的个性自带一种任性、骄傲与固执,导致她与江湖各派误会重重又关系紧张,她的江湖也必然是血雨腥风曲折多舛,她选择的是一条孤独之路。
以玉娇龙的坚强和勇气,对孤独亦能甘之如饴,只是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了她—生育。爱情往往对女性有不可抑止的诱惑力,玉娇龙都能决然舍弃,可最终还是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她一心追求自由,孩子必然会带来很多束缚,尤其是这个孩子还被别人调包了,但她并不抱怨。相反,母亲的天性可以克服一切世俗的恩怨功利,她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里写到她要追回自己被调包的孩子时的心理情形:
此时她是向东走去,意欲追赶上方二太太的车,将自已亲生的儿子换回,但这小孩藏在自已的怀里也不哭了,直用小脸儿拱奶,她的小身子倒很暖和,脾气倒很乖。……她现在的心,仿佛极容易发软似的,即使立时将那群贼人迫上,他们若不动手,她也不愿多杀伤人,她只想将那方二太太主仆救出,将小孩换回来就是。她感到做母亲的生了个小孩儿不容易,因此融化了她一向骄傲狠辣的性情,更忏悔她过去所做的事。[2]31-40
《铁骑银瓶》写出了孩子对一个女人的改造,一个习惯江湖厮杀的母亲也会被孩子软软的小身子温暖融化。波伏娃说:女人做母亲,是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也是她的自然使命。[5]创造生命是女人的自然使命,伟大到能改造一个人。玉娇龙的忏悔是对过往的深刻反省,是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命觉悟。一个嗷嗷待哺的生命等着她去拯救,激发了她母性的怜悯和仁慈,而对养女的哺育又反过来拯救了她自己的灵魂。有了养女春雪瓶相依为命的陪伴,有了母女二人对抗边疆盗匪之流的协力同心,玉娇龙便不再是一个人站在无人的旷野和风雨飘摇的江湖,她的情感有了寄托,她的内心有了爱的温暖。正是被激发的深沉的母爱,使玉娇龙更坚定决心去寻找丢失的亲生儿子韩铁芳。于是,养育和寻亲变成她后半生的人生使命。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儿子的一路照顾,虽饱受病痛折磨,却内心安宁,能病逝于亲生儿子的怀中,也算是一辈子的圆满。作为男性作家的王度庐,终于在这里把他的主人公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性,一个母性主导的女性,女性天性的力量被强调、凸显出来。
从《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虽贵为九门提督之女,但玉娇龙的一生孤独凄凉。她抛弃了家世门第,毅然走进她认为代表“自由”的江湖。可是这个江湖对她的要求却是“安分守己”,江湖领袖李慕白连她私下抄写的华山派典籍也要没收。江湖正派打压她,反派和一些不入流的盗匪流氓更是要打劫、要挟甚至诛灭她。在此情形下,危机四伏又鱼龙混杂的江湖早已击碎玉娇龙纯粹的理想,四面楚歌的现实把她塑造成大漠中让人闻之丧胆的“春大王爷”,内心的幸福和痛苦都无人过问。抚养养女春雪瓶,临终前与亲生儿子韩铁芳骨肉团聚,对玉娇龙来说意义重大。儿女们是她灵魂的港湾、心灵的归宿,他们已经成长为少年英雄,在他们的身上寄寓着母亲的希望。所以,母性是玉娇龙最后的人生救赎。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言:“母亲身份能够平息所有焦虑,带来从容平和的满足感。”[6]玉娇龙的一生因做了母亲而得以完整,仿佛之前所经历的困境、挣扎、分裂和蜕变,就是为了达成这一女性的生命使命。毕竟,江湖的血雨腥风,仅仅依靠一把青冥宝剑远远不够,江湖是李慕白为首的华山派和京城贵胄、侠义之士的天下,是男人们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