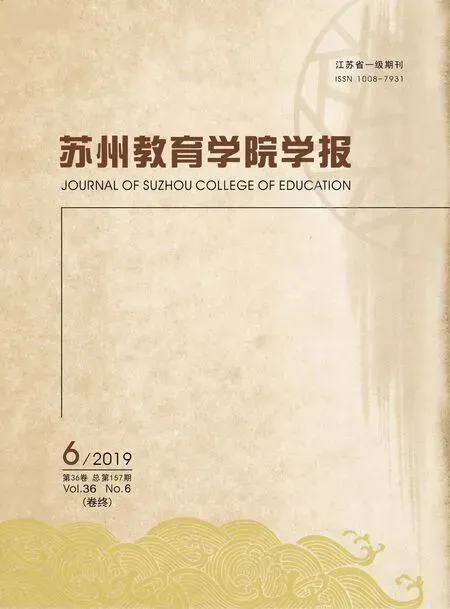21世纪以来的汉语指示、疑问代词研究(2000—2010)
2019-02-22曹炜,李璐
曹 炜,李 璐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进入21世纪,汉语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尤其是指示代词。这一时期,在指示代词研究中取得丰硕性成果的学者为储泽祥、邓云华[1],钱宗武、邹宇瑞[2],龙国富[3],张玉金[4],应学凤、张丽萍[5]等。其中,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研究以钱宗武、邹宇瑞,武振玉[6],张玉金等为代表。
钱宗武、邹宇瑞对今文《尚书》指示代词进行了系统研究,证明了今文《尚书》的指示代词已形成独立的系统,与西周金文的指示代词相似。同时,他们还指出:今文《尚书》的指示代词系统由近指代词、远指代词、虚指代词和不定代词组成[2]。并对今文《尚书》中指示代词的各个小类分别进行考察,对了解整个《尚书》创作时期指示代词系统有很大帮助。
武振玉、张玉金等考察了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中的某一小类。武振玉对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进行考察,发现了两周金文中一类比较特殊的无指代词“亡”,且指出:“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主要是‘亡’字,‘莫’、‘无’二词虽亦有用为无指代词的用例,然数量均很有限。”[6]这些发现为研究上古汉语早期的无指代词提供了新材料。张玉金考察了春秋时代的近指代词,首先讨论这一时期的“兹”“斯”“此”“是(时)”等近指代词,并对“是(时)”“此”“兹”“斯”的区别进行了辨析。[4]关于张玉金提到的“是(时)”和“此”的不同,我们大致是认同的,但关于“斯”和“此”的区别,张玉金认为:“‘此’最常见的用法是作定语,而春秋语料中的‘斯’则没有作定语的,这就是说,‘此’常仅起指示作用,而‘斯’一般是兼起指示和称代作用。”[4]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据考察,在《诗经》和《论语》中,“斯”主要的句法功能都是作定语,因此,张玉金提到的“斯”和“此”的区别是不存在的。
中古汉语指示代词的研究则以龙国富为代表。龙国富对中古时期的处所指代词“此”“是”“彼”以及平比句“如……许”等使用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汉语里表示处所的指代词经历了结构变化和词汇兴替两个层面。”[3]在考察特定时期某类处所指代词和平比句产生的原因时,龙国富从汉语双音化、佛经文献的影响、句法环境,以及方言地域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出发,分别对这几类处所指代词和平比句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于现代汉语指示代词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者为储泽祥、邓云华、应学凤、张丽萍等。一般认为指示代词的类型包括二分和多分两类,储泽祥、邓云华对不同语言中指示代词的类型问题进行了探讨,考察指方所、人或物、时间、性状程度或方式等指示代词的共性变异限度,并得出结论:“如果一种语言的指示代词,一部分是多分的,一部分是二分的,那么,指方所的多分可能性最大,而指性状程度或方式的二分可能性最大。”[1]
从语音和语用的角度来探讨指示代词也是这一时期指示代词研究的趋势,以应学凤[5,7]、贾智勇[8]等的研究为代表。应学凤、张丽萍将指示代词的语音象似性的各种表现归为两大类:语音音响度象似和复杂性象似,并提出指示代词语音象似的六个动因。[5]应学凤又用统计的方法跨语言考察了指示代词的语音象似情况,并用标记组配理论对指示代词的远指倾向于复杂的音节表示等现象作了解释。[7]贾智勇则从语用的角度探讨指示代词的用法,分析了由于概念主体指向性变化而引发的跨范畴现象,补充了传统语用学中解释指示代词所遵循的“距离原则”。[8]
学界对他称代词的归类是有争议的。彭爽将他称代词归为指示代词一类,并从基本功能、格分布的位置以及在不同格位上“的”字隐现的情况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一般认为,他称代词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彭爽对这此有不同见解:“尽管他称代词具有相近的真值语义特征,但它们的功能却大相径庭。”[9]彭爽、金晓艳又借鉴语义功能语法理论,对他称代词内部成员的小类进行划分,得到一个他称代词的内部分类系统,并提出:“他称代词区别性范畴义素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内部成员与其他成分的搭配关系。”[10]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专注于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关系的研究,其研究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所形成的结构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同形或同源关系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刁世兰[11]、林素娥[12]等的研究。刁世兰对现代汉语中指示代词“这”“那”与名词性成分组合,再与人称代词组合构成“人称代词+这/那(+数词+量词)+NP”之类的格式进行考察,且从前项和后项的结构关系,将之分为同位结构和偏正结构两种类型。[11]林素娥则讨论了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形和同源等问题,并认为这是“其内部成员在词汇形式上的互相渗透为交际过程中代词功能游移的表现,同时,这种功能上的游移并非无序的,也不是无动因的,而是指示词内部在交际功能上不平衡所促成的”[12]。
关于代词所指的研究,一些学者在乔姆斯基“约束论”三条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袁毓林讨论代词回指动词性成分和代词所指的波动现象,他指出:“现代汉语通常用‘这’和‘那’一类代词来称代由动物性成分表达的事件。”还指出,“这”和“那”在称代动作、行为等事件时,随着句法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处在宾语位置上只能表示直指,处在主语位置上则既可表示直指,又可表示照应,并分别对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中代词所指的波动现象进考察,阐释了代词所指的波动现象的原因。[1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旁指代词研究的专书,即彭爽的《现代汉语旁指代词的功能研究》[14]。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旁指代词的学术著作,该书运用语义功能语法理论,从句法功能、语篇功能、表达功能以及认知、历时演变等方面,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这种现代汉语的旁指现象,提出旁指代词的内部分类系统,把旁指代词分为体词性旁指代词和加词性旁指代词、除指代词和加指代词,并结合语义考察旁指代词自相组合、与其他语法成分组合时的有序性,结语部分简要对比分析了英语、汉语、日语和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旁指形式,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的汉语疑问代词的研究成果虽有所增加,但在整个代词的研究中仍然呈现劣势。对疑问代词发展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较有代表性的为贝罗贝、吴福祥[15],石毓智、徐杰[16]和冯春田[17]等的研究。
贝罗贝、吴福祥根据询问功能,将疑问代词分为事物疑问代词、人物疑问代词、方式和情状疑问代词、原因目的疑问代词、时间疑问代词、处所疑问代词和数量疑问代词等七大类,并对整个上古时期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考察,提出:“从西周到东汉,汉语疑问代词发展与演变的主要表现是频率变化、功能发展以及词汇兴替。”[15]并对这些变化发生的动因作了探讨,使人们对整个上古时期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演变轨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石毓智、徐杰考察以疑问代词为中心的语序变换,发现代词的宾语前置现象从魏晋以后就消失了,这是过去三千年来汉语发展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并提出:“先秦两汉时期汉语代词的特殊语序,是一种通过语序变换表示焦点的手段。”[16]汉语代词在历史上常发生一种特殊变化,即由一个疑问代词跟一个非疑问词组合而形成一个复音式疑问代词,该词又可以通过省缩原来的疑问词部分而保留原初的非疑问词部分,从而成为一个新的疑问代词,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音变。汉语史上代词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汉语代词历史演变的一种特殊规则。注意到这种特殊变化,对于研究汉语代词的历史演变及探索汉语发展变化的规律,都有很大意义。冯春田注意到这种变化,提出汉语疑问代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化规则:“由原本属于疑问词与另外一个非疑问词构成的短语变化而来的双音式疑问代词,可以通过缩略原来的疑问词部分而产生或者说形成一个可替换原先这个双音式疑问词的新的疑问代词;在省缩过程或经过省缩之后,新的词形又可能发生音变。”[17]
现代汉语中疑问代词的用法也是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重点,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为寿永明[18]、玛林娜·吉布拉泽[19]和徐默凡[20]等。疑问代词除了表示询问、任指和虚指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用法,即表示否定。寿永明以“什么”为例,分类讨论“什么”一词的否定用法及其语义特征,分析了疑问代词表示否定的形成原因及其语用功能。[18]现代汉语疑问代词除了疑问功能外还有非疑问用法,玛林娜·吉布拉泽从非疑问用法中指出不定指性疑问代词,并对其含义进行解释:“发话者不明确指明事物个体。从语用学角度来谈,这个现象与发话者的知或不知有关,有时知道可没必要指明。”[19]关于疑问代词的重叠用法,于细良已作过相关讨论①参见于细良:《“多少多少”和“多多少少”》,《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第466页。,徐默凡又作了补充,并从语法化和主观化等理论出发对疑问代词的重叠用法进行全面描写,指出:“疑问代词的泛指用法和借指用法的重叠除了单纯表示数量增加以外,已经具有了主观性评价意义,开始走上主观化和语法化的历程,逐步具备了语法重叠的雏形。”[20]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留学生疑问代词习得情况进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丁雪欢[21-22],分别对留学生就疑问代词的习得顺序、留学生对疑问代词的习得过程及其特点进行考察,对了解疑问代词整体的习得顺序有指导性意义。
单个指示代词的研究以“这”系和“那”系为主。徐默凡对“这”“那”的重要研究成果给予述评,将这些研究成果归为历时演变、语法位置、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四个部分,文章针对以往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总结也很精当,尤其是在“这”“那”语法意义的虚化和语用意义不对称性现象的研究成果的总结上,对于我们从语义、语用和认知等多角度去探讨指代词有借鉴意义。[23]曾毅平对“这个”和“那个”的讳饰用法进行了说明。[24]曹秀玲对汉语中“这/那”的不对称性特点进行考察,提出“这”“那”都可以预指的观点,只是后者用例较少。[25]杨玉玲则提出:“单个‘这’和‘那’都不能用于预指。”[26]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可及性理论对这种不对称性现象进行了解释,即“这”是高可及性指示词语,而“那”是低可及性指示词语。在此基础上,杨玉玲又对谓词性指示代词“这么”和“那么”的篇章不对称性进行考察,指出其与体词性指示代词“这”“那”的差异。[27]丁启阵从八组概念系统考察现代汉语“这”“那”的语法分布情况,以此来探讨“这”“那”指示词语的不对称性。[28]此外,他关于“这”“那”的事件、篇章以及语用功能的描述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王灿龙将“这”“那”在篇章中概括一句话或一段话的情况称为“指称事件”,并从指称距离的角度对“这”“那”充当照应语指称事件时照应功能进行考察,从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这”“那”在使用上的不对称性。[29]
“这”和“那”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化现象也颇受学者们关注。方梅通过对“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共时描写,探讨指示代词用法的虚化轨迹,并提出:“指示词在北京话中的演变与南方方言经历了不同的途径。”[30]指示代词语法化后经常作为话语标记使用。李宗江通过对“这下”作为篇章连接成分用法的描写,对指示代词加量词后形成短语后的语法化现象进行了考察。[31]郭风岚[32]和刘丽艳[33]均对“这个”“那个”作话语标记的情况进行了考察。郭风岚考察北京话中的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认为“这个”是强社会化话语标记,“那个”是弱社会化话语标记。[32]刘丽艳主要从语篇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提出:“‘这个’和‘那个’虽然已经从指示短语虚化为话语标记,但它们的话语标记功能仍然会受到初始词功能的影响。”[33]
近指代词“这”的来源问题也颇受学者关注。袁宾、何小宛从佛经中近指性指代词“这”的词义和具体用法入手,探讨为何优选“这”字这一问题。[34]刘海平通过分析“者”由被饰代词转变为近指代词的可能性,探讨“者”和“这”的关系,并就学界关于这两个代词关系的讨论进行了梳理。[35]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对其他指示代词研究的成果,其中,以指示代词“之”“其”的研究为盛。朱城[36]就先秦时期代词“其”作主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孙德金[37]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代词“其”进行了考察,邓昌荣[38]考察了《诗经》中的指示代词“其”,张玉金[39]对西周时代的指示代词“之”进行了考察。关于其他指示代词的研究,以张维佳、张洪燕[40],冯春田[41],王江[42],刘君敬[43]和林海云[44]等学者为代表,分别对“兀”“若”“每”“各”“该”“斯”等指示代词的来源、具体用法等进行了考察。
这期间,也有一些学者对单个旁指代词“它”“人家”等展开讨论,以彭爽[45]、郭攀[46]、翟颖华[47]和闫亚平[48]等为代表。
单个疑问代词的研究以“何”系疑问代词和“谁”“孰”系疑问代词为主。“何”系疑问代词的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分为“何”系疑问代词发展演变的历时研究和某一个疑问代词的共时研究两个方面。历时研究以卢烈红为代表,卢烈红先后就佛教文献中的“何”系疑问代词和“云何”疑问代词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49-50]“何”系疑问代词的共时研究以朱城[51],卢烈红[52],张幼军[53],周建姣、徐莉莉[54],陈年福[55]和张玉金[56]等为代表。朱城对康甦的《“何”字单用不能指人吗?——与吕叔湘先生商榷》[57]的补充,该文继承康甦的“何”字单用可以指人的说法,并作以更详尽的解释。[51]“云何”是东汉以后比较常用的疑问代词,常出现在佛典中,卢烈红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云何”进行考察,根据“云何”在不同时期的语法功能特点,提出“西汉时期,‘云何’肯定已经凝固成词”[52]的观点。张幼军对《道行般若经》中“何所”的用法进行了考察[53],周建姣、徐莉莉就《太平经》中“何以”与“以何”的用法进行了考察[54],陈年福和张玉金则讨论了甲骨文中“何”与“此”作代词的用法[55-56]。
一般认为,“谁”和“孰”是一对同义词,对这两个疑问代词的研究一般以比较为主,管锡华[58],邓军、李萍[59]等是该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谁”和“孰”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王海棻的《先秦疑问代词“谁”与“孰”的比较》分别从意义、用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60]管锡华对《史记》中的同义词“孰”和“谁”也进行一一描写,并与王海棻的观点作比较,进而梳理了“孰”和“谁”在上古发展的演变。[58]邓军、李萍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疑问代词“谁”和“孰”的用法,从中可以看出“谁”和“孰”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轨迹。[59]一般认为,“谁”和“孰”在上古区别是“谁”不可表比较,但李明龙、刘芳池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的语言研究,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他们认为:“‘谁’在上古后期,意义上出现了表比较的现象。”[61]这无疑推动了汉语疑问代词的深入研究。
疑问代词“什么”出现较晚,这一时期,关于“什么”的研究大多选取现代汉语中的语料,并多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王海峰、王铁利[62],姜炜、石毓智[63]等。
此外,对疑问代词的探源研究也广为研究者所青睐,较有代表性的有吴琼[64]、徐媛媛[65]、冯春田[66-67]、刘长庆[68]和汪银峰[69]等的研究,分别对疑问代词“恶”“安”“焉”“哪”“啥”“作勿”“是勿”“若为”“箇”“甚”等的来源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