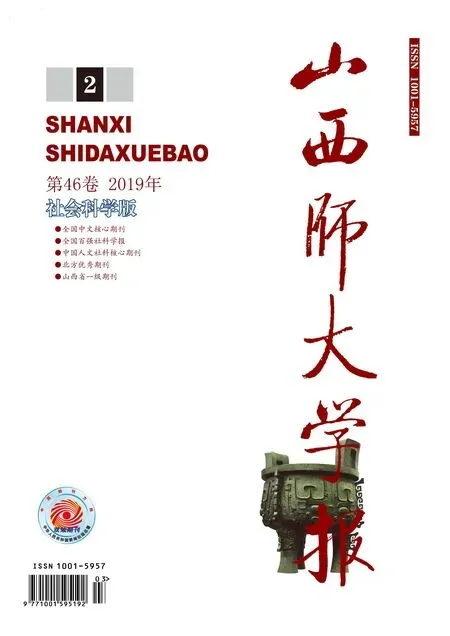重塑“忠义”:藏山文化的历史嬗变及现代转向
2019-02-22赵淑清
赵 淑 清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119)
藏山坐落在太行山西麓,位于今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苌池镇,原名盂山,后因春秋时期程婴和赵氏孤儿赵武在此藏匿十五年而得名,后世因其是赵孤、程婴、公孙杵臼亡匿之所建祠而祀之,围绕藏山神祠逐渐演化成独具特色的藏山忠义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剖析藏山忠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质,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从中吸取有益养分,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一、碑刻记忆:“赵氏孤儿”的忠义内核
关于“赵氏孤儿”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成型,虽然在《左传》出现了传说的原型人物——赵武,但记述的情节侧重君臣争权的惨烈现实——“赵氏族灭”的前因后果,至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才有了完整的“赵氏孤儿”记载。之后,刘向《新序·节士》、《说苑·复恩》对其中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此后,关于赵氏孤儿的故事基本上是以《史记·赵世家》中的记载为版本撰写的。但是后世学者多质疑《史记·赵世家》的真实性,如对于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行为,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程婴杵臼》中认为:“《春秋》于鲁成公八年,……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1],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二十三中也认为:“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史公爱奇述之。”[2]退一步讲,即使是“救孤”中两位主人公是虚构的,但从司马迁附会给他们的侠士行为来看,司马迁对视死如归的精神是推崇备至的,而“赵氏孤儿”传说中的故事情节涉及的“忠义”行为也为世人称颂。
金代大定十二年(1172年),盂县县令智楫在《神泉里藏山庙记》中的记载: “藏山之迹乃赵朔友人程公藏遗孤之处也。”①金代大定12年(1172年)盂县县令智楫为重修藏山祠而制,经修复现存于阳泉市博物馆,是现存最早记载藏山及“赵氏孤儿传说”的碑刻。这是迄今发现的现存有关“赵氏孤儿”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藏山得名也源于赵氏孤儿,“后人因名其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在《神泉里藏山庙记》里关于“赵氏孤儿”的故事版本主要来源于《史记·赵世家》,其碑文明确提到“公姓程名婴,家世史不载而后世无闻,行事见于《赵世家》也”。赵氏孤儿蕴含的忠义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释“行”时提到“言忠信,行笃敬”[3]78,讲“仁”时则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3]56,评“政”时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3]51,提“友”时曾说“忠告而善道之”[3]51,并把“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一日三省的基本。孟子谈到“友”时也有“教人以善谓之忠”[4]的说法。这都说明在儒家思想中,把“忠”作为行为和道德的准则。所谓“义者,宜也”[4],是指思想行为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的行为标准。孔子所谓“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3]73,把“行义”与“达道”联系起来,“义”作为一种观念范畴,被赋予了较高的价值地位;孟子则格外重视“义”,提倡“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提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5] 50要求人们“居仁由义”[5]173,“仁”“义”并重。
儒家的这种“忠义”观,其思想内涵就是忠贞正义的为人之道,包括诚而不欺、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等内涵。正是因为“赵氏之先有仁爱乎,有遗德乎”,程婴才有“救孤”的行动,在程婴践行诺言自杀后,“赵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不绝”。直至金代,此地还有专门祭祀程婴的庙宇,“公为人之友,成人之事,杀己之身,身没而名不没。此方之人为立庙貌其来远矣,岁岁血祭,远近归祷,云合同辐辏,故《祭法》曰: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则祀之。”并且在碑文中提及祭祀程婴的原因“公之生其义存也,公之死其利存也,有与没有兼福利,生死一也,死而不朽及贵于生”。从中不难看出,赵氏孤儿传说中所蕴含的忠义思想,对藏山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山文化生成之初就涵盖了“忠义”之本义。
二、藏山忠义文化的嬗变过程
(一)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从价值追求走向政治准则。战国中期之后,各国强权政治占据主导地位,君主施行强有力的手段让臣民听命于自己,进而实现一统大业。这种强有力的手段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实施外,在文化领域也加大了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忠义”思想在这时被作为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等级色彩较为浓厚。《韩非子·忠孝》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即认为臣民忠心于自己的君主是天下常道,把儒家思想中的“忠”归结于“忠君”。在此基础上,韩非子对“臣忠君”又作了绝对性的规定:“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汉代的董仲舒把“忠”的含义进一步政治化、等级化,“忠”被看作臣忠于君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忠义”从原始自发的朴质价值追求演变为封建政治准则。
此时,忠义文化在民间的传播并没从根本上受官方的影响而丧失本义,据最早记录藏孤洞的《神泉里藏山庙记》[注]《神泉里藏山庙记》,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六月刊,现存藏山祠。提及程婴,“此方之人为立庙貌其来远矣,岁岁血祭”可知,藏山庙是祭祀程婴的庙宇,是一座典型的报恩祠。即使到了金代,藏山庙也是主祀程婴,赵武“庙之侑坐赵孤者”,只是陪坐,未享有主祀位置,据《重修藏山庙记》记载赵武“既长以贤,遂当晋国,没谥曰文,后世于亡匿之所祠而祀之,又建别祠于城右,以便祈祷”[注]《重修藏山庙记》,元至元三年(1323年)八月刊,现存秀水镇西关大王庙。,至于赵武是什么时候陪祀藏山庙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藏山庙最初只祭祀程婴。
(二)唐宋时期:从政治准则走向民族意识。唐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民众思想上“忠”的伦理范围也被深深受制于“君臣”之间,普遍提倡“忠臣不事二君”,“忠”的绝对约束性更为明显,臣民因此被置于皇权的统治之下。据《宋史·礼八》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山西绛州立庙祭祀,“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绍兴二年,宋室南渡,庙宇隔绝,于行在所设位望祭。绍兴十一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立祚德庙祀晋赵武及程婴、杵臼、韩厥;河东神主封王爵,文子曰藏山大王;封侯爵,公孙杵臼曰成信侯,程婴曰忠智侯,以祀之”[注]《崇增藏山神祠之记》,明嘉靖四年(1525)七月刊,现存藏山祠。。宋以能存赵氏之孤,以加官进爵的方式,置两位忠义之士于封建等级秩序之中。文子为王,义士为侯,以示尊卑上下之别。《宋史·礼八》还记载:绍兴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南宋王室对“赵氏孤儿”中的忠义之士的祭祀标准上升为中祀,不仅从礼制上提升了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忠义之士的祭祀继续保持在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影响。
宋代把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进爵为公侯,想藉其“忠义”精神影响民众忠于赵宋君主,很显然是为了把原本的民间“忠义”精神转化为官方的“忠君”思想和政治需要。与此同时,统治北方的金王朝对今山西盂县藏山神庙祭祀赵氏孤儿中的忠义之士程婴、公孙杵臼、赵武给予肯定,据藏山祠现存最早的碑刻《神泉里藏山神庙记》记载,在天德年间(1149—1153年)“岁大旱,旬月不雨,邑宰尝往吊之,洎归,似有褒慢之意,须臾而雹雨大降;宰复反,已致恭虔,俄,雨作以获沾”。盂县县令智楫在大定年间(1161—1189年)也多次前往藏山神庙祈雨[注]《神泉里藏山神庙记》,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六月刊,现存藏山祠。。金代对藏山当地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利于统治该地区,而且使其可以同南宋王朝分庭抗礼。与南宋封赵武为王,以及程婴、公孙杵臼为侯不同的是,赵武自从配享藏山庙以来,当地民众对藏山庙赵武的祭祀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三神之灵,庙食兹土,其来远矣”[注]《重修藏山庙记》,元至元三年(1323年)八月刊,现存秀水镇西关大王庙。。在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庙之侑坐赵孤者,灵更明矣,人有窃负而往,亦能救旱意,其襦中之风不坠也”[注]《神泉里藏山神庙记》,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六月刊,现存藏山祠。。由此可知,赵武在藏山庙中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忠义思想的传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传统政治文化领域极具代表性的忠义伦理规范逐渐形成,并且在官方的尊崇与推广下,忠义文化中蕴含的赤诚无私、勇于奉献、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精神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元明清时期:从民族意识走向民间信仰。宋金之后的元朝是民族融合大发展的时期,思想文化上兼容并用,“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元继承了金在北方祭祀藏山神庙的传统,不仅多次修缮藏山庙,元至大三年(1310年)、元至治三年(1323年)、元至顺三年(1332年)、元至正五年(1345年),尤其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为了便于乡民的祈祷,在杜寿圣寺之右新建了一座祠庙来祭祀赵孤、程婴、公孙杵臼三人,其在“杜寿寺之右,东暨藏山祠,南面石门寺,西接文殊山,北连滴水洞,……享一郡之祭祀”[注]《藏山祠记》,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刊,现存西潘乡李庄村。。而且祭祀神灵位置也有变化,《重修藏山庙神像记》[注]《重修藏山庙神像记》,元至顺三年(1332)七月刊,现存秀水镇西关大王庙。中提及藏山神古祠“忠智侯位孤操仗侍立于其侧,盖取诸构患难而晦迹之事也”,行祠“孤坐正位,忠智侯、成信侯侧向而坐,取其患难既平而不忘厥初之意也”。此外,吕思诚在《重修藏山神祠记》碑文中对赵氏孤儿背景中的“下宫之难”提出质疑,指出赵氏的所作所为是导致其家族祸患的诱因,认为赵氏有愧于 “公孙之死、程之忠”,而藏山当地民众建祠庙祭祀程婴、公孙杵臼,“千古之下血食”,是对古之忠义的报答, 并予以提倡[注]《重修藏山神祠记》,至正五年(1345年)刊,现存秀水镇西关大王庙。。另据《重修神泉里藏山神庙记》记载“苌池、神泉、兴道,自藏山有庙已来,互主祀事”,可知当地民众对忠义之士的崇拜之盛。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藏山的忠义文化还没有禁锢在封建的等级礼制中。
明代随着专制主义的迅速发展,“忠君”思想也发展到了极致,“忠义”思想不仅被规范到了等级礼制对应的价值体系中,而且逐渐丧失本义,狭隘地局限于单一的君臣关系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藏山忠义文化中的“忠义”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赵武在宋代即被封王,但在藏山的古碑刻题名中没有明确其王的主体地位,在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树立的碑刻《西关大王庙重明藏山祠古传》中明确提出大王一词,而且在景泰六年(1455年),在藏山《新建藏山大王灵应碑记》之后又于天顺四年(1460年)重修藏山大王殿。据当时的碑文记载“……予闻藏山乃邑之大藩,其神赵武主之,而邑人报赛特重……”[注]《重修藏山大王殿记》,至正五年(1345年)刊,现存秀水镇西关大王庙。,之后,皇权直接涉入藏山文化,成化年间明宪宗封藏山为“万岁朝廷香火院”,高谅、刘允两位太监分别于成化二十一年(1484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先后奉圣旨亲临盂县修藏山庙。至此,藏山神庙及其蕴含的忠义文化被完全纳入封建等级制度之下。
此后,藏山庙宇即开启了在明朝廷主导下的营建活动,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差人修建了藏山总圣楼香台[注]《藏山总圣楼香台记》,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现存藏山祠。,嘉靖四年(1525年)朝廷遣太监并请高僧主持修建了藏山神祠[注]《崇增藏山神祠之记》,明嘉靖四年(1525年),现存藏山祠。。另据明嘉靖五年(1526年)《钦奉皇王之命重修藏山摩崖石题刻》[注]《钦奉皇王之命重修藏山摩崖石题刻》,明嘉靖五年(1526年),现存藏山祠北崖。碑文记载,明成化二十年至嘉靖四年间,朝廷曾先后派六名钦差、太监旌修藏山神庙,而参与的朝廷、晋王府、晋宁化王府重臣,山西等处承宣布政司,太原府、盂县的主要官员及名人雅士、纠首、主持僧人之名多达百余个。此后,藏山神庙体系发生了变化,忠王祭祀赵武成为主旋律,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祀藏山赵文公碑记》[注]《祀藏山赵文公碑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现存藏山祠。、万历二年(1574年)《祀藏山大王说》[注]《祀藏山大王说》,万历二年(1574年),现存藏山祠。,万历十二年(1584年)《续藏山赵王庙记》[注]《续藏山赵王庙记》,万历十二年(1584年),现存藏山祠。。另外还新增了赵氏一脉的神位,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晋上卿赵成子之神位》《晋上卿赵宣子之神位》《晋驸马赵庄子之神位》[注]《晋上卿赵成子之神位》、《晋上卿赵宣子之神位》、《晋驸马赵庄子之神位》崇祯十四年(1641年),现存藏山祠。,在这样的背景下,崇祯十四年(1641年)为程婴、公孙杵臼在藏山祠新建的启忠祠[注]《藏山祠新建启忠祠碑记》,崇祯十四年(1641年),现存藏山祠。,寓意也是十分明显的,即教导世人要效忠于皇帝。
与前代相比,明代由于皇权的渗入或参与,藏山忠义文化的本义精神发生了变化:一是突出了赵氏家族的主体地位,使藏山忠义文化的主体构成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二是凸显了赵武的独尊,使程婴等人与赵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忠义”也由普通性的人际关系准则向“对上”“对君”的单项化转化。但这种变化除了与中央集权有关外,与当时明王朝边疆的军事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清朝统一全国之后,全盘接受了明朝政治体制逐渐强化的君主专制,并在思想领域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尽管仍以儒学为正统,以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逐渐削弱其在汉族群体中的影响,进而引导其服务于清政府建立的大帝国。从《清代盂县藏山神庙碑刻题名表》中可以窥探清代藏山忠义文化信仰的微妙变化:一是藏山神庙祭祀的对象以赵文子(赵武)为主,虽然后期又增加了韩厥祠,重修了双烈祠,但依然推崇赵文子;二是参与修建藏山神庙的主体从明代的皇权直接参与逐渐变为地方乡绅和当地民众主持,与此同时空间上也固化在盂县藏山附近及其周围;三是碑刻题名很少用大王一词,主要是文子庙。此外,碑刻档案中还出现了新特征:一方面碑文中出现了文子庙与八蜡庙合修的记载;另一方面在藏山祠中祭祀藏山龙神山神。尽管盂县藏山神庙所蕴含的忠义精神在国家层面上的地位随着清帝国的统一逐渐下降,但在地方民众中的地位却未曾改变,如苌池、兴道、神泉三村谨遵古制祭祀藏山忠义之神,修缮其栖息之庙宇,地方乡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此外,清代中期以来,随着旱灾的频繁发生,民众对神灵的诉求功利性较强,如盂县民众祭祀赵文子的时候,认为其灵与龙神、山神相通,也应祭祀,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祭祀忠义之神赵文子等人的同时还祭祀八蜡神(亦名虸蚄神),这主要是因为盂县境内深受蝗虫之害,而八蜡神是治蝗有方的神灵。
综上所述,在藏山忠义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其形式上虽然因特定时期的历史环境所局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正义的思想核心始终未变,这也是藏山忠义文化核心价值所在。因此,“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重要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集体人格。”[6]77碑刻档案中所体现的忠义文化内核经由最初的朴素价值追求,发展为封建政治准则,进而上升为民族意识,最终沉淀为民间信仰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逻辑,为深入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藏山忠义文化的现代转向
藏山忠义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以忠诚和信义为中心的文化,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藏山忠义文化在嬗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使其成为不同时期历史选择的杂合体,其中不乏消极的因素,在现代价值体系下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对其进行现代转换是非常必要的。
(一)重塑“忠义”文化的现代性。藏山忠义文化核心内涵所体现的人格价值取向、明确的善恶标准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为其现代转向提供了道德基础。因此,忠义思想的现代转向过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转变,而是一方面要将忠义思想中的糟粕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过滤出去,避免其对现代人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和阐释忠义思想的现代价值,弘扬其核心价值理念,使“忠义”这种伦理上的道德升华为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重生。现代的“忠义”思想应该是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观。
(二)塑造个人崇高道德品质。藏山忠义文化并未随着封建体制的覆灭而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相反成了高尚人格和道德规范的化身。这也是传统文化向往的理想人格,追求道德精神境界的一贯优秀品质。尽管时代不一样,但社会依然需要个人具备“忠义”的品格,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很容易在各种思想和各种利益中迷失自我。因此,用忠义文化中的忠贞爱国、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知耻求荣等精神,来整合目前正在转型的个人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塑造个人的崇高道德品质。
(三)重构纯朴人际关系。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今天,突破利益至上追求,重构和谐纯朴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藏山忠义文化核心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纯朴的,其中“利他”精神和“诚信”意识,是这种纯朴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目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环境是利己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提倡“利他”思想,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坦诚交流。而 “诚信”精神,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坚持的态度。诚信一旦成为整个社会的认同价值,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就会自觉遵守,努力维护这种人际交往原则,不断完善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小到个人的人格魅力大到国家的国际形象,诚实守信依然是当今社会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
(四)凝聚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文化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又对经济形成能动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尽管中国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忠义文化所包含的诚信和奉献精神,仍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领导干部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7]所以说,将藏山忠义文化中的精髓进行挖掘与传承,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逐渐凝聚文化软实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有利于尽快实现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