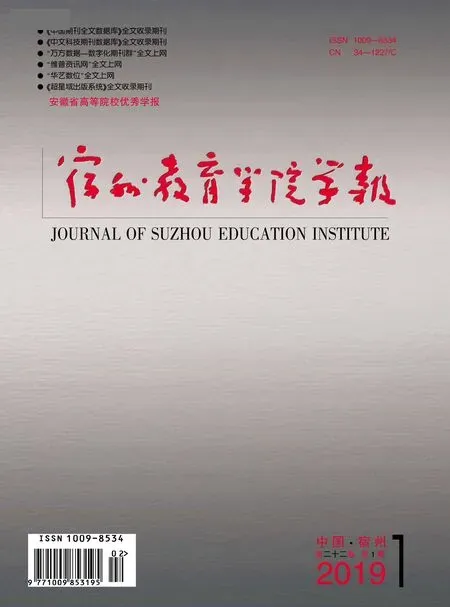一个真正的反殖民主义斗士
——评《茫茫藻海》中的边缘女性克里斯托芬
2019-02-21王菠
王 菠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简·里斯是20世纪中期英国重要小说家,以《茫茫藻海》闻名于世。这部被公认为《简·爱》前传性的小说,自1996年问世以来便掀起了持续至今的“里斯热”,确立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
对于《茫茫藻海》的研究和评论,主要集中于《简·爱》与《茫茫藻海》的比较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国外学者多从文学比较的角度研究女性的婚姻和疯癫,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第三空间身份建构,从后殖民的角度研究种族身份问题、小说的哥特式特征,或关注加勒比文学的特征,挖掘殖民对加勒比地区的破坏。国内学者多从后殖民话语和身份意识的角度,或解读女主人公的身份困境和悲剧命运,或探讨作品的叙事策略和意象,或挖掘文本中隐含的后殖民抵抗话语。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佳亚特里·查克勒维蒂·斯皮瓦克,以其“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的身份,在西方学术界素享盛名。其在《属下能说话吗》(1988)一文中,“属下”被用来指“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无组织的农民工,以及流浪街头或乡村的零散的工人群落和团体”。[1]28而关于“属下能说话吗”这一问题,斯皮瓦克并非强调应该让原本没有发声的属下发声,或者呼吁人们倾听他们的微弱声音。她致力于揭示的是:这个声音为何会被遮蔽,它被怎样的理性知识所否定。[2]92斯皮瓦克指出,“在错综复杂的知识暴力限制中,无论是历史档案中亟待被解读的下属(底层人),亦或现实世界中等待被救援的底层人,他们所说的话语都是值得质疑和分析的。”[2]斯皮瓦克认为凸显属下的声音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帝国主义与知识生产互为表里,殖民者与殖民地精英分子达成共谋,共同作用于底层人民,使之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2]
本文将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将《茫茫藻海》中的黑人奶妈克里斯托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人物形象,探寻边缘女性寻求自我的历程,尝试证明“属下”的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此进行反抗。
一、忠实的顶梁柱
斯皮瓦克认为,“为了美化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被殖民主体被迫进行自我献祭,以此方式完成其主体的建构过程。”[2]所以,《简·爱》中的伯莎必须扮演她的角色:放火烧房子,然后杀死自己;《茫茫藻海》中的安托瓦内特必须被冠以“疯狂”之名。然而,里斯在塑造安托瓦内特的奶妈克里斯托芬时,并没有让她以“死亡”或者“发疯”为结局,而是成为了安托瓦内特一家的坚实依靠。因为克里斯托芬可以被看做是作者构建殖民地女性主体的希望。她虽以陪嫁侍女的身份出现,却肩负起拯救整个家庭的重担。
安托瓦内特的父亲克斯韦原是牙买加的奴隶主,拥有大片田园。1833年英国颁布《废奴法案》,废除奴隶制。而后家里的奴隶纷纷离去,田园荒废,家境困窘。周围住的黑人不怀好意,竭力要赶走他们。住在附近的欧洲白人又自视甚高,不愿意与他们这些本土白人来往。换言之,安托瓦内特一家在当地孤立无援。唯一可以用来保证安托瓦内特家的权势和地位的马也因中毒而丧命,克里斯托芬成了全家唯一的依靠。然而,黑人们铺天盖地的敌意丝毫没有影响她对主人的忠诚。安托瓦内特说:“要是她背叛我们,我们早就死掉了。”[3]她曾告诉罗切斯特,“克里斯托芬从村里给我们带来粮食,说动几个姑娘帮她打扫、洗衣服。母亲常说,要是没有克里斯托芬,我们就死定了。”[3]显然,克里斯托芬在窘境下帮他们度过了难关。其次,她是安托瓦内特精神的依靠。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在被排斥的夹缝中,受尽了本土人的仇视和白人的鄙夷。克里斯托芬成为她可以依赖的对象。在她眼里,“克里斯托芬的头发是一袭柔滑的黑色斗篷,给她安全。”[3]9克里斯托芬像是自己的母亲,给予她温暖和安全。再者,克里斯托芬总是竭尽全力保护安托瓦内特。她虽主动退出安托瓦内特婚后的生活,但依然免不了成为安托瓦内特与罗切斯特吵架的原因之一。当她得知安托瓦内特婚后过得并不好时,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和照顾安托瓦内特: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人,不惜与罗切斯特发生激烈的冲突,即便面临被警察抓走的风险也无所畏惧。
原本不需要承担养活主人责任的仆人,硬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并时时刻刻维护小主人的周全。至此,黑人奶妈忠实的顶梁柱形象跃然纸上。
二、独立的黑人女性
斯皮瓦克后来评论《茫茫藻海》说道:“在原有的帝国主义的计划中,那原先可能并不相容或不连续的他者,总是早就经过历史的折射,成为一个巩固帝国主义自我的驯化他者。”[4]换句话说,小说中原本的他者不能转变成自我,只会被继续驯化成他者。然而,克里斯托芬是无数他者中的例外,因为她拥有独立的自我,没有被驯化成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他者。
首先,克里斯托芬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态度与安托瓦内特截然不同。她从不寄希望于男人身上。当安托瓦内特不停地向罗切斯特祈求爱情时,她清醒地告诉安托瓦内特,“男人要是不爱你,你越努力挽回,他就越恨你。如果你爱他们,他们就糟糕地对待你,要是你不爱他们,他们反而会一天到晚缠着你。”[3]比起安托瓦内特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奶妈更加深谙人性的弱点。她不愿丢失自我,乞求爱情。其次,她拥有能力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任何人。虽然在物质基础上不占有任何优势,但是她不忘自食其力,靠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她甚至说:“我自己存钱,才不会把它给某个没用的男人。要是男人对你不好,你就提起裙摆走人啰。”[3]她的话不仅显示了女性该有的独立和主见,而且还可以看出她把对于爱情的追求上升到了对自我的追求。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思想上克里斯托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黑人女性,她没有把自己放在从属的位置上,正如她对自己的定位:她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她是一个自由人。能够独立地挣得一口养活自己的面包,不像安托瓦内特那样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坚强的生存本领,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女性。
诚然,里斯作为一个一生漂泊的克里奥尔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摆脱边缘困境的强烈愿望。斯皮瓦克也认为,“指出女性主义的边缘位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为自己赢得中心地位,而是表明在所有的解释中这种边缘的不可化约性。不是颠倒,而是置换边缘和中心的差别。”[5]为满足里斯的写作需求,黑人奶妈被塑造成为一个坚强和独立的黑人女性,努力摆脱被驯化为他者的宿命。
三、勇敢的发声者
斯皮瓦克指出:“属下”并不是不能发声,而是他们根本不被纳入“人”的范畴;就算发声,也只是供主体观察探究的客体而已。通过策略性地排除“属下发声者”,欧洲中心主义得以延续其合理性。[2]在《茫茫藻海》中,反抗和发言也似乎成了男性罗切斯特的专利。但是,克里斯托芬代表受压迫的黑人妇女,以她特有的“黑色语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此反抗殖民,为被故意排除的“属下”争取到一席之地。
作为西印度群岛黑人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克里斯托芬用抵抗性的话语显示差异,是后殖民抵抗话语的负载者。小说中,克里斯托芬的言语是“牙买加的女人们从来都看不惯她,‘because she pretty like pretty self’(“因为她简直就是美的化身”)。”[3]她的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的,在形式上是突兀的——它没有动词谓语,不符合语法规范。[6]显然,在“属下”的话语里充斥着不规范的语言。他们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向白人宣布差异,故意与英国白人划清界限。语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立场。因此,不难理解“只要她乐意,就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还能把法语说得像方言一样好,但她总是小心地像其他人一样说话。”[3]其次,克里斯托芬与罗切斯特之间的较量显示了她抵抗话语的力量。正如巴特·穆尔-吉尔伯特所说:“克里斯托芬身上创造了一个被殖民化的女性属民形象,这个属民在由帝国法律强加的明确限制内,对罗切斯特控制安托瓦内特的父权制过程能够做出批判和抵抗。”[7]因此,每一次克里斯托芬与罗切斯特较量都是“属下”做出批判和抵抗的表现形式。第一次见到克里斯托芬时,罗切斯特描述到:“她平静地看着我,我想那目光中并不包含赞同。我们对视了片刻。是我先挪开目光,而她自顾自微笑了一下……”[3]显然,在“目光对视”的较量中,克里斯托芬便胜一筹。学者陈庆认为,“一直以来,欧洲殖民者所谓的传播文明的任务是以施恩的姿态在殖民地灌输西方知识。这种使命感是基于:‘属下’发声者不配归属‘人’的框架中,他们天生就是不文明的。”[2]斯皮瓦克也说:“‘下属’发声者在强大的欧洲人面前,不具备成为主体的条件,他们只能充当客体,被这个大写的主体所关照。‘下属’发声者只能隐藏在文本的断裂之处。”[2]诚然,在强势代表罗切斯特的面前,克里斯托芬的话语不能有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有一点事实仍不容忽略,即她与罗切斯特的争吵是抵抗话语的最高表现形式。她勇敢而尖锐地指出罗切斯特阴暗的目的,“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为了钱而跟她结婚的,你把钱全部拿走了。然后你就想要弄死她,因为你嫉妒她。她比你强多了,她的血统比你高贵,也不在乎钱——钱对她来说不算什么。”[3]当罗切斯特被激怒后,威胁要叫警察来把她抓走,克里斯托芬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你以为这里的男人敢碰我?他们可不像这样傻,敢对我动手。这里没有警察,没有用铁链拴到一起的苦役犯,没有折磨人的踏机,也没有黑暗的牢房。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是一个自由人。”[3]克里斯托芬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自由人”,她有自己的身份,她的黑色语言显示了一种颠覆的力量,帝国的权威和优越感在殖民地人民的抵抗话语中被挑战和颠覆。她与罗切斯特正面的交锋显示了一个反殖民斗士的风骨。
结 语
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属下’并非一个模糊的文化翻译概念……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被剥夺内在的生活,而是他们被剥夺进入政治领域的权利。[8]尊重‘属下’(底层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学习他们的语言,给每一个个体以尊重。不再是优胜劣汰的狂想,也不是主仆等级化的结构秩序。这才是人权的真正胜利。[2]可喜的是,克里斯托芬不仅在有限的文本中赢得自己的位置,她作为忠实的仆人,独立的黑人女性和勇敢的发言者形象揭示了边缘女性寻求自我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个独立而勇敢的黑人发言者代表“属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